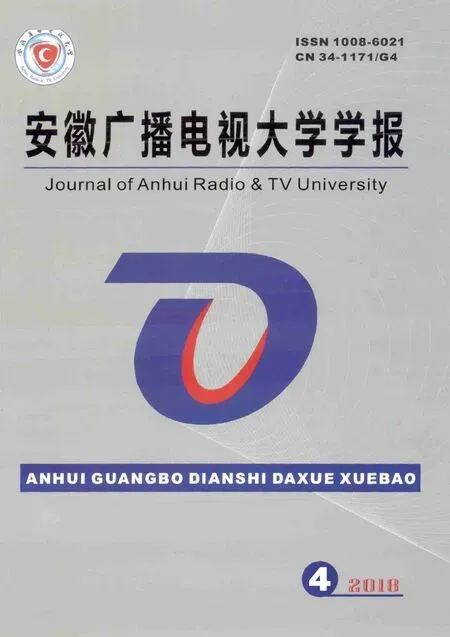论侦探小说中的“乔装查案”情节
——以《大唐狄公案》与《佛岛迷踪》中的相关情节为中心
2018-12-31王凡
王 凡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英国作家毛姆曾指出:“侦探小说的推理模式很简单:凶案发生,嫌疑产生,发现真凶,绳之以法。”[1]可以说,在侦探小说中,从排查嫌犯到发现真凶,作为主人公的侦探都需要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以便能破解迷局、缉捕元凶。为此,他们时常以乔装改扮的方式深入坊间、了解案情真相,由此在侦探小说中形成了别具意趣的“乔装查案”情节。这类故事情节虽属于整体叙事结构中的支线情节,但其却在悬念营造方面不乏特殊的审美功效,同时也时常折射出丰富的思想、文化意蕴。这在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及曹正文的《佛岛迷踪》中尤具典型性。
一、“乔装查案”情节的基本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公安人员时常身着便装探访案情、缉捕嫌犯,而这一现实生活素材在被侦探小说作家加以汲取的过程中,也逐渐发展成为这类小说中特有的“乔装查案”情节。侦探小说中的“乔装查案”情节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乔装查案”的实施者是作为作品主人公的侦探或警察,如《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佛岛迷踪》中的刑警队长郑剑;其次,“乔装查案”这一行动的实施是以查明案情为目的,如郑剑之所以伪装成驼背跛脚老头,正是为了调查女商人尤雅之子被绑架案的真相,狄仁杰乔装成算命先生则是希望能通过深入坊间,获得有关案情的意外收获;第三,“乔装查案”的侦探均是通过改变自身外形、掩饰自己真实身份为基本方式。原本儒雅英俊的郑剑为了查明案情将自己改扮为“脸上布满皱纹,戴了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一瘸一拐”[2]的怪异老头。狄仁杰的乔装改扮情况则更为复杂。《大唐狄公案》主要讲述了狄仁杰凭借自己非凡的智慧屡破奇案的故事。在小说中,狄仁杰凭借着敏锐细致的观察力、抽丝剥茧的推理能力屡破奇案,而他在民间查访过程中也获益良多,既能了解民情,亦可探查案情。《大唐狄公案》曾多次写到狄仁杰微服出行,其有时是为了察情破案,如《黑狐狸》中他以亲戚身份拜访宋夫人的姐姐家,《御珠案》中他微服探访“白娘娘庙”;有时则是以外出游乐为目的,如《四漆屏》中他与手下乔泰以牙侩的身份游览牟平县,《玉珠串》中他隐匿身份在清川镇游览。然而,与不着官袍、身穿便装、改姓易名的微服出行相比,乔装出行则可以说完全是为了调查案件,是在微服出行的基础上改变装束,令自己成为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以便有更强的隐蔽性。狄仁杰就曾在勘破“铜钟案”的过程中乔装改扮为一名游街算卦之人,他“擎起一幅青布招儿,上面书了‘彭神课’三个大字,下面则是‘麻衣相法,六壬神课’八个小字。”[3]而在调查“铁钉案”的过程中,他又将自己乔装成一名行走江湖的卖药郎中。这种乔装易容的方法也的确比一般的微服私行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铜钟案》中就写道:“狄公乔装得果然很像,居然有人前来问卦算命。”[3]224可以说,《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乔装为江湖郎中、算命先生与《佛岛迷踪》的郑剑改扮为跛腿老头都是案件侦办人为了调查案件,进而及早缉捕凶犯而采取的特殊行为,两部小说中的这种“乔装查案”情节不仅富于些许的机趣色彩,而且也具有特殊的悬念效果。
二、“乔装查案”情节的悬念效应
悬念的设置对于任何侦探小说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既是考验作家创作构想力的主要方面,更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审美元素。侦探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等诸要素虽不乏其自在的审美意旨,但其更多的还是为作品悬念的铺设与化解来服务的,“乔装查案”这一情节亦不例外,它同样具有巧设悬念的重要艺术功能。
当代作家、文艺评论家曹正文的创作涉猎极广,他不仅写作了《中国侠文化史》《世界侦探小说史》等在当时具有首创意义的评析性论著,而且还创作了不少小说、散文、随笔等,武侠小说与侦探小说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门类,而《佛岛迷踪》正是其侦探小说中的代表作。作品表现了女记者文抒与其好友刑警队长郑剑在前往佛岛的航轮上侦破一起绑架勒索案的故事,小说的情节主线围绕着文抒在船上暗查谁是绑架案犯来展开的,而这一嫌疑在船上的多位乘客之间转换游移。与此同时,作品还于其间插入了一个特殊人物——一名行迹神秘的跛腿驼背老头,其在船上诡秘的行踪和举止也引起了文抒的怀疑,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侦查对象中。然而,小说在其结尾向读者昭示了这个怪老头实际上是由郑剑乔装改扮而成的,他正是在这一特异装束的掩护下不动声色地查清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说,《佛岛迷踪》中侦探“乔装查案”的情节不仅体现了这一传统侦探小说情节的基本特征,而且还负载着悬念设置的独特功能。小说中作为警探的郑剑本应在案发现场认真勘察、以期通过蛛丝马迹来搜寻证据、求得真相,但他却未直接现身,而是以乔装的方式注视船上的一举一动,而文抒与读者对此却全然不知,加之作品对于这一神秘老头行为的层层渲染,不仅使文抒将其与真正的作案者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令读者疑窦丛生,对其真实身份和行动意图都颇感兴趣,由此便通过平素看似波澜不惊的侦探“乔装查案”情节铺设了十分强烈的戏剧性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侦探小说中的“乔装查案”情节不仅具有强化作品整体情节悬念的特殊功效,而且其悬念也与一般侦探推理情节所表现出的悬念设置方式有所区别。《佛岛迷踪》在情节结构上借鉴了国外经典侦探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展现出“负责案件调查的侦探与其他素昧平生之人共处封闭、隔绝环境中,其中一人遇害,而其他人均有作案动机,作案者也确为这些人中的一个或几个”的情节结构。这一情节模式可以说是欧美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常见模式,尤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最为常见。“克里斯蒂总是那样善于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凝聚到一个很小的空间,并且最大限度地密封隔绝这个空间。”[4]《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乃至《无人生还》这些克里斯蒂的代表作实际上都呈现出这种推理情节结构。《佛岛迷踪》虽然借鉴了这一情节书写模式,但由于侦探“乔装查案”情节的羼入而使得其在情节悬念效果上有别于传统经典模式。在克里斯蒂着意构设的“与世隔绝、多人共处、一人被杀、余人负嫌、真凶隐伏”的情节模式中,多是以外人较难涉足的封闭之地,如岛屿、列车、轮渡等特殊空间作为案发地,“在这样高度浓缩、高度封闭的空间里,情节经过挤压和浓缩,砍去了一切枝蔓,使故事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情节也更加险象丛生。”[4]268除了调查案件的侦探主人公外,其余的人多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过节或利益冲突,他们均有行凶杀人的作案动机,而经过侦探的最终揭秘,凶手确为其中的一人或多人,就在这一关乎真凶的悬念及其破解过程中,读者充分领略到了侦探小说的独特魅力。虽然在侦探揭示真相时,读者为之深感惊叹,但由于读者已在结尾谜底揭开前,将凶手的预设限定于除死者外的其余几人,因而这种情节模式与植入了“乔装查案”情节的这一情节模式相比,无疑在悬念效果上有差距。在《佛岛迷踪》中,由于驼背老头一直与船上的其他乘客一样都是被怀疑的对象,再加上他怪异的举止、神秘的行踪,这都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扮演着反面角色,而当这一所谓的反面人物在小说结尾褪去伪装、显出真容后,他变为了作品中秉持正义、足智多谋的侦探主人公,由此通过“乔装查案”情节构成了一种人物由反至正的形象骤变,作品也紧接着描写了文抒等在场者目睹此情此景的惊讶诧异之情。作者在此通过文抒等人的强烈反应凸显出郑剑这一形象转变所具有的强烈冲击力,而实际上这也表征了读者在此所表现出的惊讶之情。可以说,这种由“乔装查案”情节衍生而来的人物形象突变不仅使读者备感惊诧,而且也在“与世隔绝、多人共处、一人被杀、余人负嫌、真凶隐伏”的情节模式的基础上极大地强化了真凶身份的悬念审美效果。
三、“乔装查案”情节的多重文学渊源
文学创作在其发展进程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传承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后代作品对前代作品在人物塑造、叙事情节、思想主旨等方面的参阅、借鉴、袭用,从中不仅可以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也可窥探出某些特殊人物、情节的传播、流变过程。作为通俗文学重要类型的侦探小说亦不例外,这在《佛岛迷踪》和《大唐狄公案》中体现得十分鲜明。
《佛岛迷踪》所呈现的“与世隔绝、多人共处、一人被杀、余人负嫌、真凶隐伏”的情节模式虽然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许多代表性作品中都可寻根溯源,但其整体情节构思更多的还是借鉴了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神探波罗在游览尼罗河沿岸的客船上侦破一起连环杀人案的故事。而展现了郑剑、文抒在前往佛岛的客轮上破获一起绑架勒索案的《佛岛迷踪》与前者十分相似。除了基本情节结构的高度相似外,两部小说在案发现场(均为游览客船)、涉案人员(均为船上游客)等方面也都是一般无二,可以说,《佛岛迷踪》在人物关系、地点背景、情节构架等诸多方面都套用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但另一方面,《佛岛迷踪》又在一些局部情节设计上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代表性篇章,展现了福尔摩斯与其助手华生粉碎了一起企图利用“魔犬”传说来加害他人、夺取家族遗产的阴谋的故事。案件侦破过程中,接手案件而最初并未前赴案发庄园的福尔摩斯在未告知华生的情况下,秘密来到庄园附近,甚至一度还成为华生侦查的对象,直至两人见面。而《佛岛迷踪》也同样展现了郑剑在未告知调查伙伴文抒的情况下,以驼背老头的形象在船上暗中调查。二者唯一不同的是,福尔摩斯是在隐匿行藏的情况下在庄园周围暗暗访查,而郑剑则是乔装改扮后堂而皇之地活动于众人眼前。除此之外,《佛岛迷踪》中的侦探“乔装查案”情节也可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寻觅到艺术源流。正如英国侦探小说家、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所指出的那样:“福尔摩斯的化妆手法也比其他侦探高明得多。”[5]在《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波希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为了探查消息而先后乔装成马夫和牧师,而另一部短篇小说《空屋》又别出心裁地表现了福尔摩斯为躲避莫里亚蒂集团余党的追杀而乔装成为一名喜爱藏书的老者。可以看出,熟读众多经典侦探小说并撰写过侦探小说史的曹正文无疑从侦探“乔装查案”的情节中获得了创作灵感,从而将这一奇巧情节植入了自己的作品《佛岛迷踪》中,进而令自己笔下那个由郑剑改扮的驼背老头形象与柯南道尔塑造的、由福尔摩斯乔装的残疾老者呈现出异曲同工之妙。以此来审视《佛岛迷踪》中郑剑“乔装查案”的情节,其在营造独特悬念效果之际,也反映了曹正文对经典作品的巧妙借鉴,更折射了世界侦探小说的创作传统对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虽然极富意趣地展现了狄仁杰“乔装查案”的情节,但这一独特的情节表述却绝非作者为了强化作品的奇趣性而增加的情节,而是有着某种文学渊源和文化源流背景。就《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的“乔装查案”行为而言,其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他的这种乔装出行一方面是改易行装、侦办案件,另一方面又未尝不是地方官微服巡查民情的行为,而这种乔装行为的特殊双重性亦是源于狄仁杰身份的特殊二重性:他既是侦探小说中凭借智慧屡破奇案的神探,又是传统公案小说中忠正不阿、为民做主的清官。高罗佩“广罗中国古代刑律折狱龟鉴及公案小说素材,将其重组拼装到狄公一人身上,除了赋予他为政廉明、执法不阿、不畏权势、体恤苍生这些清官特征外,又为其叠加了注重事实、亲自侦查、严密推理的西方侦探特质”[6],作为神探的他为了及早侦破疑案,必然要走出府衙、深入了解案件的因由始末;作为清官的他为了体察自己治下的真实民情,也势必要深入坊间。前者为了获得有关案情的真实信息,时常隐匿自己的侦探身份,后者为了直击客观的民情,则必须要掩饰自己父母官的身份。因此,神探与清官都常常采取乔装改扮的方式,狄仁杰的“乔装查案”正是将清官微服私访与神探“乔装查案”融合在一起,这种双重性实际上也是西方侦探小说中的“神探”文化情结与中国公案小说中的“清官”文化情结的双重折射。
与此同时,《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乔装查案”所投射的东西方文化意蕴从这一情节的艺术流变与文学传承的层面更可见出。作为一部侦探推理小说集,《大唐狄公案》是由西方汉学家创作的,其主要读者群一开始也是针对欧美读者,但这部作品的写作初衷却是源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公案小说,对此,高罗佩曾直言:“中国公案小说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刑事案例。因此,我觉得利用过去中国小说使用过的一些情节由自己来写一部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将是一个有趣的尝试。”[3]1故而,《大唐狄公案》在诸多方面都受到明清公案小说的显著影响,其不仅在思想理念上与明清小说不乏相通之处,如其对僧侣形象的负面化塑造就是明清小说作品中“毁僧谤道”倾向的某种现代折射,其对许多女性人物的刻画又似乎不脱“女性祸水”的观念窠臼,这在明清小说中又是十分常见,而且其在情节方面也时常借鉴甚至改用自明清小说,如其许多故事篇章的情节都是取自“三言二拍”、《龙图公案》。作为唯一一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古典小说,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中的许多情节也被《大唐狄公案》所袭用,最明显的即为后者中的“陈宝珍铁钉杀夫案”几乎完全照搬自前者中的“周氏铁钉杀夫案”。另外,《大唐狄公案》所表现的狄仁杰“乔装查案”的情节亦可在明清公案小说中寻得踪迹。明清公案小说中多有清官“乔装查案”一类的情节表述,譬如《于公案》展现了于成龙乔装为道士查案的情节。而在《狄公案》中,作者不仅写到狄仁杰“换了微行衣服,装成个卖药医生,带了许多草药,出了衙署”[7],还表现了他在街市上招揽生意以及诊脉问疾的情节。由此可见,高罗佩对于“乔装查案”情节的构建很大程度上袭用了这部同样以狄仁杰作为主人公的前代作品对于“乔装查案”情节的书写理念,正因如此,“乔装查案”情节也从侧面折射了《大唐狄公案》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承继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大唐狄公案》属于典型意义上的侦探推理小说,而自《福尔摩斯探案集》开始,侦探小说这一通俗文学的主要类型就多次浮现了侦探主人公“乔装查案”的故事情节,因而,“乔装查案”情节也映射了侦探小说创作传统对《大唐狄公案》的深刻影响,由此可以说,“乔装查案”这一情节看似简单,但其却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学对于《大唐狄公案》的双向影响;亦可以说,《大唐狄公案》对于东方和西方两地的文学传统都存在明显的艺术传承关系,而这种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文学继承关系实际上也恰好投射了高罗佩在写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所秉持的“东西兼容”这一独特创作理念。
四、结语
作为侦探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的情节模式,“乔装查案”情节在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及曹正文的《佛岛迷踪》中都有着典型性的反映。这一情节表述在以上述两部作品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中不仅对悬念的设置具有特殊的作用,有助于强化作品情节本身的悬疑性、曲折性,而且也从侧面折射出侦探小说发展进程中的艺术承继关系和形象流变脉络。故而,这一情节表述对于认识、研究高罗佩与曹正文这两位作家各自的文学创作理念以及侦探小说这种受众极广、影响深远的通俗文学类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