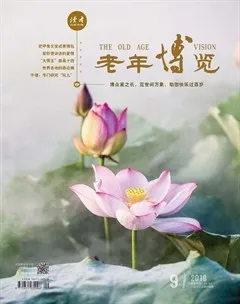食在意大利
2018-12-29利明

意大利的面食是一流的。但地道的意大利面食,比如比萨、通心粉、意大利面和一种叫提拉米苏的甜点,只有意大利境内才有,因为真正使它们美味的不在于面,而在于当地生产的奶酪、调料加上做工。就拿比萨来说,意大利境外我只在巴黎的香街和里昂吃过比较正宗的,那也是地道的意大利人开的店,其他地方的大多是赝品。
关于比萨,传说马可·波罗当年在中国吃过馅饼,感觉妙不可言,于是回去照猫画虎地制作,但把饼弄好之后,不知道该把馅儿怎么处置,没办法,就搁在上面了。为了证实这是谣言,意大利人特别进行了考古,证明他们第一份记载比萨做法的食谱早在马可·波罗去中国前若干年就已经存在了。
比萨真正的发源地是那波利,据说那边的师傅都是老人,只在晚上工作。但那波利的比萨我并不觉得好,因为上面放的是咸鱼,太咸。比萨美味的关键,除了用木柴火烘烤之外,就是饼上面的鲜奶酪,学名马苏里拉。奶酪烘烤之后呈奶黄色、半流质状态,吃到嘴里的那种香和软简直无法言说。另外,番茄酱是少不了的,至于你还喜欢加点什么,例如帕尔玛火腿、蘑菇等,则全凭自己口味。一定要尝试喝海水的滋味,那就点一客那波利的咸鱼比萨吧。
意大利面,比较合中国人口味的是博洛尼亚番茄肉酱面,你可以管它叫意大利炸酱面。其他的因为拌的奶酪过多,加上面又很硬,国人不见得会喜欢。
在什么样的店里吃正宗的意大利面食,我认为这个不重要。在意大利,大小餐馆无一例外地对他们提供的食物不会糊弄,只是价格有所不同而已。一来是因为食物质量是这些店的生存保证;二来是因为意大利人拿吃非常当回事儿,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业荣誉甚至民族尊严,马虎不得。
意大利的饮食相当丰富,即便有介绍全面的书籍做参考,还须多加尝试,才能得出经验。笔者要在此着重介绍的不是各种饮食,而是在意大利餐馆(西欧其他餐馆也一样)那种特殊的就餐体验。
对当地人来说,到餐馆就餐,除了品尝美味或填饱肚子之外,更重要的是享受那种既公共又私人的氛围。而对我们这样的外来者来说,观察其中的微妙之处,也是旅游的一个收获。例如在米兰,散团之后,我一般会去商业走廊后面的一条街。那里有家餐馆,门脸不大,但相当讲究,门口还有专门为残疾人的轮椅准备的通道。那里提供的饮食价格还算公道,而我去那里,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侍者让人心情愉快:你第二次去,他们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和你握手寒暄,还会在你耳边小声嘀咕一句,告诉你当天的招牌菜,然后把手指放到嘴唇上,扬手,同时嘴里“啧啧”有声,让你感觉不点这道菜,就会错过与意大利某个性感女郎接吻的机会似的。若是对选择酒水犹豫不决,说不定邻座的一对老夫妻会帮忙介绍。他们已经在吃餐后甜点,不时微笑并深情地凝视对方。两人的手尽管已满是皱褶和斑点,却一直在桌面上相互抚摸着。
在佛罗伦萨,有一家餐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根据书上的介绍,佛罗伦萨的一种牛排是西方世界一流的。那种牛是一个特殊的品种,据说是用啤酒和莫扎特的音乐养育出来的,光生牛肉就要70多欧元1公斤。我在那家餐馆斗胆尝试了一下,并不见得如何好,只感觉量太大,吃的时候心理压力不小,像是在对付小半头牛似的。餐后我去厕所方便,厕所门口有一个来自南亚一带的红皮肤中年女子,小小的个子,笑眯眯的—她是打扫厕所的女佣,会收点儿小费。我方便完洗手时,听见她在外面哼歌儿。出来后我问:“你在唱歌?”她回答:“是啊。”我问为什么,她笑眯眯地回答:“不为什么,就是高兴。”这件事儿让我纳闷了很久。有时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苦瓜脸,我不由得想起这个干着被人视为低贱的活儿,却高兴地唱歌的南亚女子。我多少明白了,生存的苦乐不在于一个人是什么身份,而在于是什么心态。
在罗马那天,午后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散团后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我发狠进了梵蒂冈后面一家很讲究的酒店餐厅,因为只有那里有空调。我的着装实在不怎么样:T恤、短裤加露着脚指头的凉鞋,胸口和腋下还汗津津的。迎面过来一个老人招呼我,我一下子看呆了。这位意大利老人起码65岁了,身着一身笔挺的藏蓝西服,白衬衣,鲜艳的领带,灰白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面孔光洁透红,那优雅的风度,能把一打意大利部长比下去。他是这个餐厅的经理。他从头到脚快速打量了我一下,没说一句暗示我知难而退的词儿,而是像请贵宾一样做了个手势。那顿饭吃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吃饭时我不断地盯着那位老先生,最后经他同意给他拍了张照片。回来后给老婆看,老婆说:“就这风度,绝对能迷倒一批年轻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