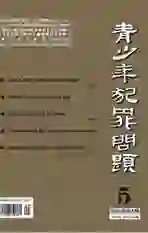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研究
2018-12-27王瑞山
【内容摘要】
在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家、国二元治理格局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教化、家庭教养、个人修身等多个层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规定不仅体现了“慎刑”“恤幼”的思想,也体现了伦理治安背景下漠视未成年人主体权益的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中一些关于社会控制的预防思想有着合理的成分,有的与当前犯罪学理论相印证,为研究制定符合中国文化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提供了参考价值,但其忽视未成年人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的传统依然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犯罪预防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不同于当代的经济基础、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也有着不同于当代的对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的观念和政策选择,形成特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至于当下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之理解和谋划有着借鉴意义。然而,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①整体上看比较薄弱,内容也不够系统,亟待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拟从厘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概念的内涵和分析框架出发,对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进行梳理,以期对理解和设计当代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有所裨益。
一、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与分析路径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是要用刑事政策的分析框架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抑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设计,所以,在研究具体的刑事政策内容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刑事政策的概念框架以及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特殊路径。
(一)中国传统社会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中国传统刑律中未成年人的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为15周岁以上。中国传统社会,男子年龄满15周岁为成童,“束发”就学,②如孔子言其“十有五而志于学”,③20岁成年,称为弱冠;女子满15周岁成年,称为“及笄”。《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然而,从刑事责任年龄来看,承担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是15周岁以上。以中国传统刑律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唐律》为例,其《名例》篇中明确了15岁以上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不满15岁的称“小”,具有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名例》篇“老小废疾”条进一步把唐代社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7岁以下(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7岁至10岁(含10岁,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对谋大逆等重罪负责)、11岁至15岁(完全负刑事责任但可减轻处罚)三个阶段。
刘斌:《浅议唐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当然,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并非是一成不变,从一些文献来看,唐代以前的规定看起来更为严格。例如,西汉成帝鸿嘉元年,颁布律令规定“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可以“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
《文献通考·刑考二》。这说明7岁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只不过是有所减轻。到东汉时,“年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皆不坐。”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可见,东汉时期比更加宽容,年龄放宽一岁,仅追究恶性极大的“手杀人”。唐代以后,除了元代,基本沿用唐律的刑事年龄的规定,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疏义的翻版,明律只是将“老小废疾”条改为“老小废疾收赎”,内容俱同。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怀效锋、李鸣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2页。可见,我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范围基本可以按照唐律的规定,即7-15(周)岁。
(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内涵及分析路径
刑事政策的讨论有广义和狭义的观点,两者均以抑制犯罪为目的,狭义的刑事政策是以刑罚的运用为核心内容,广义的刑事政策则不仅包括刑罚策略,还包括社会政策。相应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有从狭义和广义的不同视角,例如,有人從狭义角度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界定为“国家或执政党依据未成年人犯罪态势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和未成年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
张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也有人从广义角度来理解,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目的推动下,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制定的各种方针、原则、策略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
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本文采用广义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而采取的各种对策。刑事政策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种,前者是运用刑事法律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进行惩罚,后者为对犯罪发生前的防范,是非刑事惩罚措施。其中,“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
王牧:《新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282页。本文拟采取这种分类观点,对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进行解析。需要指出的是,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非刑事惩罚措施,要强调其以犯罪抑制为直接目的,这种直接目的的关联性使得这种考察的范围不至于过大。
(三)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的礼刑格局
刑事政策是治国之道的一部分,属于“治道”。
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考察中国传统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考虑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特征。礼和刑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实现治安的两种基本手段,礼是积极的规矩,“禁于将然之前”;刑是消极的惩罚,“禁于已然之后”。
《汉书·贾谊传》。礼教为本,刑罚为用,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古代经国家、定社稷的基本国策。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其(作者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根本寄托在礼俗上,而不著见于法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孔子强调以德礼教化对于刑罚惩戒的优越性,他认为用道德来引导人们,用礼义规范来约束民众,而不是用政令引导、用刑罚规范,这样民则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会心悦诚服,社会才能安定。 《论语·为政》。中国传统社会犯罪治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大化、刑措而不用,那是礼乐教化发挥到最好效果的状态。因此,要完整认识中国传统社会预防和惩罚未成年人犯罪的系统设计,必须要从礼法结合、礼主法辅这一基本战略出发。礼法结合所指导的具体实践是有先后顺序的,礼在法先,礼对为成年人行为的规范(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消弭)是其出生后的教化阶段,法是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后的惩戒和矫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法与罚不仅是在国家的法律中的,还在家庭、家族的家规中的,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人,在家长制的宗法伦理中,必须受到这双重约束。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的分析,要遵循先礼后刑的顺序。
二、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思想
以“礼”为内容的教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社会预防的核心特征。中国传统社会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推进礼的实施,特别是礼的规则在未成年人价值观中的内化,向善远罪。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一个社会成员价值追求的系统构建。 《礼记·大学第四十二》。而未成年人的社会预防核心思想是以礼节欲,实现路径则体现在国家、家庭、个人三个层面以礼为核心的规训。
(一)以“礼”节欲的社会预防思想诠释
通过以礼为内容的教化来预防犯罪,是我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基本战略。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思考是预防的前提。先贤们习惯于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将违法犯罪称为恶行,普遍认为人的欲望是这些恶行的原动力。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以及后世诸贤提出的人性观点,都认为人的无节制的欲望导致了种种不法。
王瑞山:《论养性成善的中国传统治安思想》,载宫志刚主编:《治安学论丛》(第八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8页。孔子认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无论是求富贵,还是去贫贱,都要遵从一定的“道”,即礼。否则,依据个人利益而行,不顾“道”的约束,容易招致很多怨恨,即“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所以,孔子明确反对不正当的满足自己的富贵之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提出“人性善”的观点,强调的是人的善根,即仁义礼智的向善之性(恒心),而且这种善根如果被口、目、耳、鼻、四肢追求“味”“色”“声”“臭”“安佚”的欲望所遮蔽,也会导致恶行。《孟子·尽心下》;《孟子·滕文公上》。荀子的“性恶论”实则是“欲恶论”,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但是这种欲望追求需要节制,如果人“无度量”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导致“争”“乱”,以至于“暴”,成为恶行的原因。《荀子·礼论》。后世贤哲对人性的解释很多,但几乎不会超出这些范畴,集中到一点,就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欲求,通过正常的制度化途径来实现。如何做到这一点,理论上路径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外用力,就是发展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二是向内用力,就是以礼节欲,倡导“安贫乐道”,追求平均主义;统治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选择的是后者,宋明理学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显然是一种极端表现。
何谓礼?它既包括“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又包括“黎庶车舆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实现社会生活的全覆盖。荀子认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先王制礼的原因就是针对性地解决人无节制追求欲望而导致的“乱”,通过“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制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礼制使得不同等级社会成员的物质享受都设定了标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欲望。每个人都遵从礼的安排,不要有非分之想,社会秩序得以实现。如何使人们接受“礼”,这就是“教”,因此,以“礼”为核心内容的“教”就具有直接的预防意义。“富而后教”是儒家先哲们制定的社会预防策略,其中“教”追求的目标是:“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礼记·经解第二十三》。董仲舒对教化防罪的论述较为完备,他认为通过教化成善,达到“止奸邪”的作用,教化成為防止人性之恶的“堤防”,“教化行而习俗美”,如果教化废则“堤防”坏,则犯罪会猖獗,以致于刑罚罚不胜罚。《汉书·董仲舒传》。
(二)以“礼”节欲的社会预防思想展开
国家层面,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会通过树典型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学习的榜样,这些榜样是践行“礼”的楷模,如二十四孝的典型故事主人公、贞女烈妇、孝子贤孙等;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途径是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如社学。北宋程颐论述了当时乡间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功能:“民生八年则入于小学,是天下无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从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贤能群聚于朝,良善成风于下,礼义大行,习俗粹美,刑罚虽设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伊川先生文五·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可见,通过学校教育,直接目的是修身明道,不犯刑罚,具有直接的犯罪预防功能。西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张晏曰:“聚,邑落名也。”颜师古曰:“聚小于乡。聚音才喻反。”北魏高祐在太和中曾建议,“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北史·高祐传》。。可见,当时已有比较系统的学校设置。元朝以后乡里设立社学,制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行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社学是当时农村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明清两代,社学成为乡村公众办学的形式,带有义学性质,多设于当地文庙,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乡间学校教育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如元代社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社学教育内容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学生年龄以未成年人为主,明代要求社学学生为十五岁以下之幼童;清初社学入学年龄为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而且入学者得免差役。社学的犯罪预防功能受到思想家的重视,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王守仁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推动当地社学教育。
家庭层面,家长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教化过程,是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社会预防的关键环节。《礼记》把家庭教化的地位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认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礼记·大学第四十二》。正所謂“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社会成员“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离开了家就面对着国,家庭安定,社会就安定了。梁任公称“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承担着国家的犯罪预防功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也不例外。家庭教养中,仍是礼的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孝悌”。明代王守仁的《训蒙教约》指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王阳明全集》卷一,《知行录之二·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论语》直接论述了孝悌的预防功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家庭(家族)中,家长(族长)对家庭(家族)其他成员具有绝对的权威,也承担着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行为的导师。家长用儒家纲常训导子弟,培养孩子符合礼的品格,培养孩子谋生的能力,严防子孙的不良行为。王瑞山:《试论〈世范〉中的青少年犯罪预防思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4期。南北朝的颜之推提出在婴孩阶段便加教诲,目的就是“比及数岁,可省笞罚”。《颜氏家训·教子》。同时,家庭教育的重要保障手段是惩罚。《吕氏春秋》曰:“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颜氏家训》中说,“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这就需要赋予家庭、特别是家长或族长的惩戒权威。但是,这种惩戒限于鞭扑等成分,国家否认家长对子女的生杀权力,因为生杀大权属于君王、国家。例如,北魏时期有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处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魏书·刑罚志》。唐律也规定了尊长杀死子孙皆处徒罪,明清律也有类似规定。此外,父母还有送惩权的权力。明清律规定,对被父母送惩的子女,一般处杖刑一百。清代父母还有呈送发遣的权力,要求官府将不孝子发配至云贵或两广。这是唐、宋以后,随着国家对家长、族长的倚重,其权力不断扩大的缘故。宋史载陆九渊家族中,“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宋史·陆九韶传》。此可谓当时家长惩罚权的客观写照。
个人层面,修性自防。除了外在教化之外,先哲们还强调个人修身,孔子强调“我”的主观性,怎样才能使“我”自觉为“仁”,就要注重“修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可谓,对自身有高度的道德要求。孟子指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些要求,也成为儒家塑造的一个理想人格“君子”应具有的品质。修身注重的是道德品行,形成符合统治者主流价值观的积极自我,达到个体的内在控制,直接起到犯罪预防的效果。金其高教授将其总结为“修性自防”,他认为“修性自防是依靠通过修身养性形成的自我控制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不作为为防范特征。”金其高:《社会治安防控经略》,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页。对于修身的路径有不同的表述,朱熹认为修身源于对人的善的天性的认识,具体实现方式还是克己复礼。朱熹说: “礼者,理也,亦言礼之属乎天理,以对己之属乎人欲。”
《四书或问·论语或问》。所以,克己复礼即存天理灭人欲,“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克己复礼,惩忿窒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王守仁提出“致良知”,以“真吾之好”改变“名利之好”,“防非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王阳明全集》卷一,《知行录·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他注重人的心之“养”,修养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克制自己的过程。王守仁把个人修养作为自我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并将自己的思想与社会规范融为一体,以达理想之社会状态。“修性自防”是增加个人对社会规范的体认和服从,防止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社会秩序的要求,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崇。“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的教化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教化体系,每个社会个体周围像同心圆一样被层层教化之网包围。统治者自然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以礼为核心的伦理规范,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打造天下大治的清平景象。当然,教化都存在着失败的可能,对那些不从教化的子女、乡民、臣民,需要对以家法、约法、王法予以惩戒,教育本人并以儆效尤,为教化推行提供强制力保障,形成德教于前、刑辅于后的预防思想。
三、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惩罚政策思想
现有研究认为,“恤幼”思想和以“礼”为内容的宗法伦理思想被认为是发挥着现代刑事政策作用的两种思想。“恤幼”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慎刑”思想相结合,而宗法伦理思想则是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惩罚的刚性原则,“恤幼”思想要以它为指引。
(一)“恤幼”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惩罚政策的影响
未成年人是一个弱小的特殊群体,对他们的刑事处罚有违统治者所倡导的“仁政”思想,而且,由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恕不足以危及正常的统治秩序,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恤幼”思想与“仁政”思想一脉相承。参见雷海峰:《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4期;张利兆:《“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6期。这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慎刑”“恤幼”的传统,这种“慎刑”“恤幼”的实施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让位于德主刑辅的礼治传统需要,包括对特定社会对象的“慎刑”,有尊者,还有弱势群体;二是对政权的威胁程度,威胁程度越小,越有可能成为“慎刑”的对象。显然,未成年人符合上述两项特征。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性规定散见于一些律典和最高立法者皇帝的“金口玉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不同追诉阶段的刑事司法制度中。
首先是量刑阶段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限制适用一些肉刑和羞辱刑。例如,西汉惠帝初即位时规定,“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髡剃也)”。《文献通考·刑考二》。同时,未成年人犯罪还可以适用“上请”的特别程序。例如,前引西汉成帝诏中的7岁以下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唐律中规定的10岁以下犯反、逆、杀人应死者,均可以启动“上请”程序。“上请”是一種特别程序,它起源于汉代,范围先由三千石官后逐渐扩延至六百石官,进而又扩大到公、列侯嗣子犯耐以上的罪。东汉时几乎所有官员不论犯何种罪行,均可享受此种待遇。唐律名例律中专列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怀效锋、李鸣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可见,“上请”非一般普通百姓所适用,对未成年人适用这一特别程序,足见涵养之意。还有专门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选择较轻的刑罚。例如,《大清律例统考卷》的《窃盗》篇中对于旗人中的“积匪”和“猾贼”处以注销旗籍、刺配新疆为兵的刑罚,但如果该犯系15岁以下,则处罚较轻,如就近发配黑龙江而非新疆。《强盗》篇中也有对被迫参与抢劫的14岁少年免死处流的判例。马建石、杨育裳:《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0页。另外,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上,是以犯罪实施时的时间,如唐律卷四“犯时未老疾”条规定,“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这样比较客观,不仅体现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技术,还凸显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关注。
其次是刑罚执行阶段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在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上,对特定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执行收赎。前引唐律中“老小废疾”条不仅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还规定了“收赎”的特别适用,即15岁以下犯流罪以下的可以收赎,10岁以下犯盗及伤人罪者也可以收赎。明律与唐律有着类似的规定,仅将律条名改为“老小废疾收赎”。元代刑律按照其命价银习惯法也规定了15岁以下未成年人“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因争毁伤人致死者,听赎,征烧埋银给苦主”。《元史·刑法四》。与“上请”类似,“收赎”也是古代社会中贵族、官宦及其亲属的特权,非一般民众所适用,因此,这也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别保护。在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强制方面,未成年犯罪人可以不戴刑具。例如,西汉文帝四年诏“八岁以下”未成年犯罪人当“鞫系者,颂系之”,汉景帝后元三年令有同样的规定。“颂系”又称“散禁”,古代法律中有关特定囚人不戴狱具的规定。注云:“颂,读曰容。容,宽容之,不桎梏。”与“上请”、“收赎”类似,享有“颂系”这种特殊待遇的首先也是官僚贵族,如汉代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有罪应当监禁、戴械具者,可免之。《汉书·刑法志》。在羁押期间,明朝洪武元年明令,15岁以下“禁系囚徒”与其他囚犯分别关押,“不许混杂”。万安中:《论中国古代监狱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其特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这种分押措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目的是明显的,避免其可能遭受到的成年囚犯的侵犯,或者犯罪学习,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身心健康,是一种进步。
(二)宗法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惩罚政策的影响
首先,宗法伦理则使未成年人犯罪处于不利地位,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一是未成年人可能涉及的依据宗法伦理而设置的严重罪名。礼法结合后,法典中设立了许多以违反宗法伦理为内容的罪名,包括一些非常严重的犯罪。例如,北齐律中设立的、后来发展成“十恶”的“重罪十条”,其中,“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孝”(诅骂祖父母、父母,不供养祖父母、父母及违反服制的行为)两条就是严重违背家庭宗法伦理的。之所以规定如此严厉的罪行,显然是为了实现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来维护“孝”及相关伦理秩序。二是宗法伦理影响下的“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使未成年犯罪人处于不利地位。 “准五服以制罪”始于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晋律》直接“纳礼入律”,将儒家的“服制”礼入律典,设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服制越近,以卑犯尊者处罚越重,以尊犯卑者处罚越轻;反之,越轻。从血缘关系来看,未成年人容易处在卑者地位,如果未成年人以卑犯尊,将遭受严厉的惩罚。因此,宗法伦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也说明,“恤幼”的边界是不能违反以“礼”为内容的宗法伦理,进一步证明了刑罚是礼的补充。
其次,“亲亲相隐”原则可能使未成年人犯罪从“国法”惩罚转为“家法”惩罚。在宗法伦理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刑事司法中实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该原则来自西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该诏令阐述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初衷,是不违“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应有的“诚爱”。后来唐律的规定,直接强调“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这个原则强调,为了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为孝屈法”,“为亲屈法”,增加了侦查的难度。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据此原则,卑幼隐匿有罪尊长,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隐匿有罪卑幼,死罪以下也不追究刑事责任,死罪可上请。因此,“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可能会因尊长的隐匿而不会受到官方的追究,可能包庇不受任何惩罚,也可能转而通过上述的“家法”或其他方式来解决。
上述梳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宗法伦理对司法秩序的冲击,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刑关系的不平衡,证明了刑只是维护礼的手段。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中,处罚轻重,以“礼”为准。
结语
梁漱溟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与以宗教秩序为盛的古印度文明、利用科技征服自然的西洋文明相比,认为“旧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并将之称为“中国文明一大异彩”。至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如何维持?他总结说:中国传统社会秩序“虽最后亦不能无借于国家法律,但它融国家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所以维持之者,固在其个人其社会之自力,而非赖强制之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80页。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主要在于以礼治为内涵的社会控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如此。当代社会控制理论在犯罪学中被广泛运用,如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马茨阿的中立化理论、赫希的社会纽带理论等,从大部分人为什么不犯罪出发,来探寻社会成员不犯罪的原因,进而解释人为什么犯罪。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例如,通过多种措施促进未成年人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对于挫折的包容、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制定现实目标的能力等;加强对未成年人与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纽带,发挥家庭和学校的社会控制功能;现实的溺爱、只要求孩子学习的做法使得未成年人不清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规范与责任,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纪律管束,正确引导未成年人的社会交游,增加未成年人获得接受、认同和归属感的机会。
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设计凸显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给予了保护性的安排,注意到该群体与成年人的区别,这是比较进步的。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中,未成年人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是依附于家长,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往往是家长的责任,社会所要追究的往往是家长,未成年人犯罪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因此,未成年人刑事规范并不发达,只是服务于礼治秩序的附庸。当代社会,未成年人的权益日益受到重视,从国际到国内都有给予相应的规范,但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礼治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宗法观念,未成年人在中国还是“家庭人”,而非“社会人”;是子女,不是公民。许多未成年人“既缺失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也处于缺乏国家恩泽之境地”。李霞、张艳:《论〈民法总则〉中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6期。这不利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参考文献
[1]王牧:《新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怀效锋、李鸣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王瑞山:《中国传统治安思想研究——以盗贼为考察对象》,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雷海峰:《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4期。
[8]张利兆:《“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陈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