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怀念李希凡先生
2018-12-19胡晴
胡 晴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上图:李希凡先生
2018年10月29日凌晨1时52分,李希凡先生离开了我们。他走得有些突然,10月16日重阳节还看到他出席当日的雅集,谈笑自若,精神尚好,没想到不久后就接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又得知他走得安详平静,我心中稍微安慰。白天忙乱,晚上安静下来,看着媒体和微信上的悼念消息,心中凄惶,一抹脸,泪湿一片。
我对李希凡先生第一面的印象非常深刻。2001年秋天,我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与明清小说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办完报到手续后,父亲说带我去见见李希凡先生。父亲是冯其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主攻《红楼梦》研究,所以他是李希凡先生的晚辈,两人早就相识,学术上也多有交流。不过,李希凡先生于我来说还是文学史中的一个人物,是得到毛主席关注的“小人物”之一。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李先生当时从恭王府的夹道子迎着我们走过来,高高大大,笑容和煦,望着他,我心中忽然就冒出《世说新语》中的一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紧张感一下子散去了很多。
李希凡先生带我们去了当时他在恭王府的办公室,整座恭王府以及红楼梦研究所当时的办公地点天香庭院都是古香古色,雕栏精美,我边走边赞叹,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里是藏不住的好奇。李先生看到我的样子,大概要满足下我对这个新环境的种种遐想,特意指着一处地方跟我讲,那里有夹壁墙,当年和珅曾经把家财藏在里面。又开玩笑地讲,后面有九十九间半房间,大概是王熙凤放宝贝的地方。我和父亲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果然是红学家,三句话离不开《红楼梦》。听说我考上了《红楼梦》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他非常高兴,鼓励我勤奋学习。先生风趣适意的话语如暖阳拂过,缓解了我初来乍到的局促,也让我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
聊天中,李希凡先生还说起了自己身患糖尿病多年,最近眼睛不好,刚刚完成了激光手术。可他谈起自己的病,是轻松的口气,有股豪迈爽朗的气概,丝毫不见被疾病困扰的疲态。实际上,李先生精神奕奕、中气十足,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精神不少。初次见面,李希凡先生平易近人、开朗豪爽又幽默智慧的形象,让人油然而生亲近之感。原来著名的学者是这样平易可亲的,我心中欣喜。
2004年,我毕业并留在《红楼梦学刊》工作,同年秋天,我随红楼梦所的同事参与了2004年扬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服务工作。那次会议父亲也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我们父女在学术会议上相聚,喜悦之情与普通的家庭相聚又不相同。会议的间歇,李希凡先生找我父亲一起出去买烟聊天,还特意把父亲和我叫到一起合了张影。父亲欣喜又珍惜,他说李先生很爱惜自己的声誉,并不随意与人合影,而父亲也从不愿意去麻烦他。两个人只是单纯的交往,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此后,在各种红学会议和院所的活动中也常能见到李先生,但先生德高望重,往往是被大家“包围”的焦点,所以我一般不做打扰。如果先生身边人不多,我就会上前打招呼,聊上几句家常。李先生很念旧,每次见到我,必问候我父亲,可惜父亲疏懒好静,身体也不是太好,退休后多留在家乡休养,很少到北京或外地参加学术活动,少有机会拜见李先生,只能由我代为致意。2008年春,李先生收到我父亲所做《楝亭集笺注》一书,又特意托我将《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转交给我父亲,还附短信一封说:“大作收读,我正在白内障手术中间,只看了你的长篇前言,不胜钦佩。这是一本下了苦功的书,不是我这搞评论的人写得出的。拙作人物论一本,给了小胡,忘了老胡,这是大不敬,特此致歉。”李先生是如此著名的学者,对待我父亲和我,从来没有架子,他的平易近人与谦虚幽默在这封信中可见一斑。
我与李先生有学术上的深入交流是在2005年,这是我了解他治学原则的开始。2005年正值刘心武的“秦学”盛行,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认为秦可卿是胤礽的私生女,《红楼梦》是对宫廷政治斗争的暗写。刘心武的讲座热播,《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大卖,大众反响热烈,而专家学者正常的辩论问难则不仅得不到正面回应,还被引向了“正统红学”与所谓“草根红学”的对垒,一时间乌烟瘴气,遮蔽眼目。在此形势下,学刊领导安排我代表《红楼梦学刊》就“秦学”现象采访了冯其庸、李希凡和张庆善三位先生。
彼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搬离恭王府,李希凡先生在新院址也有办公室,我就约好在他办公室里进行了访谈。李先生对刘心武提出的“秦学”说法不以为然,他坚持《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这是李希凡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也是他从来坚持的研红原则。谈到刘心武的“秦学”,李希凡先生首先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入手,他认为在曹雪芹的原定人物设计中秦可卿本来应该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现在呈现出来的秦可卿已经完全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他认为这是曹雪芹《红楼梦》艺术创作上的一大失败,还为此写过一篇《丢了魂儿的秦可卿》。他说,《红楼梦》是艺术形象的创造,是艺术典型的创造,不是在写史实,从秦可卿这个人物有限的篇幅就把她猜测为藏在曹家的一位公主,猜谜猜得太远了。李希凡先生主张“艺术形象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回归文本还是应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地位的研究,回归作品的艺术分析”。李先生还严肃批评了媒体舆论导向,认为“没有单纯的娱乐性,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寓乐于教”。他也表示,作为研究者,他并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能做好工作,做好研究。
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能够借由访谈的机会聆听大师级人物的教导,学习做人做学问的正经道理,今时今日回味起来依然无比荣幸,终身受益。又念及冯其庸先生与李希凡先生两位红学巨擘都已驾鹤西归,时光无情,无限唏嘘。不过,当时我还是认为李先生一再强调的典型论已经有些过时,直到后来,我深入专题研究《红楼梦》评点的人物论,才对典型论有了再认识。我发现中国传统小说人物论与典型论最为契合,经常可以形成中西对话,是非常适合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指导,是不会过时的经典理论,从而也对李希凡先生的理论坚持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我又访问了冯其庸先生和张庆善先生,之后整理成《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六辑上。这篇访谈虽然集中了红学界的权威学者发声,但当时外界的声音依然纷扰,我们所能做的,就像李先生所说,做好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的研究,坚守研究者的一份职责继续前行。
那次访谈临近结束时,李希凡先生再次强调对《红楼梦》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的维护和看重,他说起另一本学术著作,主要是谈《金瓶梅》的,但作者在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时,处处彰显《金瓶梅》高于《红楼梦》。李先生非常不认同,也不赞成做这样的比较,还把那书送了我一本,大概也是希望我能了解评价《红楼梦》的不同声音,有所辨别。李先生还谈起当时他正在承担的重大学术项目,即《中华艺术通史》的主编工作,他感慨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颇为辛苦。2006年,这套《中华艺术通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包含美术、音乐、戏曲、舞蹈、曲艺等主要艺术门类,集中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骨干研究力量,可称是一项填补艺术学空白的学术工程,是李先生历时十年的心血,是他晚年又一重要学术成就,足以彰显他的学力与眼界。
李希凡先生成名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契机,虽然他的理想是成为文艺评论家,做个研究型学者,但一朝成名天下知,他注定将有更与众不同丰富多彩的人生。李先生也认同,自己的文化人生,是处于时代思潮的漩涡之中的,而他也一直说“我是新中国的幸运儿,我对我的文化人生无怨无悔”。李先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时写了大量文学评论文章,甚至自称“好战分子”,“什么讨论都想插一嘴”。时人谈及他的文学评论,认为犀利而有气势,具有时代气质。但我所见到的李先生一直都是宽厚长者,有些难以想象他当年以笔战斗的风采。
谁想,在李先生妻子重病家务缠身之际,一场论战不期而至。2011年9月21日,王学典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质疑半个多世纪前“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情是否存在,认为当年李希凡、蓝翎文章是《文史哲》编辑部的约稿,而非“不得已”时的投稿。2012年4月11日,李希凡、李萌也在《中华读书报》回击以《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写作和发表过程,厘清事实,批驳王文的推断与猜测。2012年4月18日,王学典又发文《“拿证据来”——敬答李希凡先生》。2012年5月9日,李希凡先生再应战《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中华读书报》上战火燃烧,引人注目,其间又有孙伟科的《“缘起”何需再“揭秘——1954年红学运动再述评》、徐庆全《两个“小人物”的信在哪里——兼驳李希凡先生》等文在《中华读书报》刊出。《红楼梦学刊》2012第三辑征得辩论双方同意,转载了李希凡、李萌和王学典的四篇文章,记录了这场论战。这是我亲见李先生的一次战斗,他虽已登耄耋之年,家事牵绕,依然毫无犹豫,正面应战,正气凛然,坦然淡然,让我领略到他截然不同的一面。至于当年事,先生早已在各种文章和回忆录中说明清楚,斯人已逝,“青史终能定是非”。
李希凡先生年事渐高,出席活动都会有家属陪在身边,我见到最多的是他的大女儿李萌。李萌不仅照顾先生,也成为了先生的优秀合作者,他们合作了《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这本书李先生也送给了我一本,此书充分运用典型论进行个案研究,又融汇了李先生熟读红楼的感受和独到见解,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不过,李先生也曾表示这本书出版得稍嫌仓促,本来想把其中文章都发表一下,看看反响,但因为文章很长,能发表的刊物有限,只在《红楼梦学刊》和一些学报上发表了一部分,也因此为以后的修订埋下了伏笔。
可惜的是,2012年,李希凡的夫人徐潮和李萌相继去世,时间先后仅相差三个月。为免李先生遭受连番打击,家人对他隐瞒了李萌去世的消息,直到四年后才告知先生。2014年《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出版修订版,李希凡先生在《〈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修订版后记》中记述了这段伤心事,念念不忘李萌在写作和修订此书中的功绩,“书稿三十三篇,涉及《红楼梦》人物六十多位,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虽由我初稿定调,但深入艺术境界,准确发掘和突出人物的个性风采,却是李萌对这本书的贡献”。“萌儿走了,走得很痛苦,但粗心的父亲,却是在最近才知道这一噩耗。其实早在2012年他母亲去世后三个月,她也随之离去……在老伴儿葬礼上,我和萌儿互相搀扶着,她已是勉强站到最后……”在我,李先生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更是慈祥可亲的长辈。看到他在后记中所写,看到先生心中何等清明又何等遗憾,不免为他晚年丧妻失女的情形感到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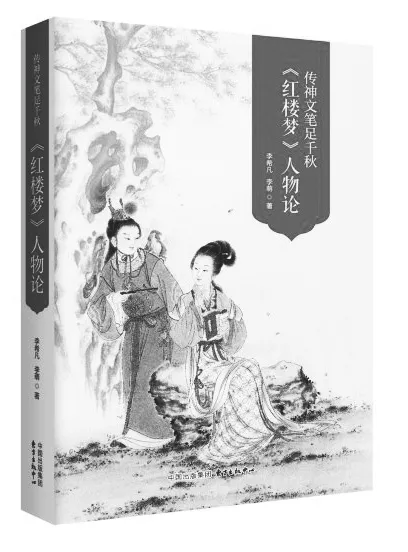
《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

《李希凡文集》
好在李希凡先生是豁达之人,他一直保有着学术热情笔耕不辍,晚年成果不断,除了《中华艺术通史》与《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李希凡文集》的出版是李先生学术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2014年,《李希凡文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我亦参加会议,躬逢其盛。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共计九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从各个角度对李希凡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李希凡文集》煌煌七卷本,逾四百万字,分为《中国古典小说论丛》《〈红楼梦〉人物论》《论鲁迅的“五种创作“》《现代文学评论集》《艺术评论集》《序跋随笔散文》、《往事回眸》,对李先生的学术生涯做了一次全面总结和真实呈现。完成了《李希凡文集》的工作后,李先生还一直心系着两项重要工程,一项是《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工作,一项是《红楼梦》新校本的修订工作。未料先生突然离世,心心念念的学术工程不及完成,竟成永远遗憾。
拉拉杂杂,语不成篇,有些东西只是沉淀在记忆深处但从未忘却,平淡的小事因时光的锤炼而显出光彩。作为后学小辈,我接触李希凡先生时间不长,与他的交集亦不算多,点滴小事完全不足以反映他的经历与成就,我仅能以我粗钝的笔和浅微的见识写出我心中的李希凡先生,以此聊表我诚挚的悼念之情。从见到李先生第一面开始,他的乐观爽朗、正直宽厚就让我心生敬爱,十几年从未改变。在我的心中,一位真正的学者,为学为人就应该是李希凡先生这个样子,在我心中,他永远都还是多年前向我走来的样子,高高大大,笑容和煦。听李希凡先生的小女儿李蓝说,先生曾有希望,想要在睡梦中安静离开,当时家人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想法。而李先生恰恰就是在睡梦中离去,安详平静,冥冥中一切自有安排。先生,愿您在天堂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