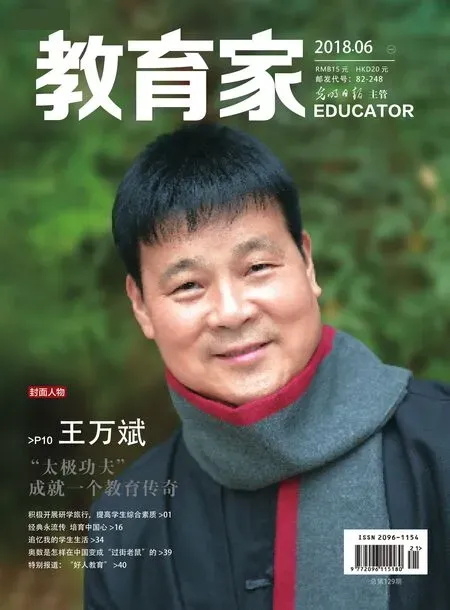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
2018-12-01吴盘生
译 | 吴盘生
2018年,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吴盘生先生的努力下,苏霍姆林斯基10封“给儿子的信”得以有机会与中国读者见面。本期《教育家》刊出的为信之三、信之四,期待读者能从教育家给儿子的信中汲取教育智慧。
之三
亲爱的儿子,你好!
你的来信使我十分震惊。现在,我满脑子都是你写的东西——一些年轻人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两个青年工人和一个大学生杀了人。事情似乎很简单,他们无所事事,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了口角,然后就杀了人。
你说的这件真人真事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冥思苦想——思索年轻人和中小学生教育的问题,思索青年人精神生活的问题。在我们国家,26岁以下的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这是我们应该铭记并加以讨论的事实。当然,我们讨论时不应欣喜,而应担忧。让我寝食不安的事实是,那些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或是早在八年级就肄业的人),完全脱离了教育的影响——睿智而专业的教育者施加的教育影响。除少数学校外,大多数大学和专科学校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德育工作,而这项工作恰恰又非常必要。我掌握了足够确切的资料,它们雄辩地证实:青少年的严重犯罪行为在很多地区都急剧增多,威胁甚大。对此我们无法保持沉默。如果道德教育不改善的话,仅仅学习数学、电子学和宇宙学等,我们今后将会哭得很惨。
两个月之前,我曾经到人民法庭的会议厅听了一次庭审。那次审问的是一个在舞池里打架闹事致人丧命的19岁男孩。当法官问及被告“从事何种职业”时,他的回答竟是“流氓无赖”,回答颇具挑衅意味,企图表现出某种勇敢。当然,结果是事与愿违的。这个特意大声的回答,让人感觉到的是痛苦。以往,我被罪犯们唤起的第一种感觉通常是同情——对死者的同情,然后是对杀人凶手的愤恨。可是,现在我确认,有错的人,首先应该是教育工作者们,因为从广义上来说教育者是指父亲、母亲、教师、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他们所犯的错就是当一个人还是孩童和少年时,当他还可能被塑造成有用之材时,教育者们错过了这个时机。
我曾上千次地指出,犯罪的根源应该追溯至童年和少年时代,其主根便是在情感和道德方面的厚脸皮性格,对于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毫无怜悯之心而抱着十分冷漠无情的态度。那些小孩——无情地摧毁花坛、折断树枝、折磨小猫小狗的小孩,就是潜在的罪犯。因为他们对于有生命的、美好的东西,持有冷漠无情的态度,这时就已经在其心灵中植下了罪恶之根。从对有生命的、美好的东西冷酷无情到对人毫无怜悯之心,其间只有一步之遥。
在人类心灵之中,与生俱来就有善良情感的家园。我把这个领域比喻为有着数千根弦的美妙乐器,其音域包括:从最灵敏的温柔和爱抚,直至为了人的尊严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素养。可是,如果人之心灵不接受教育,那些数千根弦没有被一根一根分别调音的话,这一乐器将永远只是沉睡的巨人。而在这美妙的乐器中,最灵敏的一根弦是人性。
亲爱的儿子,你将来也会有孩子,你会十分关心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人。那时,你就会知道,在创造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即培育一种能力——视人的生命为最珍贵的无价之宝的能力。一个人,他童年时能用心去感受他人的快乐与痛苦,他为了让父亲、母亲、姐妹、兄弟、爷爷、奶奶不受苦难,准备奉献自身的快乐和福利,那他是任何时候都不会举起手来加害他人的。把人的灵魂中那根最灵敏的弦——人性调好音,就意味着,首先要教会小孩子为他人创造快乐,并从中去体验那人类最高尚的乐趣。
我想,你和其他每个年轻人听听父辈这些教诲和指教并非多余。这是指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样预防最危险和最可怕的罪恶——丧失人性、麻木残忍,别让其产生和生根。
你看,就在不久前,在基洛夫格勒就出现了一个罪犯,这是一个18岁的青年,为了抢对方的手表,竟用刀刺入了一个16岁孩子的背部,杀了人。他哪来的这种残酷无情、毫无人性,甚至是兽性——这么随便地一下子挥刀刺入他人背部呢?我深入调查了凶手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原来,他从来没有为他人做过什么,从来没有为亲人的快乐而做过一件事——他没有种过一棵树,没有养过一株花,没有给母亲尝过自己亲手栽种和收获的苹果,他没有一次因为替母亲着想而放弃自己任性的想法。就这样,他长成了一个灵魂空虚的、毫无同情心的人,而在他眼中,人只是毫无价值的一具躯壳而已。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应对罪犯的行为负责的只是家庭、学校、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认为,一个人进入少年期后,即从12岁起,他就应该开始进行自我教育了;而在青年早期,也就是从16岁开始,自我教育应该成为每个人——每个中学生和大学生最重要的义务。
为证实这一设想,她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该基因编码区,被破坏掉编码区的ZmGRP1就无法正常表达。将经过此处理的植株和正常植株进行比对,发现有一千多个基因的可变剪接受到影响。ZmGRP1就如司令官指挥千军万马一般,调控着这些基因的可变剪接。
我想知道,你对自我教育持有什么观点?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写到这儿吧,亲爱的儿子。祝你健康强壮,精力充沛!
送上我的拥抱和亲吻。
你的父亲
之四
亲爱的儿子,你好!
你的一位同学,在读完《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后,问另一位同学:“该如何理解世界的可知性?”那时,我刚好在场。作为目击者,我当时听到的回答是那么的索然无味,这让我很是吃惊。我觉得,他们之中没有一人对哲学感兴趣。那一刻,我回想起30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们4个语言文学系的大一新生,也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所争论的正是关于世界可知性的问题。
对于这个最为有趣的问题,他们怎么会这么消极倦怠,抱无所谓的态度呢?为什么科学真理没能震撼心灵、没能激动人心呢?这使我十分不安。
我想给你讲一件事,这是真人真事,很有教育意义。
这是关于一位年轻女性命运的故事。10年前,她毕业于我们乌克兰的某所学院。故事的教育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如果学校的知识没有触及一个人的心灵,没有使他的内心震撼,同时他也没有把知识看得神圣、宝贵和亲切的话,那么,他精神空虚的程度,将会变得多么的严重!
她这样讲道:“我出生在一个诚实、勤劳、要求严格的家庭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在刚迈入青年的时期,我的精神世界,与俄罗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中的女主角卡捷琳娜很是相似——一样易于兴奋,但却是闭锁的、孤僻的那种兴奋,一样的敏感、细腻、多愁善感。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戏剧大作,简直是凝神屏息读完的。对于我来说,这是真正的新发现,我仿佛遇见了活生生的人,想要和她分享自己的想法和不安。卡捷琳娜在我心里激起一股旋风——思想和情感的旋风。要知道,我和她一样,也真诚地信仰着上帝,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于是,我心里对卡捷琳娜之死的悲剧产生了一丝疑惑: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性,为什么人要去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可怕的人们嘴上要以上帝的名义恶语相加?
“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假仁假义,不相信我拥有真诚的宗教情感。事实上,很多在大学里认识我的人都在谈论自然科学的系科与宗教,学习达尔文主义课程成绩优异与信仰上帝,这些难道可以结合在一起吗?所有人都认为,‘大学毕业’这个事实,已经包含了科学唯物主义教育,但有的人居然进了修道院。没错,很多人觉得我是伪善者,觉得在这个探索宇宙的时代,居然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信仰上帝,这是荒唐的。还有人说,也许我经历过不为人知的悲剧,或有一段失败的恋情……
“也许,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十分怪异的。但是,在中学学习达尔文主义的课堂上,在大学的自然科学系列课程的讲堂上,我对上帝的信仰恰恰相反地增强了。
“事实是,从中学到大学,我实际上变成了一台活着的机器——记忆并复述知识的机器。我从这节课到那节课,听了这堂讲座又听另一堂讲座,了解着科学真理——关于物质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进程,遥远星球世界上生命体存在的可能性,宇宙的诞生等科学真理。可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记住这些知识,把它们存储在记忆里,然后提取它们,来不停地答题以取得分数。于是,某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是贯穿全部精神生活的方式——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积累知识,是为了在脑海中储存,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却摆脱知识。而我,在回答完中学老师和大学教授的问题之后,就已经摆脱了这些知识,我感到很轻松,也准备好去学习更多全新的知识了。事实上,所有记住的东西,只是在意识的表面一滑而过,它们没有触动个性。老师和教授的话语里,丝毫没有专门针对我个人的东西。
“现在,我完全能够评判文学在我的精神生活里曾经扮演怎样的角色了——文学是中学里唯一关乎人学的学科。我认为,它压根儿不应该等同于其他学科。文学课堂上应该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于人的对话,而不是给出那样一堆知识,一堆只要记住,取得分数后一段时间就可以摆脱的知识。
“我现在坚信,如果老师在讲解《大雷雨》中的主角卡捷琳娜时真的注意到了我,如果他能明白我需要的是什么、我的心灵中发生了什么,如果他能以这样的思想鼓励我——人类最高尚的快乐,在于为地球上的快乐而奋斗,而这种奋斗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我想我的命运就可能是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也就不会无可挽回地浪费掉我的青春岁月了。我不是专家,不能说清应该怎样教授文学课,但我懂得这些课程是对人的认知、是对自身的认知。
“我渴望学习人学,而在中学里实际上是没有这门学科的。现在,我好奇地给我所认识的文学教授们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学的教学大纲里没有包含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为什么没有柯罗连科、迦尔洵、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库普林、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帕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等这些善于细微洞察灵魂的作家的作品呢?为什么不教,甚至都不作为课外读物推介那些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著作——可以这么说,那是揭示了人类不幸和痛苦的作品,要知道它们可是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世界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讲授《堂吉诃德》和《浮士德》呢?离开了《堂吉诃德》,怎么能想象人的教育?这是一部关于善的百科全书,是关于揭示人的热情、思索和冲动之深奥世界的百科全书啊!
“让我变成无神论者的原因恰恰是在修道院里对宗教书籍的阅读及思考。我竭力在‘上帝的’书籍中,寻求怎样使人变得高尚。而让我感到可怕的是,我越来越确信宗教在贬低人,把人贬低至如泥土、灰尘,直至什么也不是的地步。在那时,我真正开始思考中学和大学里所教授的一切。我在脑海中一页页地回忆起生物、物理、化学、历史、文学、辨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诸学科的内容。所有一切在我面前似乎都是新发现,仿佛我是第一次接触一切,它们也开始走进我的内心。
“我回想起了关于焦·布鲁诺(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因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宣传日心说而受火刑)的故事。数以千万计的罗马群众,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地、十分好奇地观看着该怎样绞死那个胆大妄为的人,此人居然胆敢放言‘世界决不是上帝箴言描述的那样’。这幅画面看上去是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触手可及,以致我不禁站了起来,走向林荫小道,登上山丘,从那里可看到河流蜿蜒、城市伸展的美景。我想要看见世界、观察生活、欣赏生命。我为焦·布鲁诺的功勋感到骄傲,他才是真正的上帝。如要祈祷,我得在他面前。于是,我笑了起来,原因是我比较了这么两种形象:一位是‘上帝的永恒受难者’,他忍受着统治并期盼来世得到好报;另一位则是自傲的斗士——焦·布鲁诺。此时,上帝在我面前显得多么可怜,又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开始可怜上帝,于是,我就笑了起来。
“我从内心感受到了人类的自豪感。在修道院里,我反思了中学里学到的所有东西,可惜的是,这迟来的独立反思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本该在16岁、18岁时就发现的东西,我却到了25岁才有所醒悟,为此我不得不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最主要的是,我在青年早期本该在文学作品里就发现人之伟大。
“告别宗教,对我来说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痛苦。于我,这一告别是快乐的,我如获第二次生命。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给我心爱的人写了信。我去修道院的事让他非常痛苦,他为此经受了许多苦难。收到我的信后,他飞奔而来。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现在我很幸福。”
这就是那个年轻女性的自白。
思考这个让人惊异的个体命运,我已经不是一天了。你也好好想想吧。你可以想想怎么做才能让科学真理使年轻人的心激动起来、感到震撼。
给我回信吧,来说说对这位年轻女性的奇特人生的想法,也思考一下为什么一部分年轻人对书籍、科学和共产主义思想态度冷漠?
祝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你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