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且真实
——马克·罗斯科的绘画艺术
2018-11-29张安明
张安明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一、原始性真实的本质追求
马克·罗斯科作为一位具有哲学思想的艺术家,绘画仅仅是作为他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思考的一种表现手段。真实是罗斯科一直追求的本质,他通过不断的舍弃事物的表象,追求最真实的存在方式,并且认为这种存在应该是厚重的。罗斯科意识到这种真实性是通过物象的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当这种精神爆发表达出来时,能够让观者与作品融为一体,那么这种真实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成功的完成了一件艺术品的社会存在功能,因为它真实的勾起观者的社会体验,这种情感不是通过任何具象的可见物象来表现。就像布拉菲尔德所说的:“通过任何其他方式的添加都是对必要真实性的否认,并且不足以创造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图画。”所以罗斯科成为一名为人所知的大色域绘画者是一种必然,但他并不像纽曼他们那样标榜成为一名前卫艺术者,相反,罗斯科从来不喜欢人们将他划入某一风格领域的艺术家,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保守者,他所探求的一直是关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存在的联系以及自然作为人生存的基本环境所带来的震撼性,而这些所有的思考都是基于人类这一真实存在的思考,人类是客体与主体统一的终极所在,故而回归于人的艺术思考和行为成为了罗斯科的主题。
对于罗斯科来说画面中的所有物象和色彩都是具有欺骗性的,尤其是给画作命名一些具有暗示意义的名称都会破坏作品给观者带来的真实性,因为这些会给观看者一种具有引导性的暗示,从而影响到观看者的感情和思想。只有纯净的东西才是真实打动人心的,最简单的给读者留下最大限度的思考空间才是真实的情感体现,艺术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于作品和观看人的干预,观看者面对作品时能够自觉的和画面融为一体,这就是罗斯科所追求的真实。对于马克·罗斯科来说艺术家的创作应该围绕着人类进行,罗斯科希望通过寻找到人类共同的相似行为,以期望达到属于人类的真实情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鸣。罗斯科认为形式和画面内容不是最重要的,他也无意于窥探你我的想法,但是罗斯科就是将这种情感真实的剥离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回归人类本体才是罗斯科探求的目标,而不在于题材,任何题材只要关乎人类的思考并引起观看者的触动就是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艺术,只有内涵的真实才是真正的具有真实性。就像乔治·莫兰迪说过“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莫兰迪就是因为通过瓶瓶罐罐抓住人们所追求的那点宁静隐秘的气息而引起共鸣。马克·罗斯科则是传达出一种希腊悲剧式的情感,对于罗斯科来说社会是现实的,悲剧情怀是真实的,悲剧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思考。“我对色彩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并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表达人的基本情绪,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许多人能在我的画前落泪的人,就会有和我作画时所具有的同样的宗教体验。如果你只是被画上的色彩关系感动的话,你就没有抓住我的艺术核心。”①悲剧性的类似于神话般的情绪是社会真实的永恒体现。
二、神秘的悲剧性

> 图1 马克·罗斯科《NO.16》布面油画1957年 207cm25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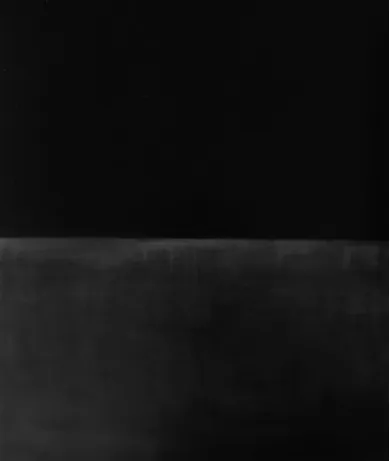
> 图2 马克·罗斯科《灰色上的黑色》1969年208cm175.6cm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
罗斯科的作品永远透漏着一股无法言语的悲剧情感,这与画家本身的生活经历有关。悲剧性是罗斯科对社会的思考,对于罗斯科个人来说,悲剧充满他的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幼年时期的贫穷、移民美国后的艰难生活和第一次婚姻的不幸,这些都造就了罗斯科的悲剧意识。社会的种种因素把罗斯科排挤在外,他在俄国与美国的底层生活经历让他产生了精神的追求,在精神世界中寻找他的安全感②。这时我们发现罗斯科对于他那段憎恨的犹太教时光还是深深影响着罗斯科一生,虽然是因为父亲的坚持被迫送到犹太教学习,但是我们可以从罗斯科一生的创作中发现“宗教观”一直贯穿着他的艺术道路。在罗斯科绘画后期抛弃了形象后,这种神秘性、宗教般的信仰以一种悲悯的情绪激荡着人心,当然我们需要明白这种“宗教”其实是罗斯科对于人类这一生命体的深度思考,他所信仰的是人类本身,而不是简单的对神的信仰,神只是一种共同信仰所创造出来的造化物,是个体寻找一种集体文化的归属感。对于罗斯科来说这种归属感就是永恒的悲剧性,这种伴随一生并深深体会到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在罗斯科这里变得神秘和纯粹,最后只剩下悲剧情感这一唯一的存在,被有意识的放大,放大到足以吞没观者。
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是容易吸引人们深究的目光,人类总是充满好奇心,而罗斯科深入的学习过心理学和哲学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尼采的悲剧意识与罗斯科不谋而合。罗斯科让这种悲剧在画面中以一种神圣的方式展示出来,形状不清晰雾化的边缘犹如圣像的光环般,隐藏着神秘的神性,给人一种崇高感。矩形的边缘模糊,内部的形状柔和地扩散,它们漂浮在地面上的方式,没有任何可能暗示体积、质量或重量的线条,似乎来自于绘画内部的亮度,强烈但不具体化的颜色,甚至是非常薄的油漆的薄薄的应用(或浸于画布中)——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创作作品,在这些的作品中,用罗斯科的话说,物质世界已经被“粉碎”③。(图1、图2)
罗斯科的作品总是被称为“宗教的”,因为悲剧被像神一样隐藏在画面中,却又可以轻易被感知到,如神灵一般无处不在。罗斯科为了强化这种神秘性,有意识的控制画幅尺寸,大尺幅的作品像教堂、神像一般高大的展现在观者面前,让其在人类共同的情感——悲剧下显得渺小,对灯光的严格把控更是让那种虚化的边缘更大限度展现出神性,崇高成了罗斯科展示这种情感的方式手段。在强光下作画,在微光下得以展示出最微妙的颜色震动,让观者和罗斯科体会一样的情感触动。从静态中立开始,通过日益黑暗和悲剧性的情绪,最后发展到越来越光明、振奋的状态,即有限与超验的对抗。罗斯科说过:“我认识到历史上创作大型绘画的功能可能是为了描绘一些宏伟豪华的事物。然而,我之所以画它们的原因——正是因为我想变得极为友好清切而又富有人性。画小幅绘画是把你置身于体验之外,把体验作为一种放大器的镜像或戴上缩小镜而加以考察。然而画较大的绘画时,你则置身其中。他不再是某种你所能发挥的事物了。”④悲剧性在罗斯科这里是形而上之上的崇高,可以说罗斯科被悲剧缠绕一生,但是却又对悲剧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的情感感到畏惧、害怕,用绘画的方式将这种情感虔诚的表现出来,不加以形象的描述。
三、弥漫式的悲剧造就“神话”
神是在人类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究其原因更多的是因为人类作为生物的不安全感,希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保护自己,这种力量有的来自于自然,有的来自于人类社会本身,当建立一种被广泛的信仰后,人类便有了依靠,这时人类自发地凝聚在一起,发挥最强大的力量。不论塑造什么样的神都是服务于人类的。悲剧作为真实的普遍存在犹如神一般无处不在,这种情绪是具有感染力的。悲剧性情感呈现出弥漫的氛围,从发散的的中心向四周扩散。真实的需求即是神——马克·罗斯科深谙神的本质。情绪化的表达被艺术手段以虔诚的方式表现出来,去除虚假的表象,展示的是社会的现实。对于罗斯科来说社会的本质是悲剧,磨难伴随着整部人类发展史,悲剧才是最真实的社会体现。
在罗斯科绘画后期,他虽然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对罗斯科本人来说悲剧在这时已经达到了最大化,与经纪人的纠纷以及仅有的好友相继英年早逝:如,高尔基自杀、54岁的汤姆林和34岁的克莱因死于心脏病、42岁的波洛克和大卫史密斯死于车祸等;而和妻子的紧张关系更是让罗斯科最后搬去工作室生活,这些都给罗斯科带来了心理上的极大痛苦,自杀成了罗斯科面对悲剧般的生活最好的选择。我们可以从西格拉姆大厦创作草图和罗斯科礼拜堂看到这时期罗斯科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想从绘画中得到情感的宣泄和慰藉。罗斯科画面方块边缘的虚化被背景色所强化,色块之间呈现浮动的不稳定感,被压缩后犹如光线一样的细窄反而向外展现出最大的张力,而大块的块状物又向四面八方扩展着,画面的力量都是扩张着的,这种张力是被压抑后的反弹。就像悲剧时刻伴随着我们,可是我们在面对这种情绪时更多的选择是抗争,但是过后我们急需一种来自同类的感同身受般的认可。所以罗斯科作品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经历性,似乎他的悲剧我们也经历过,罗斯科的作品将我们的先验性的意识直觉体验弥漫性的扩散在画面中。或者说罗斯科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性,他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情感。画面中的大色块是意识的凝聚物,这种凝聚物呈现着扩散的趋势,没有边际。悲剧性在罗斯科的创作过程中一直萦绕在脑海中并揉在了画面中,无血肉、无形象的方形块状在虚无化的边缘下显得更加庄严与神圣。当罗斯科将这种情感最大程度的放大在画布上,摆在教堂里,这时悲剧被神化了。罗斯科的艺术是无法复制的,即使是后来和他很像的肖恩·斯库利也无法达到罗斯科艺术的神性。
结语
罗斯科是20世纪后半叶艺术史上无法忽略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也是现代艺术的精神体现,从事的是关于人的艺术和思考。但是罗斯科区别于别的现代艺术家的原因更多的是将探寻人的本质精神上升到“神”的高度,这种神化不是宗教的,是本质的,本身就存在在那里的。■
注释:
① Mark Rothko.Mark Rothko:Writing on Art[M].Notes from aconversation with Sleden Rodman,1956;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119.
② 王晴.马克·罗斯科绘画主题及其表现形式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7.
③ James E. B. Breslin.The Trials of Mark Rothk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presentations, No. 16 (Autumn, 1986):1-41.
④ 马克·罗斯科.艺术何为:马克罗斯科的艺术随笔(1934—1969)[M].米格尔·洛佩兹·莱米罗,整理.艾雷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