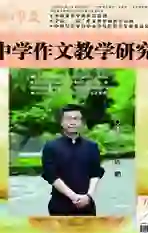故乡的味道
2018-11-28张春莲
张春莲
腊月,年近了,旅人归乡的日子到了。而身居异地远离故乡的我,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故乡的味 道了。
算来,此生在故乡度过的时光不足三分之一,其余时间辗转三地,最终落脚省城,但对故乡的印象随着年岁的增长,却越来越清晰。尤其年终岁尾,思乡之情自会缥缥缈缈,如丝如缕,绵延不绝,正如唐朝高适的七绝诗《除夜作》所描摹的: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是啊,霜鬓日日繁,思乡之情年年增,归去虽易,却不相宜了。
故乡的味道是随着季节转换的。
梯田背阴处积雪消融的时刻,山崖上金黄色的迎春花,老屋后淡粉色的杏花,农家院子里白色、紫色的丁香花也次第开放了。花香在村庄上空若有若无地飘荡,忽然就裹挟进了一股泥土气息,那气息是农人们熟悉的:有些腥,有些甜,温热而清新。农人们知道,土地解冻了,春耕马上要开始了。
端午节过后,麦子黄了,饱满的麦粒散发出缕缕鲜香。在阳光的炙烤下彎腰割麦子,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耐力。好在故乡的土地大多是山地,麦垄不长,挥汗如雨一口气割到地头,对多数农人来说,不算难事。不大舒服的是入伏天给玉米地松土。这时候的玉米已经长到一人高,加之天气闷热无风,穿着半袖半腿裤褂钻进玉米地里,如同进了热气腾腾的蒸笼。挥动锄头往玉米根部松土,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脚被长长的叶子上上下下地扎着、划着,瞬间布满了白色、红色的划痕,咸咸涩涩的汗水流进嘴里,淌遍全身,浸泡洗刷着划痕,说不出是疼还是痒,树上的知了却不知疲倦地“嘤嘤”地闹着,更增添了心绪的烦乱和不安——那滋味,实实在在不好忍受。
沁河水由黄变清,飘漾起清冽的味道,秋天到了。漫山遍野的庄稼成熟了,金黄的谷穗、玉米,雪白的棉花都开始收割。山坳里的柿子也成熟了,一盏盏橙黄色的灯笼般的果实掩映在红红的叶子中间,树梢的几只已经熟透,摘一个,揭开绿绿的顶盖,一口气把汁液吸进肚里,浑身都充满了蜜糖般的甜意。地棱边斜刺里长着一丛丛的酸枣树,紫红的酸枣密密麻麻地压满枝头。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避开尖利的小刺,摘下一粒粒紫红的酸枣放进嘴里,甜、酸,令人不由得口水四溢。
由酸枣联想到酸菜,这也是故乡人非常喜欢、冬春两季离不开的一种菜。萝卜、蔓菁连带着叶子都是制作酸菜的原料。深秋时节,家家户户先挑了菜叶到生产队的大锅里煮熟,再到沁河边,用那清澈的长流水淘洗干净,然后打成把,一层层码成垛,上面用重石压。等菜水淋干后,与萝卜蔓菁一起切细丝,搅拌均匀后装缸封存。经过一个多月,酸菜发酵,去封开缸,酸香蒸腾。此时,冬天来了。早晨的糊饭或煮疙瘩就着炒酸菜,那是绝配。炒酸菜必须用蒜蓉烹油,那味道用陕西话来说,叫“美滴太”!如果有豆腐与酸菜合炒,青青白白,色泽鲜亮;其味道,更妙!
故乡的冬天是寂静的,土地坚硬,冰雪覆盖,偶有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鸣叫,或飞落到院子里蹦蹦跳跳地觅食。劳作了一年的农人,除非有修水渠、垒河坝之类的活动,一般都会待在家里。男人们修理拾掇使用了一年的农具,女人们运用巧手剪着各式各样象征喜庆、富裕、祥和的窗花,或“呲呲啦啦”地纳鞋底,缝衣服。劳碌一年,再贫穷,也要让屋舍干干净净,喜气充盈,也要让老老少少的家人过年穿上新衣服。
腊月里,冷清的街头热闹了起来,各种味道也丰富了起来。初一爆米花的焦香味,初五软米饭的糯甜味,腊八和子饭里掺进了小猫、小狗、小兔子等杂七杂八面制品的葱油味……小年之后,各种味道更加密集:麻糖味,枣糕味,油炸馓子味,煮煎炖炒各种肉味……最最集中,也是达到高潮的味道,当属除夕到来鞭炮声此起彼伏散发的火药味。这味道和着年夜饭的菜香和饺子香,充斥着故乡的夜空,让人微醺,令人陶醉。
远去了,记忆中的故乡;远去了,记忆中故乡的味道。
(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0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