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下的细腻讲述
——评丰收《西长城 —新疆兵团一甲子》
2018-11-28沈苇
□沈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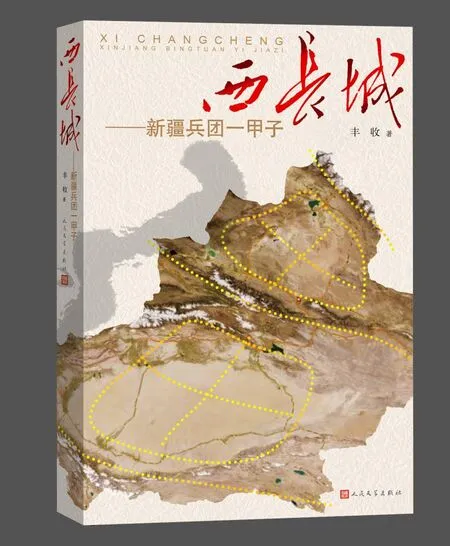
新疆作家中,丰收以纪实文学创作见长,成就卓著。作为新疆屯垦戍边第二代,他有一种强烈的兵团情结和边地意识,三十余年来持续书写兵团,将这一“群落”独有的生存风貌和人文景观,真实而丰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来自兵团的内部报告》《西上天山的女人》《镇边将军张仲瀚》等,都是他写兵团的代表作品,产生过广泛影响。诚如《新疆当代文学史》评价的那样:“丰收兵团生活的题材之所以受到世人瞩目,不仅因为他耕耘了一块往昔人们不曾深翻过的土地,而且由于他目光宏阔、胸襟博大、笔力纵横,将兵团事业放在与历史、自然、社会、文化的多向关系中去考察,从而凸显出兵团事业的伟大与特殊、悲壮与崇高、高亢与激越。”
现在,丰收又奉献了一部写兵团的长篇纪实力作《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六卷,二十八章,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展读这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非虚构作品”,不时被一种“挥剑决浮云、铸剑安天下”的兵团精神所激励,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他们鲜活的故事所感动,更被作者基于历史意识和现实责任而焕发的人文精神所感染。毫无疑问,《西长城》是近年来新疆乃至国内纪实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纪实文学,以前被叫做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它的黄金时代,与改革开放和社会启蒙同步,随着这一文体的迅速蜕化、变异和式微,人们又从西方引进“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来重命名它、变革它。但不管称谓如何变化,“纪实”仍是这一文体的本质,代表了与“主观虚构”不同的写作方式,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大概均可纳入纪实文学的范畴。丰收是从八十年代一路写过来的,对这一文体了然于心,写起来也是轻车熟路。他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写作,仍坚守了“文学”的本真理想,拒绝被平庸的“报告”拉下水去。他说:“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理性认识、把握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以精神创造为目标的人,是应该写出爱,写出人类的尊严,写出人类的同情心,写出为社会文明作出的牺牲,并致力于提升这一切,这就是文学的良知。”(随笔《一方水土一方生灵》)这种意识,决定了丰收纪实文学写作的高度、责任感和自觉精神。这一追求,延续到《西长城》中,并有更深沉、宏阔、有力的表现。
与此同时,丰收有一种很强的文体意识。他一如既往在探索纪实文学表达“现实”的可能性,变换手法,强化表现力,拓展包容度,使之呈现“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丰富与细微。《西长城》以“屯垦天山下”、“酒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西长城”、“年轻的城”六卷为基本架构,以二十八个章节为构件,尔后注入文字的丰饶与澎湃。这使全书既有骨架,又有血肉和灵魂,写得有章有法、收放自如。在一种被限定的自由中,恰恰获得了表达的自如。作者有时是言辞滔滔的政论家,有时是引经据典的史学家,有时是冷峻从容的叙述者,有时是善感抒情的诗人。丰收将这些身份融而为一,融为一个运筹帷幄的、似乎掌握了百般武艺的纪实文学家。《西长城》的写作,涵盖了兵团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的、全景式的。而支撑这一“宏观大厦”的,是分布在二十八个章节中的具体而微:事件、场景、记忆、人物、命运等等。有人将它称之为是一种“散点透视”、“撒豆成兵”的写作。在有规有矩的纪实文学写作范式中,作者引用并糅杂了史志、书信、日记、电文、诗歌、统计表、口述实录、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镶嵌、插入、叠加、切换,写作手法趋向综合,全书呈现出一种时光交错、色彩斑斓的“跨文体”效果。
“兵团六十年”这样的大题材,难写,弄不好就会凌空蹈虚、大而无当,变成了“总结报告”、“新闻通讯”。《西长城》的成功,在于丰收为“报告”的血肉注入了“文学”的灵魂,处处可见人性视角和人文关怀,自始至终都保有一种激情和热爱去书写他人。是“文学性”赋予了全书一种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更具体一点来讲,《西长城》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以小见大、以小写大,从微观、具体、细处入手,用“小”去破除“大而无当”的魔咒;二是贴近人和人的内心去写,写出了人的身世、故事和传奇,更写出了人在荒原的命运:当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时,却可以投身其中。如此,“兵团精神”不只是习见的口号和标语,历史不再是干巴巴史料的堆砌,人物也不仅仅是一些有着“先进事迹”光环的人物,他们已被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
《西长城》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上百个,他们只是兵团二百五十万人众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资料收集、实地调查、采访等方面,足见作者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丰收似乎抱着一个信念:尽量多地写出一个个快被埋没的人物,尽量客观、具体、真实,才能为今人和后人留下记忆。在他那里,写作几乎变成了一次紧迫的“抢救性”工作,写下的文字必须无愧于自己的文学,无愧于“兵团一甲子”,更无愧于众多的“他者”。纪实文学的创作使命是“体验他人”、“书写他人”,在这一点上,丰收是苦心孤诣、全力以赴的。然而,“兵团六十年”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一个话题,即使四十万言的长篇纪实,也只能容纳兵团人有限的故事,更多的“兵团第一代”已在时间长河湮没,无名无姓,甚至未能有一块最简陋的墓碑,如风中尘埃,似瀚海沙砾。这就是纪实文学必然遭遇的“遗憾”和“不可能”,也是每一个写者注定抱憾的“未竟”与“未尽”。
书中写到的人物,上至将军下至战士、农工、盲流。作者既写兵团创始人王震、陶峙岳、张仲瀚这样的“大人物”,写他们的“桃园三结义”,写他们的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以及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气度与魄力,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去书写兵团“小人物”,以及他们作为西部拓荒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通过丰收的书写,“小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的故事令人难以忘怀。我们记住了一天开荒三亩三的坎土曼大王方喜成,记住了用一公斤粮票找到老婆的理发师小麻子,记住了直到退休还是大田工人的陈淑惠,记住了三十年只回过一次老家、临终时因愧疚于母亲而哭泣的棉花专家陈顺礼,记住了在阿勒泰和海南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的育种夫妇韩新城和尚君华,记住了在博尔塔拉草原冬窝子建立第一所小学的顾薇君,记住了“一个人的哨所”里的马军武,记住了中苏冷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中国女性孙龙珍,记住了为石河子建城兢兢业业的湖南泥水工周益贵和他的八个弟子……这样的“小人物”,在书中不胜枚举。丰收的书写,有一种平等目光,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重述历史、复活细节的出色能力。他深入挖掘被时间和历史遮蔽了的“小人物”们的故事,为他们树碑、立传、去蔽,从而使《西长城》这部个人化的“兵团史”,具有包含众多“小人物”的“个人史”的深沉意味。
《西长城》贴近大地和人去写,于宏大叙事下细腻讲述,对“他者”的体验总是感同身受,最终写出了荒原和它的拓荒者群像。丰收对“荒原”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知,他的“兵团情结”脱胎于“荒原情结”,他在书中写道:“我对世界的认识,始于荒原——地窝子巴掌大的那扇小窗,走不到边的棉花地,月光明亮的雪野,冬天的爬犁,戈壁滩的梭梭……这是新疆大地给我最早的物象。而这一切都和母亲紧紧相连——雪地里母亲拉沙运肥,棉田里母亲春种秋收,母亲领着我们去戈壁打梭梭柴,去沙枣树林打黄豆粒一样大小的沙枣蛋蛋充饥……这母性的荒原啊!当我的视野里有了更多母亲,当我面对时代背景下她们的命运,思考人生的沉重,人性的依存时,我也思考着社会文明因牺牲而有的推进。”(卷三《家国女人》之《明月出天山》)毫无疑问,丰收是敏锐地发觉了这种“牺牲”的,不是一个母亲的“牺牲”,而是众多母亲们的“牺牲”。“书写他人”,则意味着视野里要有更多的母亲。“母性的荒原”,既是“牺牲”的同义词,又是“牺牲”的见证人。兵团伟业的创始和推进,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体生命的“牺牲”之上的,这是个体融入群体的自觉,也是群体消弭个体的必然;是战争年代里延续沿袭下来的人民战争意识,一直沿袭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作家丰收
丰收的“荒原叙事”并不回避早期拓荒者异常艰辛的一面,他写劳累、贫困、饥饿、死亡的片断,是书中最为打动我的地方,堪称悲怆和惨烈。这是现实超越想象、纪实胜于虚构后的“情景再现”,能真切地听到、看到和感受到人在荒原的挣扎与求生、呜咽与呼告。摘录其中的两个片断以飨读者:
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张仕杰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张仕杰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消解,张仕杰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张仕杰哭着哭着,又睡着了。还有一次,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泥淖里去了,掉进去时,她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在泥里又睡着了……
——卷二《酒与水》之《西瓜熟了》
我们没有家。鸡棚、牛舍、羊圈、林带、荒野,都曾是我们的栖身之地!我们在那块荒原上熬过了二十七个年头,搬了无数次家。比吉卜赛人的迁徙还要频繁!除了几本书,我们一无所有!连老带小六口人,每个月仅四十八元钱的糊口费!
贫穷像钳子卡住我们的咽喉。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日子里,老家的亲人受不了饥饿的煎熬。先后有五个人相继投奔我们。真为难,真狼狈,真无计可施啊!首先要吃呀,吃什么?要住呀,住哪里?添补衣服要花钱,钱又从何处来?维铭的父亲从老家来时,为他相离十八年、远去革命的儿子只带来了十多个洋芋,我们还舍不得吃!不发工资的年月还持续了若干年。为了最最必需的费用,维铭只有出卖藏书,包括《资本论》。维铭拿到卖书的钱后,虽然自己饥肠辘辘,却又不敢去饭馆吃一顿;头发长得像囚犯,却没有去理发馆。只买了一包火柴,一瓶点灯的油(因为他必须读书、写日记),一斤盐巴。
——卷三《家国女人》之《明月出天山》
前一段描写的是湖南进疆女兵张仕杰的“瞌睡”,她还亲见了四个起义士兵因不堪人变成劳动机器而自杀的事件。后一段引用了“胡风分子”贺维铭的妻子的口述实录,夫妻俩和全家在荒原上像吉卜赛人一样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这些具体而微、细腻感人的叙述,抓住了历史的真实一面,还原真相,是为了不忘却过去,提醒我们“屯垦戍边”的艰辛和兵团事业的来之不易。王震曾说过:“我们进行的千秋大业,要付出比战争更大的坚韧。”
“以小见大、以小写大”,是《西长城》突出的艺术特点之一,我称之为“宏大叙事下的细腻讲述”,足见丰收对兵团题材翻耕之深、之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大时代脉搏的把握、对大场景描述的把控有所欠缺和不足。相反,对大事件、大场景的描述,丰收也是得心应手的。譬如新疆和平起义、数千人拉爬犁运石头修和平渠、百万盲流走西口讨活命、湘女出塞、1962年边民外逃事件、中印战争、石河子建城、喀喇昆仑山公路的修筑等,气势恢弘,笔力雄健,极具震撼力,具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诗品格”。作者在《西长城》中的视角既是全景式的,同时又降低自己的“俯瞰”,在“具体”之中不断切换,从而实现了宏阔与细微、“大”与“小”的有机融合。
“往哪里去?”
“往西!”
十七岁的青年樊炳谋什么也没想,就拼命挤着往汽车上爬,又饿又渴的旅途劳顿一扫而光,也不问是到哪个地方,只要向西就上车。
他们中十有八九最终都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叫“兵团”的大单位,它的农场遍布天山南北。
那年月,尾亚、鄯善、吐鲁番的大河沿——陇海线西段沿途,兵团都设有接待站,收容接纳从河南、安徽、四川、甘肃……几乎全国每一个省区走西口的流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两个地理名词为中国人所熟知,之后也为关注中国人口迁徙的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所瞩目,一个是“星星峡”,一个是“尾亚”。
走西口讨活命的“盲流”大都是从这里进入地域辽阔的新疆的。
……
那时候,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能招来一个水灵灵的河南姑娘、四川妹子做媳妇。
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到乌鲁木。
——卷一《屯垦天山下》之《走西口》
对于受尽饥饿折磨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兵团就是远方的“避难所”。兵团掌门人张仲瀚将军曾说“兵团是座大熔炉”。组成这一独有“群落”和“部族”的有“铸剑为犁”的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十万起义部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百万盲流、内地遣犯、进疆女兵、上海知青、右派分子等,他们在这座大熔炉历经锤炼,获得新生。这是一群在荒原上扎根、在异乡建设故乡的人,新疆也以它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盲流总得有个家,而兵团就是他们最好的“塞外之家”、“移民之家”。针对“盲流”一词,丰收问:“盲流,真是盲(目)流(窜)吗?”他为百万盲流执言,其实是为历史钩沉、为盲流正名。他说:“与政府组织的移民比,‘盲流’的经历更艰难。正因为特殊的遭遇和经历,‘盲流’这支移民群落萌生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力,他们虽然不可能像欧洲移民那样,在远离故乡的异地,建立起一种他们向往并为之苦苦追寻的新生活,但他们为生存下去而有的充满活力的创造,历史地推动着西部文明的进程。”
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说,时间是不可逆转的,而记忆使生命得以重访过去。只有通过记忆,时间才获得了“物质性的重量”。《西长城》对“兵团记忆”的书写,具有这种“物质性的重量”,与此同时,书写的重量和厚度、宏阔与细微也在强化这种珍贵的“群落记忆”。《西长城》宏大叙事下的细腻讲述,催醒荒原上的“记忆之花”,朝向今天和未来开放。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这是人们从汉唐以来西域屯垦史中得出的真知灼见。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肩负起“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的新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新一轮凤凰涅槃。从丰收个人来说,通过《西长城》的写作,我者已深深融入他者,其早年的“荒原情结”已转化为今天的“兵团精神”:“正因为魂有所托的人生信仰,正因为心有所系的人生追求,这支部队才有坚如磐石的凝聚力,激情无限的创造力。”(卷六《年轻的城》之《共和国版图上新的星座》)《西长城》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中国屯垦史研究乃至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察提供了一个厚重而可靠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