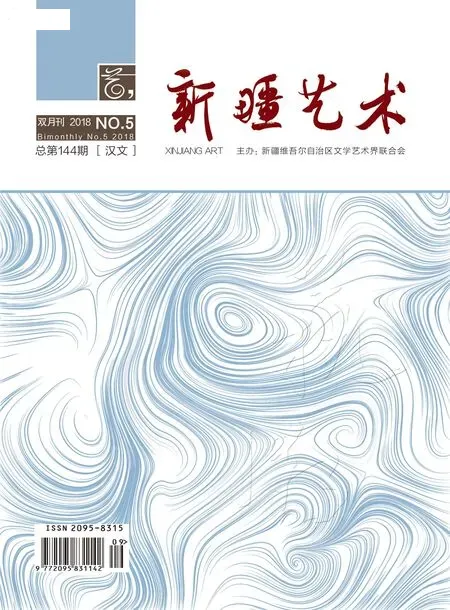李娟散文的“美”和“真”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有感
2018-11-28黄于彤
□ 黄于彤

读罢李娟的散文,感触最深的就是它的“美”和“真”。在我看来这是李娟散文最大的特质和触及人心之处。
关于李娟散文的“美”,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一、想象美
李娟对于现实的情景具有独特广阔的文学想象:她想象兔子能自由穿梭葵花地的光明与黑暗,白天它和人们相随,夜晚便进入人类无法触及的黑暗之中;想象手机面对着星空时也渴望挽留美景,也会跑到荒野深处寻找美丽的石头,会为美而惊讶、而停留;想象戈壁玉“壮阔崎岖”的一生和被人类残忍剥离土地的命运……她的想象有着她强烈的个人色彩印记,是基于她对美的不懈追寻、对宇宙自然和人生的独特思考以及她的个人经历。这想象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思想根基,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想,因此是独特、极具私秘性的,具有深刻的美感。此外,她的想象不拘泥于此时此地,而是经常跳出固定的时间空间场,借着现实触及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借着想象到达肉体所不能到达之境,充满着时间空间错位的大格局美。《繁盛》中写到她在大地上想象一百多年前农人发现沙漠深处的谷地,决定定居于此的场景,以及鱼群逐渐消失的漫长过程,这些充满沧桑巨变的想象给人一种漫游时间深处的感慨。《大地》中写道她在广阔大地中漫步,看到逝去的外婆在大地上远远蹒跚而来,看到很久以前也许在同样的地方给她打电话,问她何时归家的妈妈。站在大地尽头,所有逝去的情景涌上脑海,又幻化成可望而不可即的影像,令人不胜唏嘘。而《大地》中写到她在荒野中慢慢地走,感受到“大地渐渐轻盈无比,载着我动荡上升”,而“天空却蓝得凝固了,沉重地逼临下来”;以及《洗澡》一文中将在地底深处洗澡想象成“在星球大战时双方暂停交火的空隙间洗澡”;《兔子》中将兔子跟随妈妈在葵花地中行走与“月球紧随地球在茫茫银河系间流浪”并写,这些想象都给人空间错置的一种恍惚迷离的美感。

二、画面美
李娟的文字不乏对大场面的描写,有对广阔的葵花地、沙枣林的描写,也有对头脑中浩瀚无际的想象之景的重现。她爱用“世界上”“宇宙中”“所有”“最后一个”“唯一”这样极端夸张的词进行描写,在《浇地》中她这样形容大水灌溉后的葵花地“世上只剩下植物,植物只剩下路。所有路畅通无阻,所有门大打而开”;在《永红公社》中,她坐在驶离永红公社的大巴车上,“跟在全世界的最后面”;在《打电话》中,她与母亲在大漠风暴中打电话,她说“像是冲着宇宙深处光年之外的事物孤独地回答”,写道母亲“顶着大风,站在大地腹心,站在旷野中唯一的高处,方圆百里唯一微微隆起的一点,唯一能接收到手机信号的小土堆上,继续嘶声大吼”……
她给读者营造了壮阔无际的情景,这是无限的大,读者仿佛置身无边的寂静和空虚之中,感到一种辽阔旷远的壮丽的美。跟随作者的思路,意境变得极广,视野却变得极狭,仿佛世界上只看得到植物和路,只看得到荒野和大巴车,只看到大地和小小的母亲,这是无限的大之中无限的小,小大对比形成的视觉冲击带来强烈的画面美。同时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定点,使读者在突如其来的广阔中不致陷入茫然,读者可以依托着这无限的小去感受大地、世界、宇宙之大。
三、文字美
李娟的文字,可以用质朴、凝练、清新等词来形容,她的文字之美不止一面,然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灵活贴切。在《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中她用“被各种包劫持”形容母亲身上行李之多;在《闯祸精》中写被丑丑欺负的兔子变得“呆若木兔”;在《孤独》中她说站在空无一人的戈壁滩上,像站在全世界的制高点,“像垫着整颗星球探身宇宙”;在《鸡》中形容散养在荒野的鸡由良家妇女“改头换面而成为泼妇,继而为土匪”……这些灵活贴切可以用比喻手法、拟人手法等来解释,在我看来,它也是李娟对文字的敏感和灵活运用。她将“呆若木鸡”信手拈来,并拆解它,将之用于兔子身上;故意曲解劫持、改头换面的意思,使它们变得可爱形象;形容至高无上的地位,她用“垫”这个字;用“良家妇女、泼妇、土匪”形容鸡……她不拘于文字的本来含义和适用对象,而是用自己的思考将之加以吸收并改造,使之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想象,她的这种改造使我眼前一亮,感到她文字的新奇和变换无穷,感到文字的玄妙和包罗万象。
四、质朴美
读李娟的文字,能从中发现两副面孔:一是善于发现生活乐趣与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小孩子;一是能从生活琐事中掘出深意的哲人。她的文字往往不加过多修饰,质朴而自然,同时不避俗语,也乐意将生活中的乐趣与读者分享,读她的文章,仿佛在听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丑丑和赛虎》和《各种名字》等文章中这种趣味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她的文字又不止有趣,更有趣味后的深思,这种深思是在农人陷于丰收的喜悦时看到土地的伤痕累累;在经过卖“十元三个”的戈壁玉的摊子时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被人类毫不吝惜地挥霍;在水电站站长讲述哈萨克族的历史时、在外婆给她讲“狗带稻种”等流传千百年的故事时感慨人类口耳相传的至今不愿遗忘的文化遗产与牵系每一个人的无形的精神纽带……这种深刻的思考,用李娟想象生动、质朴凝练、充满哲理思辨色彩的语言加以表达,便形成了一种余音绕梁、令读者回想无穷的美感。她以孩童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这世界,然后用哲人的心将这些记忆和想象反复咀嚼,获得进一步的升华。所以她的文章既有孩童的天真烂漫,又有智者的深思熟虑,既童趣质朴又精辟深刻。

李娟散文的另一个核心特质就是其情感之真。对于大自然、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家人甚至人类,李娟在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真挚而复杂的情感。
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李娟选择了首先热烈地赞美自然,她赞美大地,惊讶于北方贫瘠的土地中可以诞生出“中亚腹心的金枝玉叶,荒野中的荷尔蒙之树,干涸大地上的催情之花”——沙枣、生长出充满激情的荒野中的黄金——向日葵。赞美造物主使这荒野贫地滋生出无尽生机,为生长于此的动物和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们提供无私的服务。也赞美流浪于人间之外的荒野深处的壮丽风景,它给被遗弃于此的人带来暂时的心安、给终日劳碌于土地的人们带来辛劳中的安慰。她还感叹自然的伟大力量,自然可以轻易发威,人类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作者在赞美中还带了点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作为种地者“靠天吃饭”的不安全感与焦虑。在《我的无知和无能》中,李娟写道“所有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行为都带有赌博性质”,以种地为生的人,喜怒哀乐皆系于大自然的瞬息万变,无论科技如何先进,仍然难免与大自然的博弈。《灾年》中写到由于冬天降雪量少,开春旱情严重,随之而来的抢水纠纷、病虫害、野生动物偷吃农作物等的一系列问题给农人带来的焦虑甚至绝望……作为大地上的劳动者,她对于自然的变化感到无能为力,也和其他荒野中的劳动者一样游离于自然与人间之外,时常透露出对作为人的命运的无所适从,在《大地》中她写道“四脚蛇是与大地最相似的动物”,它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也愿意张开怀抱包容它。可是“我是与大地完全相反的事物”,无论如何费尽心思,都无法相容于大地。并且还说“如果作物的生长是地底深处黑暗里唯一的光芒,那么,那个人经过的大地,随着他脚步的到来,一路熄灯。”作者暗自羡慕大地与万物的融洽和谐,也道出了人在天地间的孤独无依。
作者对于天地间的生物的喜爱、羡慕的感情在文章中也不难看出。她爱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写兔子时说它“东张西望,拒绝沟通”、“若无其事抖抖耳朵”;写鸡时用“神气的国王”“便衣警卫”“下了战场的残兵败将”来形容;写鸭时借鸭子在过冬后“太了解自己的体重、密度和脂肪比例的变化”而拒绝下水来彰显鸭子们的机智......作者运用的拟人手法不仅是一种修饰文辞的工具,更是其主观情感不自禁的流露。李娟描写动物植物时的拟人是一以贯之的,仿佛它们就是人,而没有丝毫“比”或“拟”的痕迹。动植物与人类是同等阶级,不分高低贵贱的思想的体现,是她内心情感的外化。此外,作者在《大地》中对于大地与四脚蛇的和谐融洽、种子与大地的亲密关系的描写;在《兔子》中感叹兔子能自由穿梭于葵花地的光明与黑暗,而“沮丧于自己庞大的身躯和沉重的心事”……从这些片段中也能看出作者对于大地与动植物的亲密关系的羡慕。
作者对家人甚至人类的感情则更加复杂和矛盾。在“爱”的主题下,作者通过几个与外婆生活的片段勾勒出外婆的局部形象:她是年轻时硬气的、不容他人欺负的“秦妹仔”;她早早为死亡做好准备“心满意足,准备等死”,但又会藏起存折,不容他人占便宜;她有时会屈就于草草死亡,但更多时候始终带着寿衣准备隆重地接受死亡;她欣赏美,如同常人一样想独占美,却毫不遮掩地说出“老子今天晚上要来偷”;她向往出租屋外蓝天下的世界,却害怕孤独、害怕死于陌生的异乡,所以执着于坐火车回四川……李娟笔下的外婆是可爱的,也因为沾了时刻处于死亡边缘的恐惧,她害怕外婆死去所以“依仗她的爱意,抓牢她仅剩的清明,拼命摇晃她,挽留她”。她说自己是骗子,对外婆的爱中还有无法给她所承诺的愧疚。她对外婆的爱是深沉而矛盾的,希望外婆早日摆脱孤独与对死亡的恐惧,却又百般挽留,因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与愧疚之中。作为与外婆有着深刻联系的母亲,李娟对母亲的感情则是贯穿于全书的更为委婉而简单的,她赞美母亲赤身行走于大地的豪情直率;对母亲以做饭难吃为荣拒绝做饭的我行我素、坚持经营葵花地的独立坚强暗自赞叹;为母亲将完美的树干、心爱的花慷慨地交给我之后的默默牵挂所透露出的深重的无以回报的爱……对于人类,李娟惊讶于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他们在荒漠中建起水电站,将电“禁闭在巨大的仪器之中”“摁捺于细细的管线之中”;为了求得生存,硬是在贫瘠死寂的荒野垦出一片耕地。也为人类妄图控制大自然的野心而恐惧、为人类破坏大自然而不感到愧疚而心痛。
李娟散文中的情感之真,是她文章中独特和深刻的美。她饱含个人记忆和情感的文字是不着雕饰的美,是她散文之美的核心。情感之真使得它的“美”有了凝于一体的核心,而不是飘散于种种琐碎叙事中忽闪忽逝的明星,也使得她的散文想象夸张而不失实、“形散而神不散”。情感之真与种种“美”的建构相辅相成,使得她的文章实而不俗、美而不虚。
(本文图片由刘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