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在中日书法交流中的作用及影响
2018-11-28尹晓宁
文 尹晓宁
中日之间一衣带水,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长期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杭州作为中国东南文化重镇,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在文化东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书法艺术便是其中一个代表。
在中日书法交流史上,僧侣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平安时期的空海、最澄两位法师来华求法,并将中国的大量法帖带回日本,掀起日本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杭州人褚遂良、孙过庭的书法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平安时期杭州书法已开始在日本崭露头角。
来源于中国草书的假名书法先天不足,独特而单调,只能借助色纸增加视觉感受,女性意味格外浓厚。当历史进入镰仓时期后,这种书风与峻烈的武士精神格格不入。随着南宋时期中日交流的重启,尤其是荣西和他的弟子将中国浩荡禅风传入日本之后,禅宗思想及禅家墨迹迅速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热烈追捧。两宋书家尤其是僧人书法,给难以自振的日本书法带来了迅烈刚猛的气息。而此时,作为都城和佛教中心的临安(杭州)自然成为日本的法乳来源之地。
南宋,杭州禅僧书法东传
日僧的再次大批来华,正是南宋时期。此时,杭州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大多数日本僧人参访的目的地。南宋的书法,在宋高宗的表彰和引领下继承了北宋风气,黄庭坚、苏东坡、米芾的自由尚意书风是南宋书法的主流。这种书风在日本更被认为闪耀着禅宗思想的光芒。一些被日本尊为“墨迹”的高僧墨宝,成了书法的典范,影响深远,至今被奉为日本国宝。
现存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中,最古老的一件是云门宗诗僧参寥子道潜(?一1106)的尺牍《与淑通教授道友》。道潜是杭州智果寺僧人,与苏东坡关系莫逆,其书法有明显的苏体风格。根据江静《日藏宋元禅林赠与日僧墨迹考》,现存的556件墨迹中,可以明确是宋元禅僧赠与日僧的墨迹有103件。王勇、郭万平所著《南宋临安对外交流》一书统计了当时活跃于临安五山禅林的高僧大德遗存于日本的墨迹:一共15位高僧76件作品,其中国宝级文物11件,重要文化遗产39件,无准师范禅师个人墨迹达30件。这15位高僧全部都曾住持过五山之首的径山寺。我们由此也可以说杭州是日本墨迹之源,杭州径山寺是日本墨迹的祖庭,无准师范禅师是禅僧墨迹中最重要的人物。
这些高僧墨迹成为宋代书风影响日本的最主要渠道。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禅僧的书法一般不会受到重视,受到重视的是禅僧的心,而在日本,“心即是书”,书法已超越艺术本身。因此,先是书法借禅而东传,然后是禅借书法在日本扩展。南宋传入日本的禅僧墨迹中以无准师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其大字榜书更是在日本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大字由他的弟子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辩圆带回日本。在无准师范巨大光环的照耀下,配合着临济宗峻烈禅风,这些榜书墨迹产生了直指人心的力量,受到武士阶层的顶礼膜拜。
述及大字榜书的东传,除了无准禅师以外,还不能绕开另外一位杭州的书法家张即之。张即之是唐代诗人张籍八世孙,叔父是著名词人张孝祥。《宋史》称张即之“以能书闻天下”,“大字古雅遒劲,细书尤俊健不凡”,有人将他列为“南宋四家”(另三人是陆游、范成大、朱熹)之首。圆尔辩圆在杭州期间曾经学书于张即之。日本东福寺藏的“方丈”等多件大字榜书即是由圆尔辩圆带回日本,被视为日本国宝,作者即张即之。日本室町时期著名的一休宗纯便继承了张即之的大字书法体势,而猛辣之气甚过之。日本的大字书法不同于我国以匾额为主,而是主要以挂轴的形式悬挂于室内,更夸张、更抽象、更追求造型,使禅宗法语、话头更加醒目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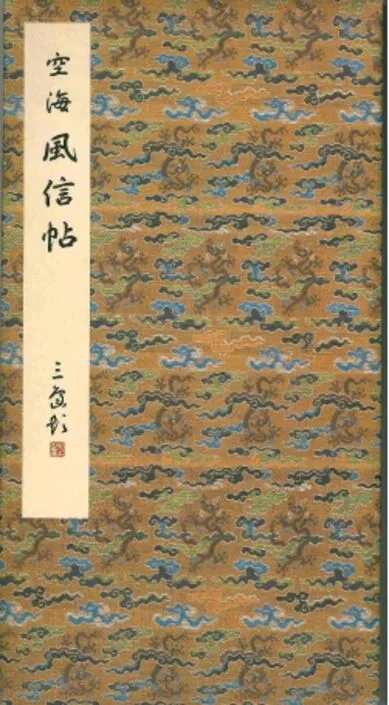
南宋禅僧的书法东传,意义不仅限于日本书法,更是保存了一直被我国忽视的禅僧们的书法。正是有了这种异地保存,才填补了我国书法史上的空缺,连同一并保存下来一批的画像,昔日禅僧的精神风采更直观地展现于今人面前。
元明时期的书法东传
入元以来,日僧来华求法的热情未减。有“江南古佛”之称的杭州临济宗禅僧中峰明本及后来长居日本的一山一宁等都吸引了不少求法僧。中峰明本的柳叶体书法深为日本禅林所珍视。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是中峰明本的俗家弟子,与明本关系密切。日僧寂室元光曾求法于中峰明本,其书法师颜真卿,亦有源于赵孟頫的笔法。一山一宁的弟子雪村友梅是日本五山文学的开山祖师,他曾在赵孟頫面前以唐李邕的笔法作书,获得赵孟頫的赞赏。
赵孟頫书法通过来杭日僧东传一直延续到明初,即日本南北朝时期。1368年,深受梦窗疏石器重的临济宗禅师绝海中津来杭求法,师从杭州中天竺高僧季潭宗泐,并向清远怀渭学习书法,他的字有明显的赵孟頫风格,京都相国寺所藏《十牛之颂》就是他写给足利义满将军参悟之用,为禅门所珍重。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实施海禁政策 ,甚至下令“片板不得下海”,中日间的正常交往受到很大影响,直至明朝后期隆庆开禁。晚明的日本已进入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期,明亡之际,一批不愿降清的文人和僧侣东渡日本,再次给日本书坛带来了明朝的书风。
主角依旧是禅僧,是一群以隐元为首来自福建福清黄檗山的临济宗僧人。他们于明亡之后,不食周粟,东渡日本。他们的气节、学行和才华获得幕府的崇敬,让他们在京都附近的宇治仿福清的样式建黄檗山万福寺。这些僧侣精通诗文书画,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将明代书风传到日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隐元、木庵、即非等所谓“黄檗三笔”。在这一潮流中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两位杭州僧人:独立性易禅师和东皋心越禅师。
独立易性俗名戴笠,号曼公。年轻时便诗名高著,为杭州府学秀才,58岁时(1653)东渡日本,追随隐元,以书画和医术闻名于日本。独立性易行草篆隶皆能,尤精草书,气韵不俗,号为“缁流之冠”。当时日本知名的书法家北岛雪山、深见玄岱都是他的弟子。他是日本唐样书法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心越禅师俗名蒋兴俦,字心越,号东皋,为曹洞宗寿昌派第35代传人,杭州永福寺住持。独立去世后5年(1677),心越禅师东渡日本,后应“水户学”领袖德川光国邀请,成为水户市寿昌山祇圆寺祖师。心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高僧,善书画,工篆刻,并将古琴传到了日本。他不仅是日本佛教曹洞宗寿昌派“开山鼻祖”,也是日本“篆刻之祖”、日本“近世琴学之祖”。
俞立德:杭人东渡开创唐风书法
当时,对日本书法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位杭州人俞立德。他是东渡日本的一位学者,深得文征明笔法。著名的北岛雪山远赴长崎求教于他,并由文征明上溯赵孟頫,并远追王羲之,使文征明在日本获得比肩苏、黄的地位。北岛雪山也被公推为江户时代唐风书法的第一人。北岛雪山将俞立德教授他的拨镫法传给了弟子细井广泽,细井广泽的书法也具有了明显的文征明体。同时,细井广泽也是继榊原篁洲之后的一位篆刻宗匠,对篆书也颇有研究,有人把他视为日本篆刻真实意义上的始祖。
日本自江户时代中后期至德川幕府时期实施了长达二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直至明治时期才重新打开国门。随着学者外交官杨守敬刮起的“杨守敬旋风”,清代的金石书法再次震撼了日本书坛。通过杨守敬的学生、“明治三笔”之一的日下部鸣鹤与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之间的交流,一批一批日本书法家来杭求教,杭州的金石篆刻之学再一次深刻影响了日本。如果说杭州是中国对日本书法产生最大影响的地区,恐怕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