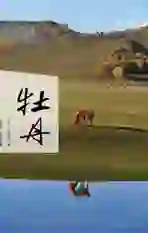脚印
2018-11-22老海
老海,原籍洛宁,现居郑州。曾在某文学杂志社供职多年。累计发表和出版小说散文数百万字。“耳顺”年后,再无“壮志”。惟以写出“有意思”小说,方为乐趣。
清晨。
这个词真好。
越写作,就越感觉汉语的含义丰沛,奥妙无穷。清晨,不仅表现天色由黑变青,天地分清,而且,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清冷的意思。
的确清冷。
这是一个冬日的清晨。
这是一个小山村的冬日清晨。
这个山村非常小,小到了只有一户人家。
村子虽小,也有名字,叫疙瘩墁。
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子不可能成为一个生产队(哦,必须说明,这是生产队时代)。翻过一个小山梁,二里外有个大村,这户人家和这个大村是一个生产队。
昨夜下了小雪。雪虽小,也有两寸厚,把树木山野全盖住了。
小山村的冬日清晨,寂静,肃穆,洁白……有一种让人感动到想哭的净美。
这家的老汉是个勤劳人,即便下雪,也不睡懒觉。天刚一漏明,就起来,出门扫雪。
吱呀一声,老汉拉开了木门,跨过门槛。正要挥动扫把,却愣住了。
他看到白白的雪地上有一行清晰的脚印儿。
那是一行男人的脚印儿。
脚印儿从对面的屋子门前出发,通过半掩的栅栏门(他记得昨晚他关严了栅栏门,并扣了门鼻儿),到外面去了。
老汉愣怔了片刻,就顺着脚印走出去。那两行脚印儿清新无比地翻过了小山梁,通到了那个大村里。
对面屋里住着他的儿媳妇。他儿子在外地教书,一年也就在麦假和过年时才回来两回。
老汉回到屋里给老伴儿说了这事。老伴儿还有点儿不相信,赶紧起床,到院子里看了那脚印儿后,喊了一声儿媳妇。对面屋里传出了儿媳妇睡意朦胧的答应声。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这是丑事,若追根究底,势必掀起风浪。儿子在外乡学校还是校长,传出去,脸面往哪兒搁?何况,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媳妇儿,若因此闹得离了婚,更是得不偿失。
生气归生气,老两口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暂且忍气吞声。
老汉再次拿起扫把扫雪去,一直扫到院外,扫到了山梁那边。那行雪地上的脚印很快就消形匿迹。
天晴后,老汉着手打土坯垒院墙,安装了大门。结实牢固的院墙代替了原来是的木枝栅栏。
后来,他们又养了一只大狗。
那年春天,桃红柳绿时分,我们村来了一位美妇人。
她来时带了个木匠,在村子的一块空地上拿根竹竿比比划划。原来她要在我们村盖房子。
我们村是方圆附近有名的大村,好村。好就好在风水优越,背山临河。想到我们村落户的很多,但队长要求苛刻,必须有强壮男劳力的才行。显然一个女人家不符合这个条件,她是怎么说动队长的?
美妇人在我们村盖房子时,借用我们家的灶房给木匠做一顿中午饭,晚上他们就回各自村子了。他们是另一个大队的人,离我们村不远。
美妇人嘴很甜,见了母亲就叫“姐”。她并非是因要用我们灶房才这样叫,而是她娘家和母亲娘家是一个村子的同姓族人。辈份相当,只是血缘关系早出“五服”了。
她给母亲叫姐,我们自然得给她叫姨。
红玫姨。
突然间来了个红玫姨,我感到很奇怪。真有点儿后来文化人常说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母亲说,红玫姨是从疙瘩墁来的。
我们村虽大,但漂亮女人不多,红玫姨无疑成为了我们村一道靓丽风景。
尽管现代文学观念早不兴这一套了,我还是想按传统的方式把红玫姨描述一番:瓜子脸白晰,齐耳发黑亮,豆荚唇红润。鼻梁左右那几颗雀斑,不仅没减其色,反而像点缀的黑宝石一样高贵。
蓝格英英掐腰大襟绳挽盘扣的可体罩衫,更把红玫姨那曲线优美的腰身很好地衬托了出来。她风摆杨柳般从村道上走过,把我们村所有男人的眼睛都拽直了。
啧,啧!你看这婆娘,长得……嘿,真带劲儿!
扎好了料礓石根脚,盖房子到了立架上梁和垒墙挱瓦的环节,就需要人多了。我们村有谁家盖房都去帮忙的优良传统。
盖房子这样的大事,姨父不可能不回。他那时候已从外地调回来了,而且做了我们公社的教改主任。
姨父叫学堂。
学堂姨父继承了父母的和善基因,殷勤地给大家让纸烟。劈柴烧火,担水舀饭,一点没当官的架子。
学堂姨父和红玫姨看上去很不般配。不仅个头矮,腿还“硬”——我们那深山区,有些水质含氟量高,导致许多孩子患了大骨节病,走路腿“疼”,一颠一拐的,其实就是天然的瘸子。疙瘩墁之所以没人去住,大约与“水土不好”有关系。
漂亮的红玫姨为什么愿意嫁给学堂姨父?想来,乡村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起着决定性作用,结婚前男女双方甚至都不曾见面。学堂姨父家境殷实,不然他也不可能上得起学,成为我们那里少有的“高知”分子。
房子盖过后,红玫姨一家正式移民到了我们村。
学堂姨父的父母没随儿子一家搬过来。人在什么地方住久了,就会产生感情。疙瘩墁有他们父母及父母的父母的祖坟。
故土难离啊!
若说我的初恋对象是红玫姨,你信吗?
暗恋红玫姨的不仅我,还有板斗哥。
我和板斗哥是“同门”兄弟,和母亲红玫姨的关系一样,我们爷爷的爷爷是亲兄弟。
板斗哥在我眼里是个神奇人物,他比我只大一岁,却什么都知道。尤其是男女之事,比我们村里的孩子都“觉醒”得早。在这之前,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母亲那“善意的谎言”:两口子过日子不过是你织布来我耕田,外加冬天睡觉有个“暖脚”的。
古老的山村,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天早晨起来,听到从哪家门扉里传出如同小青蛙似的格哇格哇哭叫声,并见门鼻儿扣上栓根醒目的红布条(宣示新添了一个小孩子,也警示外人,非请莫入)。我奇怪地回去问母亲他家的孩子从哪里来的?母亲总是笑着说,他家男人半夜到西河泊拿罩捋(竹子编的“勺子”,多用于淘洗粮食)捞的。我对此说深信不疑。
我是从板斗哥的口中第一次知道了两口子那不为人(小孩)知的秘密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是和板斗哥去地里拽猪菜,在玉米林里一边解“大手”一边讨论这个问题的。当我听板斗哥说小孩子是男人和女人“那个”后生出来的时,惊讶极了。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不信。
板斗哥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板斗哥说,孩子要是能从河里捞,那没结婚的人怎么就不能捞呢?
细一想,还真是。我把完全不信换成了将信将疑。
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板斗哥说的多么正确。
男人和女人,太“捣蛋”了!
冬天,我和板斗哥经常通腿睡。
我们那里人都有通腿睡的习惯,也是贫穷年代的不得已,这样可以互相取暖,节约棉被。
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在冬天暖和的被窝里,自然要排闲话的,女人永远是男人最愿聊的话题。
我们那时就对女性感兴趣,算不算早熟呢?
不用怎么鋪垫,也没什么难为情,我们就说到了村子里的那个女孩子好。可说来说去,没有哪一个让我们十分喜欢的。在一声叹息之后,板斗哥突然脱口而出,我喜欢红玫姨……
我太惊讶了!
我不是惊讶板斗哥喜欢红玫姨,而是惊讶他那么坦白。我的内心深处,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我没有勇气像板斗哥一样大胆地说出来。
我没有忌恨板斗哥,反而,更佩服他了。
板斗哥不仅是口头,还把他的喜欢落实在具体行动上,他经常踅摸到红玫姨家院子里献殷勤干活儿。红玫姨喜笑颜开,拿好吃的给他作为回报。
我也想帮红玫姨干活儿,可我生性胆小。我们的亲戚关系,反而成了我和她亲近的“障碍”。何况,板斗哥早就抢着把活儿干完了,哪还有我这个笨蛋的份儿呀。
在冬夜黑暗的被窝里,我有些醋意地问板斗哥,你经常给红玫姨干活,沾没沾上边呢?
滔滔不绝的板斗哥哑巴了,半晌才沮丧地说,没有。
我没有为板斗哥感到遗憾,反而欣慰。好像一颗悬着的心又落回了原来的位置里。
不过板斗哥说了一件事,让我的嫉妒心大起。
红玫姨家的房后是一个土坎,她们借着土坎就势挖了一个没有顶棚的简易厕所。土坎上是一条通往地里的村路。板斗哥那天下地回来,在厕所上方经过,正好撞见红玫姨,就看到了她那两片白花瓣儿。板斗哥不禁停住脚步,痴痴地看了起来。红玫姨站起来往起提裤子时,转身看到了坎沿上的他,板斗哥当时就愣住了。
好奇是那个年龄孩子的天性。
我问,她没恼吗?
板斗哥说,她笑着说,小鸡娃子,我还怕你看?
红玫姨多么豁达,她没有骂板斗哥“流氓”,而是用一句笑言化解了双方的尴尬。
我要用现在的语言,为红玫姨当年的善解人意点赞。
学堂姨父的教改主任是个实权职务,全公社民办老师都归他管。因此经常看到有陌生人来找红玫姨。来的人自然不会空着手,掂着点心或鸡蛋之类的东西。
那多半是想当民办老师的青年人。
这些人知道学堂姨父是“妻管严”,想当民办老师只要过了红玫姨这一关,基本就成了。所以,那些年红玫姨家门庭若市,她家的生活不用说也比其他家好得多。
红玫姨一点也不小气,那些吃不完的高级食品,除了拿给常替他干活的板斗哥吃外,也送给我们不少。
红玫姨的生活就更高级了。她像我多年以后读《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经常害病。她一有病,学堂姨父就颠颠地从十五里之外的镇街上跑回来,给她熬中药,炖乌鸡吃。
我跟着母亲去看过两次病中的红玫姨,他拥被坐在炕上,虽然鬓发有些散乱,但脸颊不知是发烧还是喝乌鸡汤的原因,看上去反而更加红润,也更加漂亮。
后来,红玫姨再害病时,母亲就不去看了。母亲颇为不屑地说,你红玫姨哪里有病?她是拿捏学堂呢。
我不明白红玫姨为什么要“拿捏”学堂姨父?
母亲和红玫姨是姐妹加朋友,拿现在的话说就是“闺蜜”。红玫姨不害病的时候,一有空就来母亲这里或排闲话,学女红。我经常看到她们坐在我们家门沿边儿的那棵浓荫巨大的核桃树下,身旁放着针线筐,一面纳鞋底子一面黄大大黑爷爷地说笑着。
蓝天白云,面拂清风。那是一幅多么优美的农村风情图啊!
红玫姨来我们村时,带着一个小孩,名字叫懒。
这当然是他的小名。
小名是月子里母亲取的暂名,也就是乳名。从这个小名上看,红玫姨他们是很宠爱这个孩子的。我们那里孩子越娇,起名越孬,“懒”“赖”“臭”“丑”等。
当然后来学堂姨父给懒起了大(学)名,不过我们谁也没叫过,到现在我都不知他的大名是什么,仍叫他懒。叫顺口了,很难改过来,尤其是人名。
孩子们总是长得快,不几年,懒就长得又细又高,和学堂姨父的小低个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没人注意到懒和学堂姨父个头长相上的差异。
红玫姨来我们村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女孩儿越长越漂亮,个儿不高,皮肤细白,越来越像学堂姨夫。
时间过得好快呀!
突然的,山崩地裂,唐山大地震了。大地震前后,三个“伟人”也相继去世。紧接着,“四人帮”被粉碎,历史以这一年为界开始了建国以来的大转折,“改革开放”成为热词。首先恢复的高考制度,让本可能一辈子禁锢在黄土地上的年青人,有机会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了。
我在一九七八年考上大学,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故土。第二年,“复活”了的县师范又召父亲回去做教授,母亲也跟着转成了城镇户口,吃上了商品粮,随父亲到县师范家属院里居住。这样,我们一家过年也就在县城了。
很少回老家后自然就见不到红玫姨了。不过从母亲(多是从来县城办事或探视的亲戚那里听的)和还在农村生活的大姐那里得知,就在母亲来县城后不久,红玫姨一家也搬到公社(那时已改叫乡)所在地的镇上住了。他们在镇上很便宜买了一所旧院,又建了新房。
他们的宝贝女儿高中毕业后也嫁给了镇税务所长的儿子。
几年后,学堂姨父退休,就在他们的院门口开了个小卖店。昔日的公社教改主任现在做了小店售货员。学堂姨父正好腿疼,能坐得住,守得住摊儿。小买店面朝街位置佳,细金常流,生意不错。
至于红玫姨是否还像在村子里的那些年一样三天两头闹“病”,就不得而知了。
懒作为红玫姨和学堂姨父唯一儿子,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和他的名字一样懒。从没见过他去地干活挣工分儿。想来红玫姨和学堂姨父也不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督促他,他们家也不靠挣那点儿工分过活。
若说学堂姨父是我们村的“高干”,懒就是我们村的纨绔子弟。他逛逛荡荡,潇洒无比地长大成人。
我大学毕业在我们为之骄傲的九朝(现在说是十三朝)古都洛阳参加了工作。一个星期天,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响起了敲门声,拉开门,一个高大威武的军人兀然出现在我面前,“啪”地向我行了个军礼。
我吓得直往后退。直到他叫了一声“明子哥”,我才辨认出是懒。
啊哈!懒呀?我都认不出来了。快进,快进。我的惊魂未定立马转成了惊喜异常。
难怪认不出来,除了穿的军装外,重新坐回沙发的我仔细一算,自我上大学并在县城过年后,有差不多十年没再见面了。我离开家乡时,他刚上初中,还是未成年人呢。
聊起来才知道,他没考上大学,又复习了一年,还没考上。第三年他说啥也不再考了。他说他要参军,开始红玫姨和学堂姨父两口不同意,他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呀!怎舍得离开?何况学堂姨父还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老思想。
懒说,当兵是他的主意,他觉得穿一身军装好神气。
球!我爹不让当,我非当。球,他不让当,我就不吃饭。
懒说话还是那样,即便当了兵,也没改掉说话带“把儿”的习惯。
斗争的结果,懒胜利了。学堂姨父同意懒参军,不过他坚决不让他走远,亲自到县武装部跑关系,让他留在了洛阳军分区。
军分区和我工作的单位咫尺之地,所以星期天没事,他就找我来玩儿。
球!懒说,我爹是老脑筋,我说不让他送,他非给县武装部长送了好烟酒,白花恁多钱。
也不算白送吧?我说,你不是留在军分区了嘛。在这儿多好啊,离家里近,我姨和姨父也放心。
懒说,要说也值。我倒不在意留不留在洛阳,不过武装部长给我爹说我有一项体检不合格,要不是部长给说话,肯定参不了军。
哦,我问,是啥问题?
我爹说的我也忘了,肯定不是啥大毛病。我没当回事儿,也许是武装部长胡扯呢,想借此说明他真给办事了,好烟好酒没白送。
我说,也许吧。不管身体有没有毛病,能让你留到军分区,人家算是真给办事了。
嘿嘿!武装部长我爹原来都认识,和我爹还是抗美援朝的战友呢。懒说。
啊?我又一次惊讶了。学堂姨父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这个人不擅于和人打交道。亲戚朋友都是联系我,才接待或应约,我很少主动和别人打打电话,哪怕是亲兄弟。
懒服役的军分区和我住的那么近,也沒去找过他。唉,现在反思,感到我太没人情味儿了。
大约又过了一年,或者一年多吧,我再次接到了懒的电话,他说他在160医院住院。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兴高采烈地,根本不像病人的样子。我有些疑惑地问他什么病?他说,小毛病,做了个手术,在病房里躺得着急,才跟你打电话。
我说在几楼几病房?我去看看你。
他说,不用,这么远。
确实远。
他说不用,却又给我说了他住院的楼房号。我思忖良久,还是决定去看看他。
160是部队医院。在上个世纪因“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主要指台湾的老蒋)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六七十年代,军事单位的名称都是编号,地址也是“国家机密”。因此这之前我们洛阳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医院。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国家战略思路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160和其他部队医院一样,也“与时俱进”地由原来的军用转向了军民两用,对外开放了。160医院因军医学历高技术精湛而很快爆得大名,甚至比洛阳市中心医院名气还大,很有点儿后来者居上的意思。
洛阳及慕名而来的外地人跑到离市区三十公里外的一条山沟里去一看,哇,真是深藏“俊鸟”啊!
人怕出名猪怕壮,市里早修通了柏油路,有一趟公交汽车直达医院。160现在门庭若市,大门外被众多的客栈饭店商铺簇拥着,昔日偏僻的山沟如今像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般热闹。周边居民的嘴巴咧到了耳朵根,他们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受益者。
部队医院和地方医院最大的不同就是管理严格,房间干净整洁。不知是不是对部队病号的特殊照顾,懒住的是个单间。他见到我,跟健康人一样兴高采烈,眉飞色舞。
到底是什么病?我问。
胸膜炎,做了个小手术。懒说。
我不懂医,不知道人身上还有胸膜这种东西,起什么作用。而且,这东西还会发炎。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的问话基本等于例行公事。
好了。懒说,上星期医生就说可以出院了。
那你为什么不出院?我脱口而出后,才感觉似乎不应该这样说。
懒并不在意,球!在这住院比回部队美多了。
嗯……
妈的!懒坏坏地笑着,我装着病没好,这痛那痛,让那个漂亮的小护士不断往我这儿跑……嘿嘿。
哦,呵……
我没想到那竟是我和懒见的最后一面。
虽不是什么亲兄弟,谈不上有多悲痛,但当听到他死去的消息时,我还是愣了半天神。
据大姐说,懒在洛阳军分区勉强服了三年役,就转业了,分配到拖厂保卫科工作。拖厂是国营大厂,是学堂姨父替他跑了关系,还是凭他的能力,不得而知。我知道有不少农家子弟当了三年兵,复员重回老家修理地球。
想不到懒到拖厂上班后的第二年就死了。
不是什么工伤事故,是病故。
据说他病得很突然,当大家发现倒在地上时,赶紧打了120,到医院没抢救过来。究竟是什么病?大姐也不是很明白,只是说很紧急。想来大约还是和胸膜和心脏有关。
懒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
那时农村还没实行火葬。学堂姨父高价雇车把懒的遗体拉回了疙瘩墁老家,埋在了祖坟里。在这之前,懒的爷爷奶奶也早去世。
事实上这个村子已不存在了。
还生活在农村的大姐去参加了懒的葬礼。大姐说,学堂姨父趴在懒的坟山上哭得很痛,比红玫姨都痛。好多人拉了好久都拉不起来。
我有些疑惑,学堂姨父难道不知懒不是他的亲子?
即便知道,人的感情也并不全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吧?
大姐说,懒还有个遗腹子。懒死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懒的女朋友就是160医院的那个小护士。
更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在视金钱为爹娘,视感情为粪土的时代,懒的女朋友竟甘愿和父母断绝关系,也坚决要生下这个孩子。
大姐说,红玫姨把懒的孩子一直带到了七岁,才交给他母亲到洛阳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懒的未婚女友临行前,拉着红玫姨的手泪水涟涟,说,妈,你放心,孬永远是懒的儿子,你们的孙子。我也永远是你们的儿媳妇,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
大姐讲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悸动,两眼发潮。
一九九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中突然接到板斗哥的一个电话,说他在洛阳长途汽车站。我立马骑车前往,在约定的车站钟楼下,见了面。
回到家在沙发上刚坐定,我就问他来洛阳有什么事?
也,也没什么事,就是想你了,来看看……板斗哥欲言又止。
我看到板斗哥头发斑白,面容憔悴,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便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这么远,农村人是轻易不会枉花路费的。
我给他沏了茶,让了几次也没喝。对于喝茶这种属于城里人的“高级”生活,他显然没感觉。为了不使场面尴尬,我吩咐妻子到菜市场买只烧鸡和几个小菜。
板斗哥轻易不来,我们得好好喝一杯。我说。
板斗哥未置可否。
妻子出去后,我没话找话,今年家乡收成怎样?
家乡来人,不都这样拉呱嘛。
果然,一下就打开了板斗哥的话匣子。板斗哥说,这些年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农业资料越来越贵,一年辛苦下来,交了农业税,若有苹果树,还要交特产税,等于双重交税。今年大旱,麦子几乎绝收。要不是还有往年余粮,老百姓快吃不上饭了……
我无言以对。能说什么呢?我们这些有旱涝保收皇粮吃的城里人,是感觉不到农民们的艰难的。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板斗哥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借点儿钱,要开学了,孩子的学费还没着落。再困难,不能不让孩子上学啊……
我没有感到突然,其实这样的事情已在我的猜测之中。
是啊,我說,再穷不穷教育嘛,得多少?
五百也中,八百也中。
现在看来,这算什么钱啊?可要知道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四百来块。
我正好刚发了工资,把皮包搜净,四百多点儿,妻子买菜回来,我问她,你兜里还有多少钱,全掏出来。
妻子兜里有三百多。正好也差不多够他说的那个数。可是,我却鬼使神差地对妻子说,你到对面看能不能再借点儿,凑够一千块钱吧?
我们住的是妻子单位家属楼,对门是她的女同事。
其实我我这样说并不真诚,多少有点儿作秀的成分儿。如果——或者说,我期望着他说,你们不用作难,已经够了。那我也会顺坡下驴,到此为止。
可是板斗哥没吭气。
妻子大功告成,拿着钱很快回来。我把钱集中在一起,动作夸张地数了一遍……八百,九百,一千。我把钱递给他,这是一千,你数数。
板斗哥把那沓钱对半折起来,装进内袋里,数啥数?这回可把你们挤得干干的了……
板斗哥这才似乎有点歉意地说。
我说,没事。明天上班,到会计那儿提前预支下月工资就是了。
板斗哥说,我有了就还你。
别想急着还。
我说。
第二天,我送板斗哥到公交车站。看着走在前面的他,背有些微驮,脚步也擦地缓慢。
再也看不到儿时那个意气风发的板斗哥了。
我的鼻子不禁重重地酸了一下。
生活把板斗哥给压垮了。
我给板斗哥钱的时候,没有说不用还的话。我还没那么大方。说实在话,那个年代一千块对于我来说,不是个小数。他要八百我之所以凑够一千,也有让他觉得沉甸甸,不好意思不还的意思。
不过,数年过去了,板斗哥再没联系。
妻子说,那一千块怕是有去无回了?
板斗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说,可能他经济还没翻身吧?
匆匆之间,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板斗哥还钱的行动和消息。就像《孔乙己》里咸亨酒店的那个老板,把孔乙己的酒账记在黑板上,每年年底时总要念叨念叨,时间一久,知道还钱无望,干脆把孔乙己的名字和欠账从黑板上抹去一样,我们对板斗哥还钱一事,也从无望到从心里完全抹去了。
二十年之间,无论物价和工资也都增长了十倍还多。那时的一千块现在感觉真不算什么,更不用说在那些大亨和高官眼里,简直连塞牙缝的钱都算不上了。
期间也有几次见到过板斗哥。母亲去世时回到老家过丧事,板斗哥自始至终跑去帮忙,还送去了一条大鲤鱼,说是在水库里抓的。能在水库里抓住这么大的鱼并非易事,怕是偶然得之,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可他把仅此一条的鱼给我们送来,除了儿时伙伴情谊外,还有点儿别的什么吧?
妻子说,他可能觉得没还钱不好意思。
是啊,肯定有这样的歉意在内……
看来他是不打算还了。
算了,那时感觉很多,现在不算个钱。不要了吧?
就是,不要了。
妻子倒不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人。
到母亲“三年”时,我们回老家又见到了板斗哥。他说,借你的一千块钱再也还不了了。本来打算今年你回来还的,可老大刚结婚,花得干干的,再等一年吧,手头宽裕了……
我说,你还记着这事?我早忘了,还啥还,我就没打算让你还。
亲是亲,财帛分,账是不能赖的。
说哪里了,咱哥俩不存在欠账的事。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说,你只要招呼着把母亲的“三年”过好就是。
这还用说,是我分内的事嘛。板斗哥说。
时光如梭,嗖的一下,七八年就又过去了。九十高龄的父亲也离开了我们。
人,总要“离开”的啊!
我再回到老家的时候,惊讶于农村这些年的变化最大。国家减免了农业税,又反过来给土地补贴,农民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日子就好过了。精神面貌也随之改观。老乡们过去多数时候的愁眉苦脸,变得喜笑颜开。穿得也好了,甚至年轻媳妇闺女们的时髦程度和城里没多大差别。
我去板斗哥家看他,捎带说事,看到板斗哥又恢复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模样。他说老大两口现在浙江打工,隔三差五还寄钱回来。老二去年也结了婚,不过咱没怎么花钱,招赘在灵宝,亲家是俩闺女,没儿子。家庭条件又好,闺女长得又排长,何乐而不为?我可不固守老传统思想,即便都留在身边又能咋?不尽孝气死父母的见得多了……
板斗哥说着,拿出二儿媳的照片让我看。
啊,真是的,这么漂亮!
确实大出我的意外。
板斗哥骄傲地说,长得排场不说,还通事理,一个月都要催着咱孩子打一回电话。还时不时地给我们寄钱,不让寄都不中……
我说,女人的外貌美和心灵美常常是成正比的。
板斗哥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對板斗嫂说,去拿一千块钱来。
板斗哥把一千块钱给我,说,早该给你了,都二十多年了……
我推回去,笑道,要还钱哪?一千不中吧?二十多年物价翻了十倍还多,至少得还一万吧?
怕他误会,我马上又说,开玩笑,我压根就没打算让你还。
板斗哥并没有难为情,也嘿笑道,你要一万,我也不给,可这一千,你不要也不中。他说着把钱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我又推回去,这样吧,两个侄子婚礼我都没参加,这一千就当是我的礼金。
板斗哥再推回来,哪能那样说,一码是一码。路远,工作忙,我没给你们说。你孩子结婚我不是也没给你吗?
又说了“过事儿”的几个细节后,我说,我走了,就突然起身跑出去。可在院子里被板斗哥追上了,他把那一千块钱硬塞进我的兜里,你要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哥了……
话说的这个分儿上,我知道不接是不行了。
在母亲和父亲的葬礼上,我只见到了红玫姨,没见到学堂姨父。
母亲的葬礼时我问及红玫姨,她说学堂姨父的腿痛越来越厉害,走不成路了,所以没来。葬礼结束后我和弟弟到镇上去看了学堂姨父,见他坐在小卖部里的轮椅上,一条腿还好,一条腿基本弯成了勾勾。他见了我们,艰难地要从轮椅里起来,被我们按下了。
学堂姨父面容清瘦,目光无神。说起我母亲住院期间的病况,和最后临终时情景,他落下泪来。
母亲去世到父亲去世,这中间隔了又有十年。
没想到学堂姨父竟“走”在了父亲的前面。听大姐说,他也埋在疙瘩墁的老坟里,和父母儿子在一起。
不知他至死到底知不知道懒不是他的儿子?
这似乎——不是似乎,而是已经——成了一个无解之谜。
我是从大姐口里听说的红玫姨早年出轨之事的。大姐正是母亲娘家大队那个村的人,她说他们村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
那么,这事是红玫姨的公婆忍不住说给了亲戚后才传出去的,还是她们村的老人们当年就看出了蹊跷。
农村有句老话,没有不透风的墙。
父亲的“三年”很快就到了。
我再次回到老家见到板斗哥和他闲聊时,说起了红玫姨当年的这件事,板斗哥并不惊奇,只是问我,你听谁说的?
我说,不管听谁说的,肯定是事实。你看懒(当然那时已看不见了)长的一点儿也不像学堂姨父。
板斗哥沉默良久,说了句粗话,妈的,狗日的也死了!
我说,原来你知道啊,怎么死的?
板斗哥没说那人的名字。只是说,听他们村人说,那一年过年下大雪,那个狗日的和他们村人在一起喝酒,喝到半夜,出来到门崖边尿尿,外面被大雪覆盖得一片白。他一脚踏空,从悬崖上摔下去,摔死了。
啊,这样死了?也算是意外。
板斗哥说,那个坏货,早该死了。
他是谁啊?
板斗哥说,说了你也不认识。
至今我也不知那“狗日的”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想来应该和懒差不多吧。
不管我们怎样爱红玫姨和恨那“狗日的”,都已成为历史。
只是,除却感情色彩,许多年前疙瘩墁村雪地上的那行脚印,颇具美感,在我的脑屏上久久挥之不去。
板斗哥说,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红玫姨现在信了佛,经常和香客们出入各种寺庙。
父亲“三年”那天,红玫姨又回村来了。我们又见到了亲爱的红玫姨。
她还是那么风韵犹存,一点儿也不显老。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