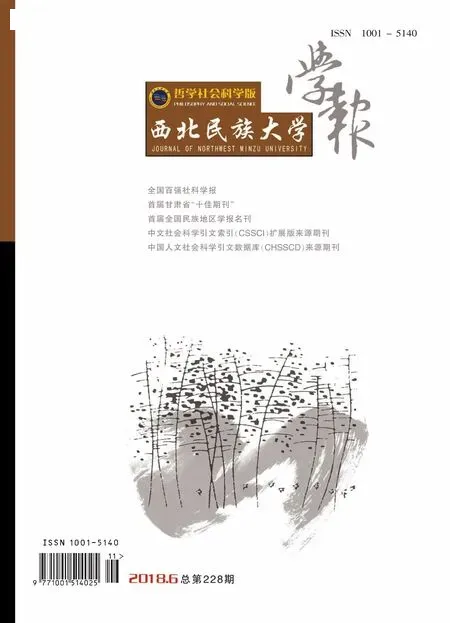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2018-11-21穆慧贤
穆慧贤
(民族文化宫,北京 100031)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的佛教遗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武周山南面,距大同市约17公里。《水经注》记载:“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1]武州塞原称“武周塞”,本因武周山而得名,始建于秦朝。《魏书·地形志》称此地为“武州塞”,大概源于东魏武定元年(543年)曾于此置武州:“武州,武定元年置。治雁门川,武定三年(545年)始立州城(州城治所在今繁峙县西)。”[2]云冈石窟属于北魏皇家大寺,原称为“武州山石窟寺”[3],因武州山而得名。又称“北台恒安石窟”或“灵岩寺”,“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4]12李裕群云:“明代为防边患,在该窟旁设云冈堡,故近人调查时称之为云冈石窟。”[5]
云冈石窟中的佛像均为石雕,开凿于北魏文成帝继位之初,《释老志》载:“和平初(460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453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6]3037在文成帝之前,太武帝曾下诏灭佛,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文成帝即位后诏命恢复佛教,兴安二年(453年)为北魏开凿石窟之始。佛像是佛教文化中的实物载体,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文成帝在云冈开凿石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
佛教造像在北魏前期已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根据现有文献记载,佛教造像在西汉已传入中国,北齐魏收云:“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案汉武元狩中(公元前122—前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6]3025按魏收的说法,佛教是在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当时在国内影响力不大。汉朝军队从匈奴人手中获得的“金人”就是用金属铸成的佛像,这是佛像艺术在汉武帝元狩年间传入中国的较早证据。《魏书》的记载说明,哀帝时期已有佛教经典的流传,但其教义还很少有人信服。
东汉时期,佛教的影响逐渐增大。孝明帝在位期间,蔡愔等出使天竺,“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7]蔡愔等人不仅将佛经《四十二章经》带回中国,也将佛教造像艺术引入国内,《竺法兰传》云:“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8]该记载说明,建寺造像在东汉前期已经开始,寺院的修建标志着佛像造型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崭露头角。
中国的石窟造像最早出现在今新疆境内,这里是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据汉文文献记载,印度、西域的佛教僧侣已经在当时的于阗、龟兹、疏勒等地传教、译经。今新疆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境内修建较早的石窟之一,阎文儒先生认为:“这些石窟,从形制上,接近阿富汗巴米羊石窟的窟形,到简单的佛、菩萨、本生故事的壁画题材,以及还十分粗糙的壁画风格。如与文献所记,魏晋时代就有从龟兹来内地的高僧结合来看,龟兹境内克孜尔的石窟创造,最早可能在东汉时期的后一阶段。”[9]新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佛教造像艺术也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传至内地,而且东传的速度很快,传播的区域也很广泛。
五世纪前后,我国境内已有较多的石窟被开凿出来。在北方,莫高窟开凿于前秦时期,坐落于敦煌,俗称“千佛洞”;甘宁黄河以东地区的麦积山石窟,始建于东晋,是以泥塑为主的大型佛像雕塑馆,塑像的世俗化较为明显,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汉民族艺术特征;此外,陕西、晋豫及其以东地区亦有石窟出现。这些地区石窟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多,“多为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10]。南方僧侣重视佛学义理的研究和寺、塔建造,所以南方地区的石窟数量不多,主要有东晋至南朝萧齐时期开凿的新昌石城山摩崖龛像、南朝萧齐时期的南京摄山栖霞山石窟等,南方石窟数量虽少,但也不乏热衷于开凿石窟者。
北魏前期,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造像技术的成熟,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二
北方僧侣的教义世俗化变革迎合了北魏皇帝的政治需要。北魏自太祖道武帝(386—409年在位)时起就开始信佛,史称:“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6]3030道武之后的皇帝,也大都敬信佛法,这与这一时期的佛教教义变革有关。佛教的原始教义中,佛教徒只跪拜释迦牟尼,对父母、君王均不行跪拜之礼,这与儒家的伦理和礼仪相悖,因而遭到儒学家、政治家的批评。东晋权臣桓玄曾就此问题与大臣、僧人进行过辩论:“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礼实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御而已哉?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曰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11]僧人则以方外之人自居,阐述僧人不遵奉传统儒家礼俗的各种理由,庐山僧人慧远云:“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12]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中,阐述了与之相近的理由,并强调:“义存于此,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13]佛教徒坚持佛教的原始教义,坚持不向君王行跪拜之礼,有挑战皇权至上的权威性之嫌,所以在传入中国的较长时间内一直受到官方的压制。
当时北方的赵郡僧人法果为了佛教的发展,积极变革佛教教义和教规,主动将儒家的伦理和礼仪融入到佛教教义当中,与南方的沙门不敬王者形成强烈对比。《释老志》记载:“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四十岁出家,深谙人情世故,作为北方僧侣的领袖人物,知道佛教如果得不到上层人物的支持就很难有较大发展,只有消除与传统的儒、道礼仪的抵触,才能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在道武帝礼征之际,法果带头礼拜皇帝,得到道武帝的礼遇。道武帝以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加崇敬,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6]3030-3031。
佛教原始教义主张众生平等,僧人只拜如来而不拜世俗帝王。法果以世俗礼法跪拜皇帝,将北方僧侣变革佛教原始教规思想付诸实践。在其之前的河北常山僧人释道安,已在《二教论》中将君王尊为教主,将古代圣王列为菩萨,开始了佛教教义世俗化的变革。他在第三章《君为教主》云:“孔、老为弘教之人,访之典谟则君为教主。”“帝王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此盖皇业之盛事也。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百王同其风,万代齐其规。若有位无才,犹亏弘阐。有才无位,灼然全阙。昔周公摄政七载,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为教主?孔虽圣达,无位者也。自卫回轮,始弘文轨,正可修述非为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谐赞,出周入秦,为尹言道,无闻诸侯。何况天子既是仙贤,固宜双缺,道属儒宗,已彰前简。”第九章《服法非老》引《须弥四域经》:“宝应声菩萨名曰伏羲,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又云:“皇帝之号,尊极天人之义。王者之名,大尽霸功之业。”[6]3030-3031北方僧侣的佛教世俗化变革符合道武帝借助佛教巩固皇权的需要,使佛教在北方的发展得到了北魏皇室的支持。
三
文成帝对佛教的支持。世祖太武帝(423—452年在位)在位时期一度下令灭佛,但在太子拓跋晃(恭宗景穆帝)的暗中保护下,许多僧侣逃过此劫。《释老志》记载:“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6]3034-3035由于时任太子的拓跋晃敬信佛道,有意延缓了太武帝灭佛诏书的发布,所以太武帝灭佛主要破坏了一些寺庙和佛塔,多数僧侣得以逃脱,佛教的根本而没有倾覆。这也说明:“佛教于汉代进入中国之后,经过数百年的潜移默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意识潮流。”[14]
东晋以后,许多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占据中原地区的广袤土地并建立政权,但这一区域内的居民大部分为汉人,汉族的文化意识仍占据重要地位,其治下的一些士大夫对佛教的抵触心理较为强烈。后赵著作郎王度云:“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15]后赵是羯族人进入中原后建立的政权,虽然任用了一批汉人,却试图利用其他文化冲淡汉文化的影响力。对于王度限制佛教的议论,石虎下诏:“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16]石虎的言论虽然不能代表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但试图用外来文化削弱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是北魏皇帝推崇佛教的原因之一。
文成帝是一位推崇佛教的皇帝,他在恢复佛教的一道诏书中云:“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文成帝将太武帝时期的灭佛事件归咎为:“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他认为官员在执行太武帝诏令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了对佛教的一概禁灭。因此诏令:“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者,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6]3035-3036此道诏书的颁布,标志着太武帝灭佛政策的结束,也标志着北魏恢复佛教的开始。“规定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寺院一所,这是中国按政区普建佛寺的先声,改变了以前佛寺建造的无序和随意状态,显示了国家对佛寺建造的重视,是佛寺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7]文成帝继位后不久便下令重兴佛教,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对云冈石窟的开凿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
师贤、昙曜等僧人对佛教造像和石窟开凿的热衷。昙曜是西凉的名僧,《高僧传》载:“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18]昙曜的出生地不详,早年在西凉国境内从事佛教活动。西凉地处河西走廊一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和佛教左相盛行的地方,“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张轨在晋惠帝永宁年间(301—302年)出任凉州刺史,后来成为西凉的实际统治者,佛教在他的支持下有较快发展。沮渠家族建立北凉后“亦好佛法”,广泛组织佛教道场,翻译佛经和开凿石窟,以致高僧云集,并成为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北魏灭北凉后,太武帝“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6]3032太武帝早年也崇信佛教,他将北凉境内的一些僧侣迁至平城,对北魏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师贤、昙曜等人大概是北凉灭亡后迁至平城的高僧,在平城僧俗中有着较高地位。太武灭佛之时,师贤、昙曜等高僧得到皇族成员的暗中保护,“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师贤是罽宾人,善于佛教造像,被文成帝任命为道人统,成为佛教领袖。“是年(452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自法果始,敬天子如礼佛的传统在北方佛教礼仪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以皇帝的形象雕刻佛像也是合乎佛教教义之事。石像雕成后,居然出现了与文成帝身体部位相吻合的黑子,这件巧合的事情被“论者以为纯诚所感”[6]3036,师贤雕刻的石质佛像出现了与文成帝身体特征吻合一事,无疑激发了文成帝大造佛像的信心,也使广大民众更加相信北魏皇帝就是“佛”的说教。兴光元年(454年)秋,文成帝“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6]3036现在学者虽然对于五级大寺的研究分歧颇多,但大都认可五级大寺为北魏平城时代的皇家寺院。文成帝诏命铸造的佛像以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恭宗景穆帝拓跋晃和他本人为原型,是将法果天子即是佛祖的思想运用到现实社会中的体现,使民众礼佛即拜天子有机结合在一起,将北魏皇帝的地位在百姓心中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境地。
师贤之后,昙曜继任佛教领袖,称为沙门统。昙曜建议文成帝于京城西的武州塞开凿了五座石窟,各雕刻佛像一躯。“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4]12昙曜开凿的五座石窟在云冈石窟群的西端,现在的编号自西向东依次为20、19、18、17、16窟,“各窟内雕刻三世佛,正壁主尊均为高达15~17米余的巨形佛像,佛像占据了窟内大部分空间。从窟前远处穿过明窗仰望,即可看到主尊佛像的面相,可见洞窟的设计别具匠心”[5]141-142。学者大都认为昙曜五窟中的佛像是以北魏的五位皇帝为原型,但每窟所指哪位皇帝却分歧较大。山西省文物工作者认为:“这五所石窟,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一像来考虑,16、17窟是从西数的最后两窟。主像是单一释迦像的16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的17窟,相当于没有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18、19、20窟,则应分别相当于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19]宿白认为:“18、19、20三窟为一组。都是以佛装的三世佛为主像。左右两主像分别处在左右胁洞的19窟,是这一组的中心窟。”“处在东头第二窟主像是交脚弥勒的17窟,应相当于没有即位就死去了的景穆帝;”[20]赵一德认为:第16窟,“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第17窟,“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第18窟,“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第19窟,“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第20窟,“高祖孝文皇帝拓跋宏”[21]。日本学者石松日奈子认为:“石窟五所的营建与兴安三年(四五四年)‘为太祖以下五帝的五尊丈六释迦像’是在同样的意图下计划的。五帝五佛的造像活动,从道人统师贤开始,到第二任沙门统昙曜继位,昙曜也为太祖以下五帝开凿了石窟。”[22]日本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云冈石窟,关于昙曜五窟中佛像的研究成果较多,石松日奈子的结论是日本学者观点的概括和总结。由于昙曜五窟中佛像的意指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所以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但认为五窟中的佛像代表北魏五位皇帝却是公认的。五窟是昙曜迎合北魏统治者的佛教发展新举措,并由此开启了北魏大规模开凿石窟的序幕。
五
北魏从文成帝时期开凿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一种表现。早期石窟以“昙曜五窟”为代表,造像气势宏大,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风情,这与昙曜等人来自西域不无关系。中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是北魏最为稳定、繁荣的时期,国家有能力调集全国优秀的雕刻人才,造像侧重于形象和装饰,所呈现出的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出雕饰精美的艺术风格。晚期作品开凿于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受汉化改革的影响,佛像也多呈现出汉族人的某些特征,如面形清瘦、肩窄下削的艺术形象。云冈石窟的开凿历时60余年,佛像大约有五千余躯,每座佛雕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惟妙惟肖,不同时期的雕刻风格各有特色,石窟内的造像气势宏大,所蕴含的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石刻之冠和雕刻艺术宝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云冈石窟的开凿,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像造像者,加之造像技术的成熟,使石窟开凿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昙曜为北魏五位皇帝开凿石窟造像,是以佛教迎合皇帝的政治需要而发展佛教的重要策略,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昙曜用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将北魏皇帝比作现在佛,让人们在礼佛过程中礼拜皇帝,将皇帝即佛的思想融入到现实社会之中。昙曜的做法深得文成帝的赏识,而文成帝则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为佛教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提供了财力保障,开凿石窟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这是云冈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在云冈石窟开凿前后,文成帝下令全国广修寺院,以礼佛的形式敬奉北魏的历代皇帝,说明佛教在此时已经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中国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