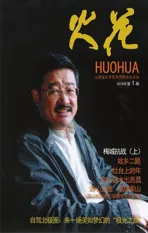消失的老屋
2018-11-21王友明
王友明
故乡的老屋尽管消失了,然而,老屋的故事却长久地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老屋,如潮的往事刹那间就会涌上心头……
家在哪里?
当兵第一天,排长就告诉我们说:“咱们军人是四海为家!”
客居异乡数十载,我不仅有第二、第三故乡,而且有第四、第五故乡,但我却一直执拗地认为,家在老屋。
因为,老屋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啊!
老屋是我的诞生之地,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先世人生的终点。
不是么?顺着老屋门前芳草萋萋的那条土路望去,四个土堆、四尊石碑映入眼帘。那是坟墓,是爷爷奶奶、伯父伯母、父亲母亲、叔父叔母等先人安息的地方,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做的持续的梦。
老屋,满盛着我剪不断的乡愁,是我温馨的摇篮,是我心灵的寓所,是我情感的寄托,是我生命的律动。
有了老屋,田野才凸现辽阔;有了老屋,家园才属完整;有了老屋,我们才显得年轻。
老屋,盛满乡愁,是我心中一个永恒的情结。
静寂的夜晚,每每思念老屋的时候,我腮边总会挂有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打湿那座小小的村庄。
记事起,我家的老屋,是用麦秸草和泥堆砌起来的泥草房。听父亲说,这座老屋是新中国成立那年建造的。
老屋真的是有点太老了,屋顶明显塌陷,不太粗的檩条被压得弯曲了,墙皮四处脱落。时逢雨季,屋顶遍漏,父亲便在要紧处放上盆盆罐罐承接雨水,再用一块厚塑料布在土炕上搭一个棚子,我们一家五口人就蜷缩在塑料棚子下。听着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的响声,我的心里好烦好烦。
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住在一间不漏雨的屋子里。
家穷鼠却多,老屋的墙四周到处都是鼠洞,漆黑的夜晚,在屋子外面便可看到从鼠洞里透射出来的微弱灯光。如若站在村口看老屋,“她”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蜷伏在那里,显得格外凄凉。
六十年代末,父亲看着摇摇欲倾的老屋,实在是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便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拆除了老屋,原地盖起了四间里边是土坯,外包一层砖的“夹心屋”。
相对于泥草屋来说,那可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档”屋啊!
新屋盖起后,家里的生活更苦了。每到过年时,父母还要将拼死拼活挣来的几个钱用来还债。
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母亲得了一场重病,又给这个贫穷的家平添了几分艰难。
生活虽然艰苦,但住在新屋不用遭受漏雨之罪,心里还是挺满足的。
1970年冬季,我当兵走出了老屋。
客居异乡,每每听到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我就仿佛听见了父母亲一声声回归老屋的呼唤,越是遥远,越是揪心,越是抒情。
当兵第七年,我脚下已不再是母亲在老屋就着小油灯微弱的光线,一针针、一线线缝制的那双千层底,而是一双油光锃亮的黑色皮鞋。但是,我却永远也忘不了初次探亲时的那个除夕之夜。
夜半时分,当从伯父家喝完守岁酒回到家,透过老屋窗户,看见母亲仍坐在土炕上缝制布鞋的不倦身影,我流泪了。母亲啊,您为儿子操劳的太多太多了,而儿子回报您的却是太少太少了。
本欲进屋劝阻母亲,可深知母亲脾气的我,还是止住了脚步。
大年初一的早晨,刚进入梦乡,母亲就把我叫醒,一双棉布鞋递到面前:“快试试合脚不?穿上布鞋又轻快又暖和。”我一试,正合脚。
穿着新布鞋,我孩子似的在老屋里走来走去,口中不停地赞叹:“真轻快,真暖和,还是娘做的布鞋好!”母亲疲倦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早春的阳光里,我又探亲走进那座老屋,在渴望团聚的呓语中,寻找童年放飞的鸽子。整整绿色的军装,双手托起一轮朝阳,在绿色的年轮里燃起挚情,所拥有的理想便从老屋注视的目光中升腾;阳光穿透小院里的树丛,把一缕光线投进老屋,我看见母亲聚精会神地穿针引线,在回眸一笑中,掩饰着母亲永不可破的坚毅。
身居闹市多年,我更觉得老屋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结婚那年,按照老家的风俗,我没有占用那座正屋,而是把两小间东屋作为新房。
其实,那是两小间十分简陋的小草屋,与其说是屋,倒不如说是草棚更合适。屋顶是用木棍、高粱秸和杂草铺就的,上面抹了一层黄泥,四壁全部用黄泥围成,屋内低矮、光线昏暗,这里便是我与妻度蜜月的地方。
虽然两间小草屋简陋不堪,但毕竟可以遮风挡雨,心里也没有多少怨言。
生命的音符跌宕起伏,在火热的夏日里,蕴藏着无数的色彩:红的、紫的、绿的、蓝的、白的、黄的,还有老屋那迷人的风韵;伴着风的走向,季节渐渐沉寂。可老屋却成了一首歌,一首欢庆丰收的歌。
打开老屋的每一扇门,都能看到盛满粮食的囤、装满棉花的包,我便在这喜悦的氛围里读懂了老屋的厚重。老屋也用灿烂的希冀,在这成熟的日子燃起照亮前程的火把。
下雪了,飘泊在外的我,回到家,一头钻进那座老屋,围炉而坐,听父母亲讲述我童年的故事,老屋就更充满温暖的魅力。
1978年初,因弟弟要说亲,父母说得把屋子明确一下。
当时,我们家就这一座“高档”屋,剩下的就是那两间小草屋。我和老伴二话没说,让父母将四间正屋分给了弟弟,把村里作价二百元的两间小草屋留给了自己。
那时,我在部队服役,老伴在家务农。
1982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收到老伴的来信。信中说,有天晚上下大雨,小草屋的土炕正上方塌了一个很大的窟窿,泥土掩盖了多半个土炕。幸亏老伴走亲戚不在家,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看了信,惊得我冒出一身冷汗,即刻给父亲写信,商量盖新屋的事。
村里得知情况,按军属给予照顾,让老伴随意挑选宅基地。老伴觉得选屋址要离伯父家近一些,有事的时候好有个照应,便选中了一个大土坑,坑里堆满残砖碎瓦,面积也只有标准宅院的二分之一。
为了垫平大土坑,瘦弱的老伴经常在下地劳作之余,独自拉着笨重的地排车,从村西的小河堤坝上取土,再气喘吁吁地拉回来填在大土坑内。有时上坡,老伴实在拉不上去的时候,就喊来四邻帮忙。白天没有空闲,就趁明亮的月夜来回拉上三五趟,每每累得腰酸背痛,却咬牙坚持着。
年愈七旬的父亲和刚刚转业的小弟,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也赶来帮忙。每天用地排车拉土十余趟,就连大年初一也没有得到完整的休息。一直忙乎了三四个月,才把大土坑垫平夯实。
秋天,便着手盖屋修院了。
对农人来说,秋天是个繁忙的季节,既要收,又要种。可盖屋修院对于无栖身之所的老伴和女儿来说,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因而,父亲、老伴和小弟,不辞辛苦,边忙碌收秋种麦农活,边操持盖屋修院事宜。
我得知消息赶回家时,三间红砖到顶的新屋已经盖起,只剩下铺地面、灰墙、打围墙等扫尾工程了。
因操心过度,加之农活太累,父亲和小弟同时病倒了。心急如焚的我,只好跑东家奔西家,请求乡亲们帮忙。所到之处,有求必应,令我着实感动不已。
在乡亲们的热情帮助下,扫尾工程终于完成了。尽管屋子的主砖墙是八寸的,窗户也不大,门是古老的板式黑漆扇门,屋内地面是用半拉砖头铺就的,与邻居那高大漂亮、精巧雅致的红色瓦房相比,确实是显得太低矮破旧了些,但我们毕竟拥有了一处自己的屋。
立于这和着心血、和着汗水修建的新屋前,我们全家人都心满意足地笑了。
由于急着居住,父亲教给我一个让潮湿的墙壁速干的办法:用火烘烤。我和老伴赶忙拉来两大车棉花柴,在屋里点起七八个火堆。
经过三个昼夜的烘烤,潮湿的墙壁真的被基本烘干了。
搬家那天,我们放了好几挂鞭炮,以庆贺乔迁之喜。
安置好简陋的家,我和老伴又在小院里栽上了三棵槐树,一棵枣树。
几年过去,槐树就枝繁叶茂了,绿树掩映下的老屋呈现出一派勃然生机。
清晨,阳光洒满小院,更富有一种乡村情韵:老伴坐在门墩上,精心地摘着蔬菜;雪白的公鸡站在墙头上,伸着脖子打鸣;邻居家的小黑狗也跑过来,守在屋门口,摇头晃脑地叫个不停;槐树叶子上,兜满夜里落下的露水珠儿,风一刮,噼哩叭啦往下滚,像掉下一串串银豆子;挂在屋檐下的辣椒,在晨阳的照射下,闪着红红火火的光……
生活在这个老屋和小院里,我感到格外惬意。
一到晚上,我和老伴、女儿,或坐在老屋前的槐树下吃饭,或坐在老屋后的空地上与邻居们聊天,房前屋后总是溢满浓浓的亲情和乡情。
1985年春节过后,老伴随了军,父母便从小弟家搬到了这座老屋居住。虽说人老了,但父母还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1998年腊月二十八,我回家陪父母亲过年。
除夕那天,我亲手把红红的对联贴在老屋的门上和院门上,把福字倒贴在老屋内的水缸上、箱子上、柜子上,并在老屋门口和街门口安上了电灯。
夜幕降临后,通明的灯光,映照着红红的对联和洁净的老屋,为故乡的年意营造了一种祥和红火的氛围。
因我在家,前来串门的乡邻和拜年的亲戚很多。从初一到十五,每天客人不断,老屋内外始终沉浸在一片喜气之中。
年迈的父母亲,此时也仿佛年轻了许多,立于老屋门前,迎来送往。
望着笑容满面的父母亲,我的心湖也绽开了开心的浪花!
正月十五那天,吃过晚饭,我便悄悄地走出老屋,走出家门,趁着月色,漫步在宽阔的街道上。
只见一排排整齐漂亮、扁砖到顶的新房屋的房脊上,全部耸立着电视天线。轻快的音乐声,戏剧的锣鼓声,飘出屋子,飞向空中。
蓦然,我想起了早在1983年,村里就专门拿出数十万元,补贴给各家各户用于购买电视机。那时,故乡小村就成为了全镇唯一的“电视村”。为此,我骄傲和自豪了许多年。电视机的普及,不仅使老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而且让父老乡亲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边走边想,想我的故乡小村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已走上了富裕之路。如若不是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之久,我简直不敢相信,此处便是我的故乡。
自从确定我转业地方工作后,我和老伴就年年回到那座老屋,陪伴年事已高的父母亲过年,盛满乡愁的老屋,便会洋溢着欢声笑语,浓郁亲情。
过完年,一步一回头,踏上回归的路程,我的心中却依旧装满老屋的温情。
尽管山水阻隔,我总觉着走不出老屋的视线,走不出那份痴情的牵念。
老屋,让我所有的故事重新开始;老屋,让我的记忆常想常新。特别是年根儿,我总想携妻带女奔向老屋,用心把老屋装点得富丽堂皇。
何故?只因我觉得年不在城里,年在乡下;家不在高楼,家在老屋。
虽然城里风情万种,可那上了防盗锁的门,永远也不会像乡下人那样有一种充满温情的表达;虽然高楼巍峨壮观,可那只“猫眼”,永远也不会洞穿坐井观天、彼此孤独的心灵。
在老屋过年,我宁愿花两三天的时间,把一年来积存在老屋的灰尘打扫干净,然后去购置年货,去张贴春联,去加入拜年的队伍。
在城里过年,哪怕用一天的时间去擦拭,我都嫌累。两种地方,两样心情啊!
老屋,是我心神的供奉,是我情感的归真。老屋就是家,家就在老屋。老屋,盛满乡愁,是我永远牵念的地方。
2000年6月,母亲不幸去世。
回家奔丧的我,一踏进那座院子,便有一种悲凉的感觉,似乎那座老屋也随着母亲的离去更加苍老了。
送走母亲,我用了两天时间,挥汗如雨地把老屋又打扮一新。
至此,我方才深刻领悟到余光中先生《乡愁》中的“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的由衷感伤。
弟弟那边因规划新农村,先前的老屋被拆除了,早已盖起了五间宽敞漂亮的新瓦房,还在院子西面盖起了三间红砖到顶的新厨房,想让父亲搬过去住。可父亲说啥也不愿意到弟弟家去住,依旧住在这座老屋里。
国庆节放假时,我回到仅仅别离四个月的老屋,看到的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景象:这里已是人去屋空,屋门紧紧地关闭着,那把已锈迹斑斑的铁锁,孤独地“卧”在屋子的门栓上。院落之中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犹如足迹罕至的荒原,风儿擦过宁静的小院,槐树叶随风翻飞,滚落在脚下,我心中一阵发酸,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踩着茂密的杂草和厚厚的落叶,我走进老屋,一股呛人的霉味扑鼻而来。环视屋内,到处都是乱乱的,桌子上、床上、土炕上全是一层很厚的脱落下来的墙皮。屋子东南角已严重漏雨,仍不时有水滴叭哒、叭哒地往下落。屋顶、屋角遍布着蜘蛛网,还不时地看见老鼠乱窜。
看着遍体鳞伤的老屋,我心里疼痛不已,一片孤寂和凄凉的乌云笼罩在心头。
愣了片刻,我便开始动手打扫老屋,收拾小院。
老伴劝阻说:“咱爹老了,不能在这里住了,就别费劲收拾了。”
我含着眼泪说:“看着这乱糟糟的屋子和院子,心里难受啊。要是咱娘还健在,咱爹还住在这里,老屋和院子咋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伴见我动了感情,便不言语了,也动手帮我收拾起来。
忽而,一只鸟儿在槐树枝头凄切地叫了几声,仿佛在诉说它的孤独悲凉之感。
弟弟感伤地说:“哥,屋子没人住,很快就会毁的,还不如趁早拆掉算了。”
我和老伴不同意:“留着吧,这是个念想!”
又过了七年,父亲去世了。
埋葬父亲归来,我特意跑过去看了看老屋。
老屋依然站立在那里,却被风雨侵蚀得顶部已经完全坍塌了,只剩下四周的墙壁还顽强地耸立着,地面上到处是孩子们玩耍时扔进去的树枝、砖头、瓦块,靠近东墙边竟然长出来几棵大拇指粗的槐树。
一阵微风吹过,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腐木和青苔的气味,我的心隐隐作痛。
此刻,一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又落在老屋前面的槐树上,冲着我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仿佛在告诉我:“快看看吧,这就是你的老屋!”
望着老屋凄惨的样子,父亲、老伴和弟弟,挥汗如雨、拉土填坑、搬砖建屋的情景,不由得浮现脑海。我赶紧掏出数码照相机,将坍塌的老屋和荒凉的院落摄进镜头,让其永远感光在心灵的底片上,珍藏于永久的记忆中!
一晃,又是六年过去了。回家探亲的我和老伴,再次去看老屋。此时的老屋情景更惨:西面的厨房和围墙已经坍塌殆尽,一排干槐树枝插在那里,权作围墙;老屋前面的窗户也已破烂不堪,墙壁上的砖块有许多松动掉落,出现了大小不同的窟窿;后面的长山墙和左右两边的短山墙,只剩下一副躯壳倔强地挺立在那里,迎接着春夏秋冬的检阅,风霜雪雨的洗礼。
目睹老屋惨状,我和老伴的心疼痛难忍,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时隔两年,堂叔伯侄子找到在老家小住的我和老伴,说是想把我那个小院要了去,开办一个加工厂,老伴百般不舍。
我清楚,那个小院和那座老屋,是老伴心血与汗水的结晶,一下子要交给别人,肯定是难以割舍。在我的极力劝说下,老伴才勉强同意。可侄子一走,老伴就泪流满面了。
从此,我的老屋便在那块地标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句号,永远地消失了。
没有了老屋,我就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可老屋里那段曾经温馨与幸福的岁月,却刻骨铭心,永远不会消失。
只要看到老屋的照片,我就会触景生情,过往的片断一幕幕浮现脑际:飘雨时候,我一个人撑着伞,伫立于老屋前,凝神静思;幽静庭院,一杯白开水,几张报纸,酿成一片浓郁的记忆入怀;明亮月夜,沐浴着月光的清辉,吟诵几首古诗,与古人一同享受追思的静谧;独依门前,任微风吹拂,看花开花落,放飞思绪,遥想当年;台灯之下,翻阅昔日著作,咀嚼生活的真味,回窥过去,感念生活,体认生命……
老屋,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成为一帧蕴意深厚的历史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