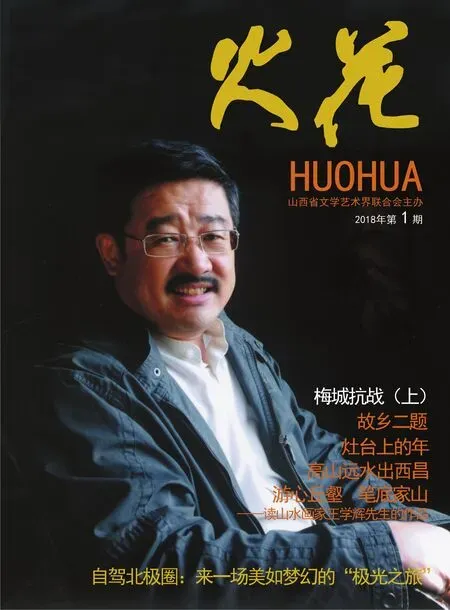朱墨春山(七)
2018-11-21王克臣
王克臣
陈快腿答应把药单子交给孔大学问,挑帘出去了。
杨二嫂说:“玉明,陈嫂去请孔大学问,也就一句话的事儿,你放心罢!我也该回去瞧瞧了。”
“叫你多操心了。”
“瞧你说的,咱们两家,谁跟谁呀!”
“慢走,不送了!”转脸朝里屋叫道,“金花,过来,赶紧说声谢谢!”
“你的礼儿倒多!”
当金花刚刚开口说“慢些走”的时候,杨二嫂早已出了院子。
金花走过来,不知啥事,疑疑惑惑望着妈妈。
蔡玉明读懂了闺女的眼神,说:“金花,你杨二娘托人,给你在县城找了一份儿差事……”
没想到,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金花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滚落下来,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你看,你看,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可急的哪门子?”
“我不去。五九六九,抬头看柳。眼看春天就来了,开荒种地,挑水劈柴,推碾子拉磨,这些累死人的活,您说,银花、五丫头、成子,这几个孩子家家儿,谁能帮您?”
蔡玉明听罢,一下子把金花揽在怀里,眼泪噗嗒噗嗒砸在金花的脸上,哭道:“孩子,妈的好孩子!”
银花、五丫头、成子看见妈妈搂着姐姐哭,一个个也呜呜咽咽地哭开了。
霎时,一家五口,哭成了一团。
突然,蔡玉明推开金花,擦擦眼泪,说:“金花,妈妈想好了,去县城学徒,是你的出路,咱们朱家也该有个顶门立户的人!”
金花说:“我哪儿也不去,本来就有吃的,没干的。我一走,地里拉墒打砘子,指望谁?家里吃喝拉撒睡,谁来管?还不把您累死!”
蔡玉明说:“傻闺女!也没听说谁活活累死的!”
金花执拗地说:“反正我不去。再说,顶门立户的差事,应该是男孩子。丫头顶不了门,立不了户!”
“庄稼人,一辈子受苦的命!能逃出来,谁不逃出来?”
“越苦,我越不能离开您。我不为您分担,谁为您分担?”
蔡玉明拍拍金花的后背说:“好孩子,听话。好闺女,别把妈急死!”她老泪纵横,哽咽在喉。
金花看妈妈哭成了泪人,开始犹豫了。
第二天,老爷儿依旧从东方升起,鸟雀照样在树上啁啾。
蔡玉明早早地从炕上爬起来,去趟茅房,抄起立在墙角的扁担,前面挂一个大水桶,后面挂一个小水桶,出门去挑水。
栅栏门“吱嘎嘎”的声音,惊醒了金花。她侧歪起身,趴近破玻璃,看见妈妈挑着水桶往外走,知道她去挑水,她着急忙慌地蹬上棉裤,披上棉衣,趿拉着鞋,追了出去。
当金花追到时,妈妈已经走到西井沿儿了。
蔡玉明刚刚放下扁担,正准备往井里续绳子,突然,她发现自己的肩膀上,有一种柔柔乎乎的感觉。回头一看,原来是金花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她吃了一惊,说:“你怎么来了?大正月初二的,多躺会儿!”
金花什么也不说,从妈妈手里夺过绳子,续进水井。
井口的冰,冻得很厚,溜溜瓶儿似的,人在打水时,极容易滑倒,蔡玉明看着闺女的一双小嫩手,白白净净的,干这种粗活,鼻子一酸,泪水险些涌上来。
金花双脚站在溜溜瓶儿似的井口上,一下一下地向上拽绳子,把打满水的木桶提上来。
蔡玉明站在金花身后,捏着闺女的衣角,唯恐出现闪失。
谢天谢地,两桶水,一先一后,都安安稳稳放在井台上了。
蔡玉明弯腰抄起扁担。
“妈妈,我来挑,我都十六啦!”金花伸手就抢扁担。
“十七十八力不全。十六,咋是十六?前儿个十五,睡了两宿觉,就十六了?”
金花不顾妈妈的劝阻,挑起担子就走。
“这咋说,嫩胳膊嫩腿的,别闪了腰!”她絮絮叨叨地只顾嘱咐闺女,却忘了提防脚底下,“啪嚓”摔倒了,顺着溜溜瓶儿似的井台儿,一直出溜一丈多远!
金花急忙放下担子,扔掉扁担,从地上抻起妈妈,说:“妈妈,摔着没有,您怎么不加小心呀!”
“没摔着,就是来个老头踹被窝儿!嘻嘻——”
金花重新挑起担子,头也不抬,昂昂地走。
蔡玉明跟在闺女的屁股后面,颠颠儿地追。
金花挑到家里,把水倒进水缸,放好木桶,这才说:“妈妈,玄不玄呀!这要摔坏您,老胳膊老腿的,可咋好?”
“没事,这些年,跑东跑西的,啥没干?瞧你说的,离老,还差得远哩!”
“您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
“眼不见,撂一片。你去你的,去了就安心给人家干活。吃人家饭,就得给人家干。不然的话,人家凭什么白养活你?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她一面磨叨,一面抱柴,好歹也得吃几口呀!唉,大人好说,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哪行?肚子饿了,就哭,就叫,哪里像金花那么懂事!饿就饿了,累就累了,这孩子懂事早,可人疼。
金花手脚麻利,帮助妈妈往棒渣里放碱面,搬凳子挪椅子,拿筷子拿碗。这些零碎小活,都不让妈妈干。等到粥熬熟了,一碗一碗盛好,然后,一一叫道:“银花、五丫头、成子,洗手洗脸,上桌子吃饭!”
于是,银花、五丫头、成子嘴里叫着,挤在一块儿,连洗带闹,叽叽喳喳,围着炕桌,坐上一小圈儿,吸溜吸溜喝稀粥。有时嚷,有时叫,有时连嚷带叫,有时连哭带闹,整个一台戏,一台闹剧!
金花看了,又愁又喜。心里想,姐姐走后,都指望着妈妈一个人伺候你们,忙得过来吗?
蔡玉明说:“金花,你也赶紧吃。不然的话,陈快腿、杨二嫂说不定谁来!”
金花说:“妈妈,您可别再管人家叫陈快腿,兴别人叫,不兴您叫。我陈婶为我的事,跑前跑后的不容易!”
蔡玉明抿嘴笑笑,说:“全村的人,都这么叫她。这人,从来没跟人恼过!”
这一家人,大大小小正吃得热闹,老老少少正说得投机,一掀帘,进来一个人,说:“谁跟谁恼?大正月的,至于嘛!”
陈快腿的突然出现和没头没脑地发问,使蔡玉明、金花娘儿俩猝不及防,一个个都愣住了。
陈快腿说:“谁爱跟谁恼,跟谁恼,也不关咱们的事。”
蔡玉明说:“那是,那是,咱们就管好眼面前这些事,就成!”
陈快腿说:“玉明,我告诉你,我到孔大学问家里去了,跟他前前后后一通说,把中草药单子也给他了。你猜怎么?孔老爷子倍儿痛快,他说,容他准备准备,调整调整。不出正月,就能教会金花,你信不信?”
“是吗?”
“不是咋的?还能掺半点假?”
蔡玉明大声叫道:“金花,快给你陈婶儿拜个晚年!”
金花走上前来,刚要拜年,却被陈快腿一把拦住,说:“别,快别,点个头儿就得了。再说,我也没带压岁钱呀!”
蔡玉明笑笑说:“行了行了,金花给你陈婶点个头儿,只当拜年了。不是别的,你陈婶怕花压岁钱!”
陈快腿说:“玉明,别闹了,快说点儿正经的。让金花哪天到孔大学问家去呀?”
蔡玉明说:“哪天去都行!”
陈快腿说:“金花,你说呢?”
金花说:“我听我妈的。”
陈快腿笑道:“瞧你们这娘儿俩,谁都不做主!”
蔡玉明说:“依我看,再听听杨二嫂的,你们姐儿俩给跑的,咋能不听听她的呢?”
“也好,别剃头挑子一头热。咱们这头儿准备好好的,到了人家那头,好家伙,没事儿。那不瞎子点灯白费蜡嘛!”
“是呀,还没等人家回话,咱们先忙乎上了!”
“玉明,要不这样,我去杨二嫂家问问,要成呢,脆快的。别温水泡黄瓜,蔫了吧唧的,谁也别耽误谁。办事嘛,就得胡萝卜就酒嘎嘣脆!”
蔡玉明笑笑说:“瞧你,咋那么多俏皮话。行了,行了!要找杨二嫂,也得我去,就算你腿快,总不能让你一个人跑瘦腿呀!”
陈快腿说:“只要这件事跑成了,真把腿跑瘦了,也值!”
“那、那我不成老太太捡鸡蛋——尽情了!”
“你看,你看,你的俏皮话也不少。你别送,我这就去找杨二嫂!”说着,早就挑帘出去了。
蔡玉明自言自语道:“这陈快腿的外号,真没取错!”
陈快腿从蔡玉明家里出来,径直奔了杨二嫂家。一进门就说:“我说杨二嫂,你怎么属牛的,闷着!你给玉明家办的事,咋连个回音也没有,叫人干着急,玉明家的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
“我刚刚从县城朱二先生那里回来,还没等我去玉明家呢,你倒先找上门来了,好你个陈快腿!”
“那我就放心了。你呀,不是我催你,赶紧把你去朱二先生那儿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跟玉明说说。金花到底什么时候去孔大学问家,心里好有个准谱呀!”
“看把你急的,你入洞房那天,大概都没这么着急过!我这就去,说去就去!”
两个人,一面说笑,一面往蔡玉明家里走。
走到她家门口,陈快腿说:“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刚刚从她家出来,就不进去了。”
“你这娘儿们,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行行,你赶紧回去吧,你家孩子爹,恐怕早就等急了!”
“损吧,当心我撕烂你的嘴!”一面说,一面伸出一只手,就奔着杨二嫂的嘴去了。
杨二嫂打掉陈快腿的胳膊,“咯咯”地笑着,踹开了蔡玉明家的破栅栏门,逃了进去。
过了正月十五,东家走西家串的人,日渐减少。河南村整条街,渐渐变得热闹起来。卖烧饼的,炸油鬼的,吹糖人的,锔盆锔碗的,铉笸箩簸箕的,都出摊了。稀稀拉拉的吆喝声,叮叮当当的磕碰声,交织在一起,好像一曲杂乱无章的练习曲。
金花走在河南村的大街上,低着头,生怕碰见熟人,心里好像总有人问她“到哪儿去呀”“干啥去呀”之类的话。有时悄悄向大街两旁溜溜,又好像并没有人注意到她。她终于走到了村东南角的黄土坡上,顺着曲里拐弯的小路往前走,来到孔大学问家门口,慢慢地停下了脚步。仰起脸看了几次,她清清楚楚记得妈妈的话:门口有两扇大红门,门框上有肥肥实实的黑漆大字。金花心里断定,这就是孔大学问家。当她决计敲门的时候,却又把手缩了回来,心里打开了鼓:第一句该说什么呀?她怯生生的,此刻,哪怕手里领着个小孩也好呀!她第一次感到孤独,竟有几颗泪珠子滚出来,砸在她的胸脯上。她挺了挺胸,终于鼓足了勇气,伸手敲了几下门环。
里面应道:“谁呀,进来吧!”
金花迈开双脚,踏进了门槛。踏踏踏,一步紧似一步,往前走去,踏上青石台阶,稍有迟疑,开口道:“孔老爷子,我是金花,我妈叫我来的。”
孔大学问嘻嘻笑道:“你妈?你妈妈是谁?”
金花说:“我妈妈叫蔡玉明,我是蔡玉明的大闺女,名叫金花。”
孔大学问听了,很是高兴。在他看来,这小姑娘说出话来“叭叭叭,叭叭叭”,跟机关枪似的。他天生就喜欢这样的人,不由朝她面前走了几步,说:“你就是金花,金花就是你?”
金花见他并不可怕,胆子也壮了,说:“孔老爷子,我妈叫我跟您学习中药名谱。”
孔大学问放下手里拿着的一摞小卡片,说:“你看,我的条案上,摆满了卡片,上面写的都是中药名字。”
金花心里想:呀,这么多,我啥时候才能学得会呀!
孔大学问看出金花面带难色,于是,慢慢走近她,语速缓慢地说:“姑娘,别怕。也许,换个人教你,真难;我来教,就不难。你信不信?”
金花不语。
孔大学问说:“中国的方块字,就好像人的面孔。初见时,你只记住了名字,见的次数多了,也就认识了。这一堆中草药名,一共九九八十一种。我先把它们的名字告诉你,然后,对号入座。一天重复多次,不认识也认识了,你信不信?”
金花木讷,疑疑惑惑,将信将疑,愣愣地看着孔大学问。
“为了好记,我把这一堆编成顺口溜。”
“顺口溜,啥顺口溜?”
“别忙,还有话呢!中草药,分花、茎、根、果四种。这四种,我分别在红、绿、黄、白的纸上书写。为的是顺口,易念、易背、易记。”
“咋这么难?”
“金花,你听我念念写在红纸片上的这四行字。记住:我每停顿一次,就是一味中草药名。一句三味,四句就是十二味。”
金花心里打开了鼓:这谁记得住?
孔大学问眼睛盯着在条案上摆放整齐的纸片片,抑扬顿挫地朗朗读道:“槐花、桃花、山茶花,梅花、桂花、百合花,红花、葛花、金银花,芫花、菊花、藏红花。这些写在红纸片上的十二味药,都是花类。”
金花想笑,没有笑。
孔大学问说:“顺口吗?”
金花点点头。
“我全都给你念念,就是先让你听听。然后,我再一句一句地教你。念熟了,背熟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号入座。久而久之,药名自然就记住了。”
金花轻声说:“嗯。”
孔大学问清清嗓子,念道:“听好,我念了:荆芥、芫荽、半枝莲,白英、龙葵、苦地胆,水芹、木贼、八仙草,燕麦、泽漆、绞股蓝。这写在绿色纸片上的十二味,都是茎类。”
“什么叫茎类?”
“茎,就是草药的莛,学名茎。”
金花“哦”了一声。
孔大学问继续说:“下面是果实类:川椒、谷芽、香椿子,豇豆、橘皮、覆盆子,鼠李、皂荚、龙葵子,辣椒、番茄、车前子。这些草药名,我都写在了这些黄纸片上。”
“我知道,这回,该说根类了!”
“这丫头,真聪明!听好根类这四句:当归、玄参、八角莲,漏芦、细辛、胡黄连,天冬、木香、龙胆草,白芨、紫苑、千年建。这些药名字,我都写在白纸上。”
金花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谁记得住?”
孔大学问说:“一段一段地记,一段四句。我真不信,一天连四句都记不住!再说,一天两天不行,三天行不行?四天五天总可以了吧!”
金花半日不语。
孔大学问用眼睛在金花的脸上扫了扫,说:“古人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金花,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
金花摇摇头。
孔大学问说:“以后,我会慢慢儿给你讲。今儿要你背的,就是花类的这四句。不要求你会认得字,背下来就行。听好,口传。我说一句,你跟着学一句……”
结果,孔大学问念一句,金花跟着学一句。鹦鹉学舌,周而复始,你不烦,她不恼。
日近黄昏,连残阳都感到有些疲惫,坐在燕山顶上歇息,孔大学问和金花却依然兴趣盎然。
孔大学问终于说:“金花,你试试从头给我背一遍?”
金花的脸,稍稍泛起红晕,还是开口试了试。有些结巴,总而言之,还是背下来了。
孔大学问高兴地说:“好丫头,再给我背一遍!”
金花又从头背了一遍,显然,这一次好多了。
“下一步,就是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什么是对号入座?”
孔大学问把第一行字,摆放整齐,然后说:“孩子,你把第一句给爷爷背背,慢着点儿!”
金花节奏极好地从头背起。
孔大学问伸出长长的手指,一种一种草药名地指点。
金花突然说:“孔爷爷,我明白了。我自己试试,您看对不对?”
这一次,金花口中一面背诵顺口溜,一面伸着手指头点那字。背完了,手指也点到头儿了。她高兴地叫起来:“嗷,嗷——”
孔大学问满意地说:“好孩子,真叫爷爷高兴!你呀,也先别嗷嗷地叫。还有一招儿,爷爷教你。”
金花说:“还有呢?”
孔大学问神秘兮兮地说:“这是一柄杀手锏。到了朱二先生药铺,把他的中草药匣子,完全按照咱们顺口溜的顺序摆放,横着放,每排一首顺口溜,共十二味中草药,摆到最下面,一共七行,八十四个药匣子,富余最后三个,留作它用。”
金花听了,似懂非懂,眯起眼睛想了半晌,好容易弄懂了,想通了。然后,按照孔老爷子的话,把桌子上的红、绿、黄、白四种卡片,完完全全按照顺序调整了一遍。然后,站在条案近前,若有所思,半晌,仿佛突然醒悟,大叫道:“老爷子,孔老爷子,您今儿教的,我会了!”
孔老爷子哈哈大笑道:“金花,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刚刚开始,再说,要学到熟练的程度,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不过,别害怕,先把刚学会的练练。久练久熟,熟能生巧。回家后,好好练习,可别就着饭,都给吃了!哈,哈哈——”
朱二先生药铺在石幢北街路西,门脸不大。从门洞进去,就是一道月亮门,穿过月亮门,是一座小院。小院上房三间,窗明几净。对面是几级台阶,每一级台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花盆。正对月亮门,是一棵干枝梅,虽说腊月已过,依然有几朵梅花零零星星地挂在枝头。
朱太太朝朱二先生点点手,轻声叫道:“他爹,你过来,有话对你说。”
朱二先生正往屋外走,听见老婆子叫他,稍有不悦,可还是扭身回来,问:“咋?”
朱太太说:“进屋里说。”
朱二先生不耐烦地说:“有话说,有……”没有敢往下说,憋在肚子里了。
“说呀,咋憋回去了?”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赶紧说,我到前堂还有事呢!”
“我早听说了,河南村那个叫金花的姑娘,才十六岁,本分人家,来咱们这儿学徒。我先提醒你,凤奇这小子,可不是省油灯!”
“凤奇、凤奇咋了?”
朱太太压低声音说:“小点儿声,凤奇这小子刚满十八,血气方刚,干柴烈火。早了晚了的,盯紧着点儿,可不兴跟人家姑娘动手动脚,传出去寒碜!”
“我当啥事呢,就这破事!”说着,抬脚就往外走。
“好,你听不进去,我可有言在先!”
朱二先生早已迈出二门子,直奔店铺走来。
凤奇正在里里外外地归置,药架子的每个格子上,都有一个小抽屉,小抽屉的迎面,写着中草药的名字,左右九空,上下九行,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只是靠近窗户那边,留下空档,码了一堆坛坛罐罐,极煞风景。
朱二先生迈着方步走进店铺,扫视了一下四周,点点头。当他走近那一堆坛坛罐罐时,说:“凤奇,哪儿都挺好,就是这一大堆,总让人感觉不舒服。其实,这一大堆精致的铁盒、古老的瓷罐,里面装的都是名贵药材,堆在这个犄角旮旯,倒显得是一堆破烂儿!”
凤奇为难地说:“那、那咋办呀?”
朱二先生无可奈何地说:“那咋办?就先这么办吧!”说着,走出了店铺。
凤奇小声地嘟囔:“问我咋办,我能咋办?”
人世间,充满了辩证法。有些事,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事,看着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一天书都没念过,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硬要她在半个月里,认识八十一味中草药,会认会写,点到哪味,就能指出哪味来。难不?说不难,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别人,也许真的难于上青天。可对于金花,好像就没有那么难。难道老天爷就那么不公平,唯独青睐金花姑娘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女孩儿,在不到半个月里,会背几段用中草药编成的顺口溜,会认、会写八十一味中草药的名字。是的,老天爷一丁点儿也不青睐这个可怜的女孩儿。老天爷看到金花这半个月的辛苦与努力了,夜晚漫天的星斗,疲惫得眯上了眼睛;墙上的油灯碗,心疼得流干了泪水。
当妈妈送出来吩咐“处处当心”的时候,金花早已踏上村头小路,迈出了第一步!
就是这样一个乡下女孩儿,夹着一个铺盖卷,单枪匹马,闯荡县城来了。
金花沿着河南村通往县城的路,艰难地行进。刚才还觉得冷风嗖嗖,走不到一半路,就早已汗水津津了。她走着走着,回头望望,村北口的老槐树,老槐树下面那盘碾子,碾子西面那口古井,离她越来越远了。她停下脚步,好好地想一想妈妈,想一想银花、五丫头和成子。在家里时,总嫌妈妈唠叨,总嫌弟弟妹妹们闹腾。此时此刻,她多么想听妈妈的唠叨,多么想银花、五丫头、成子追打她、搂抱她、撕扯她呀!她想回去,回到那个整天介挨妈妈数叨、挨弟弟妹妹捶打的篱笆院,整年介急急匆匆、忙忙活活,累得腰酸腿疼的土窝窝。她的眼睛有些湿润了。她想哭,大哭一场。不知为什么,她似乎骤然清醒了:不能,要是往回走,妈妈不得骂死,不得打死!还指望我为朱家顶门立户!她必须回过头来,脚尖冲着县城的方向,大胆地朝前走,莫回头!
她终于还是战胜了自己,很快进了县城南门,目不斜视地一直向北走,早有人告诉她,绕过石幢,北街路西的灰色门楼,就是朱二先生的中药铺。
金花站在朱二先生中药铺青石阶的下面,望着里面那一字排开的中药匣子,心里想:往后,难道我就在这里干差事了?她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正在这时,凤奇从里面走出来,看着这位乡下妞儿,她不走进,也不离开,光在外面往里瞅,感到怪怪的。可是,他又想,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海去了,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金花走上前来,向凤奇行了一个礼,轻声问道:“小师傅,这里是朱二先生药铺吗?”
凤奇靠近栏柜说:“是呀。”
“我从河南村来,是杨二婶叫我来的。”
“杨二婶,哪个杨二婶?”
金花感到惊慌失措,心里想:难道会有假,让人家当猴耍啦!
凤奇说:“姑娘,别忙,我到里面给你问问。”
金花好像得到了些许安慰,站着等。
一会儿,出来一群人,争先恐后地说:“进来,进来吧,姑娘!”
金花仍在犹犹豫豫,迟疑不肯迈步。
直到大家伙拉的拉,拽的拽,金花才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药铺门洞,穿过月亮门,被推进上屋的木床上。
朱太太拉拉金花的手,嘻嘻笑着说:“路上,冷吧?”
金花说:“咋不见我杨二婶?”
朱二先生说:“她早跟我说了,她河南村的婆婆家,有个姑娘,又有文化,长得又俊,出正月,到我的药铺来帮我。”
“是吗?”
“我们盼呀,盼呀,像盼凉水似的,好容易把你给盼来了!”
朱二先生的一席话,把屋子里的人,都给逗乐了。
可巧,外面有人叫:“有人吗?拿药!”
凤奇颠颠跑出。
朱二先生说:“在我这儿,就是缺个字眼深的。你看,凤奇这小子,看着机灵鬼怪的,驴粪蛋子外面光。急了忙了,顶不上去!”
金花听了,深感担子太重,她真的想说“我更不行”,可话刚来到嘴边,又被噎回去了。
朱太太上下打量打量金花,心里说,这姑娘,心像水晶石一样透亮,看不出一星半点儿有藏着掖着的地方。够高够样儿,就是瘦了点儿。往后,吃得好些,时日一长,肥膘自然会上来。那时候,还得漂亮!
金花傻傻愣愣地站着,伸长耳朵静听大家吩咐,却怎知朱太太的思绪,刚刚从地球的那一面绕回来。
朱太太拉着金花的手说:“来了别忙,先留在我屋里干几天杂事!”
金花说:“奶奶,您屋里能有多少杂事呀?抽空就干了。我还是到前厅干点事吧!”
朱太太说:“这孩子!”
朱二先生也走过来搭言:“金花,你新来乍到,里里外外多走走,都看看,熟悉熟悉。”
金花说:“我从乡下来,干惯了活儿,闲不住!”
朱二先生顺坡下驴,说道:“也好,也好!”
凤奇在外面偷听,当听到朱二先生说“也好也好”时,赶紧轻手轻脚退回药铺,等候金花的到来。
金花进了药铺,站在九九八十一个药匣子跟前,一时眼花缭乱,头脑发晕。这时,她有些动摇,她原本大字不识,经过半个月,要背这么多中草药名字,会认,还得会写。其实,当初并没有觉着有多难,可到了眼下,那黑压压的一片方块字,就像张飞、李逵、包公那些人一张张黑乎乎的脸,一个个“哇呀呀”地叫着,随时朝她扑将过来。她吓得退后几步,险些跌倒。
凤奇见金花愣愣的,呆呆的,心里好生纳闷。上前搭个话吧,怕太冒失;不搭话,又觉失礼。进亦忧,退亦忧,犹豫不决。此刻,一眼看见金花正要跌倒。说时迟,那时快,凤奇飞步向前,迅速伸出一只胳膊,从后面接住。金花不偏不倚,可巧倒在凤奇的肘弯里。
金花急忙站稳,下意识地向四周望望,幸亏没有人看到。她悄悄吐出一口气,胸口“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凤奇讪讪地说:“金花,往后,你就留在药铺,跟我一样,整年介跟这些药匣子打交道。”
金花望望凤奇,没开口。
凤奇说:“整天介在这些药匣子里找草药,抓草药,称草药,包草药。客人来了,人家问东问西;客人走了,咱得客客气气。一天到晚,转转悠悠,出不来,进不去。吃喝拉撒,没个消停时候。四月二十八赶庙会,大街上热热闹闹,人山人海,咱就跟牛犊子一样,在屋里憋着;八月十五元宵节,家家团团圆圆,有说有笑,咱就跟孤雁似的,在旮旯蹲着。唉,真没劲!”
金花听了凤奇的一大堆昏话,觉得这人怪怪的,心里说:“唉,人家是干一行,爱一行。这人,干哪行,烦哪行。就他这种人,就欠饿死!”
凤奇唠叨了半天,本想得到她的同情,却没有,感到很失望,便不再开口。
金花安定一下情绪,这才说:“在这里干活儿,不是挺好的嘛!”一面说,一面找抹布。
凤奇深解其意,赶紧递上。
金花从上到下,从窗台到草药架子,仔仔细细擦了一遍。
凤奇不前不后地跟在金花屁股后面,有时擦擦脸盆,有时涮涮抹布。说讨好,献殷勤?都不像。
就这样,金花一直归置到第三日。
人心是秤,凡是朱二先生药铺里的人,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看得见,心服口服,都得说:金花勤快。
第三天,金花更是摆开了架势,彻底改变草药铺里的陈设。她要按照孔大学问教的,一排十二种中草药排列。这样,从北墙排到南窗,严丝合缝。把那些堆在墙旮旯里盛着名贵草药的坛坛罐罐,搬到顶层。这样一来,那些委屈多年的精致铁盒、古老瓷罐,跃上高位,摆在顶层,突然显得神气起来!
掌灯时分,朱二先生药铺里的人,吃罢了饭,一个个都上炕睡了。金花却累得爬不上炕,湿漉漉的内衣,渐渐变得凉飕飕的。她拨拨油灯碗,趴在高桌上,闭上眼睛,恍恍惚惚,迷迷糊糊……
突然,妈妈搂住她的肩膀,嘴巴贴近她的耳畔说:“孩子,累吗?”
“不累。”
“想妈妈吗?”
“想。”
“不兴想妈妈,好好干。你孔爷爷说,中草药,学问深着呢!要识别出,得靠眼看、手摸、鼻子闻、舌头尝。不练几年苦功,是学不会的!”
“那,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家看妈妈和弟弟妹妹呀?”
“总惦记家,没出息!农村是一个苦坑,咱家就在苦坑里的最深处扑腾。好容易爬出你一个,还想再爬回来呀?你咋这样不懂事!”妈妈急了,向她拍了一巴掌。
金花突然醒了,她迷迷糊糊回头看了看,有个人将手臂搭在她的双肩上。
金花大吃一惊,不由叫道:“咋,咋是你?”
凤奇轻声说:“我是怕你着凉!”
金花说:“怕我着凉?”
凤奇慌了神,急忙把手缩回。
金花说:“我们黄花姑娘,从不这样。”
凤奇喃喃地说:“我是看你忙活了一整天,太累了!”
金花说:“凤奇哥,往后、往后别这样。让人家看见,还咋活,咋有脸见人!”
凤奇像是犯了错的小孩子,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不停地搓弄着一双手,随时等着金花的发落。
自从金花来到朱二先生药铺,好像处处都起了变化,干净了,利落了,窗明几净,锃光瓦亮。以往那些盛着名贵药材的铁盒瓷罐,被堆在犄角旮旯,委屈得要死。如今,把它们请上药架子的最高处,大模大样,神气十足,身价十倍。
最显眼的地方,还不在这些,是来买药人的眼神。在他们看来,朱二先生药铺咋会有个姑娘卖药,况且,那么年轻,那么俊俏。最令人感到稀奇的,金花在寻找草药的时候,完全同旁的伙计不一样,她是毫不犹豫,快捷利索。
一传十,十传百,朱二先生药铺,居然名声在外,不仅来药铺抓药的人络绎不绝,连奔朱二先生看病的人,也日渐增多。
学徒的规矩很严格:一是三年零一节,二是师徒如父子。在学徒期间,只管吃,不管穿。大年三十吃到大钱饺子里的钱,给长辈拜年得到的压岁钱,可以装进口袋。其余,一年到头,分文不见。因此,学徒不如当半伙。当半伙的,虽然活计多,“喂猪打狗挡鸡窝,拿了尿盆算完活”,下贱,地位低,可无论怎么清苦,多少能积攒个仨瓜俩枣,捎回家帮助爹妈过日子。
金花学到点儿本事不假,可一年到头见不到一个子儿,家里丝毫利益也得不到她的。妈妈拉扯着一群孩子,依然受穷。
县城南街有个姓马的瞎子,其实,并不真瞎,左边二五眼,右眼玻璃花。他到红螺寺拜过高师,会算命。年岁大了,再马瞎子马瞎子地叫,有失体面。于是,改叫马半仙,喜欢开玩笑的,也有叫他“马半瞎”的。叫来叫去,文雅多了,便成了“贾半仙”。
其实,贾半仙也并非别人,他就是连汤嘴的亲爹。
四月二十八的庙会,对于顺义,仅次于春节。往东能闹到呼奴山,往西闹到温榆河,南起通州,北至密云。在这个圈圈儿里,四月二十八这天,找不到消停的地方。
顺义人都知道:西街夏连茹京剧唱得好,东街陈皮匠破鞋锥得好,北街朱二先生脉搏切得准,南街马瞎子的命算得准。
树的影,人的名。树越大,树的阴影也就越大。人也一样,名气越大,影响力也就越大。
四月二十八那天,连汤嘴来到县城看爹,说是看爹,实际是逛庙会。
贾半仙眼瞎心不瞎,他凭着一根竹竿,能带女儿走街串巷,到西街戏楼听夏连茹唱《龙凤呈祥》。
“爹,您知道哪个是夏连茹呀?”
“甭瞅我的眼睛迷迷糊糊,耳朵灵。我一听就知道,那唱青衣的就是夏连茹。”
“爹,哪个是青衣呀?”
“最俊俏的小媳妇。”
“知道了,知道了!”
可是,这最俊俏的小媳妇的两只袖子,做得太长了,两只手好容易抖落出来,往下一撂,“噗踏”,又把两只手盖住了。周而复始,看着太费劲,没看头。于是,连汤嘴一次次地催促:“爹,不听这个,没劲,换个地方!”
好好一出戏,听不成了。毫无办法,贾半仙只得拄着竹竿,走出戏楼东门。
刚出门口,就听见嗷嗷的叫声:“出来瞧,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
连汤嘴好奇,拉着爹爹的竹竿,朝那声音寻去。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人,依然嗷嗷地叫道:“出来瞧,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
连汤嘴拉紧爹的手,说:“爹,这是干什么的?”
“拉洋片的。”
“什么是拉洋片的?”
“这个,少问。”
“少问,干嘛少问,凭什么?爹,我非要看看!”
“这孩子,都这么大啦,还叫大人劳神。别老看,看两眼就得!”
看完拉洋片,父女俩又往前走。刚过石幢,就听见踢里踏拉的噪音,连汤嘴嚷道:“不去,不去踢里踏拉的东街,又脏又乱还又黑。臭气烘烘,脏了吧唧,黑了吧唧。快,快换个地方!”
贾半仙说:“待一会儿,踩高跷的就过来了,你听,远处,是不是有声音传过来了?踩高跷,县城里的高跷可有名了,等着看看!”
连汤嘴说:“踩高跷的?看就看看。”
不一会儿,高跷队果然从东边过来了。
“你听,那家伙点儿,越听越像:净光净,净光净,卖了桌子卖板凳,卖了尿盆儿算干净!”
“爹,别瞎说!”
高跷队扭扭搭搭,走三步,退两步,终于走近石幢莲花瓣。
看热闹的人,像潮水般涌来涌去。
高跷队中,有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耷拉鬼”,猫下腰敲着惊堂梆子,故意逼退看客,腾出场子。然后,出人意料地第一个跃上石幢莲花瓣。动作敏捷、干净、利落,博得一片喝彩欢呼声。
接着,扮作老汉、老婆、小伙子、大姑娘的,相继蹦上石幢莲花瓣。绕着圈儿,翻跟斗,打把势,扭秧歌,耍杂技,逗得看客们捧腹大笑,声浪滚滚,此起彼伏……
连汤嘴拽了一下爹,说:“看来看去,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换个地方吧!”
“你咋吃一看二眼观三,啥都想看看!”
“忘了,差点儿忘了。爹,去县城北街朱二先生药铺看看,有个叫金花的姑娘,在那里学徒。”
贾半仙说:“好吧!”
连汤嘴拽着竹竿,弯弯绕,绕弯弯,穿过人群,来到北街朱二先生药铺前,站在青石台阶上,好奇地透过玻璃窗向里看。
整间药铺空空荡荡的,除了一排排码放整齐的药匣子,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连汤嘴说:“爹,里面没人。也是的,街上这么热闹,人家就不兴出去转转?看金花的事,那就下次再说吧!”
贾半仙听了,就坡下驴。
连汤嘴索性连踩高跷的也不想再看,拉着爹,一同往回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