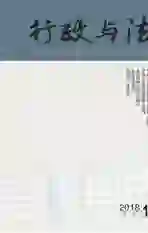论人类基因发现权的不可专利性
2018-11-19葛淼
摘 要:人类基因有伦理性和社会性,对于不涉及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原生基因发现不应授予专利权。对于发现权与发明权的区分,并非只要存在人类劳动就认可其发明专利性质,还应当考虑人类创造性劳动的参与程度。专利权扩张易引发社会负效应,必须考虑其社会效应和权益平衡问题。从知识产权的性质和目的而论,单纯的科学发现不应给予专利权保护,但应考虑在传统专利垄断权以外给予科学发现权利人其他形式的补偿,以达到社会福利和个人利益的相互协调。
关 键 词:人类基因;基因技术;发现权;发明权;不可专利性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10-0108-10
收稿日期:2018-07-20
作者简介:葛淼(1983—),男,安徽合肥人,復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国际法学。
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和排他权。近一个世纪以来,可专利性的主题持续扩张,引发了人们对于专利权扩张正当性的思考,人类基因的可专利性尤其受到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基因专利案件的判决,对界分可专利困境中的发现和发明具有重大参考意义,也有助于我国《专利法》重新确认科学发现权以及建立相应补偿机制。
一、Myriad案引发有关人类基因可专利性的重新思考
基因是自然界客观存在之物,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生物载体,是人类繁衍的关键物质,因此基因有其天然的生物性和伦理性,与具备完全经济属性的传统工业产品(材料成品、机械设备等)有本质区别。基因具备生物性,取自人体,在无介质的状态下直接干预人类的健康、疾病和生命,而后者没有。因此,基因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人类对于自身健康、生存条件的干预程度。不仅如此,基因通常居于生物医药及其产业链的上游区域,对生物制药产业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所以,对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问题直接关系到生物技术产业和医药产业的前景。[1]
美国是全球生物技术发展最快的国家,其高度发达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也是世界各国借鉴和模仿的典范。美国给予基因最宽泛的专利权保护范围:基因并非因其自然产品属性而不具备可专利性,只要有特定、真实、可信的用途,就可以被授予专利,自此美国向基因专利敞开了大门。[2]1996年到2002年,美国涉及生物专利的申请增长了154%。基因专利蜂拥而至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且负面效用凸显,因此,关于人类基因的可专利性问题开始引致关注和反思。历史上,美国法院有诸多相关典型案例的判决,对基因技术的专利性问题给予较为详实的司法解读和阐释。“现今全球知识产权的价值链主要是由美国法院的判决支撑起来的”。[3]作为基因技术研究及立法的后进国家,悉心研究美国的司法案例及关于基因专利问题的文献,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构建和完善以及界定有关基因专利保护范围等均大有裨益。
(一)Myriad案折射基因专利是否体现人类劳动至为关键
201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结的Myriad案释放出来的强烈信号,对全球生物医药技术产业链及世界各国有关基因专利的立法思路和政策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Myriad公司以研究并建立人类基因与特种疾病的关联性为主营业务,其间Myriad公司发现了人体内BRCA1和BRCA2两种基因的精确位置及其序列,而两种基因的突变可以显著增加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患病风险,对此,Myriad开发出诊断检测试剂,用以检测病人的基因是否发生突变,并评估病人罹患癌症的风险。Myriad围绕对基因 BRCA1和BRCA2的发现,申请并获得了大量专利。如果专利合法有效,那么专利权将赋予 Myriad 相应的排他权,即禁止他人破坏连接DNA与人体基因组其他部分的共价键而分离出BRCA1和BRCA2基因,这些专利还赋予Myriad通过合成方式制造BRCA基因的互补 DNA 的排他权。[4]Myriad公司因广泛的专利授权获得在相关癌症诊疗必须的基因检测技术和设备上的排他权,据此要求其他拥有基因诊断实验室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立刻停止向社会提供基因检测服务。Myriad公司长期对市场的垄断以及由此对其他科学家从事继续科研活动产生的阻碍作用遭到公众抵制和批评。2009年5月,分子病理学组织(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AMP)等20个署名原告提起针对美国专利商标局和Myriad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告Myriad公司持有的7个专利的15项权利要求无效。该案历经美国州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及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对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基因技术可专利性问题的判断带来颠覆性影响。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支持原告的观点,裁定Myriad公司15项权利要求全部无效。Myriad公司随即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1年7月,上诉法院部分推翻了一审判决结果。原告又上诉至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作出结论,自然生成的 DNA 片段属于自然产物,不具备专利性,但是互补DNA属于可专利主题。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部分撤销、部分维持。
该案涉及到基因科学技术中的一个概念,即互补DNA和自然DNA。自然DNA是人体内天然存在的DNA片段,未经过任何人工的提取或者纯化手段,保持原生的自然形态和功能。而所谓互补DNA(又称为合成DNA),是科学家通过实验合成的DNA,最大的特征在于互补DNA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提取生成的。显而易见,互补DNA由于经科学实验提取,满足了可专利性的要求。而分离DNA之所以引发分歧则在于分离DNA因其天然存在的属性,更符合是一种科学发现,而不是一种科学发明。
Myriad案内含最高法院对于基因可专利性问题的解读逻辑,天然DNA或者原生性基因存在于自然界中,并不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不足未被发现而否认其先天性质,即使被认识的过程充满了人类的知识运用和创造性劳动,并且确实耗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也只能被视作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互补DNA并非天然存在于自然界中,若非人力干预就不可能出现,因此符合专利法要求的构成条件,可授予专利。应该在自然的物品和人为的发明之间而不是在“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事物之间划一条可专利性的界限”。[5]体内存在的天然基因不能称为可专利的客体,但如果通过人力将基因进行分离或者提取纯化,并且揭示了该基因的特殊用途,该基因可以被授予专利。[6]在Myriad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了自然DNA与互补DNA之间存在的显著不同,承认了后者的可专利性,最终认为它是实验室的技术人员确实制造出的新东西。互补DNA保留了自然DNA的外显子,但与原始DNA绝不相同。因此,互补DNA不是“自然产物”,属于专利法第101条规定的可专利主题。
(二)基因专利持续扩张引发的社会负效应
美国对人类基因的可专利性问题的价值判断和立法权衡长期奉行的是一种绝对性保护,给予专利持有者控制所有其它用途的垄断权,新发现的基因序列用途可以成为后续专利申请的主题,但是这些后续专利属于产品专利的从属专利。[7]美国有“太阳之下,一切人造之物皆可授予专利”的先训。但在生物科学领域,生物类发明往往是自然和人类双重干涉的产物,因而与自然产物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清晰,美国法院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某一种发明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问题。[8]
实际上,由于人类基因专利赋予大型研究机构和商业机构垄断权力,社会福祉方面的负面效应早已凸显。一直持有开放和激进态度的美国也在反思,过宽的基因专利是否实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最终目的,即促进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美国在2007年提出了《遗传研究和可及性法案》(genomic research and accessibility act,GRAA),如果通过,这项法案将核苷酸序列从可专利客体中移除。[9]因专利保护的存在而导致非正向结果确系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缩小基因专利保护范围、对基因专利的权利施以限制、增加科学研究豁免的情形等,已成为美国基因专利立法的大势所趋。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能力的持续纵深,必然有更多的自然界奥秘和禁地被探知,基因发现绝不是人类认知进路的终点。
二、人类基因发现抑或发明之辩识困境
专利法中的发现与发明之辩长期以来即存在。“专利权只授予给发明创造,而不授予给发现,这是专利法的基本原理。”[10]因为发现得到的知识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应该为全体人类免费的获取,对于未知的已存在自然界的现象或物质,发现者对其没有垄断之权利。[11]如何准确区分发现与发明是研究基因技术可专利性的先决问题。一般认为,发现是指已经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是当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得以提高的基础上才逐渐被揭示的事物或方法;发明是指该事物或方法原本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通过人们的智力劳动,利用已经掌握的自然规律创造出的新的事物或方法。[12]但实践中想要对二者进行截然区分并非易事。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曾在na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 corp.v.commissioner of patents一案的判词中表明:准确界定发现与发明其实相当困难。[13]于生物技术领域更彰显判定上的复杂性。生物技术领域是人类认识程度仍然浅显的处女之地,相比较更加具象的物理世界,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对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抽象性,人类智慧的触角可谓刚刚探入广袤深邃的生物科学领域。生物科学领域还是基础研究为王的国度,而基础研究充满偶然性,大量新的科学发现通常在基础研究阶段产生,这些科学发现有些可能会引导科研人员以此为基础再行继续研发,以期在将来实现重大的科学突破。但基础研究往往进程缓慢,研究前景不明朗,即使获得一定成果也不能立刻应用于市场,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商业变现能力并不乐观。最为关键的是基础研究通常是先进工业技术成果的前提,很多大型跨国医药企业将资助基础研究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目的就是寄望于未来获得有形科技成果、授予发明专利、抢占市场先机。如前所述,对人类生命的认识首先是科学发现的過程,如果没有人类对于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劳动,人类业已存在的生命奥秘将永远不会被揭晓。这样的科学发现即使没有产生最终能够进行工业应用的技术成果,无疑也应受人尊重并且获得奖励和回报。
(一)人类创造活动参与程度是区分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应修正并且提升现有的对于基因可专利性门槛的认识,引入“人类创造活动参与程度论”。判别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人类的劳动,而是人类劳动的参与度,是仅仅认识到了客观的自然规律,还是包含有对已认识到的客观规律的改造和创新,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对于自然物质经由原始状态到工业应用状态,是否存在运用科学手段加以重大的改进和修正。换言之,人类的活动对于自然物质或现象的干预,必须达到显著提升了该物质工业实用性的标准,并且这种人类干预活动本身具备足够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造性。“额头流汗”并不是获得专利权的条件。[14]德国学者柯拉认为:“发明是通过技术表现出来的人的精神创造,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且产生一定效果者。”[15]对于基因技术而言,揭示了基因的存在和通过对基因性质机理的认识提取个别有用的基因片段,不可能同日而语。前者只能是一种科学发现,而后者才能构成发明。专利性发明的标准是必须具有新颖独创性并且有应用价值。如果只是发现自然界本已存在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新颖、不显而易见,而且有一定用途,但因发现并非人类的创造,故而不是发明,所以不应该获得专利。[16]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专业性和更加深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即便作为一种科学发现,也不可能是外行人的随意为之,没有经过系统性的专业知识储备,没有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归纳,没有历经长时间的艰苦研究和辛勤开发,即使产生了某种发现也很难说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发现。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恰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发现是否应该被授予专利权保护的问题,因为专利制度的本意是保护由智慧和知识凝结成的智力结果,是对必然性的奖赏,而不是对随意性和偶然性给予褒奖。随意性和偶然性难以维系持久永动的活力,社会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依赖于随意性和偶然性,这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精神相悖。
基因技术的可专利性讨论应当围绕基因作为一种物质或者现象的基本性质、专利制度的旨趣以及基因专利化的社会效果。《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任何人发明或揭示了任何新的、有用的过程、机器、产品、物质的组成,或者任何新的、有用的改进等,都可以获得专利。”以文义解释方法析之,至少没有将科学发现的可专利性一概排除。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专利法有一个重要的、隐含的例外,即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抽象思想不可专利。当今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也规定,对一切领域的发明都应给予法律保护。TRIPS协定第五部分明确规定对于产品或过程都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只要他们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能够进行工业上的应用。相比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IPO),TRIPS协定已经不包括科学发现权及过于宽泛的“一切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专利制度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充分尊重人类的创造性劳动的过程及结果,不仅反映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律制度中,在全球知识产权法律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下,也充分彰显于有关的国际性知识产权法律文件中。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关涉到人类的创造活动并且实现了生产效率提高和技术水平进步,无论是有形的成果还是无形的方法,都应以给予专利权保护为原则,专利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照此看来,似乎基因的可专利性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其实不然,对该问题的最终认识还应回归于基因物质的本身特性以及分析基因可专利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上来。首先是对基因物质的定性,基因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物质,是附带人类遗传信息的载体,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粒子。人类认识生命如何起源及演进就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DNA双螺旋模型才为科学家研究发现。由此人类开始了对生命本源的全新探索,科学家们也持续发现着那些对人类的疾病、健康、衰老、死亡至关重要的基因的存在,生物医疗技术因此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外生性的物理疗法开始让位于内生性的基因替代疗法,通过对可能引起人体病变的致病基因的预测和替换,人们极有可能彻底攻克那些过去被认为不可治疗的绝症。
基因技术的巨大潜力当然不会被束之高阁,科研机构和生物医药公司为此展开合作,后者向前者提供科研资金和设备,资助前者进行研发,一旦技术转化为成果,不仅意味着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更会给投资者带来高额的经济回报。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为了巩固这种可期待利益,将基因技术及成果专利化以此获得垄断利益,无疑是最有效率和最有保障的措施。在发现基因的过程中,研究者实施了创造性的劳动,充分体现了知识和智慧的光芒;生物医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也为此支付了研究开发成本,期望从未来的专利权保护中获取回报。但基因作为一种自然物质或者现象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基因物质的存在及其机理的发现,最具意义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基于对天然存在的人类基因的充分认识,可以预见到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至于人类可以参透健康和疾病的秘密,让人类远离遗传性病症的困扰,实现人类生命健康领域的重大福利。基因的价值是前置性的,如果基因在被发现的阶段已经被授予排他性的专利权保护,正如Myriad案所体现的,专利权人的垄断行为必然损害后续的研发活动,这将意味着基因技术的后发性价值也是最大价值——社会意义的完全落空。
(二)基因技术的社会权益衡平分析
世界上具有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国家都确认,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天赋人权,相对于生命权、财产权等人类基本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派生权利和次生权利。因为人类一切知识应为公共之財富,本无对其给予特别保护或经济特权之必要,但是,为了鼓励发明创造,期望技术的进步,从制度导向上给予发明人一定时期的垄断特权,作为弥补研究成本并获必要物质回报之保障。对个人给予知识产权的专有保护,最终目的是构建一种激励机制,促进产生更多创新发明。[17]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赋予其排他性的独占权,目的在于提供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创新,从而促进国家产业的发展。[18]因为发现得到的知识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应该为全体人类免费的获取,对于未知的已存在自然界的现象或物质,发现者对其没有垄断之权利。[19]不难看出,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知识产权法天然具备的法社会属性,因为追求实现公共利益是任何社会规范内含公平正义之价值取向的当然体现。尽管对于基因专利包括哈佛、耶鲁大学或者诸多生物医药业巨头们都在加快申请获得基因专利的节奏和步伐,专利权要求几乎覆盖了人类20%的基因,但许多权利人并没有积极实施专利权带来的排他性权利。[20]而在Myriad案中,Myriad公司获专利权后,借其垄断优势排除其他机构及科研人员在此基础上继续研发,并且收取高额的检测费用,此举不仅导致基因技术放缓,阻碍继续取得重大突破的步伐,而且造成技术进步的最大社会效益缺失,那就是惠及人类社会之公共福利。授予基因专利严重妨碍了基因诊断的开展,不但个体患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公共健康也终将受到损害。[21]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基因类专利的合法化可能会阻碍基因类科研,基因类专利授予及相应的垄断已经在减少基因类知识的获得。如果不使基因类专利合法化,人类对基因的了解及有关知识会更深入。[22]这也将导致科学家从事一些阻碍较少、不太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观点进一步认为,研究文化也将因此改变,基因专利迫使科学家不断研究专利地图,从事非生产性工作,进而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23]在评价有关基因专利的存在对相关遗传检测影响的研究中显示,有25%的检测机构由于担心专利保护而终止遗传检测,53%的实验室由于相同原因转而花费更大成本研发新的检测手段。[24]近年来,Myriad公司被民间组织及公众批评并最终诉至法院,与其滥用专利权带来的垄断地位有重大关系。在专利权人的私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永恒的主题。“专利制度需要在发明者的利益和一般公众的利益之间达成平衡。”[25]TRIPS协议第一部分“一般规定与基本原则”中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有助于促进技术的革新和技术转让与传播,使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互相受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增长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26]我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吴汉东教授始终坚持利益平衡原则为现代知识产权法基本精神的观点。[27]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两者的平衡遭遇维系困境而必须进行孰者价值优先的选择时,公共利益必须得到优先考虑,私权益让位于公权益是唯一的立法选择。人类财产制度的历史显示,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自所有权诞生那天起就存在。因为个人是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赋予个人对财产所有权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财产,因而有利于整个社会。[28]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宗旨不仅在于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者,更重要的是在于保护社会公众参加社会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产生的利益权利,在于通过促进科技的创新与应用以实现全社会福利的增长。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应该享有比知识产权更优先的保护。[29]因此,可专利性问题还必须结合相关社会效应分析。基因技术的研究涉及全体人类,技术成果的实施也将普惠地适用所有人。美国司法部在Myriad案的法律意见中指出,授予人类基因片断专利与否是一个关乎国家的经济、医疗科学及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30]生物技术非常复杂,一项科研成果的产出要经历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基因技术的发展呈单向性而非扩散性的特征,也造成了基因技术彼此替代的可能性很小,技术更迭的频次较慢,因此,相关技术一旦被专利化,给专利权人带来的垄断利益会非常惊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远非其他领域的技术可比拟。基因技术的每一个突破都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基本生物属性和生存条件,相比较于农业、基建等传统产业,基因技术的变革效应会非常突出,且对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基因技术并不是在改变人类的外部条件,而是在改变人类自身。基因技术的每一次发展,无论其产生怎样的后果,人类社会都将作为无差别的整体共同承担或福利或毁灭的局面。同时,生物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基本遵循渐进式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呈线性状态,新发现依赖于前次科学发现的基础和研究成果,技术进步的周期是稳定的、可预期的,不太可能出现跨越式的科学进步,比较符合人类认知能力累进的规律。
(三)基因专利的滥用可能阻碍技术的继续创新
基于上述,目前基因专利的现实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困境,如果单纯的基因发现具备可专利性,那么一项新的科学研究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也即前一次的科学成果很可能掌握在不同的专利权人手中。新的研究者如果继续当前的研究,必须分别取得不同的专利权人的许可,这种专利权许可的碎片化将极大地延缓基因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速度,在申请不同的专利权人许可的过程中将耗费无数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有学者也将其称为“专利丛林”,造成搜索潜在的相关专利、查看每项专利包含的权利要求书,以及评估侵权风险和许可需求已变得无法实现。[31]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研究机构,或者有意对研究活动提供资金的市场主体来说,都只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吓阻效应。
基因技术专利化之所以受到争议,也有对大型生物科技企业垄断产业链的担忧。事实上,这种垄断的威慑效应早已显现并不断威胁着人类共同福利目标的实现。Myriad公司获得基因技术相关专利权多年,民间组织才正式向法院起诉,原因并不在于基因技术本身的专利化损害了社会福利,而是由于Myriad公司获得专利权后对该专利权的滥用使专利的垄断效应无限负面化,本来价格还算低廉的基因检测被提高,造成大量急需进行检测的病人由于无力支付检测费用而放弃治疗。技术的进步本应实现人类的福祉,本应帮助实现公众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但Myriad公司在追逐经济利益时完全忽略了社会责任。创新积累理论认为,专利权虽然重要,但是不能被授予无限制的排他性权利。[32]对于事关人类健康、生存和命运的基因技术,即使暂时搁置可专利性的争论,基因技术专利的排他权和垄断权也不应完全放任。
三、基因技术发现权机制分析
考虑到基因技术发展的现状以及生物科学领域研究的特殊规律,确有必要着重考虑生物技术领域发现权的保护和补偿问题。目前,世界上明确给予发现权立法保护的国家并不多,科学发现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始于前苏联。1947年3月14日,前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第一次规定了发现权登记。[33]有关科学发现权的最早国际立法是国际联盟专家委员会起草的保护科学产权国际公约草案。公约草案前言提出,科学发现者应分享企业由于使用其科学发现而得到的物质利益。[34]但由于争议颇多,这一公约草案并未正式生效。
(一)發现权具有客观利益性应得到法律保护
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秉持的是这样的逻辑,保护私权并非根本目的,激励创新从而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实现整体福利才是题中之义。因此,必须考虑对获得发明创造的私主体给予必要的补偿和物质奖励,至少应涵盖其在研发过程中支付的成本和一定的利润,否则将无人会在失去制度激励的情况下耗费精力和财力进行研发,知识产权制度的要旨必然落空。对于基因技术领域而言,科学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物技术的每一次向前发展都凝结着科学家的汗水和心血,困难重重,且成本巨大。如果按照现有的发明可专利、发现不可专利的专利权授予原则,基因技术的发现毫无激励可言。科学发现是科学发明的前提,正常情况下,发现的缺失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基因技术领域的发明,基因技术的持续进步将成为空谈。但是,如果授予基因技术发现人以专利权,专利权固有的垄断性和许可性又可能被专利权人滥用。或许解决问题的最终思路在于跃出“专利=垄断、非专利=公地”的传统思维窠臼,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总体框架下探寻一种新的模式,既给予发现权人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又不至于形成垄断导致权力滥用,损害整体技术的进步。科学发现权难以在现代专利制度体系下寻找到可专利性的正当理由,完全排除科学发现权的专有性将其变成自由出入的公地又可能损害研究者积极性,不利于鼓励基础研究,最终仍将损害社会的整体技术进步。为科学发现权设置独特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权利行使模式,或可成为有意义的解决之道:一是承认科学发现权的独立权能。发现乃发明之母,[35]科学发现权客观存在,没有科学发现,就不可能有科技进步,发现一定是任何有形发明成果的前提。在如今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可以分为发现、发明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三个层次。[36]科学发现凝结了人类知识的运用和智慧的创造,是人类对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系统认识。但必须明确,这里的科学发现不是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发现,而是具备科研价值和工业实用性,能够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发现,是可以被反复论证和有效传播的发现,此意义上的科学发现权是一种实在的权利。二是科学发现权具有不可专利性。发现权人不能像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那样取得垄断地位,因为保护发现权的出发点就是鼓励人们发现“未知”,从而为发明创造条件,赋予发现权人以垄断地位无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37]科学发现权不能被专利化,理由在于科学发现是后续研发及最终发明成果的前提,科学发现权被专利化将迫使后续的研发者必须征得发现权人的同意,否则将无法继续从事研究活动。如果最终的科学发明成果无法诞生,那么授予科学发现权以专利授权毫无意义。有学者分析认为,在某一技术领域,倘若各项技术由太多的厂商分别拥有,则将导致该领域的技术合作无法完成。这好比在原来的公用草场上,牧羊人为了界定产权在自己的土地上圈上篱笆,反而阻碍了大规模的机械耕作。[38]正是因为科学发现与科学发明存在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授予科学发现权以专利权即显非理性。
(二)发现权人得以相应补偿是现代价值论的要求
科学发现权具备价值性。在现代商品社会语境下,价值性就是对其他社会主体的效用并可换算为一般等价物的内在属性。科学发现经后续研发有可能产出有形的发明成果,对于该有形发明成果授予专利权具备完全的正当性,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专利三性法定要件,专利权人可以凭借专利权的排他性和垄断性获得经济利益,此时,如果不承认在先的科学发现权具备价值性,明显对发现人显失公允。尽管专利权人利用科学发现时无需经过发现人许可,亦不支付对价,但在后期以专利权获得经济利益后则应对发现人进行经济补偿。在发现可专利的场景下,发现人的经济利益是前置的,在发现不可专利的场景下,发现人的经济利益是后置的。尽管发现权的客体是自然界业已存在的事务、规律或者现象,但这种发现毫无疑问不同于一般发现,是具备相应条件才能达成的。此外,先作出科学发现的科学工作者与后作出科学发现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这时间差在科学领域内就是一种时间价值,也是一种财富。[39]因此,发现权人应当获得相应的报偿,这也符合洛克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当然也可考虑构建鼓励第三方购买以建立科学发现的机制。科学发现池意指多个科学发现的汇集。大型生物医药企业与科研机构或者大学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由前者向后者提供资金帮助,即使后者的研究活动没有具体产出,没有最终能够形成专利产品,但研发活动中形成的科学发现权应归于资助机构所有。以国家财政设置的基金也可购买科学发现权,通过向发现权人支付费用实现激励研究人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继续从事科研活动,并且无需担心自身科研活动有可能最终无法形成包含有可专利产品的成果,财政基金则以公开询价的方式向社会主体转让科学发现权,实现公共资金回转,社会主体则可有偿获取科学发现,再行研发获得有形的专利产品。此过程中,财政基金充当了做市者的角色,通过公共支付方式先期补偿科学发现人的研发成本,使发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避免了科学发现人因利益实现滞后而挫伤研究的积极性。
发明可专利,发现不可专利,是迄今仍然适用的专利权授予准则。人类基因原则上是不可专利的,但基因发现权应当受到保护。发现权不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而是一种利益补偿权,相比较专利权其具有鲜明限制性的权能。专利权的扩张必将于未来产生更多的可专利性困境,因此要构建统一的发现与发明的界分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应针对不同的拟专利性主题,在分析本身性质和社会效应后,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保护,毕竟专利权与国家产业政策相关,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利制度。
【参考文献】
[1]Andrew W.Torrance.Patenting Human Evolution[J].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 Review,2008,56.
[2]Byran Nese.Bilski on Biotech:The Potential for Limi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ene Patents[J].California Western Law Review,2009,46.
[3]王岩.知识产权资产——从法律到经济的枢纽概念[J].知识产权,2013,(07).
[4]宋建宝.DNA可专利性问题在美国的新进展——以介评美国Myriad案为中心[J].中国基础科学·管理论坛,2014,(05).
[5]吕宪栋,徐磊.基因专利保护法律问题探悉[J].现代商业,2007,(30).
[6]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Primer:Genome and Genetic Research[J].Patent Protection,and 21st Century Medicine,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116.
[7]李轩.基因序列专利保护范围的界定——瑞士专利法修正案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知识产权,2006,(06).
[8]赵雷.美国2011年专利法第一案Myriad案评——人类基因可专利性的再思考[J].知识产权,2012,(06).
[9][12]曹丽荣.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及其限制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5.
[10]何怀文.“发现”与“发明”的重新界分[J].知识产权,2013,(09).
[11]Nuno Pires de Carvalho.The Problem of Gene Patents[J].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2004,3.
[13]See Lisa Taliadoros&Anthony; Muratore,Patenting and Ownership of Genes and Life Forms—Australia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yer,March 2000,p119.
[14]佘力焓.从自然界取得标的物可专利性的判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Myriad案”判决评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
[15](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M].宋永林,魏启学等译.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
[16]陈少英,蔡达莉.试论基因的专利保护问题[J].科技与法律,2002,(12).
[17]Gaia Bernstein,In the shadow of Innovation,Cardozo Law Review,2010.
[18]张平.论知识产权制度的“产业政策原则”[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19]Nuno Pires de Carvalho,The Problem of Gene Patents,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2004,3.
[20]REICA L.ANDERSON,finding a “fit”:gene patents and innovation policy,hastings science&technology; law journal,2012.
[21]See Sam K ean, The H um an G enom e (Patent) Project, Science, Feb. 2011, 530-531, available at http://www.sciencem ag.org/content/331/6017/530.
[22]See U.S. Dept. of H ealth & H um an Serv.,Gene Patents and Licensing Practices and Their Im pact on Patient Access to Genetic Tests (2010),http://oba.od.nih.gov/oba/SACGH S/ reports/SACGH S patents report 2010.pdf.
[23]肇旭.Myriad案與基因专利的未来[J].河北法学,2014,(01).
[24]Cho Mk,Illangasekare S,Weaver MA,Leonard DG,Merz JF,Effects of Patents and Licenses on the Provision of Clinical Genetic Testing,Services,J Mol Diagn,2003.
[25]Steven B. Garland and Jerem E.W ant:The Canadian Patent System: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The Rights of Public and The Patentee,1994.
[26]刘颖,吕国民.国际私法资料选编[M].中信出版社,2004.
[27]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8]高富平.物权法原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9]付霞.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博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应然发展趋势[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02).
[30]See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Neither Party at 1, Ass'n for M olecular Pathology v.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653 F.3d 1329 (Fed.Cir. 2011) (No. 2010-1406), 2010 W L 4853320 at 1.
[31]马大明,杜晓君,宋宝全,罗猷韬.专利丛林问题研究——产生与发展、经济影响及度量[J].产业经济评论,2012,(03).
[32]林秀芹.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专利制度的利弊——兼谈我国专利法的修订[J].现代法学,2004,(04).
[33](苏)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苏联民法(下)[M].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译.法律出版社,1986.512.
[34]周忠海,阎建国.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大全[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35]郭成安.浅议发明与发现[J].发明与革新,2000,(12).
[36]苏建军.研究所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机制探索[J].中国科技博览,2015,(26).
[37]童全康.发现权之法理解析[J].法制与社会,2012,(12).
[38]沈晗,徐懷伏.药品专利的博弈分析——从“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J].上海医药,2008,(07).
[39]高映.论科学发现权之知识产权属性的合理性[J].法学杂志,2009,(02).
(责任编辑:王秀艳)
On the Patentability of the Rights of Discovery of Human Genes
Ge Miao
Abstract:The human gene has its particularity.It can not be judged by the standard of the general patentable object.It also needs to be evalu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ocial effect.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ght to discovery and the right to invention is not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the invention patent as long as there is human labor,and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of human labor should be considered.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should not give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tent right, but should consider other forms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the right holder outside the monopoly of the traditional patent.
Key words:gene technology;right of discovery;right of invention;non-paten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