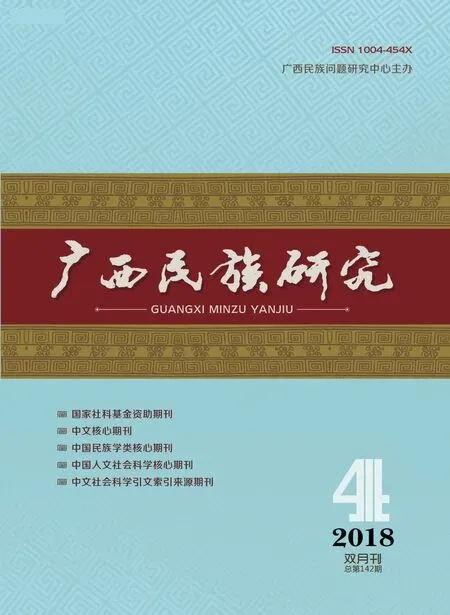花山岩画与蚂 节:大河流域壮族稻作文化的表征
——花山岩画与“蚂 节”比较研究论文之一
2018-11-19何永艳
何永艳
从花山岩画“蛙人”原型图式来看,红水河流域壮族蚂 节是与花山岩画联系最为紧密、最具可比性的活态壮族民族文化事象。2018年2月笔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吾隘镇那地村“蚂节”进行了田野调查,结合三年来对花山岩画的研究与调查,笔者认为虽然不能断定花山岩画与红水河流域壮族“蚂 节”之间具有继承、传承关系,但是可以断定二者之间的确存在诸多的相似点、重合点及相通之处。对二者进行关联比较,发现“蚂 节”与花山岩画最确凿的核心关联是“蛙”,它是“蚂节”的主要祭祀对象,也是花山岩画核心图式“蛙人”的原型。“蛙”是这两大文化事象共同的、核心的意象,是壮族稻作文明制度性、物质性、观念性文化层面的核心载体、精神内核和动力表征。笔者认为从这一关键点入手进行花山岩画与蚂 节的比较研究,从活态的“蚂节”侧面反观花山岩画,揭示二者在经济基础、生计方式上的深刻联系,在文化比较中窥探花山岩画的隐秘内涵,挖掘其存活在壮族文化中的文化潜流,具有重要意义。
一、花山岩画是左江流域稻作文明的表征
花山岩画生成的总根源在于壮族地区原始经济和社会形态,花山岩画的产生必然以一定的生业模式为依托,“那”经济是壮族先民创作岩画的经济生境和生存依托。
(一)左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壮族是历史悠久的农业民族,壮族地区原始农业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在经历过漫长的渔猎采集经济以后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步过渡到原始农业时代,甑皮岩时期壮族先民已会用磨棒加工稻米,大石铲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广西许多地区在距今五千年前,已经是成熟的稻作农业区。壮族先民开垦骆田“麓那”,“从潮水上下”,“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据‘那’([na2]指水田)而作, 依‘那’而居, 赖‘那’而食, 靠‘那’而穿, 因‘那’而乐, 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及‘那文化’体系”[1]。
农业专家证实广西壮族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产区之一,广西自古分布有野生稻,20℃左右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平均降水量、全年无霜雪的季风气候等条件适于野生稻的生长发育,广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稻作农业,距今至少有着10000年以上的历史,“广西境内的早期稻谷种植比河姆渡早2400—3000年,比云南目前最早的白羊村遗址早5000年左右”[2],康德尔等外国专家认为水稻是从岭南传到印度,而后传到欧洲和非洲的。甄皮岩等遗址还出土了石杵、磨棒、石锤和石磨盘等稻谷加工工具,桂北资源县和桂西那坡县都发现了炭化稻的存在,亦可证。在《稻作农业史》一书中,作者认为桂南大石铲就是骆越先民植根于稻作农业的特殊文化形式,“迄今,在广西的42个县、市发现了石铲遗存约145处,以南部地区,尤其是左江与右江汇合的三角地带,分布最为密集,左江流域的龙州、宁明、扶绥、崇左、大新、南宁及左江、右江交汇处的隆安等市、县境都有发现”[3],除了广西外,广东、海南、越南等地都有大石铲分布,以广西最多,“大石铲是源于古骆越民族稻作农业的特殊的文化形式,而这种文化是以邕江及其上游的左右江流域为中心向四周传播的……这一中心地区可能就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文明的中心地区之一”[4]88。学者们认为大石铲是稻作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进步的标志,是为适应稻耕发明的稻作农具,后来发展成为稻作祭祀礼器。除了大石铲文化遗存外,分布广泛的“那”地名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活化石,“那”字地名“分布地域连成一片,北界是云南宣威的那乐冲,北纬26度;南界是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北纬16度;东界是广东珠海的那洲,东经113.5度;西界是缅甸掸邦的那龙,东经97.5度。这些地名的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度至24度,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就广西而言,70%以上集中在左、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易于稻作。[5]梁庭望也认为:“左江文化区,包括崇左、宁明、凭祥、龙州、大新、天等、德保、靖西、那坡等县,地处左江流域,为丘陵和台地,土地肥美,气候炎热,雨量充沛,为壮族重要的水稻产区,与邕南一样,一年可以两熟到三熟”。[6]22
可见,左江流域是西瓯骆越民族原始居民的家园和发祥地,也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左江流域稻作农业生产为壮族先民的生活提供了充实的物质生活资料。稻作文化是该地区主要的文化特质。
(二)花山岩画是“那”文化的结晶
左江花山岩画古朴粗犷、气势磅礴、规模庞大,运用剪影平涂、概括、写实、夸张、变形等手法将举手顿足的“蹲踞式”人像描绘得对称均衡、有力传神。许多学者认为, 左江花山岩画图像表现的就是壮族先民模拟蛙图腾形体和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诞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壮族最主要的生计模式——稻作农业,是“那”文化的艺术结晶。
壮族神话叙述,雷公为老大,蛟龙为妹妹,雷兄与妹妹私通,生了怪胎蛙神,标志壮族先民从渔猎经济走向稻作经济,稻作经济占主导地位后蛙神也就上升为民族守护神,于是创造了绵延数百里的蛙神供奉之所——花山岩画。“壮人以青蛙为图腾,这是稻作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壮族祖先所铸铜鼓上有单蛙、群蛙、累蹲蛙等立雕,蛙皮都有十字交叉的稻穗纹,这一画龙点睛之笔充分体现了蛙图腾的稻作民族早期标志的性质”。[6]131
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壮族先民在农业中对水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左江流域,旱季缺水对于水稻种植影响很大,于是人们只好求助神灵进行求雨,在古骆越人的神话传说中有《特康射日》等神话表达了对太阳的恐惧,当与干旱有关,这是许多学者认为花山岩画与壮族稻作农业相关的结点所在,水稻—雨水—青蛙—祈雨—祭祀—舞蹈,从花山岩画引发出的系列文化现象的根源正在于壮族人民的主要生计稻作以及稻作文明生发出的“那文化”。
稻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壮族先民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花山岩画艺术风格的形成,简练平涂的绘画方式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岩画绘制方式,统一的赭红色是作用广、意义深的时代色彩,以“那”文化为核心的稻作文化使得左江花山岩画彰显出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模拟蛙人的统一的舞姿正是对稻作图腾——青蛙的模拟和崇拜的表现,造型丰富的人物头饰正是骆越先民在稻作文化基础之上的服饰文化的表现。“花山崖壁画是壮族祖先祭祀蛙神的圣地,它寄托了稻作民族对农作物丰收的强烈愿望,花山崖壁画是原始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分化初期的祭祀图,也是壮族社会分化初期的生动写照,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已经有了不同的地位和财富,但小人物仍还围绕着大人物,祭司扮成的蛙神向他欢呼,彼此亲切,尚不严重对立,整个画面活泼生趣,然而人体却是鬼影式的透视图,平涂法显示出冷峻、严峻、划一、不可一世的奴隶制传统画风,可以说是家长奴隶制初期的形态,崖画还描绘了当时的蛙形舞姿,是一种群体性质酬神舞,铜鼓及铜鼓棺上打扮成鸟的图像的羽人,头上羽翎迎风飞舞,裙裾飘逸,体态翩翩,舞姿优美动人。”[6]56
与内蒙古岩画、贺兰山岩画、新疆岩画以狩猎、放牧等动物主题为主不同,骆越先民进入稻作农业阶段后岩画主题已经从动物世界过渡到人的世界,“左江崖壁画以大量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当时重大的社会活动,这一现象无不充分反映了当时艺术已由客体的动物描绘转向主体自我表现——即对人自身肯定的新时代的风尚和精神”[7]388。
(三)左江岩画是壮族稻作文明的图像化总括和表征
陈嘉在《广西左江岩画与稻作文化》一文中认为左江岩画与石铲遗存具有分布地域上的一致性、发展时间上的衔接性和族群的同一性,考古学家杨清平也认为左江岩画对大石铲有继承和发展,因此,左江岩画是骆越族群以大石铲文化为基础,在大石铲文化结束后的稻作祭祀文化一脉相承的延续,“桂南石铲遗存与左江岩画,维系着骆越稻作文化的传统,是稻作祭祀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战国时期的左江骆越人不仅延续着先民的稻作农业, 同时也传承着先民稻作祭祀文化”[3]。黄成贤在《壮族先民的雷神崇拜——左江流域崖壁画性质初探》一文中认为花山岩画是壮族雷神崇拜的表现,梁庭望在《花山崖壁画——祭祀蛙神的圣地》一文中将花山岩画定性为壮族祭祀蛙神的圣地,潘其旭在《花山崖壁画——图腾入社仪式的艺术再现和演化》一文中认为花山岩画是壮族图腾入社仪式的再现,另有壮族的族徽、方国的门神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从根源上看“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他的心理所决定的,他的心理是由他的境况所造成的,而他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他的生产关系制约的”[8]350,因此,归根结底左江岩画的蛙人图像即是壮族稻作文明的表征,所表达的雷神、蛙神、雨水、丰产等信仰元素都是以稻作生产为基础的客观生存所需的稻作祭祀文化,左江岩画上交媾图像、孕妇和带生殖器的男性图像都是将怀孕生殖与稻作生产联系的巫术行为,鸟图像、羽人图像等也是基于骆越鸟田、饰羽而舞祈求稻作生产的意图,供奉牺牲、船图像等也是祈求稻作丰产,甚至花山岩画上头戴面具的蛙人像(傩神)也是稻神的象征。类似的稻作文化事象还有陇峒节“求务”、稻谷收割前“跳岭头”等,都是骆越稻作文化的产物,目的是祭祀稻神、以舞娱神、求得丰收,左江岩画是这一系列的稻作丰产文化的图像化总括和表征。
放眼世界,与同样具有稻作文明积淀的同根生的泰族也有岩画,而且其岩画与壮族左江花山岩画有相似性,差异性也很明显。覃圣敏主编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一卷)》一书中,作者对壮泰两族的历史地理、种族特征、文化等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都以稻作生产为生计基础,地理环境方面也有相似处,在岩画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泰国岩画分布在北部普潘山脉和碧差汶山脉的崖壁上,以湄公河沿岸最密集,泰国岩画也以人物图像为主,也主要以赤铁矿加动物胶为颜料红色、赭红色绘成,选择上凸下凹的岩厦作画,表现舞蹈、仪式、游行等现实生活场景,壮泰两族的崖壁画相似处“表现了当时东南亚人们的日常生活、仪式活动和各种风俗习惯,不同的只是人们的种族或民族不同而已,当然这些都取决于地理位置、生活环境和地理状况的不同”[9]648。可见,壮族花山岩画与泰族岩画相似处是类似的稻作生产基础和日常生活方式使然,差异则是环境、族群等的本质差别。
二、蚂 节是红水河流域稻作文明的表征
“节日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10]1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笔者在对那地村“蚂 节”动态仪式过程和静态道具物品参与观察中发现,“蚂节”民俗文化的物体、行为和事件整体传达着壮族稻作文化的象征意义,而当地壮族人民 “蚂 节”文化意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对稻作生长与青蛙习性的良性共生正确认识与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的,是稻作文明的文化表征,彰显了百越“那”文化圈内稻作文明的多姿多彩以及当地壮族人民奇特卓越的生态智慧。
(一)红水河流域属于壮侗语族“那”文化圈
吾隘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下辖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乡镇,“吾隘镇属亚热带季风区,年均气温18.1℃,年降雨量为2500毫米。全镇有耕地面积15783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999亩,林地面积20.8万亩,荒山荒坡650亩”[11]。吾隘镇位于“红水河”中游东侧,壮族人口达80%以上,除了马帮五尺驿道外,红水河水路成为当地在没有公路之前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那地村是红水河沿岸至今仍完整保留着“蚂 节”民俗文化的村落之一,属于壮侗语族“那”文化圈,与镇政府相距16公里,地处群山环绕的盆地之中,四周有同贡村、杨州村和纳湾村等村庄围绕。该村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甘蔗、油菜,兼种植板栗、黄腊李、蚕桑等经济作物。村民李元文说他们村附近的山上以前种着很多板栗,后来才开始种植桑树养蚕的。那地村的主要生计方式是水稻,那地村水资源丰富,有一条从红水河分流出来的小河穿村而过。该村水稻种植一年一熟,水稻收获以后会种植油菜花,“蚂节”举办的时间正是片片金黄油菜花灿烂盛开的时节,小河潺潺、青山环绕、美不胜收,“村落面向田峒,房屋掩隐在绿树清竹丛中,溪流从村前流过,呈现出一派典型的依‘那’而居,据‘那’而作,以‘那’为食的壮乡田园景象,具有壮族先民的‘那’文化特色”[12]11。
(二)那地“蚂 节”蕴含丰富的稻作文化内涵
在那地村蚂 节上,笔者还观察到了富有特色的壮族服饰文化和富于特色的蚂 道具,表演耙田舞的村民身穿蓑衣、头戴斗笠,赤脚,裤腿高低不齐,与农田耕夫无异;跳田间舞的妇女们,头戴有黄色流苏的头巾,身穿民族服饰,头巾上的流苏随着播种、薅秧等动作整齐地摆动,充满动态的美感和生活气息;表演蚂 舞的蚂 仔们穿着类似青蛙皮的衣服,形态动作模拟青蛙,生机盎然、活泼可爱,天峨等地的蚂装扮则有不同,有的以墨汁在上身、后背、脸庞及小腿描画出蚂 纹样,再配以三角头巾,独具特色;在天峨等地蚂节中还会出现头戴面具,身穿破衣烂衫的“卜娅”,此人为秘密选定,在隐蔽处装扮,在会场中维持秩序、震慑妖魔、驱逐鬼怪,保护蚂 魂魄,之后又悄然离去,充满了神秘色彩,据说扮演此角色者可积德消灾。
(三)那地村蚂 节蛙崇拜具有稻作文化根源
“蛙是两栖动物,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天然的游泳能手,在陆地上跳跃敏捷,是技巧专家。蛙又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是春雨最灵验的预报员。”[14]蛙崇拜并非壮族所独有,纳西族、普米族、彝族、黎族等都有蛙崇拜遗风,纳西族妇女的羊皮披肩上有蛙图案,黎族妇女筒裙上有青蛙纹饰,普米族称蟾蜍为“波底阿扣”(舅舅),彝族长诗《勒俄特依》中将蛙与人并列分类;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印第安人和北美也有蛙崇拜习俗,弗雷泽在《金枝》中记录了印第安人将蛙视为雨水的主人以巫术扮演的习俗,列维·斯特劳斯在《嫉妒的制陶女》中记录了北美关于蛙与月亮的神话,北美人认为月亮中的斑点就是蛙贴在月亮身上而来的。
众多族群对青蛙崇拜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人自身的生产:生殖,二是物的生产:雨水(气候)。仰韶、庙底沟文化遗址都有数量众多的蛙纹彩陶,四川纳西族供奉的生殖女神“巴丁拉木”,即为青蛙,壮族神话《祭青蛙》[15]55记录:雷王的儿子青蛙下来玩,它说它可以去犁田。谁知它到田里专门捉虫吃,没有去犁田。人们恼火了,就用开水把青蛙泼死了。天上的雷王知道了,就再也不下雨了。布洛陀让人们祭奠青蛙给雷王赔礼。于是人们就祭奠青蛙。后来青蛙死而复生,但它上不了天了,不过,只要它一喊叫,天上的雷王听见,就一定降下雨来,避免了赤地千里、水田干涸、溪河断流的悲惨境地。从此以后,青蛙在人间便成为人们的朋友。有时天旱了,人们就要祭青蛙,唱“蚂拐歌”。武鸣县壮人称蛙为“龚叟”(自己的爷爷、祖先);龙州县壮族也把蛙叫做“阿祖”;田阳一带流传的《洛陀洞与蚂拐节》神话将蚂节与布洛陀紧密联系;广西三江侗族三王庙相关蛙神话传说将蛙视为三王,其庙为祖庙;广西罗城仫佬族在与壮族蚂节相同的时间模仿青蛙形态动作跳蚂狮舞。老挝《蛤蟆国王》的神话传说中讲到蛤蟆国王与雨神战斗战胜了雨神,签订和平条约:地上的人以芒飞射入天空提醒雨神给稻田降雨,青蛙鸣叫是开始耕作的信号,风筝和长笛声是收获的信号,该神话揭示了当地“芒飞节”的来历,对于壮族“蚂 节”的渊源有启示作用。
那地村人崇拜青蛙的原因也不例外,那地村“蚂 节”中埋葬的青蛙以雌雄一对为佳,这一特殊要求涉及青蛙的生殖习性,也与人们对青蛙的生殖崇拜相关。青蛙属于卵生动物,它们的时令季节性很强,冬天的时候青蛙进行冬眠,春节过后二月间万物复苏的时节,青蛙们逐渐苏醒,呼唤雨水,“青蛙有雌雄之分,雄蛙口角旁有一对鸣囊,当鸣叫时,将口腔内的气体压进鸣囊,使其扩大成球状,起共鸣箱作用,发出咯咯声,十分响亮”[16]83,4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抱对繁殖。
那地村地处群山环绕的一个小盆地中,大部分农田属于水田,在该村“Y”字型的道路街道两侧几乎全是油菜花盛开的水田,油菜花是在水稻收割以后种植的,一条清澈的小河沿着道路田边缓缓流淌,山脚下有些田地种植甘蔗,小河边少量田地种植桑树,而板栗、李子、杉树等果木多种植在山上,大部分田地以种植水稻为主,可见,稻作农业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吾隘镇文化站站长梁祖曾向笔者解释说:
青蛙的皮肤很薄,因此能够敏锐觉察到周围气候环境中空气湿度和温度的细微变化,所以我们才说‘青蛙叫,雨水到’“青蛙田里叫,谷种田里跳”“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青蛙确实具有气象预报的功能,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我们壮族人通过青蛙骨头的颜色来判断来年是否风调雨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蛙骨的不同颜色都是不同的气候特点造成的,因此对来年的气候预测具有参考作用。
的确,科学家观察显示青蛙是两栖动物,可同时在陆地和水中生存,它们与雨水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这一点与水稻对水的依赖具有生态上的共性,青蛙的皮肤确实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呈现不同色彩,雨水降临前空气中湿度较大,蛙皮颜色较浅,青蛙感知雨水来临而高兴和兴奋于是集体欢呼鸣叫。尼泊尔巴格玛堤河谷的居民每年雨季时节都要在青葱的稻田中供奉鲜花、米浆等,并用米饭和九种豆做成的汤“喂青蛙吃饭”,以祈求及时降雨、水稻丰收,傣族人也有类似的祭蛙求雨仪式,都与蛙的稻作丰收象征有关。
在远古的夜郎国时代,那地州(今南丹县境内)一带连年闹“蝗兵”灾,据后人考证“蝗兵”乃今日的“蝗虫”,夜郎王下令谁能带兵征剿“蝗兵”便封为大将并招之为驸马。时有那地永安山一青年名叫骆吉,他智勇过人,土著族人推之为族长。他奉旨带兵征剿“蝗兵”,他所到之处,“蝗兵”溃不成军。后“蝗兵”将领施法术,变成数不清的蝗虫,铺天盖地,吃光庄稼,骆吉也用法术披上一件似蚂 皮的大衣,挥手一指:大地上突然出现了无数的蚂 ,把蝗虫吃光,骆吉讨伐“蝗兵”取得胜利。皇帝招他为驸马,骆吉不从,愿回乡务农。一天夜里,皇帝令人把骆吉的蚂衣烧掉,骆吉没有蚂 衣,不久便死去。
骆吉死后不久,天下又闹蝗虫灾,当地师公说,骆吉是天上蚂 星转世,也有人说骆吉是布洛陀的后身,要消灭蝗虫,要一年一度每逢农历正月选个吉日为蚂 节。在节日里安葬蚂 ,要做一口石头棺材,里面装一双雌雄蚂 。用“金童玉女”抬到庙里安放(叫埋蚂 )。待到当年的三十夜(春节),全村老少舞狮到庙里打开棺材观看蚂 遗骨,若骨为黄色,预示来年粮食丰收;若骨为白色,预示来年棉花丰收;若骨为红色,预示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若骨为黑色,预示来年定有灾难。
从古至今,原属那地州所管辖的天峨、东兰、南丹、河池边界的乡村,每年农历正月吉日,家家户户按传统习俗过“蚂 节”,在节日里,男女老少跳蚂 舞,唱蚂 歌,吃蚂 饭,以祝愿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那地壮族“蚂 节”2006年已申报为国家第一批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种植水稻的水田为喜水的青蛙提供了生长繁殖的生态环境,再加上青蛙是益虫,以捕捉稻田中的蝗虫、稻螟虫、稻卷叶虫等为食,能为水稻的生长保驾护航,二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良性生境。研究显示:“在丘陵和山区水稻田和池塘的青蛙主要是中国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蛙类是否有益和益的大型通常用‘有益系数’来表示,蟾蜍和黑眶蟾蜍的‘有益系数’分别高达90.14%和71.88%,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分别高达71.15%、93.33%和97.84%”[17]。在那地村流传的蚂传说故事中英雄骆吉(索吉)正是因为披上了蚂衣之后战胜了蝗虫灾害,为人民的生产丰收做出了贡献才得以被众人敬仰膜拜,这是当地壮族人民对青蛙生物有益性的形象外现,对青蛙的崇拜也是由此而生,并将之拟人化、艺术化,在那地村“蚂节”的蚂山歌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以下吾隘文化站站长梁祖曾向笔者提供的翻译成汉语的蚂歌文字材料,与东兰等地蚂歌歌词略有差异:
壮家爱唱蚂 歌,蚂 欢叫春雨落;蚂 捉虫禾苗好,秋后带来好收获。
正月里来是新春,蚂 洞中未翻身;祝愿蚂 冬眠好,好为壮家闹春耕。
二月里来桃花红,春回大地春意浓;只要春雷一声响,蚂 感到一身松。
三月树木标了苗,蚂 出洞伸懒腰;人间春光无限美,蚂 欢笑呱呱叫。
四月壮家忙耕田,蚂 戏水在田间;低头戏水抬头看,一个叫比一个甜。
五月蚂 心也飞,为情叫来做一堆;不信你到田中看,小的总要大的背。
六月二十米胞胎,蚂 吃虫忙起来;人来世间善为本,保护蚂 理应该。
七月初几米勾头,这时蚂 蹲水沟;奉劝世人莫去打,壮家美德留千秋。
八月十五是中秋,米黄只等人来收;丰收不忘敬蚂 ,壮家习俗要保留。
九月来到天气寒,蚂 要把石缝钻;钻进石缝把冬过,来年开春再来玩。
十月来了翻北风,这时蚂 无影踪;它为壮家做好事,愿它今年过好冬。
十一月份雪纷飞,蚂 冬眠不做堆;只有三月出来耍,不见寒冬出来陪。
十二月间冷得多,天当被子地当窝;虽然蚂 穿得少,天寒地冻睡得着。
壮家要唱蚂 歌,传统佳节年年过;泼水祈求天下雨,蚂 欢叫壮家乐。
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在没有科学的气象预报的情况下,那地壮族人对蚂的生活习性了解得非常系统透彻,具有关于蚂 预测雨水、干旱、洪涝等气象知识以及捕食害虫、消灭蝗灾的生物学知识体系,因此认识到了青蛙与水稻作物生长的特殊良性共生关系,他们意识到蚂关系到整个族群的生计生活,因此以巫术祭祀的形式奉蚂为神明,借助超自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气候环境对稻作生计的影响。
三、大河流域壮族稻作文明的表征
自然环境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左江流域花山岩画与红水河流域蚂节文化在生境、族群、文化表现上相似、相通,有着显性的关联,这些显性关联背后蕴含着蛙崇拜的深层关联,这些深层的和显性的关联又都是以共同的稻作文明为根基,二者同为大河流域壮族稻作文明的表征。
(一)类似的大河生境
壮族人的祖先很早就缘水而居,这种对水的崇拜和依赖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左江两岸的壮族村寨依然呈现沿江分布的特点。
左江位于广西西南部,是郁江支流,属珠江水系,全长约345公里,流域面积约13000多平方公里,该流域雨量充足,河水水量丰富,洪水期与枯水期流量相差192倍之多,左江花山岩画被誉为“崖壁画的自然展览馆”,它们分布于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到扶绥县的明江、左江两岸,绵延250多公里,作画风格、选址和绘制技术、绘制颜料整齐统一,各岩画点往往存在于河流拐弯的地方,且大多位于河流的凹岸处,左江之水是影响古骆越人选择岩画点的主要因素之一。
红水河位于广西西北部,为西江水系重要干流之一,因雨季洪水冲刷两岸红土使河水呈红褐色而得名,干流全长659千米,流域面积6.32万平方千米,约占广西总面积的37.4%。“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皆起源于大河文明的情况相似,壮族蚂拐节的流布地域也散见于壮族红水河流域百余里的壮族村寨,且是沿着红水河沿岸自北向南呈带状分布……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农业往往很发达。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13]5
左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都是壮族先民的栖息地,考古发掘显示,新石器时代这两大河流域就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时代,当地居民开始铸造农业生产所用石器和脱粒工具,并已经学会制陶,满足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基本要素,很早就发展出有特色的稻作农耕文化,成为壮族人民栖息地。可见,左江和红水河这两河流域都是壮族主要的聚居地,早在数万年前,壮族先民就已在该流域耕作生息,开创了以稻作文化、干栏文化、歌圩文化、铜鼓文化为主要形态的壮族文明,被称为是“壮族母亲河”“壮族文明的摇篮”。这两河流域都属于喀斯特地貌,群山绵延、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崇山峻岭之间田峒交错,“八山一水一分田”,属亚热带气候,古人类化石、古代文化遗迹较多。
(二)共同的族群渊源
民族主体一致。红水河流域与左江流域现阶段都以壮族为民族主体,壮族先民都是这两片土地上的土著民族,这两大河流域都在数万年以前已有古人类居住,这两大流域壮族人口比例都较高,外来民族为后迁入者,壮族是这两河流域的土著原生民族,壮族文化是其原生文化和主体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壮族传统文化保留完好,融合统筹了该地区的农耕、居住、饮食、宗教信仰、歌谣、婚姻、服饰和铜鼓文化,体现了壮族的精神信仰、宇宙观和价值观。
左江流域与红水河流域都具有水稻种植的从选种、育秧、插秧、耕作、灌溉、施肥、耘田、收割、气象观测到宗教信仰、节日习俗、称谓、地名、思想观念、饮食等一整套的稻作文化体系,体现了壮族人依水而居、以那为本、凭那而歌、以那为乐的那文化特点。
(三) 共同的蛙信仰
壮族先民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人工栽培水稻,开始了原始稻作农业生产。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壮族稻作农业就有了很大发展,生产力提高,种植面积扩大,种植技术完备,左右江流域的大石铲文化以及在那坡感驮岩和全州晓景发现的碳化稻谷是广西稻作农业的文化遗存。开始的时候,壮族人是在河滩湖区随雨季潮水涨落进行水稻耕种,后来随着耕种面积扩大,生产力水平提高,他们开辟出田峒种植水稻,依靠泉水溪流和天然雨水灌溉,水稻时常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大雨连连、洪水泛滥的时候会冲毁田畴;久旱不雨,泉溪干涸,又造成禾苗枯萎,颗粒无收。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壮族先民首先发现先打雷后下雨,而在人间则是“青蛙叫、雨水到”,于是他们洞见到支配着雨水和稻作生产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正是雷神、青蛙,于是他们创造了雷王主管雨水、布伯斗雷王的神话故事,青蛙是沟通人间与天上的使者,与雷神具有特殊联系。
显然,壮族的蛙崇拜具有双重的文化本质,一是生殖繁衍,二是稻作丰饶,与蛙崇拜关联的最早的原因是生殖崇拜,基于蛙腹与孕妇腹部、蛙口与女人阴户外形的相似,壮族先民想借助蛙产子繁多的神秘力量增强族群的繁衍生息能力,人蛙婚媾的神话传说即是力证。随着壮族进入稻作农业时代,生产能力提升、对蛙的生物性认识加强,洞见了蛙与水稻生长之雨水和病虫害相关的利害关系,蛙的身上增加了稻作丰饶的使命,与生殖崇拜交融合一形成双重的蛙崇拜精神内涵,实现了人与蛙的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生态境界。因此,青蛙从多子多孙的生殖之神又成为呼风唤雨的雷王的女儿,雨水的使者,壮族的蛙神崇拜从对青蛙繁殖力的自然属性的崇拜,发展到农业社会保佑风调雨顺的社会属性的崇拜,是壮族人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鲜明抽象思维能力和生产实践发展的结果。青蛙由此发展为保佑壮族人民风调雨顺、幸福吉祥、稻作丰饶、生息绵延的全民崇拜对象。
“从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壮族先民形成对青蛙的崇拜习俗以后,历经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直至唐宋元明时期,青蛙崇拜习俗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伴随着壮族的不断繁衍和发展而世代传承下来。到了清至民国时期,壮族对于青蛙的崇拜形式逐步发生变化,形成了以崇拜青蛙,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为核心的蚂节习俗。”[10]13花山岩画、蛙饰铜鼓、蚂节是壮族蛙崇拜的三个典型文化事象,这三者的先后顺序大致为,花山岩画距今2600年以上,蛙饰铜鼓1000-2000年(秦汉、南朝至唐代灵山型铜鼓),“蚂节”数百年以上(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对青蛙的崇拜早先是出于对青蛙旺盛繁殖力的崇拜,继而将稻作丰饶的内涵叠加融合进来。“蚂节”中对青蛙生殖内涵和丰饶内涵的表现:寻蛙者多为男性,找到蛙者称为“蛙郎”,东兰长江地区“蚂节”中女子以缠发银钗敲击铜鼓寻找意中人,蛙郎与蛙妹(雷女、九天玄女的结合)的配合、东兰女子寻找意中人都充满生殖意味,同时可促进稻作丰饶;男性表演耙田舞时群蛙在侧,表演田间舞的都为女性(女性本身有丰饶之意味),蛙舞动作在整个节庆中伴随始终,这些都具有稻作丰饶意味,同时又渗透有生殖繁衍之意。将生殖繁衍的内涵加入到稻作丰收的目的之内,将蛙的繁衍力借助到稻作的生长上来可促进稻作丰收。“两种生产”内涵的融合渗透在这三大文化事象中都得以囊括,生殖与稻作两种内涵的比重有所不同,时间越早生殖崇拜的内涵比重越大,时间越晚稻作内涵的比重越大。
规模庞大、时间久远的花山岩画,众多的人物画像整齐划一模拟青蛙舞蹈跳跃,就是在祭祀蛙神,既是以岩画创作和祭祀仪式等特定的交感巫术,包括了获取生殖繁衍这种神秘力量,实现族群的凝聚和生息绵延的内涵;又是在向雷王表达雨水要求的形象再现。对于花山岩画中的蛙人原型,丘振声有精妙的论述:“广西左江流域的摩崖壁画,那些两脚叉开,两手高举的正面立像,既是人的造型,也是蛙的变体……花山摩崖壁画众多的形象组成的壮观画面, 其气势更是咄咄逼人。在那画面里,不论是正面的立像,身躯前冲的侧面像,或由正面、侧面像组合的群像,都有一种动力感, 给人一种阳刚的美。这实际上是壮族人民刚强性格和他们审美情趣的具体体现”[14]。
铜鼓面上的立蛙和累蛙造型也是对蛙神的崇拜,铜鼓的类似呱呱蛙鸣的洪亮声响可以穿越长空传递向雷神求雨的功能,累蛙抱对又体现了生殖崇拜的内涵。
(四)文化艺术表现上的相通
四、结语
以稻作为基础的文化内容渗透到壮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壮族神话大多与稻作相关;壮族社会中将稻田和稻米视为财产的象征;有完整成套的稻耕技术、饮食文化和相应的宗教仪式和人生礼仪,稻作文化还体现在故事、歌谣、戏曲、舞蹈等文学艺术领域中。现如今在广西地区依然有着许多著名的优良稻作品种,其季节安排、选种育秧、插秧耘田、管理储藏的技术都相当卓越,磨砺出壮族人坚韧沉稳、勇敢细致的民族性格,壮族人的血液中流淌着稻作文化的基因,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蚂 节”和花山岩画都是壮族稻作文明青蛙崇拜的文化表征,表明了壮族蛙崇拜民族意识具有久远的历史性,寄托着壮族人民希望稻作丰收、种族繁衍的美好愿望,渗透着壮族人民质朴、沉稳、向上的民族精神,显示着壮族独具特色的审美追求。作为同在大河边缘的壮族同胞兄弟,虽然左江流域与红水河流域中间隔有一段地理距离,但在共同的稻作经济基础和稻作生产生活实践之上出于对暴雨洪水、久旱不雨、高山密林的恐惧和人丁兴旺、风调雨顺、稻作丰收、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在滔滔奔腾的大河边以铜鼓为核心道具的巫术祭祀的仪式活动表达同样的蛙神信仰观念,展现了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以青蛙为核心文化意象的稻作文化内涵,在蛙神身上凝聚了他们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功利目的。壮族人民在这样的全民聚会狂欢活动中获得精神的归属和心理的安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社会治理者通过这样的活动获得了族群的认同与统治的合法性,共同彰显了壮族人民借助青蛙崇拜表达的对生命永恒、种群繁衍、稻作丰收的追求,对自然万物的崇拜,人与万物生存发展休戚相关,表现了人类永恒的生命、生存主题,体现了壮族人民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是壮族生态文化观念的最集中反映,在现代科学生态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依然是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的生态典范。壮族的青蛙崇拜客观上实现了生物平等基础上的动物保护,原生态的稻作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利于壮族地区的生态平衡,真正实现了当地的青山绿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蛙声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