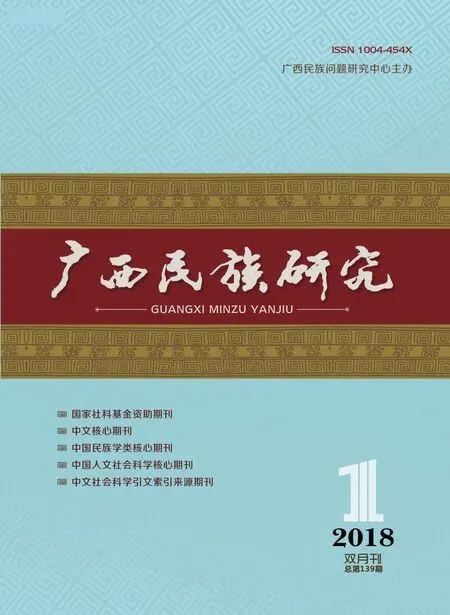从“象—形—意”到“物—符—音”: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演绎之路向*
2018-11-19米恩广
权 迎 米恩广
“坡芽歌书”乃现今存活在壮族民间的古老文化形态,是壮族构造化活动的产物,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坡芽歌书”的创生则是壮族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更是人类智慧的外在表达。[1]但“坡芽歌书”产生年代、使用范围等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加之该符号文化仅在云南富宁坡芽村的一块土布留有记载,是仅存的物质记录形态,这使其有了神秘性。因此,对“坡芽歌书”的独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从更微观的层面诠释壮族民族性以及符号文化与壮族人民间的内在逻辑的重要范式。
一、“坡芽歌书”符号文化的多元价值意蕴
(一)从结构来看,“坡芽歌书”体现了社群主体与个人主体的统一
2006年春,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坡芽歌书”走出大山被外界所知,其独特性和神秘性引起诸多领域专家的关注。对世人和研究者来说,“坡芽歌书”是一种古老而新颖的文化形态,古老因其产生时间的未知,新颖则是因其表达形式的独特。“以图载歌”是其所富含特殊价值意蕴的凝练表达,壮族人民通过符号直观形象地完成了抽象、无可言状的情感表达,实现了歌书创生的初衷。[2]因此,歌书符号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物化的意向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其承载了成百上千年壮族人民的集体智慧。
“坡芽歌书”由81个符号组合而成,学术界已将其认定为“文字之芽”,认为是比东巴文更原始的图符文字。[3]133实际上,“坡芽歌书”中的每一个符号都被赋予了特有的内涵,直接承载了对应角色即个人主体的内心情感与现实诉求,而个体乃是壮族社群主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社群主体性乃是个体共性的凝练表达。因此,81个符号既代表了壮族人民社群主体的价值与信念,也具体到每一个社会个人主体的价值追求,诠释出了符号文化在壮族社会中的社群主体和个人主体的统一。
“坡芽歌书”以其“象形意”相结合的固有结构形式,实现了对社会群体、个人主体与符号关系的全面透视与阐释,歌书符号成为壮族人民情感世界和内心独白的物化表达。81个符号向人们展现了壮族人民与社会个体对情感的深刻认知,通过以物传情、寄情于物的方式阐释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对爱情的独白,通过符号将个体与整体相融合,不仅展现了物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意蕴以及人与物之间所表现的和谐化生关系,还表达出以壮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固有的思维与内心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睿智。
(二)就行为过程而言,“坡芽歌书”诠释了符号创生中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在壮族赖以生存的天地系统中,他们历经观物、取象和构形的过程,通过意向与实物之间的转换将可观可感之物物化成像,实现了“坡芽歌书”符号的创生。歌书符号的创生实质上是一个将意向转化为现实、用可观可感之实物来承载壮族人民意识形态与文化意蕴的能动过程,既满足了壮族人民将内心诉求付诸现实表达之需,同时也解决了情感、文化记录的现实诉求,又实现了认知方式的外显,彰显了壮民与外界相处之道,壮族人民进而通过符号的创生诠释了生产生活与内心情感世界之间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坡芽歌书”符号一经生成,其创造者和符号传承对象间便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来完成符号文化的认知与传承,进而符号也在无形中参与到壮族生产生活之中。在生产生活中,壮族人民通过特有的方式使得各种符号在民族社群主体间实现无障碍使用,使符号所凝结的意蕴在更广阔的时空内得以播化,因此,在壮族人民创生“坡芽歌书”符号文化的过程中,巧妙地实现了抽象与具体的有机统一。实际上,歌书的播化是符号文化在壮民间的播化与实践,而播化不仅仅是对歌书中81首情歌的简单传唱,对81个朴实符号的临摹书写,更是对歌书符号创生过程中所蕴含的壮族人民固有的智慧理念和民族文化的沿袭。壮族人民将其思想中美妙意境与其所思所想附着于现实物体,通过构形加以表达,使歌书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世代相传,这也是壮族人民思想意识抽象层面的意境在现实中的具体表达,进而“坡芽歌书”符号也实现了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这也是歌书历经百年沧桑依然能在现代社会中存续的要义所在。
(三)内容表达上,“坡芽歌书”实现了内心与外在的统一
“一般认为人类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并把自己所居住的世界秩序化,这就是把自然改造成文化的活动”,[4“]坡芽歌书”符号则是壮民从事构造化活动的产物,是壮族将其内心意境和情感诉求在自然世界中以物抒情,把自己内心世界向外界表达的文化写照。“坡芽歌书”内涵丰富,意境优美,用歌声的委婉动听来展现壮族人民内心情感的细腻,更为重要的是歌书符号背后体现了壮族文化中物我关系的和谐相融,此乃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显现。从“坡芽歌书”81个符号取象的现实依据上来看,均源自于壮民生活与栖居其中的自然界常见之物,如月亮、白菜、三脚灶等,“在壮族先民的思想观念中,月亮是一位女性,慈祥而又温柔的善神”[5]40。符号构形的本源之物虽原始而简单,但却是壮民文化生活的历史见证,承载了壮族人民现实中独有且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因此,歌书符号通过优美动听的81首歌的传唱、81个符号的书写来实现内心多样化活动的生动表达,以声表行,以行达意,来实现着歌书的价值和符号所蕴含的现代性表达以及历史性的沿袭,从而使歌书蕴含的文化意蕴代代相传,彰显其时代价值,此乃内心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
“坡芽歌书”符号是壮族人民基于现实诉求参与自然物化的创生之物,是壮族人民在其农耕生产与现实生活中生活经验和文化知识的载体。在壮民实现歌书符号的描绘与书写之时,符号承载了他们世代积累的经验知识并将其以传唱方式在社会中传递。而将文化和经验播化与传承是一个长期过程,传承中壮民将其文化和价值意蕴附着于生产生活常见之物,在现实生活中将实物的象、符号的形、声音的美与内心之意完美融合为一体,实现了物、符、意的相融相生。“坡芽歌书”符号在内容的表达上巧妙地将壮族人民的智慧与内心活动附着于生产生活之物,在“形式”与“内容”的整合中实现了情与物在“象、形、意”的完美结合与有效表达,实则实现了从事构造化活动之人繁杂的内心与多变的现实之间的有机统一。
二、从“象—形—意”到“物—符—音”: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演绎之路向
在现实的生产生活情境中,对所观之物的认知是壮民歌书符号习得的重要基础,而将情境之物的象、形、意相结合乃符号文化创生与认知的关键。壮族人民通过取象、构形、赋意为符号创生夯实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物—符—音”的融合来完成歌书符号的创生、传承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从“象—形—意”到“物—符—音”的转化也成为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的演绎路向。
(一)象、形、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创生之源
取象:符号文化创生之源。壮族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在漫长的农耕岁月中与生产生活中所见、所知、所感之物结下不解情缘,并与物共同构建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坡芽歌书符号乃壮族人民集体智慧的凝练表达,并非凭空而生,它是主体之人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取象,对其抽象意境加以构形,再通过寄情于物的表达方式而最终成像的过程。因此,人成为“坡芽歌书”符号的创造者,而符号则是创生,是社群主体抑或个人主体与环境互动与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坡芽歌书”符号的创生过程乃是壮族人民自觉而主动地对外界事物进行观察、类分的过程,即取象的过程,进而实现物色之动,情亦传焉。此过程不仅使主体意象表达所需的物化形象通过符号的建构得以建立,并通过符号的多元使用使主体所欲表达之意附着于符号之上,以实现用原物之象传达人文之理、欲表之意之目的。本质上而言,是壮族人民通过符号完成了从自然之理到人文之化的物化表达,因此,生产生活之物成为歌书符号创生之源、生存之基础,亦成为符号播化的重要情境和载体。例如:壮族先民用农作物以及与农作物相关联的动物来记录和辨别时节,指导生产,他们将播种、育苗、翻地、灌溉、插秧、收割整个过程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知识来指导他们的农业生活。在水稻栽种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诸多事物也成为壮族先民辨识时节、指导生产的重要参考物。他们通过观察稻作生产中的所视之物“浮萍”的颜色等来辨识稻谷的生长期,他们将浮萍叶子的颜色变化与谷穗成熟度相关联,浮萍老了说明稻谷到收割时节了。因浮萍的熟知便于习得和传承,在歌书的创生中便将其作为歌书符号的原生物,成为歌书第72符号——浮萍,从通过观物—取象—表意的文化创生过程培育出了具有“地方性的农耕文化”,符号也承载了壮族人民内心意境的表达功能。
构形:符号文化创生之关键。“壮族生产生活的环境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场域,但壮民世代以农为生、倚靠山水而居,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能掌控与熟知的外界条件的有限性,熟悉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周边事物自然成为他们传承民族文化和经验的依托和载体。在壮族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深知岁有其物,物有其容,因此他们通过观物以取其形,来实现内心所思所想的有效表达。而壮族人民“情以物迁,意以情发”的行为则是通过对所观之物进行构形,进而实现以形表意。“寄情于物、借物抒情”是壮族人民在其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表达方式,因此“坡芽歌书”符号成为壮族人民抒情、表意的重要物化表征。“坡芽歌书”的81个符号的产生均源于壮族人民生产生活之物之原形,进而81个符号之形展现的是壮族人民生活与生产的现实缩影。诚然,田间地头的野花小草、生活中的火塘晒台、劳作中短暂休憩、闲暇之余的凉亭圩场等习以为常的场所和情景呈现出的象与形,成了壮族人民取象—构形的重要素材。
壮民先辈为使年轻一代在生动具体的环境下掌握其中所涉及的事理和人情,他们将内心的情感表达与民族习性、经验文化寄于身边感知到的具体事物,以利用熟悉事与物之形的构建,向晚辈们呈现难以言表的文化和经验认知。如“七个石子,是壮民用来计数,表示7天;为了便于记录,壮族先民以身边司空见惯的小石头原形作为符号的形象表征,用石头原形来表达壮族先民欲表之意。同时,壮民还通过稻田里常见动物的形象、活动、出现频率等来表达所欲之意。如壮族基于对蚂蚱的熟悉,以蚂蚱形象、数量、活动、频率等来记载和传授农耕知识。蚂蚱便也成为歌书的原生素材,于是产生了歌书符号12——油蚂蚱。实际上壮民欲表之意的实现则是“观物—取象—构形”过程的现实演绎,也是壮族民族性与民族文化得以存续的重要方式与路径。因此,生活中的每一事物皆成为壮族符号文化“构形”的基础,而“构形”乃符号文化创生的关键。
附意:符号文化创生之所归。“取象—构形”乃是实现意向表达的前提,实现所表之意的有效表达乃是符号文化创生的落脚点。壮族人民通过现实情境中将物之形与人之意相连,完成歌书符号创生与习得,因此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意向表达乃是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创生之所归。现实中,壮族生产、生活情境之物乃壮族歌书符号创生的重要素材与来源,因此,素材的多元化决定了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意象表达物化表征的多样性。如火塘,它不仅是壮民家庭的重要生活器具,是壮族老少均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具,其特点也深烙在壮民内心深处,同时火塘的场景和形式也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媒介。生活中的诸多事务是由壮族妇女承担,尤其是烧火做饭、带孩子。传统壮族家庭都设有火塘,壮族妇女便在火塘边准备家人的伙食,长辈们在火塘边用餐或休息时惯于在欢声笑语中完成对下一代的教导,包括生活技能、行为规范、经验常识等。基于生活现实情境,壮族先民借用人们熟知的生活实物作为歌书符号的本源物,用歌声将歌书符号及其寓意传授给晚辈,便于传授对象接受和识记。因此,壮族先民将火塘及其部件与歌书符号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并将其欲表之意附着其上,进而便形成了歌书符号19——三脚灶,以便于后人熟记此符号的内容和寓意。同时,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素材也成为壮族人民内心意境物化表达的重要素材,如歌书符号18——白菜、符号13——韭菜,均源于日常生活的饮食素材。诚然,壮族代际之间在生产生活场景中巧妙地完成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特性的创生与传承,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内心意境的现实表达,继而进一步实现了符号文化创生的目的。
除了与饮食相关实物被壮族先民用作歌书符号习得与播化的重要素材外,生产生活中的常规性活动也成为壮族歌书符号“取象—构形—表意”的重要素材,如刺绣。传统中刺绣等手工活动是壮族女性在农闲时节从事的主要活动,而壮民又已养成“活动中播化”的固有文化表达方式,因此,农闲时节也成为壮民开展代际教育以实现符号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时间。农闲时节,壮族女性凭借自己灵巧的双手从事织布、刺绣、缝衣等活动,按照惯例此类手工活都是家中女性长辈传授给女性晚辈,一般女孩到10岁就开始接受长辈的技能传授,日积月累在壮族民间已成为一种习俗,形成了一种氛围。女孩子到了年龄也自然地去学习织布、染色、刺绣等技能,他们将生活中熟知的、漂亮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绣到衣裤之上,创作出精致而又惟妙惟肖的图案作品,同时,壮族女性将其所表之意寄于所制衣物,以表其意,并将其绘制在歌书之中,形成特有的符号文化,因此“坡芽歌书”中也就形成了符号31——上衣和符号43——阔脚裤。
实际上,刺绣过程乃是壮族女性完成“取象—构形—表意”的符号创生过程,最终将符号附着于衣物之上,以实现内在意向的物化表达。诸如此类的过程乃是壮族人民将特有民族文化和固有民族性由抽象意境到具体物化表达的过程,他们不仅通过实物实现意向的表达,也对身边事物有了更加清晰而深刻的认知,通过不同个体、群体以及代际间的互动,无形中提升了壮族人民的动手能力,并将该行为培育成为一种民族习惯,为“坡芽歌书”符号形态的创生提供了技能支持。因此,以物传情乃壮族表达其所思所想的重要方式,“坡芽歌书”则以“以符载歌,以图表意”的形式实现了符号文化在壮民代际间的创生与传承,更为重要的是此过程完美地实现了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使得情感与实物的链接得以建立。
综上所述,现实情境是壮族歌书符号创生、习得和传承的重要素材来源,他们巧妙地将实物之象、器物之形与其内心之意关联到一起,无形中积累了符号文化创生与习得所需素材和经验,从而完成“坡芽歌书”符号在群体、代际间的播化。通过生于斯长于斯的具体情境,壮民基于对生产生活中事物的不断“同化”与“顺应”,完成了对歌书符号原生之物和外界环境的认知。通过日常活动在实物与形象之间建立起了内在关联,借用他们生产生活中熟知事物的“象与形”去表所欲之意,从而使歌书符号文化通过“象—形—意”在壮族社会中得以建立并深化。通过“象—形—意”的结合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积淀了生产生活常识,为歌书符号在代际间的播化、在现实中的再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物—符—音”:“坡芽歌书”符号文化的实践
“坡芽歌书”因其跳动的符号而成为一部活的文字,传承符号文化则是民族性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知道,壮族先民在现实情境中创生了歌书符号,又依托现实情境实现了歌书符号的传承。事实上,除了依托具体情境实现歌书符号的习得与传承外,符号借用的实物所蕴含的本质意义、符号化表征所形塑的符号形态与意蕴以及每一个符号所对应的歌曲等共同缔造出了“坡芽歌书”符号的实践路向。
绘物:“坡芽歌书”符号文化之要径。壮族自古就有“以歌传情、以音表意”的传统,使得男女老幼爱歌爱唱,并形成爱学歌的风气。在符号创生与习得过程中壮族先民巧妙地将物体、符号、声音连接起来,将物之形与歌之意通过物化符号建立起对应关联,并将之传唱。正如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写道:“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人生之首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择偶的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6]156因此,依托于壮民对所创生之符的本源之物的形、音、意的喜爱来实现对符之蕴的掌握,进而坡芽歌书也实现了“物为符所依,符为物所用,音为意所表”。
生产生活中,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参与到大人们的劳作之中,长辈常在劳作休息之余放开歌喉,常常边画边教,教孩子们唱他们所喜爱的歌曲,并让其掌握所绘之物的深层意蕴。如巧遇山中鹧鸪鸣叫,父母长辈便会告诉孩子,此叫声是鹧鸪鸟的声音,同时用树枝之类的硬物在沙土地上画出鹧鸪鸟的图案(歌书符号5),并用歌唱的方式让他们认识鹧鸪鸟及鹧鸪鸟所蕴含的歌词大意。实际上,传唱过程并非是单一的演唱,在传唱中大人们要求孩子通过实在之物转化而成的物象熟练地记住歌词,而后通过所画图案符号将歌词含义告诉晚辈,进而巧妙地在“物—符—音”之间建立其关联,以便他们记忆。久而久之,借物传唱成为壮族人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代际间被内化为一种习俗。在生活劳作中,如果看到与所教歌曲相对应的实物,长辈们便会提醒孩子与此物相关的曲目,并带头歌唱,以达温习、巩固之效。日常生活中,孩子们看到与歌曲相关的实物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歌词,并在心中回想大意加以识记,随性而唱。唱山歌作为壮族的一种习惯,生产生活中的实物为歌书符号的代际传承创造了条件,成为歌书符号在现实中运用的重要实践与参考对象,绘物也成为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创生、传承的重要路径。
制符:“坡芽歌书”符号文化的运用。对壮族而言,唱歌其实就是一种学习,他们常常采用“念唱”结合的方式教授歌曲,而通过熟知的实物画出晚辈喜闻乐见的图案乃是传授符号文化的重要方式,符号也成为壮族欲表之意的重要载体,实则是对符号文化的具体运用。一般情况下,所见、所感之物在人们脑海中已形成具体的形象,长辈会灵活借用身边熟知的事与物开始符号文化的习得,他们边画边说所教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接着念完全部歌词。画完图案符号便对孩子进行强化练习以加深对符号及其歌词大意的记忆,同时叮嘱孩子,以后见到这个符号,要记得第一句和随后的内容,并以歌唱的形式加以传授,“歌书中的歌曲就像汉语学习中的拼音、英语学习中的音标一样,当他们看到某个符号就知道要唱什么”[2],以便孩子们通过对实物的物化形象加强对符号的记忆,进而掌握符号之蕴。可见,壮族人民以熟知的动物、植物、天体乃至人物形象等生产生活实物为符号创生之原形,巧妙地在符号原生与次生之间建立了逻辑关联,在具体情境中不断寻找出符号之根,且通过寻找到的符号逐步构筑出与壮族人民息息相关的风俗、生产、生活、神话等文化事象,勾勒出了壮族文化的画面,不仅有效地将“物—符—音”融为一体,实现了符号文化的习得,更为重要的是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意蕴也伴随而传承。
此外,提升符号认知也是壮族实现“坡芽歌书”符号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环节。除了长辈传授外,年轻一代自身也形成了独特的学习方法以帮助自己完成歌书符号的习得,以达到见符起歌的目的。例如,初学者上山放牛时,会把符号画在纸上,自己不会画的时候,就请家中长辈帮着画,画好后随身携带以防忘记歌词。实践中,初学者个体难以记住或记全歌词,他们就相互邀约外出劳作,在劳作中即兴起歌,忘词或不会唱之时,相互提醒,经合作记忆与反复练习,初学者对歌书符号的认知日益加深。晚辈们一般到成年之际,便能够记住歌书中的81个符号,掌握81首歌的不同唱法,其意蕴也随之内化成为永久性记忆。实际上,“符号一经创造,相比其原生之物具有稳定性和功能性:能指代一定的事物、传递充沛的情感、指令特定的规则、表达丰富的涵义、呈现不同的美感、交流深邃的思想”[7],使人能够“借助符号表现情感世界和认知世界,并借助符号系统实现文化的传承与人性的塑造”[8]120。 因此,符号成为“坡芽歌书”文化价值意蕴的载体,是壮族人民对民族符号文化习得与传承的重要媒介,且符号在壮族“坡芽歌书”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作用。诚然,绘制壮族司空见惯、喜闻乐见的符号图案乃是实现壮族“坡芽歌书”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对民族文化的现实再现与运用。
音律:“坡芽歌书”符号意蕴之表达。事实上,“坡芽歌书”中的每一个符号不仅仅代表了壮族生产生活中的一件或一类实物,更关键的是壮族人民通过“物与符”的结合,共同缔造出具有特定内涵与意蕴的民族音律,而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均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歌声背后则蕴藏与凝聚着壮族符号文化的深刻文化内涵。而歌曲音律的传唱则是将壮族对自然、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特有的认知与思维方式一代代传递下去,是壮族独特的民族性形成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环节。音律乃“以音传情”的具体表现,因此,“音”(即歌曲)固然成为壮族对符号应用与文化意蕴表达的重要载体与实践形式。进而言之,音律在“坡芽歌书”符号文化物化表达中的表现形式具体有三:
其一,直表其意,暗露民族智慧。构成“坡芽歌书”的81个直观符号表达了一对壮族男女青年的曲折爱情历程,实则自然地体现了壮族婚姻风俗与情感文化,更深层次的则是通过歌唱的形式培育出了“以歌择偶”的民俗,而通过歌声进行试探与了解,则是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诠释出了壮族人民的巧妙和互相考问的智慧。
其二,以情表意,揭示礼俗规仪。“坡芽歌书”表面上通过歌声表现对爱情故事的描述,实际上向人们展现了壮族人民固有的风俗礼仪。如歌书中以发未辫的符号形象地代表了壮族未成年女孩,一个符号表面上是关于一个女孩的歌曲,实则是巧妙地将歌声与内涵附着于特定符号之上,进而呈现了当地壮族社会中的民间风俗,即壮族女孩到十三四岁之时,需在女性长辈的帮引下举行蓄发、修眉、染齿的仪式,仪式完成后就意味着该女子已成人,可以恋爱、成家、生子,而该意义的表达则是以歌曲传唱的方式实现,可见,音与符的相融实则是对壮族女子成年礼风俗的再现。同时,同时“坡芽歌书”以声音透射出了壮族社会中的服饰、饮食等物化习俗与文化。
其三,以声传情,诠释人生规律。“坡芽歌书”以优美旋律展现了壮家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与人生风俗,旋律背后则诠释了人自身生产的循环和发展。一言以蔽之,歌声乃是壮族“坡芽歌书”符号文化得以存续百年的重要媒介,歌声所形塑的音律承载的不仅仅是符号与歌词大意,更为重要的是担负着传承壮族固有民族文化与民族性的使命。
综上所述,“坡芽歌书”通过“象—形—意”的转化将壮族的风俗仪规附着到特定的符号载体之上,以传授给更多群体成员,将“物—符—音”巧妙结合,用“以图载歌,以声表意”的方式通俗易懂地向人们诠释了壮族社会特有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特性,实现了社群主体与个人主体间的和谐互动。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所构筑的风俗礼仪等特有文化通过符号的直观形象与歌曲的动感优美,在符号使用中相伴而承,并在传承中,滋养着个体的发展,从而完成个体民族性的培育与发展,实现了壮族社群主体与个人主体的统一。在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壮族代际间进行包括符号原生之物、符号形体书写、歌曲的传唱,实现了符号“代表项、对象、解释项”[9]58的完整统一,使人们在歌书符号习得过程中实现了对歌书符号从“象—形—意”到“物—符—音”的全面认知和整体把握。加之在生产生活中的反复练习,通过相互学习和对歌等运用方式,将习得的歌唱技巧付诸实践,无形中提升了自己对符号文化的认知,从“象—形—意”到“物—符—音”的实践与转化则成为画布上的符号存活至今的重要传承路向,也使得“以图载歌、以歌传情”的技能得以传承,符号蕴含的优美歌曲得以千古传唱。
壮族人民通过对原生之物的“取象—构形—表意”实现符号文化的创生,在生产生活中强化着对符号的使用,实现了壮族符号文化“象—形—意”与“物—符—音”的转化,转化过程中使得壮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得以构筑,并在实践中加以彰显。在取象、构形、附意的过程中不仅使符号自身内容世代延续,其背后丰富而深邃的意蕴亦得以播化,使得符号生成中所涉及的壮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经验,风俗仪规等也得以传递,从而化生为壮民精神成长所需的养料。另外,符号习得方式的灵活性在“象—形—意”到“物—符—音”的转化传承路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为壮族民族文化与民族性的化育效果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使得整个化育过程完整而丰富。
总而言之,任何文化现象的存续抑或拓展,不仅有赖于从自然系统获取所需养分,而且更离不开文化主体自觉能动的传扬,壮族“坡芽歌书”也不例外。然而,在内外环境剧变的情况下,将“坡芽歌书”置放在不受外界影响的纯净的真空中,让人们重塑过往的生产生活情景均已不可能。那么,歌书如何在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以应对外界变化的冲击,成为歌书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议题。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每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该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10]。那么“坡芽歌书”应该拿什么去与他文化交流,从而实现传承、拓展的目的?诚然,有效的构建和应用“坡芽歌书”符号的习得机理,弘扬“象—形—意”到“物—符—音”的民族文化演绎与传承路向仍是壮族人民不可规避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当代壮民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米恩广,权迎.创生—传承—化育:符号教育的内生逻辑——基于对壮族“坡芽歌书”符号的调研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2]权迎.云南壮族“坡芽歌书”符号创生与传承的教育人类学阐释[D].西南大学,2013.
[3][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M].张晓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4]赵丽明.“坡芽歌书”的符号是文字吗?[J].文史知识,2009(7).
[5]黄庆印.壮族哲学思想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6]刘锡蕃.岭表纪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7][法]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M].怀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8][法]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张祖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9]丁尔苏.语言的符号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10]张诗亚.“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