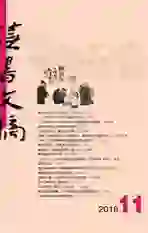陈明眼中的丁玲
2018-11-17陈家鹦
陈家鹦
很早我就知道,有位赣东北鄱阳县籍戏剧家叫陈明,也晓得他与享有盛誉的现代女作家丁玲夫妻相伴。上世纪80年代,我偶然得知,陈老的一位亲戚也算是我的亲戚,于是心生寻机接触他的念头。谁想十年后,我竟接连获机会,先后三次赴京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陈老。
1991年3月初,我趁因公赴京之便,带着亲戚的嘱托,前去拜访陈老。陈老的住宅在木樨地22楼公寓里。这天,他客厅的条桌上摆着一盆常青树,正面墙上悬挂着丁玲带着微笑的大幅彩照。后来接连在1992年6月和1993年5月两次得机会进京拜访他,也是在这个客厅。
初次谋面我有些拘谨。寒暄之后,不像“采访”,由着陈老兴致随便聊。开始陈老总是谈丁玲的晚年写作与生活,我则时时捕捉机会,发问其生活经历,尽管陈老不大愿意说自己,几次接触后我还是渐渐了解了他与丁玲相知相伴的风雨人生……
走向革命 奔赴延安
陈明,原名陈芝祥,农历丁巳年 (1917) 正月二十日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小华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祖父是个有声望的老绅士,有4 个儿子,陈明的父亲叫敦敏,排行老二 ,大伯父敦安是长子,从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海关做事。大伯是陈家的顶梁柱,思想开明豁达,热心公益事业,经常资助家乡修桥补路,在乡亲中口碑颇佳。
陈明从小在家中读私塾,10岁那年 (1927)随回乡结婚的四叔来到北京,住在大伯家,并插班到附近的北师附属小学三年级学习。在这里只读了半年,陈明就跳到高小一年级。
1929年冬,伯父升迁调动到上海海关工作。1930年初,陈明也随伯父全家迁到上海,在上海培成女中附属小学继续读了半年高小,下半年入读东吴大学附属二中。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学校被迫停课,合并到湖州东吴三中,陈明也随学校转移到湖州学习。
1933年秋,陈明被录取到上海麦伦中学高中部。从小就关注社会并爱思考问题的他,在学校受到校长沈体兰和教师曹亮、魏金枝等人进步思想言行的影响,积极投身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学校发起组织话剧社,先后演出过田汉、于伶、陈白尘等人创作的 《走私》 《顾正红之死》 《放下你的鞭子》 《扬子江风暴》 《到那里去》 等剧本,颇具影响。
在上海“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陈明参加了宋庆龄等人组建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废寝忘食地组织宣传演出,参加游行示威、演讲等各种活动,很快成为麦伦中学的斗争骨干和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并先后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秋,陈明考进上海商学院。1937年1月,由于他的身份及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注意,后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陈明离开上海,经北平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结识丁玲 成就奇缘
1937年5月初,陈明来到延安,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十三大队学习,毛泽东、博古、张国焘等领导人常来讲课。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宣部部长凯丰的秘书朱光,朱光极为欣赏这个刚满20岁的青年。1937年6月,延安文艺界举行高尔基逝世纪念会,陈明参演了田汉根据高尔基长篇小说 《母亲》 改编的独幕话剧,在其中扮演“母亲”的儿子伯惠尔。演出非常成功,陈明因此成为延安抗大文艺活动骨干。
比陈明早到陕北的丁玲,曾是上海“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到延安后又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当选该协会主任,并与抗大教员、作家吴奚如商议,决定组织一个战地记者采访团到火线上去。后中宣部指示,把抗大演出 《母亲》 和 《回春之曲》 主要演员留下来,成立一个宣传队也随同派出去。最终约30余人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简称西战团)成立。按毛泽东的提议,西战团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下设若干股。陈明与丁玲就是在西战团内相识的。
1937年8月12日,西战团召開第一次会议,丁玲同张天虚、戈矛、李劫夫等延安文艺界名人及30余名男女团员一一握手。当其与年轻的陈明握手时,不禁被他那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给怔住了—— 这不是 《母亲》 中的伯惠尔吗?
真的,他就是“伯惠尔”,就是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
随后,西战团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奔赴山区。慰问前方军民,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在频繁的接触中,丁玲不知不觉喜欢上这位精明能干的宣传股长。
陈明也感觉到丁玲对他好,但好得有点过分。于是,他私下向关系很好的领导倾诉了自己心底的不安,领导劝其调离西战团,可他说:“要我离开西战团,实在舍不得啊……”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延安。不久,丁玲和陈明同时被组织留在马列学院学习。丁玲仍像以前那样对陈明关怀备至,但陈明内心却仍然充满矛盾和痛苦——与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女性相恋,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呢?
不久,陈明找了个机会,向丁玲把话挑明:“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谁知丁玲立即反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陈明一时竟无言以对……
陈明知道,丁玲是第一位从国统区来到中央陕甘宁苏区的著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器重。她是名人,地位高,且两人年龄差距又大,将来能否融洽地生活在一呢?陈明在一篇日记里记录下自己这种迷惘矛盾的心境:“让这日子快结束吧。”说来真巧,这段表露内心隐秘的日记偏偏被丁玲发现。她热烈而真诚地对陈明说:“为什么要结束?我们刚开始……”
1939年9月,陈明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社任社长并背着丁玲作出了一个看似“理智”的抉择:斩断情丝,另与他人结合。于是,他决定与剧社里一位对他很好的女演员席萍建立恋爱关系,并坦诚告诉了对方自己与丁玲的情感情况。不久,在驻地首长的支持下,陈明与席萍匆匆地结了婚。得知此事丁玲深受打击,陈明为此十分不安。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席萍自然也感觉到了这其中的情感矛盾和尴尬,三个人很快全都陷入到更大的情感煎熬之中……
一年后,陈明离开烽火剧社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任职时,与席萍分手。
1942年2月,在經历了一番痛苦的波折之后,丁玲和陈明这一对爱得太深、爱得太久的情侣,最终在中央组织部陈云的理解与支持下,于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这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陈明与丁玲一起度过了50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岁月。
婚后,丁玲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陈明自1941年延安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就一直在研究院辖下的新闻研究室工作。在这里,他们两人一起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审干。1943年7月,康生作了 《抢救失足者》 报告后,丁玲和陈明都成了运动对象被审查,和不少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一样,受到“左”的迫害和打击。
1944年,丁玲调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专职写作。随后,陈明经胡乔木安排,也离开了党校去边区文协,这是两人婚后度过的一段难得的较为安稳的时光。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明和丁玲在晋察冀开展工作。1946年5月,丁玲随陈明为组长的工作组,来到桑干河畔,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土改斗争中,并开始酝酿她的鸿篇巨制。1947年11月,丁玲在阜平县一边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一边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初稿进行修改。在此前后,陈明一度到野战部队体验生活,但刚一回来,他便成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1948年丁玲的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出版后即产生轰动效应,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丁玲一下子大红大紫。但是,在那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的扉页上,丁玲却写道:“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致为外界影响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选择去国家电影局,丁玲则被安排在中国文协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组长等职。正当他俩准备在不同文艺领域中投入更大的热情时,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灾难突袭而来。
1955年年底,丁玲被打成“丁 (玲) 陈 (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接着,又于1957年和冯雪峰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挺身为其抱不平的陈明也因此受到牵连,于1957年年底受到严厉处分,被开除党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从此,俩人的事业和命运直转急下,一下子从山巅跌入低谷。
相互支撑 共度时艰
1976年“文革”结束,此时的丁玲已年逾古稀,伤病缠身,十分虚弱;而陈明健康状况尚好,跑腿的事自然由他承担。和许多人一样,陈明一直为讨回公道、获得平反而奔忙着。一回到北京,他就先后找了王震、胡乔木等比较关心和了解他俩的领导和友人。1978年夏,丁玲所在的公社终于宣布摘除丁玲的“右派”帽子。年底,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3日,丁玲和陈明两人一同返回阔别20年的北京。陈明为安排家庭生活,为丁玲治病以及为她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再次整日奔忙。1979年10月22日,中央组织部宣布,自即日起恢复丁玲的党籍,恢复组织生活。至此,丁玲再度回到党的怀抱。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紧接着,陈明的一切“问题” 也随之解决,他被安排到文化部工作。
丁玲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
丁玲的晚年虽说是艰难的,但也算充实。从复出文坛到走完人生最后里程只不过6年多时间,她却以多病之躯,凭借顽强毅力写出了 《杜晚香》 《“牛棚”小品》 《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 等近100万字的作品。其间,陈明也写了相当于 《“牛棚”小品》 续篇的 《三访汤原》 等作品。
熟悉他俩的人都知道,在丁玲生命最后的辉煌之中,无不凝聚着陈明的心血。晚年病中的丁玲,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在我与陈老的交谈中,他告诫我说要重视文章“修改”,并援引丁玲的话,证明“改”字在写作中的重要,说丁玲许多好作品都是他俩配合着共同改出来的。
此话不假。丁玲家乡湖南的一位作家就曾撰文讲述:丁玲1982年秋回到家乡临澧县,在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 陈明协助她斟酌改动过的痕迹。
1986年4月3日10时45分,长期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心力衰竭,终于夺去了丁玲这位文坛巨星的生命。就在她生命行将结束的前几天,丁玲又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对着一直守候在旁的陈明轻轻地嗫嚅道:“亲亲我……”
陈明俯身听清了这几个字,他强忍着泪水在她的额上、唇上轻轻地吻着,丁玲脸上露出久违的祥和与满足……
五十春秋 问心无愧
1992年6月中旬,陈明再次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我将一份早已准备在身边的1992年4月16日的 《文艺报》 递给陈老,指着报纸第一版文章 《“丁玲文库”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 中的一段文字:
丁玲同志家属为“丁玲文库”捐献了丁玲藏书2110册,珍贵文物181件。“丁玲文库”占据两间房,一间按丁玲晚年在木樨地22号楼公寓里的书房兼卧室的格局,放着她的书桌、木床、衣柜、床头柜、坐椅及躺椅,另一间布置她的纪念展览室,放着她的藏书和各种文物。展柜中有丁玲的手稿,本人所作水彩画和速写画、证件、照片、斯大林文学奖状和奖章以及生前穿过的衣服鞋子……
话题就从这则消息谈起。
“‘丁玲同志家属显然主要是你吧?”
陈明点点头,指着客厅、卧室,兴致勃勃地为我描述“丁玲文库”的摆设。确实,在丁玲离开后,陈明不仅为整理编辑丁玲遗稿付出了心血,还给予了相关部门大力的支持。他曾多次请丁玲研究会的同志和丁玲过去的秘书到家里来,帮他整理丁玲的遗物,并将遗物分类处理。譬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等重要手稿交送北京图书馆;文学馆建成后,有些手稿、书信、照片等则要送到文学馆;也有的物件要赠给丁玲家乡的丁玲纪念馆。另外,上海的“左联”纪念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鲁迅纪念馆都有陈明整理和捐赠的丁玲遗物。
这次交谈,陈明主要讲述丁玲在事业上的成就,当然也不时地插叙一下他自己的感受。在我离京与他告辞的那天早晨,他取出早已备好且签上了他名字的《丁玲论创作》 和 《丁玲散文选》 两本书赠我。
1993年5月在我第三次赴京拜访陈明之前,看见一篇题为 《毛泽东与延安文艺》 的文章说,毛泽东曾叫人找来宣传大队 (烽火剧社) 的队长及陈明谈话,并留他们吃饭,后来主席还慷慨赞助他们200元,表示他支持当时延安的戏剧活动。对此我很感兴趣,拜访陈明时就询问此事是否真实,还有什么细节?
陈明激动地告诉我事情是真的。他说那时的延安上从我党我军的领袖统帅,下至广大军民都很热爱并支持革命文艺。同样,延安文艺界,包括蒋管区进步文人抗日救国热情也十分高涨。
正因为陈明的这种资历,他于1986年起就开始担任延安文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与文艺界的不少朋友都有往来,特别是与延安时期的老文艺家们联系密切。这个时期,除了潜心整理和研究丁玲的作品,他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处理一些其它工作,似乎有些不堪重负。于是,就在丁玲离去3年后,陈明与在中国科学院退休、曾担任过编辑的张珏生活在了一起。张系民国著名报人张友鸾之女,有很好的文化功底。婚后,她成了陈明忙碌生活中的理想伴侣和帮手。
离别时,陈老又赠我一本 《丁玲创作生涯》。这本作家生活与创作的自述,依然是他前些年呕心沥血一篇篇整理、一个个字校勘出来的结果。
“丁玲,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位评论家在书末写的最后一句话。我想,早已融为丁玲生命和事业一部分的陈明,自然也是属于人民的。
后来,我又获得陈明于2010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 《我与丁玲五十年》。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在该书结尾说“……半个世纪和她经历了人生的沉浮,尝遍了世间的喜怒哀乐,锤炼了永不后退的意志,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动摇后悔。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虚度此生。”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