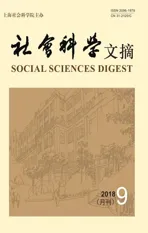国外学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争论与反思
2018-11-17
20世纪末至今,国外学界在认识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主要以“动机·行为·影响”为分析模式,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视角、理论、方法出发,展开了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并在中国和平崛起相关实践对既往争论的证实与证伪中不断反思,体现出明显的两阶段性。
西方政治思潮激荡中的“中国问题热”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潮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与视角,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在“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分化出三大研究学派,产生了新的研究热点。
(一)新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新的政治思潮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存在多种政治思潮的争锋与对峙,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超多强”历史新纪元开启,各国间“去意识形态”交往与合作才得以走向正轨。此时,国家安全方面的危机意识与和平发展的来之不易成为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声音逐渐弱化,国际社会转向正视生存与发展的残酷现实,力图探究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新突破口。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组织结构为背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潮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的修正与扬弃而活跃起来。其中,新现实主义以“霸权维稳”和“零和安全”理念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安全与“权力政治”的关系,认为国家间军事实力对比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根本,倡导以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安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各国的上层建筑造成的,强调文化、制度、观念等因素对各国国际战略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倡导通过建构国际社会共识性的规则、认同、理念来维护整体安全与发展。
(二)新的政治思潮分化出对应的研究学派
过去,国外学界倾向于研究国家主体的具体实践及其造成的现实影响,一定程度上缺乏能动性与预测性,日前,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它做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由此,“动机·行为·影响”的分析模型先于学派划分而产生。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分离,就始于它们对决定国际主体行为的动机认知出现差异。自此,新现实主义从“生存”出发,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发展”出发,建构主义从“认同”出发,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
然而,同样的立论点并不总能对应同样的结论,各学派内部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例如,新现实主义学派在“一国崛起是否势必称霸”的问题上逐步分化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规避”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和认为“各国竞相称霸将促成各方威慑制衡”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在“经济依存是否必定带来和平”的问题上逐步分化出认为“各国经济依存有助于各国外交稳定”的肯定派和认为“新兴国家势必为改写不公平国际规则而与既得利益国发生冲突”的否定派;建构主义学派由于过分看重规则、文化和理念的力量,导致对规则、文化、理念不够明确的新兴国家的认知较模糊,逐步分化出认为“新兴国家国际战略转型方向与影响不可预测”的困顿派和认为“新兴国家已接受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既定规则体系”的乐观派。
(三)“中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还是建构主义学派,都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是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保障。因此,国外学界尤其关注可能挑战或打破“一超多强”稳定结构的力量主体,即在全球化中崛起的新兴国家。
而在众多新兴国家之中,中国又有其特殊魅力:在历史文化和区域秩序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曾长期在亚太地区维持以朝贡制度为依托的“华夷秩序”;在意识形态与内外政策方面,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外与各国积极开展“去意识形态”的交往与合作,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地理位置与综合实力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天然具有发展制造业和作为世界市场的优势,近几年更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地位与周边环境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创始会员国之一,其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台湾问题上,还表现在与多国的领土和海域争端上。
由于多数国外学者在预测国际格局、分析国际关系时逐渐习惯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视角、理论和方法出发,因此他们也大多以此为基点研究中国。自此,国外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中国通”和“知华派”学者,在众多学派的交织与对峙中展开了长达30年的争论与反思。
“认识中国”和“预测中国”过程中国外各学派的争论与反思
伴随中国的国际战略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变为“奋发有为”,国外学者从各自学派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出发展开了长达30年的争论。其中,第一阶段的争论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测色彩,第二阶段的争论更偏重理性反思。
(一)第一阶段: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两场“臆测性”争论
1. 第一阶段的第一场争论
第一场争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彼时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一员。在这场新旧世纪之交的争论中,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是否应该抛弃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
一是以比尔·格茨(Bill Gertz)为代表的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中国政府不仅背叛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承诺,而且势必挑战美国霸权,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当局不能低估中国威胁;二是以安·安娜诺斯特(Ann Anagnost)为代表的学者鼓励中国开展积极外交,建构起符合自身实际的国际、国家、议题叙事,不应强迫自己吸收西方理念;三是以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迫于美国亚太战略而崛起,应继续韬光养晦,捍卫国内核心利益。
这个时期,国外学界普遍将中国定位为致力于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新兴力量,着重关注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国际战略转向。
2. 第一阶段的第二场争论
第二场争论发生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这场争论围绕“中国崛起是否威胁西方各国发展”展开,参与学者形成两方阵营。
一是以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 Steinfeld)为代表的学者否定了“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经济方面,全球化规则、理念已全面渗透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政治方面,中国已呈现西化的政治倾向;国际角色方面,中国作为区域发展的参与者,将共享西方的价值、利益和形态。
二是以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为代表的学者认同“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经济方面,中国遵循西方规则只因有利可图,其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病态自由主义”并非真正融入世界市场;政治方面,中国地缘政治野心膨胀,反抗西方民主政治渗透,必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文化方面,中国民族文化意识逐渐觉醒,一旦崛起便会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展示其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特色。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主要从中国崛起的经济影响出发,将中国看作现有国际秩序的潜在挑战与威胁。
事实上,第一阶段的争论源头在于“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模型中“行为”素材较少导致的“木桶效应”,即中国外交政策过于保守、国际定位不够明晰和尽可能搁置争议的做法,使国外学界只能根据经济数据和刻板经验臆测其战略动机和影响。其次,不同学派对动机的臆测差异是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否定派集中力量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崛起势必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肯定派、建构主义乐观派认为中国正积极融入全球化规则与体系,逐步西化为既有国际秩序和制衡力量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困顿派则由于对中国的国际战略理念、文化、历史认知不足,陷入“不可知论”的迷潭。
(二)第二阶段:围绕“奋发有为”的两场“反思性”争论
1. 第二阶段的第一场争论
第一场争论发生在中国国际战略转向“奋发有为”之初,彼时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场争论围绕“中国是否会在21世纪称霸”和“中国经济是否会走向崩溃”展开,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称霸论”和“中国崩溃论”的集体反思,其间形成两种不同观点。
一是以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称霸能力受国内外诸多因素制约。于内,改革开放累积的社会与生态矛盾集中爆发,且其军事实力不足以抗衡美国;于外,既有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已明显制约中国未来发展,且其不结盟外交也束缚了其称霸可能。
二是以安德鲁·胡瑞(Andrew Hurrell)为代表的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在国际秩序方面,中国崛起并不等于西方衰落,而是意味着共享治理式的国际秩序兴起,还需观望中国“双赢”策略是否有效实践;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具有政策、资金、技术、内需等优势,不会因过分依赖世界市场而走向崩溃;在国际角色方面,中国应在当前阶段承担起更多引领全球化的责任。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从内外条件、共治理念等角度,尝试反思中国内外发展境遇和国际责任,否定了中国在21世纪称霸的现实基础。
2. 第二阶段的第二场争论
第二场争论发生在中国以“一带一路”为突破点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国外学界围绕“这一战略是否可行、是否将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展开争论,形成两方阵营。
一是以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为代表的学者持否定观点,其论证方式偏重价值理性。他们认为,在文化方面,中国自古奉行“华夷秩序”,其“双赢”理念太过理想,且其至今未能明确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实务方面,其国际援助具有“新殖民主义”倾向;在国际秩序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旧有经贸与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大国博弈难以避免。
二是以巴斯·维维恩(Bath Vivienne)为代表的学者持肯定观点,其论证方式偏重工具理性。他们认为,在区域发展方面,“一带一路”试图建立协调式单边主义,保持经济带内经济增量、区域安全和资源整合;在拓展趋势方面,“一带一路”早已超出了“经济边界”,有深入文化、社会交往的趋势;在实践性质方面,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正帮助非洲走上“去殖民化”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已不再囿于中国是否称霸等既往争论,而是在肯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国际战略布局、实践、成效,反思其动机、性质、影响和未来发展。
整体上看,国外学界结合不断丰富的中国“行为”素材,遵循“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模型,在反思既往臆测中展开新的争论,对中国大多抱有既期待又紧张的心理。此外,不同学派对中国和平崛起和国际战略转型的认知有了新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肯定派认可中国对国际社会安全与发展秩序的维护与责任;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对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对区域冲突持消极态度;新自由制度主义否定派一方面肯定中国国际战略的正面意义,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建构主义学派在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可行性上发生分歧,其中,困顿派认为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建构及其角色定位仍然模糊。
国外各学派“从争论走向反思”的研究审思
30年来,国外学界对中国和平崛起之争论与反思虽然存在误解,但总体上看,却为人们理性认识中国和平崛起、正确预判世界未来格局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外学者在“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模型、多样化研究视角、综合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了自身特色。
首先,这场争论与反思对于实现上述目的起到了积极作用:理论层面,这场争论与反思逐步改变了国外学界对中国的刻板认知,使其尽可能理性看待新兴发展力量的作用,并结合共赢、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革新,增强了其现实解释力与回应性;实践层面,多元研判中国等新兴力量的未来发展,有助于各国抛弃过去单一的争霸思维,而通过了解国外学界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变化,中国等新兴发展国家才能从侧面丰富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认知,并正视自身问题,及时把握国际局势变化和他国政策转向,展开适应性变革。
其次,这场争论与反思也暴露了国外学派各自研究的不足:一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否定派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困于“零和安全”的惯性思维,将新兴发展力量妖魔化为西方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违背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规律;二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肯定派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学派或片面强调中国的责任与重要性、忽视国际社会整体发展应是多国共同推动的事实,或放大中国的威胁性、呼吁各国合力限制中国的发展;三是建构主义学派过分强调已发生或存在的规则、历史、理念,易陷入“不可知”的漩涡;四是极端宗教、国际组织、国际资本涌现,学者们却仍将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理论研究明显滞后。
最后,这场争论与反思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深化国际战略理论研究。内容上,深化对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实践经验与发展规律的研究;警惕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多元化政治思潮的影响;积极、及时、有力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与争议,并通过战略实践与实效增强回应的可信度;方法上,学习与借鉴“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模型,以多样化研究视角、综合研究方法展开实务层面的实证研究,增强理论的时代性、阐释力与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深化国际战略问题与实践研究。既要正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又要把握国际组织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局势越发复杂的现实;既要坚持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合作的和平发展道路,又要对有可能爆发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危机做好应急准备;既要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大国博弈与区域摩擦,又要勇于承担联合各国共同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责任;既要尊重与包容世界文明多样性、认清政治思潮多元化的现状与趋势,又要在世界文明交往中兼收并蓄,在冲突争议中寻求共识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