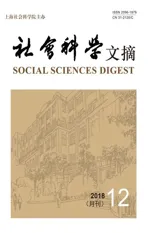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2018-11-17
研究问题与文献起点
中文“公益”一词在今天是常见用语,基本表示“公共的利益”,并常与“慈善”连用而呈现“公益慈善”的整体表达。据朱健刚的梳理,当代公益慈善研究主要由三股思潮构成:第一股是以慈善为主题的研究,在中国语境中多理解为慈心善念的驱动,具体表现为好善乐施与好人好事;第二股来自对民间组织的讨论,研究对象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大量并未注册或非正式注册的志愿团体,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主要聚焦“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及有关市民社会的种种可能;第三股则是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路,公益慈善既是政策的关注焦点,亦是政策法规的专门用语。
以上三股思潮中,第二股思潮的影响尤为显著,故相关研究对于中国当代公益的理解也较多地参照西方学界对于“philanthropy”以及“public interest”的界定与阐释。其中,对公民性、志愿性和公共性的强调与第二股思潮的旨趣彼此呼应,逐渐形成以公益慈善领域探讨当代中国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的研究脉络。
与此相应和,历史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向近代公益转型的研究亦与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术语勾连对接,但基本认为明末以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并未形成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那么,中国近代公益在其诞生之初究竟蕴含着怎样一种新型的公共意味?这一问题始终模糊不清,因为学界对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公益”具体何时出现及其话语构造的现代特性尚未展开充分研究。
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公益的解释大体呈两种路径。第一种即以当代公益观念或西方“philanthropy”或“publicinterest”的理解来整合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实践,于是历朝历代皆有例可举,多指建桥修路、围堤筑坝、出资教育、赈济灾荒等关涉公共福利之事。但记载这些史实的原始文献语境其实并未使用“公益”二字,而是多用“义行”“义举”或“善举”。
第二种则将“公益”视为中国整体发生近代转型过程中一个子领域的转型产物,基本沿用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界进行论证,故将清末民初视作中国传统慈善向近代公益转型的发端,并从中阐发了慈善思想与观念从“重养轻教”转向“教养并重”、实践主体与关怀范围由富人精英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转变为普通公民对广泛社会议题的回应,以及筹款融资方式的多样更新等“近代”特征。然真正与“公益”二字连用的事物究竟何时出现?它们具体所指何事?上述两种路径的研究仅零星涉及。研究者们发现,中文的“公益”概念似乎在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
如果中文“公益”概念果真自清末这一现代国体开始生成的时段出现并普及,那么“公益”语汇的内部构造必与当时国家话语的建构及其现实基础有着错综复杂的逻辑关联。因此,本文将从概念谱系与思想观念的角度入手,尝试回归中文“公益”使用普及之初的时代语境,在其概念视野具体化的展开之中,进一步厘清中国“近代公益”的本土脉络,探索晚清慈善领域内部诸种近代特征之间的结构联系及其可能揭示的“新型公共意识”之实指。
中国本土的“公益”概念
学界基本认为中国“公益”的概念自日本舶来。刘珊珊的发现则将舶来时间从20世纪初提早到戊戌维新。至于“公益”一词是否具有本土渊源,仅有一点模糊不清的蛛丝马迹,让人难以判断。笔者进行了专门留意,发现“公益”二字的确在甲午海战以前就已经连用,并且形成了至少三种主要的语义用法。
(一)经济收益
第一种是作为金融语汇,表示共同的经济收益。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公益”二字与表示商行或金融机构的名词连用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如“公益洋行”“公益当铺”“公益汇利公司”,等等。作为金融语汇的“公益”主要表示集资者或参股人共同的经济收益。
(二)地方公事
第二种用法主要表达涉足地方公共事务的士绅善举。在1884年贡生冯骥声为户部四川司主事举人陈尹东所撰写的一篇墓表中,即有“公益”一词。墓表历数陈氏种种地方善举,既有善待异母兄弟与组织建祠修谱等家族事务,亦有书院讲学、赡养友人遗孤、救助贫困乡亲、排解纠纷和立定乡约等家族之外的地方事务,最后全部归结为“种种公益之举”。由此可见,墓表语境中的“公益”之“公”是包含了家族事务在内的地方公事,其实践主体士绅亦往往具有“族长、地主和道德(知识精英)三重身份”(金观涛、刘青峰)。因此,这一语义所对接的现实空间,乃是以家族及其精英代表为本位的一种地方公共空间。
(三)国家利益
第三种是作为法律语汇,主要表达国际交往间的国家利益。这一用法始自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该书译自美国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将惠氏原著与丁氏译本两相对照,可知译文中出现的8次“公益”所对应的英文表达其实各不相同。具体可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表达国际交往间的常例与习惯;二是表达与私人利益相对的国家利益;三是表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有利益。由此亦可知,最早与西文进行对译的“公益”更有可能为中文语汇,而非日语。
中国“公益”语汇的观念资源
(一)思想观念中的“公”
既往研究发现,中国的“公”观念的两组关键雏形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第一组观念成型于战国中期,有通众、普遍、平等、平均之意,经常与“平”连用,指涉范围极广,涵纳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故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经典名句,与表示“自环”“偏也,侧面于人,掩匿其奸”的消极之“私”全然对立。第二组观念源自甲骨文,形似王宫建筑,有祖先、尊长、国君、朝廷之义,春秋晚期以后,逐渐表示朝廷、政府和国家的公务,形成“国家之公”。其中,表达“天下之公”的第一组观念势力最强,贯穿整个中国的思想主脉及其在各个时期的不同流变。
(二)民间日常中的“公”
中国本土“公益”中表示“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观念渊源已经比较清晰。那么,表达“经济营利”的“公益”将作何解释呢?沟口雄三曾专门指出,“天下”与“国家”这两组基本的“公”观念其实还只是对“士大夫、知识分子头脑中酝酿和继承下来的治世观念、秩序思想”的梳理,它们与民间日常的“公”之间有明显鸿沟,并不能直接反映“生民”的现实生活。对此,沟口举了一个例子,即宗族内部的“公业”,但未做出具体解释。
日本“公”的观念相对单一,仅有中国“公”系统中的第二种类型,即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之公。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在沟口看来,直接决定了两国近代转型的深层走向。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动立宪,尽管改变了国家权力的构成,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其“公”观念的最大极——国家,而是将王权与国家的关系作了调整。中国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明末以后,“天下”作为“公”观念的最大极,不仅逐渐压倒了王权式的国家,还反过来成为赋予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换言之,抽象的“天下”观念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制度。于是,如何重构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公私关系成为实现这一转化的逻辑重点,其中个体、国家与地方关系的逻辑关联与内在张力亦大体统摄了戊戌维新以后中国“公益”语义的重构格局。
戊戌维新以后的“公益”语义
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中搜索“公益”一词,库内出现的最早记录是1903年,随后频率逐年上升,1908年以后成为高频用语。此间,清廷主动实施新政,废除科举,预备立宪。与此同时,各地起义不断,革命蓄势待发,直至辛亥鼎革,帝制结束,可谓“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可知,来自日本的“公益”概念与中国“公益”概念的原有格局正是在这剧变的十年之间发生互构并得以普及的。那么,这一时期的“公益”主要表达了哪些内容?
(一)地方公事
首先,前述陈尹东墓表中所列“地方善举”的语境依然沿用,以表达传统精英对地方事务的承担。同一时期,随着新政施行,各地发起易风俗、兴学堂、办实业、治警察、行征兵以及地方自治等多项举措,这些内容逐渐成为地方公益的重要组成。表达“地方公益”的语汇成分一方面继承了原有的语义内容,一方面展现出与清末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新生内涵,且新生部分所论及的公益实践主体日益多元,既有传统士绅,亦有志士、留学人士甚至普通乡民。事实上,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和教育,使之具有权利观念,明白国家乃“君与己共之”的道理正是新政的核心目标之一。
(二)启迪民智
在当时,开设阅报社和举办演说会是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的常见途径。1906年,《时事画报》报道两广总督周馥路过江南地区,见到“东西各国报馆林立,虽厮养走卒,无不阅报”,故而感到“人人明义务、知公益,而合乎立宪国之资格……”。1907年,四川洪雅县的杨氏家族创立“公益书社”,开放家藏古今书籍,“任人阅抄,并添购时务书报多种,务期开通智识”。1911年,三位志士欲在京城会友轩茶馆组织阅报社,《浅说画报》称他们“热心公益”。与这一系列蓬勃实践相同步的是当时风行的群学理论,旗手正是梁启超。1902年,他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告白即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三)爱国合群
随着群学理论的流行,强调爱国合群、戒除自私自利的“公益”用法也日渐成为主流。新政时期颁布的《大清光绪新法令》即将“公益学”列为大学堂的修读科目,并附有专门解释:“日本名为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专讲公共利益之礼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1903年,郑贯公等人在香港创办《世界公益报》,专门说明“本报为国民代表,乃社会之公器,而非一家之私言”。时人亦开始撰文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实践可以称为“公益”。
(四)地方自治
与新民的塑造同步,培养民众参与实际治理的政治实践也自戊戌时期开始兴起。成立于1898年2月的湖南保卫局和南学会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自治组织。1903年,攻法子撰文阐发“欲养人民奉公之念,莫如使之从事于公共事务,使人民无(此处疑应为“有”——作者注)参与公共事务之机会,则不至人人依赖国家,谋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国家之公益”的道理,明确指出自治乃“代议政治之基础”。随后,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中山等人亦纷纷撰文论述自治与宪政之关系,认为“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1906年,端方、刘直等人将地方自治作为预备立宪之基础提上新政议程。同年,一些以“公益”冠名的自治团体开始出现。1908年底,清廷仿效日本《市町村志》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明确提出,“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章程所列“地方公益事宜”包括本城乡镇之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以及各种善举,“公益”遂成为自治语境中的高频用词,同时引发了有关民间公益与自治公所管辖范围的讨论。这说明新政部门与民间公益团体的角色正在发生重叠,亦表明中国近代公益的开端即包含了地方共治的深刻意涵。
(五)铁路利权
甲午以后,日本被允许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欧美列强“利益均沾”,亦先后在华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展开利权争夺,掀起瓜分狂潮。清廷虽意识到筑路之重要,却苦于资金短缺,商界无力,只得借款筑路。1897年1月,清廷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专门负责借贷洋款筑路。1898年8月,清廷成立矿务铁路总局,改变思路,鼓励铁路商办,但仅过一月,又会同总理衙门宣布铁路建设由中央统筹规划。反复之中,中国路权几乎丧失殆尽,激起举国公愤,收回利权运动遂于各地相继爆发。自此,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次第成立,筹款宣传之中,表示国家利益的“公益”成为高频用语。铁路语境中的“公益”经常游走在具体的地方利益与抽象的群体利益之间。
(六)经济收益
最后一种“公益”沿用前述的金融语义,表达共同的经济收益。此外,正如表达“地方公事”的语义在延续原有内容的同时还衍生出与清季十年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新内容,“公益”的经济语义也发生了相似的重构。1908年底,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缴纳“公益捐”者可以成为选民。自《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出台后,“公益捐”作为地方自治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政府公牍与法律文书之中,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
结语与讨论
本文从概念与思想的角度入手,爬梳中文中“公益”的语源流变以及与此同步的观念再造和社会现实,从中形成如下三点主要发现和研究启示:
其一,中国近代“公益”观念实则是嵌入在明清之际公私问题与群己关系不断重构这一漫长过程中的一项子过程。因此,它的具体生成涉及长时段的思想变动以及复杂多次的跨国互动,并非简单地藉由维新风潮舶自日本。
其二,清末新生“公益”语义的现代特质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支持政体转型的群学理论与变革实践,另一方面亦承载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实际张力。在此过程中,国家力量与地方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及其对“公”资源的争夺,直接导致了新生“公益”语义呈现出趋向“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两个走向。
其三,如果以中文“公益”的近代使用和普及时段作为理解传统慈善转向近代公益的一个面向,那么戊戌以来的维新人士以及后来扩大到各种身份的“志士”乃至商人、平民和女性基于公民意识而开展的非营利实践,可谓中国近代公益的开端。这些个体尽管身份各异,甚至怀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主张,但他们所共享的群学理念其实极大地贯通了社会公众与国家政府的共同利益。当时的“公益学”也因而等同于“群学”或“社会学”,既为“天下”向“国家”的转化提供最为实用的“公”之资源,亦为培养现代制度的基层土壤提供学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陈若水所言晚清“公益”所带动的“新型公共意识”,之所以“新”便在于其对现代国体的明确意识与推动转型的切实努力,但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社会与国家的局部同构。这一同构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国公民性在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养成,或能为今天探讨公益慈善与公共精神提供一种关注本土内生属性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