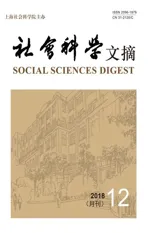论田野哲学的兴起
——兼与张卫博士商榷
2018-11-17
田野哲学兴起的背景
张卫博士在《哲学在行动:当代美国“田野哲学”的崛起》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认为,“‘田野哲学’的兴起与美国当今社会‘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盛行有关”,“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田野哲学’即在此种语境下应运而生”。但本文认为,田野哲学兴起的背景并非“新自由主义时代语境”,而是西方哲学危机的加剧。
(一)学科哲学与哲学的危机
当代西方哲学被看作是在学院存在的、仅仅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一门学科,“如果哲学想在学院占有一席安全之地,它就需要有自己的独立领域、自己的专业语言、自己的成功标准、自己的信息传递者和自己的专业化问题”。哲学愈发想在学院寻得安全,就愈发需要变得“独立”、“专业”,愈发需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属于“自己的”更加系统、独特的学科特性。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学科化”的过程。当哲学学科化到形成“排他性的单一文化”时,就把自己完全限定在学科(或学院)的高墙深院之内,把自己完全与高墙之外的其他学科和生活世界隔离开来。这样,哲学就纯粹成了一种哲学同行们用特定的行话术语(通常是晦涩难懂的)为彼此或自己写作的内部游戏。至此,哲学完全成了“学科的俘虏”(disciplinarycapture),哲学就只是学科哲学。
学科哲学,亦即当代西方哲学的这种内部游戏,由于其排他性的单一文化,而使其过度专业化和职业化。过度职业化的结果,可以借用梭罗的话来描述:“如今有许多哲学教授,但没有哲学家。”过度专业化的结果,可以借用奎因的话来描述:“说到有机化学,我承认它很重要,但我对它没有兴趣,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哲学外行们应该要对我关注的哲学问题感兴趣一样。”过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哲学只在学院存在,哲学家作为学科专家也只在学院活动。在哲学家曾经活动的生活场所再也不见哲学家的身影。这表明哲学脱离了日常生活,丧失了关注、批判现实世界的能力,更遑论改造世界了——哲学已经背离了它的本性,这造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危机。
说当代西方哲学正在经历的危机是学科哲学的危机,并不是说“学科哲学”本身就是危机,而是说学科哲学的排他性的单一文化造成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当西方哲学经由学科化而成为学科的俘虏时,当西方哲学只是学科哲学时,西方哲学就背离了其本性和根本任务,就产生了危机。
(二)新自由主义时代与哲学危机的加剧
西方哲学的学科化仍在持续,它排他性的单一文化也仍在蔓延。在今天弥漫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西方社会,学科哲学的命运如何?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由追求真理转变为追求利润,大学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变为学术资本主义。而且,大学形成了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不发表,就出局”的研究审计文化,出版物成了“资本”的等价物,大学教师为达到预设的“目标”或“关键业绩指标”。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沦为边缘学科的哲学和人文学科出现了知识生产过剩现象,从而造成了一种学科繁荣的幻相。绝大多数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出版物无人问津,更别说要产生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了。今天的哲学家已经背离了苏格拉底赋予“哲学家”的“牛虻”的社会角色。
对这种知识生产过剩现象,政府和社会用新自由主义赋予的经济理性思维方式(如成本/收益分析)去考量哲学的投入和产出——一如考量自然科学那样。虽然哲学以“学科”的形式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了,但外界(政府和社会)却对哲学学科做出了反应:大幅减少资助、选择不报考、严格控制教工数量等。然而,高校的哲学院系、学科哲学家们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各种财政资助和学生的学费得以维持的。所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学科哲学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哲学的知识生产过剩这种学科繁荣的幻相,其实是对哲学危机的一种遮蔽。哲学学科从知识生产过剩,到资助锐减、招生和学位授予数量下降、教工数量减少等的事实,反映了学科哲学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艰难境遇,也凸显、加剧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如果学科哲学继续躲在高墙深院里玩与生活世界无关的内部游戏,继续无视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要求,那么,长此以往,学科哲学便会终结。
面对西方哲学的危机及其加剧,美国学者罗伯特·弗洛德曼(Frodem an R.)、亚当·布瑞格尔(Briggle A.)等认为,哲学需要冲破学科化枷锁,从学科的俘虏中解放出来,需要走向田野,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哲学家需要在书房和图书馆之外的场所工作,需要与科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公共机构及社区人群一起在项目层面上做哲学,需要在学科外的世界通过对社会需要的回应而增加工作价值。
田野哲学的内涵
张文认为,“‘田野哲学’是美国近来兴起的一种从事哲学研究的新理念”,是“元哲学理论”。本文认为,“田野哲学”是一种从事哲学的新理念,但它更是一种哲学实践。田野哲学充满了浓厚的实践性。田野哲学的内涵,需要从“规定性”和“机制”两方面去把握。
(一)规定性
第一,定位。田野哲学的定位,是哲学家以尽可能开放的态度,从哲学维度参与现实的社会问题,从而充当“沟通学院哲学和无形的、不断发展的技术化‘文人共和国’的桥梁”。弗洛德曼和布瑞格尔给“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技术化的‘文人共和国’”指代当代西方社会生产知识的校外场所,其边界是可渗透的和不断变化的。对于田野哲学家,确定某种理论、进行学术争论或探求矛盾和意义是他们可能要做的,但他们必须要做的是介入具体的决策过程。哲学家保持开放的心态,把自己的视野不要限定在哲学学科内,积极应用哲学知识,运用哲学思维,通过发现、挖掘、阐明、讨论和评估等方式去参与处理社会实际问题。这就是哲学家走出“学科”的高墙深院,走向“田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田野哲学家需要在学院哲学积累的哲学智慧、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田野哲学家要积极介入到技术化的文人共和国所关注、研究的社会问题中去,比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全球化、新媒体以及人类基因组重塑的可能性等,所以,田野哲学充当着沟通学院哲学和技术化文人共和国的桥梁。如是,哲学便逃离了学科的俘虏,哲学也就不只是学科哲学,还包括非学科哲学,即田野哲学。
第二,研究方式。田野哲学主张包括跨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以及哲学学科在内的“多学科”或“后学科”的研究方式。“田野”就是多学科、后学科的实践及作用的地方。田野哲学应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的或“超学科”的研究方式,其实就是在“去学科化”。可见,田野哲学是在“破”“学科化”。另外,田野哲学要通过“破”“学科化”去“立”某些东西,但要“立”的东西并非“跨学科”。“跨学科”只是田野哲学所凭借的研究方式之一,是手段,并非目的。
第三,受众。田野哲学的受众由各种非哲学家群体构成。田野哲学家并非“公知”,而是从事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的“实干家”。“受众”一词能表明田野哲学实践的多样性:田野哲学家们不只是为非哲学家群体而“说”,还为其而“写”、而“做”。更重要的是,“田野哲学家与非哲学家们共同合作生产知识”。与田野哲学家们共同合作的非哲学家们主要指“面对现实生活问题的非学科利益相关者”,双方共同合作生产的知识“在使用的语境中产生”。
第四,制度配置。“田野哲学”作为一种新事物,目前还不具有成型的制度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去学科化哲学,田野哲学的制度配置不是现有的学院体系,或着说,不是学院体系的现有状态。田野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田野哲学“驻留在现有机构的边缘,穿梭于学院和更广阔的世界之间;但也在学术界和不同的实践社区寻求自身的制度化”,“应该包括反思自身的制度现状,确保有适当的标准和程序在适当的地方去评估非学科实践”。这是对田野哲学的制度配置的大致构想。
第五,评价。由于田野哲学是“去学科化”的,所以,评价田野哲学的标准不能与评价学科哲学的标准完全相同,即不能完全靠传统的文献计量学来衡量。在整体上,学科哲学的标准是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田野哲学的标准是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田野哲学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种继承。田野哲学家倡导一种由受众定义的非学科指标方法——替代计量学。
(二)机制
田野哲学是在“中观”维度运行的,即田野哲学家在项目层面上进行哲学实践。田野哲学家的工作从非哲学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开始,为问题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从哲学视角提供一种公正、文明的对话模式,寻求做出具有时效性的、根据多学科的标准而被认为是成功的贡献。最初,“问题”是什么,其解决办法是什么,都是由非哲学行动者界定的。哲学家会对此再进行周全的慎思,并与非哲学行动者就此进行进一步交流,以促成、推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最终协商解决问题。在交流、对话中,哲学家通过鼓动、提示、追问、启发和建议等精神助产方式,使利益相关者提出他们自己对问题的答案。哲学家不提供答案,提供答案的是专家和科学家。当然,哲学家有时候也提供答案,“但这应该服务于哲学的质疑功能”。这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生成而非既成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家的智慧、激情、技能与社会的需要相重叠,最终也会产生社会影响。在结束了一个田野哲学项目之后,田野哲学家会回到学院充电,准备开启下一个项目。田野哲学家通过这样的哲学实践而确证自己的存在,同时也扩大了学院哲学的领域。
田野哲学是要“破”哲学的“学科化”,并不是要否定学科哲学。相反,田野哲学家们“坚决支持理论哲学、学科哲学”。田野哲学家参与解决项目问题的智慧、知识和技能主要来自学科哲学。他们在田野与书房之间、实际与理论之间、实践与思想之间、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之间无限地辩证循环。这是田野哲学家与学科哲学家、哲学家官僚的本质区别。“哲学家官僚”这个术语,是弗洛德曼和布瑞格尔受“哲学王”的启发而创制的,指“虽然受过哲学教育,但却离开了学院,永久工作在公共或私营部门”,且“致力于制度层面的哲学家”。他们认为,21世纪西方哲学的生态系统应该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学科哲学家、田野哲学家和哲学家官僚共同构成。这比当前学科哲学排他性的单一文化更健全和富有弹性。
对田野哲学的评价
张文认为,田野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是对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传统和中国哲学中实践精神的回归,是对西方‘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的超越。”本文认为该评价不够中肯,田野哲学应享有下述两份“殊荣”。
(一)田野哲学为哲学实践争取与学科哲学相同的地位
田野哲学不仅注重实践,更注重田野哲学家们以何种形式进行实践。个体形式的哲学实践活动相对于学院体系来说是“例外”而非“例子”。田野哲学要在组织层面以哲学组织机构普遍、正式认可的形式运行。
哲学实践早已有之,但真正意识到哲学实践的制度配置问题,并努力进行制度化的,是田野哲学。“目前的情况是,非正统的实践者(这是他们的自我认定)处于边缘化,过着格格不入的职业化生活。”这里,“非正统的实践者”指没有制度归属的哲学实践者。田野哲学倡导进行组织层面的哲学实践,是要把田野哲学和田野哲学家从制度上纳入学院哲学之中,从而获得与学科哲学一样的“正统”地位。
田野哲学的制度化是一项十分复杂且艰巨的任务,因为哲学的制度化“关系到哲学家的所有方面:如何写、为谁写,何为‘真正’的哲学工作;吸引什么样的学生,如何培养他们;雇用谁,谁晋升为终身教职等”。在具体操作层面,大学现有的学科哲学的“学院”体系需要做出改变。从课程设置、学生培养目标设定,到教师工作考评办法、终身职位晋升标准等,都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需要在社会系统内发生。
在组织层面进行哲学实践,积极追求哲学实践的制度化,是田野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类型哲学实践的本质特征。田野哲学家要在组织层面进行哲学实践,就如同学科哲学家在组织层面进行哲学研究那样。田野哲学要把那些一次性的、个体的哲学实践者,或者进行一系列一次性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家,通过制度化升级为稳定的、成熟的、富有更大影响力的哲学实践共同体,要为哲学实践建立稳定的制度文化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田野哲学为哲学实践争取与学科哲学相同的地位。
(二)田野哲学为哲学在商业社会里寻找光明的未来
学科哲学宅在哲学院的高墙大院内,靠渗透(rickledown)模式或机缘巧合(serendipity)模式,等待哲学的学术价值慢慢地、自然而然地产生社会影响,或者等待社会组织、个人等“有缘”者自行、自由提取需要的学术成果,从而把其内含的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影响。“影响从来不是有意要产生的,但它们总会产生。”于是,哲学便是“无用之大用”。田野哲学则不以为然。田野哲学家必须走向田野,在社会中积极搜寻、发现机会,并通过哲学实践的方式,主动把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影响。田野哲学家不仅要掌握、了解哲学知识及其学术价值,还要掌握如何实施和调配这些价值。如此,哲学便“有用”。
田野哲学更注重社会影响而非学术价值。它所注重的社会影响被称为“更广泛的影响”(Broader Impacts)。田野哲学家认为“更广泛的影响”是“运用在学术价值方面所发挥的创造力,去阐明和确定研究结果对社会带来好处和对实现不断增加的社会需求的可能性”。田野哲学家所进行的田野哲学实践项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项目”。在项目结束后,田野哲学家可能没有发表一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但没有关系,田野哲学实践项目的“结项”并不以学科同行的评议为准,而是以“更广泛的同行”所受到的影响为准。在学术期刊发表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并不是评判田野哲学家工作的唯一甚至最重要的标准。田野哲学家的广阔天地在田野,在田野他们会大有作为,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更确切地讲,田野哲学注重的是“更广泛的影响”中的“好影响”。田野哲学家认为,许多研究、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在结果上都不全是好的,往往具有混合性。因此,他们认为“问责文化、更广泛的影响制度或负责任创新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是进步,即,什么是好的影响。”田野哲学家考量“好的影响”,并不是以某个利益集团或组织的利益为中心,而是尽可能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中心。田野哲学注重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中的好影响,这说明田野哲学注重社会的“需求侧”,体现了田野哲学家更注重社会责任。这是在积极回应国家和社会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哲学、哲学家的希望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田野哲学为哲学在商业社会里寻找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