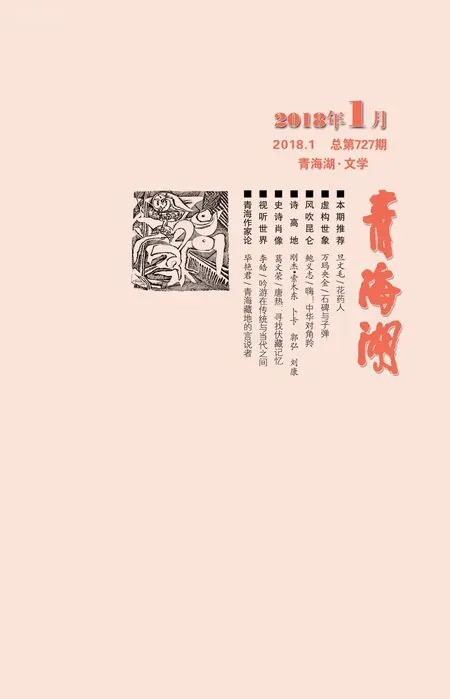眉户戏,家乡的戏(外三篇)(散文)
2018-11-15周尚俊
周尚俊
眉户戏,根植于陕西,流行于西北,也落户于青海河湟。自从它流传到青海东部这块肥沃的大地,就与河湟人民的生活紧紧地联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两百多年来它渗透在河湟大地的角角落落,响彻在河湟两岸的山山野野,活跃在农耕庄户的道道巷巷,流连在东部农区的男男女女,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孕育出新的文化底蕴,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一种戏剧、一种音乐、一种文化,能够接受于一些人们,渗透于一个人家,扎根于一些地方,就是地方的。眉户戏融入河湟文化,成为河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为这种戏剧文化与河湟土壤有着天然的关系,在渗透中生生不息,在融入中发扬光大。因此说,眉户戏,是家乡的戏。
青海河湟民间有句俗话:“有钱没钱,光光头过年。”还有句俗话:“锣鼓不响,庄稼不长。”“不管社火耍不耍,眉户戏必定要唱响。”从这些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河湟人家对“过年”与“唱眉户戏”的重视。因为什么?新年,是日月轮回中新一年的开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河湟人家通过辞旧迎新寄托对新一年的希望。在已流逝的岁月里,尽管为柴米油盐操劳得精疲力竭,尽管为衣食住行奔波得万苦千辛,尝尽了苦辣酸甜,领够了人世沧桑,但新的一年一定是美好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还因为什么?眉户戏,是自己的戏,它演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说的是老百姓掏心窝子的话,讲的是方言方语,唱的是乡音乡韵,表现的是家长里短,演绎的是人生哲理。一个动作、一句话语,令人捧腹大笑,忍俊不禁,活脱脱是一个文化大餐,把一个春节过得有滋有味,把一个年节搞得红红火火,把一个地方带得热热闹闹,把一片希望托得高高升起。
农耕人家需要这样的戏曲,农耕文化适应这样的艺术。这种戏曲找几人就可以学起,拉几天就可以演出,而且由于中国传统农家生活中的传帮带使每个人起码都有点演唱基础,小小的时候就经历了这种文化熏陶,人人都能哼几句、唱两段,再加上舞台可因地制宜,戏曲服饰简化,化妆粗浅条,因陋就简,随便的一点代价、一些努力,一场眉户戏的演出便可随着锣鼓家什的敲响、乐队音乐的奏起粉墨登场、咿呀开始了。
眉户戏是属于年节的。每一个新春的来临,河湟人家人人关注的是社火,个个期盼的是眉户。富裕农家在眉户戏的说唱逗笑中感受生活的幸福美满,日子的和风细雨;贫苦人户在眉户戏的敲打伴奏里体验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岁月的艰辛历难。高兴的人在演唱声里寻找着生活的红火希望,愁苦人在伴奏声中感悟着生命真谛。一年之计在于春,看完了百看不厌的眉户戏,赏够了经久不衰的社火剧,他们便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耕种,很现实地面对生活、面对自然、面对命运。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一年排练的锣鼓响起,道道巷巷的农户人家不论男女老幼常常钻进排练场,或站在凳子上,或扒在窗子上日日看、夜夜观,毫不错失,毫不缺席。尽管他们已知道演出的全部内容,熟悉戏剧的全部戏文,掌握演唱的所有技巧,明白调腔的所有音节,尽管被每一出戏中的滑稽搞笑笑过无数次,但对每一次演出,不管是自己庄子上的,还是邻村的,都看得非常重要。每当社火队的锣鼓一响,他们闻风而动,早早地站好了位置,焦急地等待着拉幕的那一刻。当看到精彩处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乐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跟着戏剧的情节、台词、唱腔、动作,心与身一起舞动,眼与脑一并用心,真是不知道此时谁在演戏,谁是演员。说穿了,这会儿他们不是在看,不是为追求新鲜,而是自己在动,只图过把瘾。古老的乡村戏在庄稼人的心中扎了根,这些历经岁月磨砺的民间艺术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石,成了正月里精神聚餐的一种民俗、一种流行、一种必备的活法。
眉户戏是属于老百姓的。它活跃于乡土,扎根于民间。像河湟谷地农户人家饭桌上的红辣椒,缺了扫兴,少了无味,哪怕饭餐中很少有鸡鸭鱼肉,但不能缺红辣椒;更像湟水沿岸漫山遍野盛开的馒头花,虽为野花,但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每一个春天的过去,每一个夏天的到来,如果看不到馒头花,哪怕天再蓝,地再绿,庄户人家是感受不到真正春天的来临、夏天的光顾,日子的有滋有味。在河湟大地,唱“花儿”跟唱眉户戏一样,老百姓别无选择。夏天的漫“花儿”,冬季的唱眉户,叫老百姓过上两把瘾。唱眉户,他们唱的是希望,“从今后不要赌要把个人做,到明日要努力定把个家业建”。他们从初六七唱到正月十五,甚至唱到二月二,把所有的戏唱完,把所有的乐取尽,“二月里龙抬头,犁铧遍地走”,于是拾起犁铧,播种庄稼,也播种希望。唱“花儿”,他们唱的是收获,“东方红拖拉机你开上,收割机后面儿连上,我把阿哥紧跟上,丰收的花儿漫上”。整个夏季,河湟两岸,山野田园,到处响彻的是“花儿”,流连的是“少年”,直唱到大通的老爷山、乐都的瞿昙寺,唱得花儿火红,唱得麦穗泛黄,尔后走进秋季,走进沉甸甸的庄稼地,收割庄稼,也收割梦想。这就是“花儿”、眉户与河湟百姓的不解之缘、难舍之情。他们说“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
生于斯,长于斯。它与黄土地紧紧相连,它与老百姓心心相印。它成了没有走出农家院的乡妹子,它成了长在田野里的青稞穗,真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深度加工,具有馒头花般的野性与纯洁,具有黄土地般的裸露与无遮。它的曲调耿直流畅,它的语言原汁原味,它的唱腔激昂动情,它的白口土里土气,没有故弄玄虚,没有装腔作势,有的是真真切切,有的是酣畅淋漓,在这儿能嗅到湟水河的清秀,能闻见黄土地的芳香;能体验到灶房里柴火的炽热,能感悟到炕头上驴粪蛋的暖温;能回味到多年前日晒天旱颗粒无收上山打柴艰难度日的窘境,能感受到至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粮食满仓的心悦;能想象到新婚之夜新男处女遮遮掩掩推推搡搡的羞恋,能发现到寻常人家平常日子妯娌小姑婆婆儿媳磕磕碰碰真真假假的互依。说到底,这种戏是老百姓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老百姓的戏,老百姓就在这样五味俱全的生活里,就在这样流连忘返的戏情里延续着生命,追求着幸福,也感受着苦乐。
眉户戏是属于河湟大地的。湟水河流经的海晏、湟源、西宁、互助、平安、乐都、民和,原则上称河湟谷地,而广义的河湟大地指的是青海东部的所有地区。这块青海东部肥沃的土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有肥沃的田野,有辽阔的草地,有一望无际的平川,有波澜起伏的山峦,有火红的红辣椒,有金黄的油菜花,有香美鲜嫩的牛羊肉,有肥壮厚实的山药蛋。这块土地孕育出的河湟文化更是星光灿烂,五光十色。大通的“花儿”会、贵德的梨花节、西宁的平弦戏、互助的轮子秋、湟中的酥油花以及乐都的射箭赛马,还有绽放在东区山山野野的花儿,形成了河湟文化的多元品牌,造就了河湟人们的精神食粮。眉户戏就在这样的多元文化里与河湟大地融为一体,在如此文化情缘中与河湟人家打成一片,裸露得像黄土地,流长得像湟水河,淳朴得像山里人,芳香得如馒头花。不是雾里看花,而是贴近如身;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触手可摸,与黄土地相依相存,与河湟人难舍难分。
河湟人追求美,追求至真至善的美,朴素自然的美,清澈如水的美,原汁原味的美,而眉户戏体现的就是这样的美。它的说白,全是地道的老土话、厚道的家乡腔,没有经过任何的装饰加工和精雕细琢,而且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听说似唱,听唱似说。说白讲究押韵,顺畅流利,其内容笑语不断,幽默风趣,体现的全都是家长里短、大姑小姨。它的表演,一抬头、一举足、一步法、一身法,简单明了,干脆利落,有时唱中有舞,有时舞中有唱,有时唱舞结合,手脚并用,使出的是浑身解数,演出的是鲜活多样,观看的无不拍手叫绝,赞唱赞舞。它的音乐自然流畅,婉转悠扬,丰富多彩,五颜六色,“七十二大调,三十六小调”的曲调听起来真如痴如醉。东调的婉转曲折,冈调的刚劲有力,五更的缠绵柔软,紧诉的赤诚激昂,还有掺杂的民间小调的多情多彩,似乎令人步入了民间音乐的殿堂,走进了桃源生活的境地。喜从眼前起,美从戏中来。眉户戏真是一种河湟神韵、一种河湟精华、一种河湟文化、一种河湟境界。
眉户戏是河湟的戏,眉户戏是家乡的戏。这种乡土文化大戏不在教科书里,亦不在戏剧大全中;不在繁华似锦的都市,也不在五光十色的剧场,而在尘土飞扬的黄土地,麦穗摇晃的庄稼院;在七梁八湾的巷道里,雪花飘动的山岭上;在八旬老人的嘴边里,七岁顽童的笑容里。总之,在老百姓的心坎里。
眉户戏,是河湟的,它像湟水河,长流不停,而且涌入黄河中,也涌入中华文化里,光彩夺目。
眉户戏,是家乡的,它像馒头花,常开不衰,同样盛开在中华大地的百花园中,年复一年,岁岁年年。
家乡的“花儿”
“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广泛流传,历史悠久的一种民间音乐。是产生和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一种以情歌为主要内容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以及部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演唱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形式。它深受老百姓的喜欢,颇得年轻人的追爱,适于西北人的性格,顺合黄土地的需求。
家乡的“花儿”,属于河湟“花儿”。经两三百年的流传,历经风霜雪月的磨炼,到今天这个社会日新月异,文化异军突起,人们的玩法五花八门,娱乐活动形形色色的时代,亦然有着较强生命力和广泛群众性,亦然在百花齐放、万盏灯火的艺术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
只有真善美的艺术,广大群众才喜欢,才能被接受,才能被传承;只有经受了历史和时间考验的艺术,才是大众的艺术、民族的艺术、永恒的艺术。
家乡的“花儿”,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几百年来它与黄土地紧密相依,它与河湟人心心相印。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无论百姓的生活怎样苦辣酸甜,家乡的“花儿”仍然如此炽热地竞相开放,争芳吐艳。尽管有时它朴素得如裸露的黄土地,清纯得似湟河水,但大多的时候如阳似火,令人狂欢不已,如痴如醉,流连往返。
“花儿”的美首先表现在其语言上。这种民间口头流传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有着严谨的表现方式。它的唱词以七字句(一三句)与(二四句)相间的四句体为主,特别是二四句句尾必须是“双字”词,另外一三句和二四句分别押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唱词格律。“花儿”多用赋、比、兴等修辞手法,讲究的是抑扬顿挫,使用的是拟人比喻,语言极其生动、形象、诙谐、明快。“上山的老虎下山来,下山着吃一趟水来;阿哥是蜜蜂儿探花来,探花着看一趟你来。”这种比拟贴近诙谐,对仗明快;这些语言自然流畅,朗朗上口。难怪那些务弄农事的庄稼汉们能脱口而出,引吭高歌,也难怪人们听两首花儿便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花儿”的美其次表现在它的音乐上。“花儿”曲令繁多,唱腔丰富,如直令、三闪令、尕马令、马营令等等。这些曲调韵律独特、唱词直白、高亢嘹亮、婉转悠扬。一种唱腔有一种韵味,一种韵味有一种表达,一种表达体现着一种艺术,一种艺术带给人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给人们深旷的空间想象感、回味无穷感,即使一曲终了,听者还沉浸在那种音乐带来的余韵里,不能自拔,难以回头。
“花儿”的美就表现在这种语言和音乐上。这种民间艺术一开始就萌生于黄土,扎根于民间,活跃于乡土,响彻于田间。它的曲调直亢激扬,优美流畅;它的语言一比一兴,简单明了,不掩饰什么,不伪装什么,有的是自然流畅,有的是朴素大方,有的是热烈激扬,有的是淋漓尽致。这种艺术就是生活,这种生活就是艺术。
“花儿”纯真、泼辣、激昂、热烈,这是河湟大地独特土壤孕育的结果,这是河湟人家心情的表达。生活在河湟大地的人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他们在这块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改变着大地,也改变着自己。他们需要五谷粮食来养育自己,同样需要“花儿”、文化这些精神食量来充实自己。忙碌的日子,他们要耕作,需要细心的精耕细作,为自己生产粮食,也为别人提供果菜;稍有空闲,他们需要火爆,需要奔放的热热闹闹。这便是“花儿”与河湟大地的不解之缘、难舍之情。
“花儿”是属于老百姓的。河湟大地是一块具有悠久历史的热土,几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勤奋劳作。在那些已逝的岁月里,在那些过去的年代里,青海东部地区的人们在湟水这条母亲河的两岸辛苦劳作,细心耕耘,推日度月,传宗接代,尽管他们的生活是那么艰辛,条件是那么落后,但是他们认真地面对生活,现实地谋划未来,知足常乐、自得其乐。那些物质贫乏的年代,那些娱乐匮乏的岁月,他们编创出的“花儿”,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力量,为个人物质生活增添了后劲。从而他们与“花儿”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花儿”结成了难舍之情。过节的时候他们要唱,这时他们唱的是高兴、唱的是喜庆;平常的日子也唱,这时他们唱的是向往、唱的是未来。夏天的时候要唱,这时侯他们唱的是兴奋、唱的是激昂;冬天的时候要唱,这时候他们唱的是忍耐、唱的是等待。悲苦的时候要唱,他们要把岁月的艰辛、生命的磨难唱出去,像在悲痛时把眼泪哭出去一样;高兴的时候同样要唱,他们把生活的乐、人世的喜唱出去,让自己再舒畅一次,让别人也感受一回。在饭桌上要唱,当然是在方便的时候,他们唱日子的和和美美,唱岁月的年复一年;在巷道里要唱,有时也会偷偷摸摸,他们唱人世的复杂多变,唱人情的纠葛难清;在田野里要唱,这时候便无所顾忌,放开嗓门,敞开心扉,唱生活、唱爱情,唱苦乐、唱希望。年轻人要唱,他们要唱爱情与人生的幸福;老年人要唱,他们唱对人世的留恋与感叹。“白杨树叶叶儿尖对尖,哪一个叶叶儿不圆?年轻年老的都一般,哪一个少年里不贪?”
“花儿”与黄土地生生不息,花儿与老百姓朝夕相处。有了“花儿”,河湟两岸的人们才有了生命的坚韧不拔,向往追求,多少年来,“花儿”与老百姓就在这样的难舍之情中同生同长,就在这样的难解之缘中互从互依。难怪老百姓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在今天这个物质富裕的年代,在今天这个娱乐多元的时代,“花儿”仍然焕发着生命的活力,在五颜六色的艺术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那么艳丽、那么灿烂。
“花儿”是属于爱情的。“花儿”是爱的体现,“花儿”是情的表达。从一开始,这种原生态的艺术就与爱情连接在一起,或隐或现,或明或暗,总而言之,河湟地区的男男女女就在这种艺术手法里传递着爱情,就在这种唱腔信息里感受着情怀。在过去,人们之间的交往渠道单一,情感表达方式狭窄,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花儿”,吼一声“花儿”,让远方的他或她感受到一个人的等待、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的思恋;捎带一首“花儿”,让梦中的他或她明白一个情怀、懂得一种表达、实现一种夙愿。这便是“花儿”的无边之力、非常之用。在河湟男女的心中,任何关于爱情的表达都是苍白无力,任何关于思念的比拟都是微不足道,只有“花儿”的语言才是那么真实、贴切,令人如痴如醉,令人淋漓尽致,令人动情不已,令人激动万分。“怀里抱的是三弦子,弦子上连的是码子;连上的梦见了三晚夕,睡梦里哭成个哑子。”对于正在爱慕或思恋中的男女,还有什么样的语言能胜于这首“花儿”的表达,有什么样的表达才能胜于这种艺术的讲白?
河湟人少不了爱情,河湟人也离不开“花儿”。在这样的“花儿”情缘里,爱情是那么的触手可及,生活是那么的幸福美满;在这样的爱情氛围里,“花儿”是那么的多彩多姿,生活是那么的有滋有味。说到底,“花儿”是属于爱情的,同样是属于生活的。
家乡的“花儿”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这样的一种生活。它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物,它只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它没经过艺术大师的精雕细琢,它只是自然真实的乡里乡音;它没有被主流社会推崇与包装,它只是被老百姓传承与接唱。然而它有的是悠扬婉转,酣畅淋漓,情真意切,激情火爆。
家乡的“花儿”,也不单是一种小唱、小乐,它成了河湟民众的狂欢,如今它已从山野走向平川,直唱到大通的老爷山、乐都的瞿昙寺,唱得花儿芬芳,经久不衰。
家乡的“花儿”,不单是传统的,同样是属于现代的。在今天文化活动百花齐放的时代,它仍是艺术百花园里的一枝独秀,同其他艺术花朵一样,饱含着真情,灿烂夺目,光彩照人。它不仅仅是田野上的歌唱,也是现代舞台上的闪亮,激情四射,光芒四照,芳香四溢。
家乡的“花儿”不单是河湟的,同样是属于民族的。河湟人在流唱,西部人在讴歌,全民族在感受,它婀娜多姿的身材也不断步入北京的大舞台、黄浦江的大剧院,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木工李师傅
那是十年前的事。
那年我在县城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楼房,要进行简单装修。经人介绍,我找到了木工李师傅,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也为了对这个小木工讨点小好,让他把我的新房装扮得漂漂亮亮,收拾得温温暖暖,我世俗地称他为“李老板”。
李老板是从浙江来的,大凡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做木工装房子的、做衣服当裁缝的、开汽车修理铺的,都是从浙江、四川等地来的,一般这些行当都被这些外地人“垄断”。他们肯吃苦,不论干什么都做工精细,颇得当地人的好感。
李老板个头不高,身材瘦小,全身上下除了一双机灵的眼睛,再基本上没有什么特点,一看就是典型的南方人。他干的这种需要力量的活儿似乎与他的身材有点不相称。他的文化素质也不太高,我想,干这种体力活的人,自小不安分守己,逃学、抽烟、打架,是令家长和老师讨厌的人,尔后在家长的强迫下,他才从事这种又苦又累的行当,我开始怀疑,他能干好我的活儿吗?
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的楼房里,我打通电话后他说马上就到,几分钟时间,我想光爬上我在六楼的新房也得费些工夫,可只有七八分钟时间他就到了现场。
李老板,不“老”,看上去他只有三十来岁;也不“老板”,充其量只是个“打工者”,而我不能不这样称呼他。听到我这样叫他时,他脸上一时茫然无措,继而又似乎心安理得,因为按世俗的惯例,我们这个地方对做生意的人不管生意大小,有没有钱,都这样称呼。随后,我俩进行共同的设计,厨房该装什么,客厅该怎样做,厕所如何通风、透光,卧室安什么灯有一种温馨感等,而他的设计使我对他的看法有了大的变化。尽管只交流了半个小时,但我与他之间的陌生感悄然消失,我与他之间的雇主与雇工的身份随即打破。后面,他讲了些自己的事,最后说,请你放心,我一定干好你的活,但请你不要叫我“老板”,我一年能挣个三四万元,这个数目不少也不多。他说了句经典的话:“拿我现在的钱回到上世纪的80年代生活,我就是老板,可现在还差得很远。”我开始不再称他为“李老板”,而叫他为“李师傅”。我也想,这样称呼既合他的心,又合他的身份,也拉近了我这个“雇主”与他这个“雇工”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何必那么“矗一堵墙”呢。每天我都去看一看,看他做工怎样,是否节约材料了,是否做得认真细致,是否抓紧时间而不磨洋工,等等,但我每一次去,他与他带的徒弟都认真干活儿,从没见过休息,也没见过抽烟,只见到浑身的灰土和木屑,甚至满头满脸,连眼睛上都是。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说,该休息的时候还是休息一下,可他说了句地道的谚语:五黄六月站一站,十冬腊月少顿饭。我问他到这个县城多长时间,他说,也不短,已经一年半载了。但这句谚语是地道的老土话,其实随便的人是说不上的,而他在这里仅仅生活了一年多一点。
二十多天他就干完了所有的活儿,把房子收拾得有棱有角,有声有色;把一个家居装饰得温温暖暖,热热烈烈。我心中在窃喜,我只花了四万多元的钱,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想八成是他挣不上多少钱。结账时,我怀疑地问,是否开得少了些,他没有像其他生意人那样强争硬要,只是菀尔一笑,又说了一句本地的谚语:别看买卖小,本小利钱大。
住在这样的新房里,我真是有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刚住下的那段时间,我还不时想起这个给我带来温暖的小木工,但时间一长,我就忘记了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师傅。我想他们这些人,凭着手脚的勤快、脑子的灵光,充其量也只能挣些小钱,以养家糊口,一个外地人能干出什么?
木工李师傅,消失在我的眼里了,当然他会继续奔波在这个县城的楼楼道道、街街巷巷里。
转眼已经六年时间了,我的一个亲戚要装修新房了。他找我要我联系一下装修老板,把他的新房好好装修一下。我想,我基本上不与这些行业的人打交道了,我也给他提供不了合适的老板,最后思来想去,我想到了木工李师傅。但我又想,五六年前与今天已今非昔比了,我们这个县城楼房越修越多,装修的档次也越来越好,一般人都找的是装修公司,这个说民间谚语的小木工能做好吗?在亲戚的一再催促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找这个小木工李师傅,在尘封的电话号码簿里居然联系到了他——木工李师傅。
这次不是他到需要装修的楼房,他说让我们到县城东头的一个二层楼里去一趟。我想,这个昔日的小木工还真有点架子了。
我和亲戚前往那里。一到这栋二层楼,赫然出现“小李装修行”这几个新颖鲜亮的字。一进门,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看着什么。这是一个中等铺子,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烤漆门、地板砖等。一听到我们进来的声音,看电脑的人马上站起来,我一看,这不是李师傅吗。几年不见,他还是那样子,穿着朴素,还有点土。我问,现在给谁打工?他说,给自己打工哩。我又说,你不干你的活儿,到人家这儿干什么?你不是曾说,五黄六月站一站,十冬腊月少顿饭吗?
他笑了个前仰后合。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还干公务员,我说的时候带有一种优越感、满足感。他又是一笑,说你们端的是铁饭碗,变了的是年龄,不变的是思想。又反问,看电视上你们不是在天天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吗?
我一下子傻了,也一下子惊了。傻的是他的观念与我的思想,惊的是他的进步与我的原地踏步。我明白了,眼前的这栋二层小楼是他的,一个到这儿谋生的外地人的;眼前这个装饰公司是他的,一个到这儿挣小钱的小木工的;眼前的这个人也是他的,一个曾说民间谚语而现在讲“政治语言”的“小混混”的。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他的一切。他从带徒弟的小木工变成了有公司的小老板,从一个租房打零工混日子的土老帽变成了一个有二层楼用电脑的生意人。他还把老家的媳妇接到这儿给他打理铺子,把儿子接到这儿上学。他说,男人在外没有家不行,同时他又讲了一句经典:家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世界,孩子的乐园。
有些事情是可以想象的,有些事情又是无法想象的。
谈妥价格后,他开始为我的亲戚装房子。与上次不同的是,他在电脑上购材料、做设计,只有他手下的人进驻楼房做装修,他只是发号施令而已。与上次相同的是,他们把房子装得有条有线,五彩缤纷;把家居饰得明亮大方,舒舒畅畅。我的亲戚自然高兴不已,与我原来的感觉如出一辙。
房子装修完后,我和亲戚到他那儿结账。我的亲戚问他,县城就这么些人而已,该修的楼房已经修了,该买楼房的人已经买了,该坐家的人已经坐了,以后还干什么?李师傅,噢,不对,我现在应该确切地叫他李老板了。他不假思索地说:人的美丽需要美容师的装扮,房子的漂亮也需要装修工的装修。有人的地方就有房子,有房子的地方就有我的饭吃,世界这么大,房子这么多,还愁我赚不到钱吗?
他的话与他的人一样经典。
邮差石有辉
30年前家乡的小村纯属是一个封闭的山村。
这里在湟水南岸乐都老鸦峡至大峡段的南山脚下。南山地区是一种独特的地理地貌,从湟水河南岸开始,一座座从北向南的山峰有规则地伸向南大山,每一座山之间又排列着仍是从北向南的沟壑,依次向南,依次升高。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使南山地区的交通格外崎岖,也使南山地区的出行异常艰辛。家乡的小村就坐落在从北向南横亘着的其中一座山里。
小村不通水,人们吃的是窖水;小村不通电,家家户户照的是油灯;小村自然也不通公路,只是山间小道,密密麻麻曲曲弯弯的山间小道可四通八达,忽隐忽现地伸向左邻右舍的村子。那条崎岖不平、迢迢千里的邮路永恒地开通在什么也不通的山村,自然这条邮路也就成了山里人了解外部、沟通世界的希望。
邮差石有辉就是这条路上的唯一行进人。
那时候的邮差石有辉三十出头,由于家住在条件较好一点的沟岔,脸上没有明显的高原红,皮肤白白净净,身体壮壮实实。他话不多,办事却干净利落。我父亲是村小学的校长,我家自然而然地成了村里联系人们的中心,也是传话捎带东西的捷径,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村里的邮点。每一次到来,他十分熟练地取出大摞小摞的报刊信件,再拿出收报收信单让父亲签字,然后拿上乡亲们早已送过来需要发向四面八方的信,小心翼翼地装进另外的邮包,道别一声便消失在忽隐忽现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虽然他已汗流浃背、精疲力竭,但你怎么敬他、让他、留他,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出发,不抽一口烟,不喝一口水,不坐一席地。
我家可红火了,邮差一走,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有来看报纸探消息的,二三十年前的村庄没有电视、电话这些玩意,信息十分闭塞,纯属“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行路基本靠走,通话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酒”的原始生活,看报纸是了解新闻、消息的唯一渠道。有来取汇款单的,有来拿信件又代回信的,乡亲们看完报纸,拿上宝贝般的信件陆续又回去。每一次邮差的到来,在我家是人们聚集的一个高点;每一封信件的收看,在小村是人们兴奋的一个极点。
邮差成了村庄的贵客,邮路成了乡民的希望。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六,按惯例这天是邮差石叔送报的日子。父辈们已说过,以后让我们见了邮差石有辉叫石叔,要礼貌些,人家是我们村里的贵客、阳光,他名字就叫石有辉,时时处处能给我们村带来光辉。村里的人什么也不稀罕,缺的是信息,盼的是信件;村里人什么也不重要,想的是亲情,等的是邮差。而只有邮差石有辉能给我们这一切,你们不尊重他还尊重谁。于是石叔就成了我们的敬称,时间一长村里的大人也就这么叫开了,“石叔”成了全村的关键词。这天家家户户已杀猪宰羊,蒸馍煮肉,准备好了过年的一切,等待着邮差石叔送来的新年祝福。上午的时候,天空中雪花飘零,午后天气变得阴沉,忽然下起大雪来,寒风凛冽,刺骨难忍。三三两两的乡亲们打问信送来了没有后,失望地回家了。我们想着这样的天气里是无法出行的了,更何况他要背上百斤重的邮件要串几十里山路。石叔送的不是我们一个村,是一个乡的,他要把全乡18个村的邮件从邻乡的中心邮局用自行车运回到他的家里,再重新分拣归类,背上邮包,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来回得走百八十里,遇到晴天还算幸运,能顺利完成分送任务,若遇上刮风下雨,尤其是冬天下雪,山里的小路实在难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在我们大失所望,关门闭户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响起,“开门,开门”。
打开房门,外面寒气袭人,冰天雪地,邮差石叔身上裹着一层雪,但满面红光汗气腾腾。他说今天对不起,路上雪厚难行,加上春节期间信件很多,邮包超过了往日的一倍,从早上出门一村一村地送,到这里已黑了,还有下面的一个村未送。我们说,这样的天气,可以缓几天再送,过年后送来就行了,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石叔断然否定地说,就你们村这次信最多,有四五十封,从西宁来的,甘肃、陕西来的,还有从新疆伊犁来的,都是家人亲戚过年前的问候、祝福,甚至可能有其他重要的事,我哪能拖得起?
这次石叔破例在我们家坐了半小时,喝了些茶,吃了些饭,还喝了父亲敬的两杯过年酒。父亲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不喝哪能行。他笑了,这是少有的笑,笑里分明带着一种满足,一种如释重负,然后说了多谢,消失在夜色里。我们说走好,我们知道留他是无用和多余的,什么样的语言都留不住他,正如什么样的天气都挡不住他一样,还有一个村在等待他,还有一些乡民在期盼他,方圆几十里的村村庄庄,就这么一条邮路,就这么一个邮差。
一个邮差送来了一份份亲情,一条邮路改变了一种种生活。
一次石叔很早就到了我们村子,按照他的送报路线,我们村是倒数第二站。那天的报纸和信件不多,但是邻居家有三封信,其中有一封是急件,放下报纸和其他信后,他要我们带他到邻居家亲自去送,这是少有的事,每家每户送他是无法送完的。邻居家阿爷从石叔手中颤抖抖地接过信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拆开信要石叔念给他听,石叔一字一句地念着,邻居阿爷字字句句地听着,焦急的脸上也慢慢地出现了笑容。原来邻居家阿爷有哥哥,二十年前远走新疆谋生,一直音信全无,双方没有一点联系,只是天天盼着消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这一条邮路把远在天边的兄弟连在了一起,这位邮差把日夜盼望的消息送到了亲人手里。信中还说,他们在新疆很好,比老家要好得多,改革开放了,那里搞得活了,他们在市里开了商店,要让侄儿们春节后到新疆打工,看商店、挣大钱,不要老是窝在山沟里过穷日子。邻居家人从惊喜中回过神来时,邮差石有辉已消失在村行山道里。老汉三番五次嘱托我,下次你们石叔送信来时,千万要领到我们家来,给他喝点茶、敬支烟,不然就对不起他了。我们说,要请你自己去,我们是领不来的。
一个邮差送来了一份份信件,一条邮路拓宽了一片片希望。
我们是在石叔的满面红光中一天天长大的,村庄也是在石叔的热爱与关切中一天天变化的。他每次都翻山越岭、风雨无阻地接受着村民们的等待,村庄也每次都热烈急切、实心实意地迎接着石叔的到来。我们的等待,是因为他知道那些邮件的分量;他的到来,是因为我们懂得那个邮包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有分量,所以他从未有怠慢;因为有希望,所以我们也从没敢轻视。以至到后来,他认识了村里的每一个人,村里的人也都熟悉了他,尽管他没有一家一户地串过。他还掌握了村里的所有外界信息,谁家的娃娃在县城读高中,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外地的什么大学,谁家的弟兄在新疆生活,谁家的女儿嫁到了甘肃等等。他把送报送信看作一种责任。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县邮政局聘用的临时人员,报酬很少很少,甚至比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拿的报酬还少。但他还是春夏秋冬义无反顾地奔波在山间小道、村巷人家,把一封封信件丝毫不差地送进每一个村落,又把一封封回信带到邮局,邮向各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再后来,我们在石叔的信件里一个个外出上学、工作、成家,离开了那个山村,也远离了石叔的邮包。
村庄也发生了巨变,独特的南山地区,公路从沟岔修到山间,村庄连着村庄,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通信网络覆盖了村村庄庄,电视网络联通了家家户户,村庄也随着外面的世界慢慢步入了网络时代。
那条坎坷不平的邮路也发生了变化吗?
那个邮差石有辉,那个村村庄庄天天等待与期盼,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敬称的石叔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