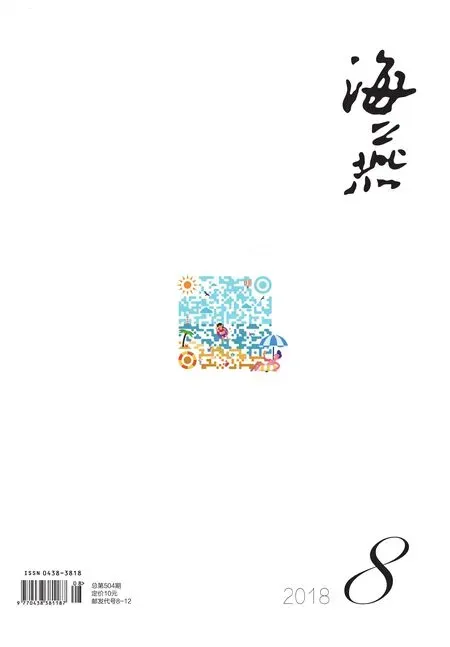关于一匹枣红马的记忆
2018-11-15于博
□于博
一碗高粱米,磨得有些破碎,里面夹杂着糠皮儿。德才死死地盯着,气喘得也粗,手心有些发热,他使劲儿在大衣襟上搓揉着,咽了一口唾沫,四下瞅了瞅,四周很黑,只有马槽上的马灯有些明亮。四周很静,狗叫的声都没有,只有马吃夜草的咔咔声。德才终于一咬牙,把那碗高粱米慌乱地倒进大衣兜里……
这碗高粱米是枣红马的夜宵。枣红马怀了驹,但日渐消瘦。生产队长就叫饲养员每天夜里给枣红马加一碗高粱米,补身子。德才就是队里的饲养员,这活自然就落到了德才身上。
德才的老婆也怀孕了。因为粮食不够吃,多半是吃烀土豆,老婆有些浮肿,这几天总吐,德才担心她一不小心把孩子给吐出来。于是,这天夜里,他把枣红马的夜宵偷回了家,老婆喝上一顿香喷喷的高粱米粥。
德才剥削了枣红马几碗高粱米呢,不知道,但德才媳妇自从喝上了那晚的高粱米粥,浮肿慢慢消了,也不吐了。德才很高兴,看着枣红马,他的心却有点发酸。
枣红马要生产了,德才媳妇的肚子也拧劲儿地疼上了。生产队的大院里围了一帮人,德才家也围了一帮人。德才媳妇满脸是汗,大骂德才缺德,惹得接生婆抿嘴直乐。
德才媳妇一阵折腾,孩子顺顺当当地生出来了,哇的一声啼哭,声音特别响亮。
枣红马产驹却不那么痛快。好半天,马驹生下来了,枣红马却意外的死了。队长心疼得直叫,说枣红马是因为缺营养,后悔高粱米加少了。
德才喘着气跑到生产队时,正好听到队长这句话。他心一蹦,脸色就跟枣红马的毛一样。他低着头,看着枣红马的尸体,手心里出了一堆汗。他不明白,这么大的一匹马,咋还没媳妇尿性呢?想着想着,心里又是一蹦……
队长说,这是两匹马的命。母马死了,小马驹还能活吗?可也怪,从那天起,家家轮班给小马驹喂饭米汤,小马驹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生产队长叹了口气,吩咐人给枣红马扒皮。忙了小半天,枣红马被按户数卸成了一块块肉,分到了各家。
德才拎着一斤多的马肉摇晃着回到家,媳妇乐了,说枣红马是可惜了,但好歹能吃上一顿马肉馅的饺子。说完,拿刀就去剁肉。倚在门框上的德才呼地抢过菜板子上的马肉跑出了门。媳妇当时愣住了,撵出去。德才跑得飞快。他出了屯子,在东山湾把马肉埋了。坟堆不大,在一棵老榆树下。老榆树上蹲着一只老鸹,盯着德才,一动不动,或许也是闻到了马肉的香味。
不知什么时候,媳妇已经站在德才身后,抹着眼泪,她不明白德才为啥这么做。德才眼珠子有些发红,回过身狠狠说一句话:你想吃肉?你早就把马肉吃了,你吃了一匹马,一匹枣红马!
德才媳妇看着德才,有些害怕。结婚两年了,没见到老实巴交的德才这般吓人。嘴张了两下,想问问这话是从哪说起呢,但没有说出来。
德才在马坟旁边坐了好长时间,太阳落山了才往回走。屯子里到处弥漫着马肉的香气。德才媳妇吸了吸鼻子,眼睛有些湿润……
小马驹长大了,又成了一匹枣红马。
德才也成了生产队里出了名的车把式。
这年,他领着队里的三挂马车去山里倒套子,就是从小兴安岭上把木头运下来,再拉回屯子。那时,屯子里无论是生产队还是个人家,使用的木头都是这样弄回来的。结果,在下山时,枣红马不知什么原因受惊了,突然狂奔起来。跟着德才的掌包的,就是赶车的副手刘二急忙跳下车。德才拼命地拽着枣红马,刘二大喊,叫德才赶紧撒手,不然被卷到车底下或者挤到树上,德才肯定得成为馅饼。德才没有理会刘二破嘶拉声的喊叫,他使劲儿地一边拖住枣红马,一边喊叫着。德才说他要撒手,枣红马就成了馅饼。
结果,德才被挤到一棵粗大的松树上,成了馅饼。马车卡在树上,枣红马仰脖嘶叫一声,前蹄抬起,然后落下,浑身的毛被汗水湿透了,喘了几口粗气,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低下了头,站在那一动不动了。
马坟旁,多了一块新坟。德才媳妇跪到坟前烧纸,眼睛瞪得老大,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转,但始终没有掉下来。人们奇怪,不是因为德才媳妇没哭,而是坟头有一碗新磨的高粱米……
德才的儿子长大了,上了小学,上了初中,然后到县里念高中。最后考到省城师范大学,学的是画画。
毕业那年,德才的儿子画了一幅画,老师挺惊讶,说画得真好,推荐他参加省里的美术比赛,一准能获奖。交作品时,老师却找不到他了。
德才的儿子这时已经坐着火车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二佐村。
在那棵榆树下,在德才的坟和挨着德才的马坟旁,德才的儿子磕了三个响头后,慢慢站起身,打开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匹奔腾的枣红马,昂着头,鬃毛飞舞,四蹄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