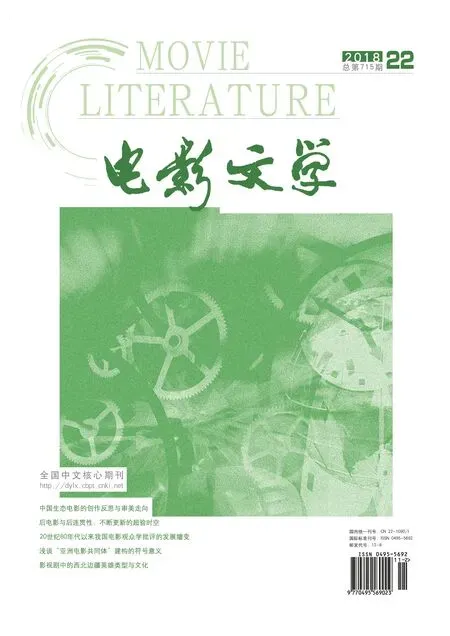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阿凡达》中的资本逻辑与个体反抗
2018-11-14高超
高 超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济南 250002)
电影《阿凡达》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经典高概念电影,其高识别度和高传播性对观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电影描述了后工业时代,下肢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杰克,在潘多拉星球执行任务过程中与部族公主产生感情,最终与原住民一起反抗资本集团并获得成功的故事。
卡梅隆导演利用自己拍摄科幻电影的娴熟技术与丰富经验,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3D技术,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奇幻绝美的潘多拉星球。然而在视觉美感之外,我们深入发掘,不难看到资本逻辑贯穿影片之中,与此同时,资本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个体反抗与资本逻辑不时碰撞,一步步加深的冲突推动剧情发展,最终达到影片高潮。
一、后殖民时代的资本逻辑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社会组织与经济权力以资本为中心得以构建。资本遵照资本逻辑以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同时继续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持续性的投入产出以获得资本增值,在此经济关系中,经济体系得以扩张,科技水平获得突飞猛进的突破,反过来继续促进资本手段进步和资本扩张,社会得以高速发展。然而资本的快速扩张若失去控制超出底线,必会带来巨大的危机。
影片伊始,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就被展示出来。杰克说:“如果你有钱,他们就能治好你的腿骨,但单靠那点儿抚恤金,简直痴人说梦。”同样的话,在杰克降落到潘多拉星球后又加以重复。而后,杰克弟弟的死因再一次影射金钱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揭示出财富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至高无上,暗示着这种失去控制的资本追逐将带来的无穷危机,为影片中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和最终溃败埋下伏笔,加深了观众对资本主义扩张悖论的认识。
接着,影片介绍了在地球上本为自由而战的军人,因金钱来到潘多拉星为资本利益集团所驱使,揭示出资本逻辑的又一特点:资本雇佣劳动,资本的拥有者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影片片头完整地向观众展示了资本逻辑的双重性:追求资本增值和雇佣劳动的过程。资本逻辑的双重性,构成了资本逻辑的自我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遭遇着内在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本身就是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而资本逻辑作为一种生产经济关系的发展规律,必然与外界社会和自然界产生交集,发生关系。其内在矛盾的演化,使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外部矛盾与外部界限,甚至危及文明与生命。潘多拉星球的文明,以树的形式覆盖着整个星球,资本主义的代表者在渗透和同化潘多拉星原住民失败后,对剩余价值的欲望突破底线,开始无视文明与生命,对资源进行暴力掠夺。
二、个体异化与反抗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的本义是指主体的创造物同创造者相脱离,不仅摆脱了主体的控制,而且反过来变成奴役和支配主体的、与主体对立的异己力量。在个体的异化中,主体能动性的丧失,使主体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地发展。而异化的个体对丧失的能动性的觉醒和追求,形成了个体的反抗行为。
在影片中,个体的异化与反抗紧随资本逻辑的双重性贯穿影片情节发展。在潘多拉星工作的两位科学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了解潘多拉星球而非对金钱利益的获取。这种不追求剩余价值与价值增值的意识形态将其与资本利益集团和雇佣军对立起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的工作本身也是雇佣劳动的一种,他们为了获得科研经费而参与利益集团的项目,因而其本身也是资本逻辑的一环,构成了劳动的异化。随着剧情的推进,资本扩张逐渐脱离正轨,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主观能动性觉醒并开始反抗,女战士和雇佣兵首领助手的反抗印证了这一内部反抗的形成。丧失能动性的个体与资本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形成雇佣劳动的个体化反抗。
再来看影片主线的个体化反抗。资本主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日益强大,对价值增值的渴望日趋强烈,资本的扩张步伐逐渐失去控制,开始寻求利用殖民方式获取资本。卡梅隆导演在影片中试图还原资本主义在殖民过程中的探索。影片通过雇佣军首领的话语,为观众交代了资本集团的殖民探索。其曾试图通过建立学校、教授语言等文化渗透手段来同化潘多拉星球的原住民。然而资本主义的意图和目的终是逃不过原住民的眼睛。原住民终于在资本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并开始反抗。
对杰克的设定也在最开始就埋下了个体异化的种子。杰克作为为自由而战的海军陆战队员,自由在其内心深处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战争夺去了他的运动能力,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让他康复无望。所以当他穿上阿凡达的躯体,双脚着地重获自由时,立刻解开束缚不顾一切地奔向自然感受自由。这一设定暗示着杰克与资本利益集团及其他雇佣劳动者的本质区别,也为其之后能够被崇尚自由的纳美人接纳并被生命之树选中做好铺垫。
提到生命之树,不得不探讨卡梅隆导演对资本逻辑的修正愿望。综观影片,资本主义沿着资本逻辑逐渐走向扩张悖论,为了追逐价值无视文明和生命,最终被个体的反抗打败。在卡梅隆导演的构想中,不受控制的资本扩张必然走向末路,然而对打断资本主义扩张步伐的潘多拉星球和纳美人的设定更加值得寻味。作为纳美人最高信仰的生命之树以女神的形象出现,并在影片中多次以圣树和圣母作比,不禁让人思考影片是否含有宗教性的隐喻。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两个重要问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在肯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巨大作用的前提下,阐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逻辑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某种潜在联系。在影片中,生命之树作为社会文明的象征和宗教伦理的隐喻,选定了本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但内心崇尚自由的杰克,暗示着文明和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潜在联系。而潘多拉星球原住民推举原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身份的杰克为首领并接受他的领导和杰克利用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习得的作战技巧带领原住民反抗资本集团的资本暴力扩张,更加证实了无论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个体异化还是外部的矛盾与界限,都仍然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或许能够挽救部分文明与生命,但最终无法动摇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
三、结 语
综观影片,卡梅隆导演在电影中想要表达的并非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对资本逻辑的修正,是希望资本在扩张过程中能够尊重文明与生命,始终在正确的轨道发展。也许在潘多拉星球,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开始,资本逻辑能够得以修正。正如纳美公主初见杰克时对他所说的,你只是一个婴儿,懵懂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