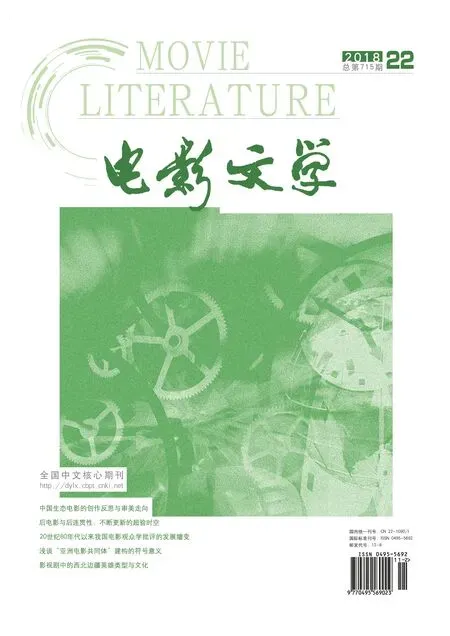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历史叙述
2018-11-14范瑞利
范瑞利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艺术学院,重庆 401524)
毋庸置疑,“在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是在社会变革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政治文化。就是说:若从大文化的视角来观察电影,在近百年的中外电影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哪段历史时期的电影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会像这时期的中国电影那样,如此直接、如此强烈地受到政治的影响。”整体来讲,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在政治文化上既有30年代的延续,更有着40年代独特的进程,其显为鲜明的节点则应在1945年。即,1945年以前,中国在政治上的主要格局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的“大后方”语境下的国共统一战线的全民抗战;而1945年以后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共和谈失败,中国开始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新纪元。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影视艺术,中国纪录片在20世纪40年代也呈现出了其独特的历史叙述。
一、国统区纪录影像的历史叙述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1938年,国民政府完成西迁,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由此,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电影虽然呈现出较为复杂、多样的态势,但国民党政府的电影企业的创作始终是主导,其主要机构有“中电”“中制”。其中,“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是国民党的官方电影机构。抗战爆发后,拍摄了一批表现抗日的纪录片,如《卢沟桥事变》《活跃的西线》《西藏巡礼》等;“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是国民政府的官营电影机构,其在30年代比较有名的纪录片有《抗战特辑》《电影新闻》等,所拍摄的内容十分充实、丰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抗战的意志、现状和决心。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民族万岁》。该作品共九本,记录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境况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所独有的风情地貌。
显而易见,“纪录影片在这个时候受到了全世界各国报道机构的重视,纪录影片在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地位,纪录电影家们也已经习惯于接近权力中枢——纪录片被看成是有力量、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它们大有要凌驾于故事片之上的趋势——纪录电影的观众增加到了一个庞大的数量,似乎所有的影剧院、部队的宿营地、俱乐部、学校、图书馆、工厂都在放映纪录电影”。尤以新闻纪录片创作为首要,“因为这里边有我们最真实的东西,反映出我们活生生的斗争生活”,这也是在重庆1940年举行的“中国电影的路线”研讨会上关于新闻纪录片探讨时的有力声音和表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大搞“劫收”和“霸权”,垄断电影企业。在电影业的经营形式上,除了官办体系外还进一步加强民营制作;在作品形态方面,虽然出现了延续30年代新兴电影文化运动的“进步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呈现出故事片创作的艺术高峰,但纪录片创作式微、薄弱。“中电”“中制”也仅有《中国新闻》《国民大会》《中国新闻华北版》等少数纪录影像作品,且多是反映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宣传教化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思想等。
另外,西北影业公司(1935年阎锡山等在山西太原开办)在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进步力量,邀请阳翰笙(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主任秘书)、瞿白音(进步电影、戏剧工作者)等电影从业者加入,拍摄制作《华北是我们的》(六本),颇受关注和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唯一一部国统区出品的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战斗和生活的影片。“《华北是我们的》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禁映,仍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上映,给予了大后方群众以重大鼓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0年8月,影片由当时在香港的民族革命通讯社南分社重新编辑后,易名为《华北风云》,还在香港放映过。重新编辑过的影片已不及原片那样鲜明,但仍受到香港爱国同胞们的热烈欢迎。”
同时,1942年,“中教”(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建立,直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摄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影片,如科教片《水利发电》《常山》《疟疾》等;风光片《三峡风光》《大足石刻》等;教学片《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等,也都可列入纪录片范畴。
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的纪录影像的历史叙述
虽然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已在国统区进行了大量的革命电影运动,但一般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电影事业始于1938年“延安电影团”的成立。而若以1945年为节点,40年代的社会语境里探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的纪录影像则可具体分为根据地和解放区。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多方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多部长、短纪录片及新闻片等的拍摄制作,其中,最为有力的是“延安电影团”。其摄制出品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多部影片。其中,《延安与八路军》历时两年多的拍摄,最终完成于1940年。由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等担任摄影。其内容分为“延安”和“八路军”两个部分。在“延安”部分中,除了记录了延安的自然风格和社会面貌,还拍摄了毛泽东及党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形象等;在“八路军”部分,主要是对主要战役和部队生活的摄制,取得了过去纪录片都没有取得的成就,而拍摄过程也确实是极其艰险。在拍摄中,“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有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最多的一次跑了一百四十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部队保护突围出来”,参与影片拍摄的徐肖冰曾如是感叹;《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由钱筱璋任编辑,吴印咸、徐肖冰为摄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方针和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全面记录了八路军在南泥湾开荒的情景,也由此被亲切地称为《南泥湾》。该片1943年首(公)映,受到高度欢迎和赞誉,并随后放遍陕甘宁边区,产生了较为显明的宣传、鼓舞功效,对中国纪录片创作观念和走向影响至深;《白求恩大夫》由吴印咸拍摄,主要讲述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我国抗日根据地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是素材汇编式的“汇编片”;而影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则全程记录了会议实况,成为弥足珍贵的一手历史文献资料。只是,随着时局的不断发展,1945年8月,延安电影团调整为“延安电影制片厂”。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拍摄条件较为艰苦,设备也较为紧张,除了因摄影机损坏而导致中途停拍的《边区劳动英雄》外,“延安电影制片厂”主要编制新闻纪录影片,如《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还我延安》等。而到了1947年,终还是因物资短缺致难以开展工作,宣告结束。
解放区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空前地繁荣和发展,主要的创作主体除了上述提及到的延安电影制片厂,还有“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电影队”。其中,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共产党在接收“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7年8月成立,主要目的是通过所摄制的影片来灌输其军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于1946年建立起来的,袁牧之任厂长。东北电影制片厂虽然也有其他片种的拍摄和制作,比如《瓮中捉鳖》(动画片)、《预防鼠疫》(科教片)、《皇帝梦》(木偶片)等,但最注重的还是纪录片的创作。其曾在建厂后就派出了专门的摄制人员到前线拍摄新闻纪录影像,生产出了较为著名的作品《民主东北》(17辑)。该片内容充实、丰富,有影响力较大的战役记录,如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有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血肉联系;有东北解放后欣欣向荣的建设气象;还有内蒙古的一些内容等。“《民主东北》分十六毫米和三十五毫米两种,主要观众对象是部队战士和后方广大人民。单是1948年一年,在东北解放区就有382个地方放映了《民主东北》一至七辑,1093场,观众达2374741人次。《民主东北》还注意向国外发行,第八辑就是专门为国外观众而编辑的国际版”;“华北电影队”前身是1946年晋察冀根据地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1948年更名,汪洋任队长。1949年,华北电影队接收国民党在北平的电影机构,又调整为“北平电影制片厂”。随着华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由最初的20多个人扩充到了百余人规模。主要拍摄有关华北解放的新闻素材和纪录片,如代表作品《华北新闻》就包括《解放定县》《正定大捷》《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等,反映了华北地区广大军民的战绩和英雄业绩,为解放区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而重组后的“北平电影制片厂”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拍摄有《百万雄师下江南》《淮海大捷》《七一在北平》等纪录片。
同时,1949年,针对依旧盘踞在西北、西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大追歼,拍摄有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解放西藏大军行》等。华东野战军也较早地开始了新闻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如,1945年,薛伯青拍摄《彭雪枫师长追悼会》;1946年,薛伯青又拍摄了《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等影像。其中,《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在1946年7月的国共“调停”期间,被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小组”的共产党的代表带到南京,有力地反驳了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
三、结 语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跟随时代的,纪录片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重要形态亦如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较为动荡的“战争”时局,且在动因上有着一定连续性和交叉性,都处于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的背景下,但又确可谓中国影视的一个黄金时期,这是时代的必然,源于复杂的历史、政治格局,更是“战争文化”裹挟着的社会心理、审美诉求的高度统一,是历史的镜像,也还掺杂着拍摄条件、技术的客观实际所限的无奈和演变。但在本质上,4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兴盛更与纪录片这种艺术的精神相通,是纪录片在体裁形式上对客观、真实的记录和还原而带来的直接震撼,更是视听综合艺术审美下的共鸣和移情。由此,在20世纪40年代特殊的“战争”语境中,电影创作者强烈的时代责任和社会使命感、全国人民强大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在艺术审美上的心理朝向以及政治表达的急切主题需要等,在艺术创作上的最好释放口必然是纪录片这种影视艺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