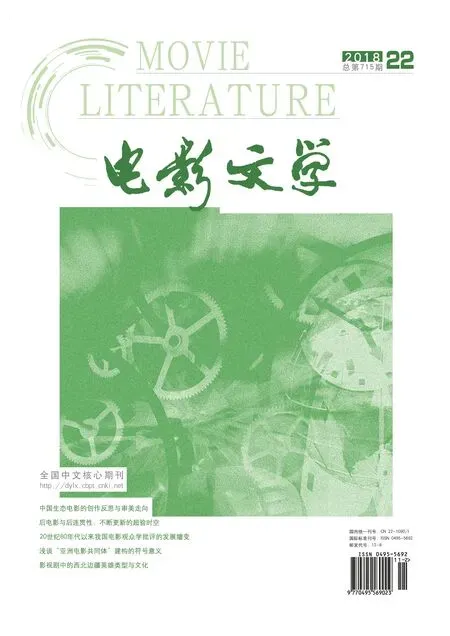后电影视域下网络大电影的文化特质及其意义
2018-11-14马楠楠张书端
马楠楠 张书端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2014年3月,爱奇艺在“网络大电影成就梦想”高峰论坛上正式提出“网络大电影”概念,并对其做出精确定义,即时长超过60分钟、制作水准精良、具备完整电影的结构与容量并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以互联网发行为主的影片。近年来,在各大视频网站的强力推介下,网络大电影和网络剧、网络综艺作为网娱的三大主要类型,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追捧。随着我国网民付费观影习惯的逐步养成,网络大电影盈利模式日趋成熟,发展势头愈发迅猛。据统计,2014年仅爱奇艺一家网络平台发行的网络大电影已达400部以上,2015年则有612部网络大电影在爱奇艺上线,远超当年全国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网络大电影在观众规模、作品影响力和单片票房等方面都持续保持增长。除了票房收益和网络红利,网络大电影的兴起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有何深层意味?作为电影艺术和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我们应当如何审视网络大电影的价值意义?
在影响深远的《电影》系列著作的结尾,德勒兹指出,随着数码技术的兴起,传统电影的基本形态正在或已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电子影像,就是说电视或录像影像,新兴的数字影像,可能转换电影,或者取代电影,宣布它的死亡。”所谓后电影,其实是数字影像时代电影的一种新的生存形态。从“电影作为媒介”这个基本立场来看,电影从未死亡,也不可能死亡,而是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演进过程中。这一点在当下电子媒介时代显得尤为突出:“电影并未处于退化、消失或湮没的过程之中。正相反,伴随着其形式和实践的日新月异的多样性,电影从未如此充满活力,如此多元而丰富,无所不在。”在数字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共同作用下,电影的本质、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我们很难再对其属性做出某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网络大电影可以说是后电影的一种典型形态,并呈现出与传统电影截然不同的后电影文化症状和美学风格,这些特质同时也彰显了人类感知模式、情感结构及主体性建构方式的深刻变化。
一、数字技术语境下审美趣味的异质化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证了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的民主化倾向。他认为由于电影的出现,“任何人都可能发现自己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电影拉近了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消除了艺术品自身的“光晕”。本雅明所谓的电影的“民主化”倾向,主要关注的是维尔托夫拍摄的《持摄影机的人》一类的纪录片。在这些影片中,人民群众被摄影机拍摄入画,作为画面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从而“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民主化”只是民众与电影之间的浅层次交会,与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融合还相去甚远,因为传统电影生产需要高昂的成本,只有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编、导、演人员才有机会参与电影拍摄,加之电影的放映需要专业的发行和放映渠道,普通人很难亲历电影创作。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成熟,电影制作不再遥不可及。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数码相机之类的拍摄设备,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使得摄影越来越简单、便捷和日常。贾樟柯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数字时代来临之后,每个人都拥有影像表达的可能性”,他甚至表示,“如果是放在今天,《小武》可能是用iphone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电影的发行和放映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拍摄的内容轻松上传网络,实现大范围传播。借助网络平台,网络大电影的制作、宣发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可以被长时间存放在网络播放平台,不再受院线档期的限制,以时间换取收益,更加有利于成本的回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网络大电影为怀揣梦想的青年电影人提供了圆梦的机会,也为中国电影输送了新鲜的血液。
从消费层面来看,网络大电影满足了当下观众多元化的观影需求。一方面,网络付费观影费用较低,比之影院观影,网民通过购买某一家视频网站VIP会员便可坐拥庞大的电影资源,享受更多的观影选择;另一方面,网络大电影丰富的题材类型也为当下观众差异化、小众化的审美趣味提供了个性化服务。例如,长期以来,受审查制度影响,许多喜欢恐怖片的观众无法在影院中看到地道的恐怖片,特别是国产恐怖片,由于网络平台监管相对宽松,网络大电影恰好可满足观众的个性化口味和需求,这也正是《笔仙大战贞子》《道士出山》《阴阳诡捕》《僵尸归来》等众多网络大电影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中,《道士出山》《僵尸归来》等影片也是对林正英港产僵尸片的致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港产僵尸片拥趸们的怀旧心理。类似的网络大电影不胜枚举,如《奇侠》戏仿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港产武侠片,《无主之地》则致敬香港黑帮电影,此外还有日韩小清新电影、二次元动漫电影、另类冷门文艺片等影片都因满足了某一特定群体的观影喜好而获得高点击率。在当前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品位越来越多元化,一些之前属于边缘群体的文化行为也逐渐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然而具体到电影文化层面,院线电影在这方面的反应还相对滞后,浸淫于开放的网络文化的网络大电影的涌现及时捕捉住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回应了时代的文化转变。例如,《错了性别不错爱》《类似爱情》等网络大电影都以较为直白的方式触及了同性恋话题,折射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性别认同的多元化取向,并满足了社会边缘群体的观影趣味。
得益于中国网民数量的巨大规模,网络大电影通过分众化、差异化营销,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观影趣味便可实现成本的回收,这也反映了后现代状况下人类身份认同多元化的特征。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步入了一个“脱部落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遭遇了一次身份认同的危机;而在电子传媒阶段,人类又经历了一次“再部落化”的过程,后现代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的崛起便是人类社会“再部落化”的突出表征。摆脱现实束缚的虚拟网络空间为人们创造了理想的交流环境,所有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可以得到自由表达,网民们可以在这里迅速找到同好并建构起庞大的社群,进而建构和确认自我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
二、互联网时代艺术体验的深度交互性
传统艺术欣赏需要的是凝神静观的方式,“绘画呼唤观看者凝神注视,面对画布,观看者能够在自己的联想中放弃自己”,欣赏者与艺术品之间隔着一段无法逾越的心理距离。电影的发明打破了这种艺术欣赏的定式,“电影娱乐人的成分首先是这种可触摸性”,一格格的画面“像子弹一样射向观看者,它碰巧撞上了他,因此它获得了一种可以触摸的质地”。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借由与摄影机的认同,可以全身心、沉浸式地体验电影所带来的愉悦。不过,囿于技术条件和观影环境的限制,传统电影影院欣赏的交互性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观众只能被动地坐在影院中接受画面的冲击,却无力做出回应。网络时代的来临弥补了这一缺憾,Web2.0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特质便是其交互性。在网络界面上,用户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很多时候,互联网用户甚至成了更为重要的内容生产者。在网络文艺生产中,创作者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接受者的反馈,并据此调整创作思路。美国网络剧《纸牌屋》的制作便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观众信息反馈的即时性和大数据搜集、分析的重要性,该剧是由Netflix公司在搜集并分析3000万网络用户搜索和观影习惯的基础之上,为最具舆论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的“中年男性专业人士”用户群量身订制的剧作。制作者将大卫·芬奇导演、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和“政治惊悚剧”这些最能吸引“中年男性专业人士”用户群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并且在播出过程中对用户的收视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挖掘,根据受众反应及时做出相应修改和调整,从而打造出一部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成功的网络剧。同样,网络大电影的生产也是建立在对网络用户观影习惯、行为模式的海量数据分析基础之上,其播出效果可同步反映在网络点击率和用户实时评价中,从而为创作者确定选材和创作思路提供重要参考。例如,《赌神归来》和《驱魔保安》的选题和策划都是在爱奇艺的用户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有的放矢,上线之后,《赌神归来》一周点击量破千万,一举创下爱奇艺平台单日票房分账的新纪录,《驱魔保安》也获得了单日播放量破百万的不俗成绩。
网络大电影的交互性体验还集中体现在它对弹幕的倚重。以往的用户评论被设置在视频内容的下方,按照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可见度低,互动性相对较弱。弹幕则不然,“评论区就是视频窗口,评论内容按照发送时间点在视频上方‘飞过’,评论内容可见度高,便于对某一特定画面及时进行评论,观众互动程度较高。”弹幕最初是流行于“二次元”人群的小众行为,是在90后青年群体中崛起的网络亚文化现象。其后,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主流视频网站发现了弹幕的商业价值并对其进行收编,使之成为一种相对主流的网络文化,发展至后来,甚至传统院线电影也开始发掘弹幕的市场价值。如《秦时明月》《小时代3》《绣春刀》等电影在院线上映时都创造条件去满足观众发送弹幕的需求,但是最终市场反应并不理想,因为大多数观众到影院观影是为了追求一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铺天盖地、频繁闪烁的弹幕则严重干扰了观影过程,弹幕电影作为商业噱头很快便遭弃用。
然而,对于专门针对网络平台制作的网络大电影来说,弹幕却是必不可少的,网络对弹幕的迷恋甚至抵消了网络大电影粗制滥造所导致的观影不悦感,有网友甚至宣称:“我不是来看电影的,我是来看弹幕的。”弹幕取代电影反客为主,似乎是一种反讽,但也折射出了互联网时代的深层文化征候。正如金元浦教授所言:“弹幕观众体验和追求的是槽点引起的应激反应以及反应传递、叠加而形成的爆点。”观众在看到某一槽点借弹幕吐槽直至覆盖屏幕的行为,不仅带来一种强烈的参与快感,而且也在无形中产生某种内在的联系和认同,使之感受到虚拟的社区感和归属感,从而建立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借由弹幕,网络大电影充分发挥了网络文化的互动性优势,激发起观众的参与热情,并挑战了传统的艺术观念。
三、后现代文化状况下影像生产的碎片化
20世纪80年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指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表意的链条断裂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只能是一堆支离破碎、形式独特而互不相关的意符”。后现代主体已经失去了驾驭时间的能力,无法在时间的演进、伸延或停留的过程中把过去和未来结合成为统一的有机经验。今天,数字技术和电子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更加生动地应验着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状况的描述。当下人类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大量电子信息流的冲击,处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各种可穿戴设备的包围中,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移动终端和 “人—机合一体”。电话、短信、微博、微信等各种各样的信息流随时会打乱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早已告别了统一、稳定的时间感,主体性和身份陷于无尽的流动状态之中,与后现代主体的这种感知方式相对应的是,碎片化叙事已成为当前文艺创作的一种常规手法。
网络大电影便是这种碎片化影像的最佳载体。从时间上来看,网络大电影通常时间较短,适合人们在休息、乘车、吃饭之类的碎片化时间观看。从叙事上来看,为适应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里注意力分散的认知特征,网络大电影一般不讲究叙事线索的清晰严谨,也不追求影像背后的深刻含义,而是试图通过富有冲击力和刺激性的奇观影像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如《我的同学不是人》《道士出山》《阴阳先生》等影片以惊悚场面引人入胜;《以为是老大》《无主之地》《我的哥哥是特工》靠暴力场面取胜;《不良女警》《一夜疯狂》《护士也疯狂》《校园风骚史之舞动青春》将大量篇幅放在女性身体奇观的展示上;《奇侠》《赌神争霸》等影片则通过对经典港片的桥段或风格的戏仿式拼贴来制造噱头和看点。正如后现代理论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所言:“后现代艺术在审美形式和平面中寻求快感,回避意义体系,回避要求深度解释的、倾向于制作有个性的和政治性的描述的多义的和重叠的复杂的艺术制品。”
当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很多网络大电影都欠缺情节的完整性和叙事逻辑的严谨度,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为招徕付费用户而推出的“免费试看前6分钟”的商业策略的作用之下,大部分网络大电影都致力于营造前6分钟的奇观影像,并不惜用暴力或色情吸引观众,导致影片叙事的碎片化问题愈加严重。这固然与网络大电影行业发展初期的不成熟有关,但从更深层面来看,它反映了当前社会人类注意力普遍匮乏的现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碎片化显示出反语境的特点,要旨在让信息脱离所赖以产生的具体情境,从而赋予新的意义。相对于原先的语境与文本而言,碎片化意味着解构;相对于新的语境和文本而言,碎片化意味着建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艺术生产者的作用大大降低,意义的生成更多依赖于接受者在不同语境下的再生产,网络大电影的碎片化影像与观众的碎片化时间体验和认知模式相吻合,并昭示着一种全新的、游牧的、撒播的、去中心化(德勒兹和瓜塔里语)的人类主体性的诞生。
四、结 语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网络大电影正加速进入“内容为王”的时代,蹭IP,炒热点,兜售色情、暴力,打擦边球、重复雷同、粗制滥造等现象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已被有效遏制,网络大电影市场的精品化意识愈发明显。近年来一些宣扬普世性价值观念、弘扬正能量的网络大电影不断推出,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评价。如《妈妈,我爱你》《再喊一声爹娘》歌颂了父爱和母爱的伟大,《特殊逃犯》通过一桩充满悬疑的命案弥合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和隔阂,《呼唤》《云烟深处》等影片则将镜头对准偏远农村的教育问题,歌颂了志愿者们自我牺牲的精神,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更难得的是,一些题材冷门,关注社会底层、边缘群体,难以在主流院线上映的影片,借助网络平台也获得了不俗的表现。我们相信,随着网络大电影管理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和透明,以及观众观影经验的丰富和甄别能力的提升,网络大电影的题材类型必将愈加丰富和繁荣,亦会走向以质取胜的良性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