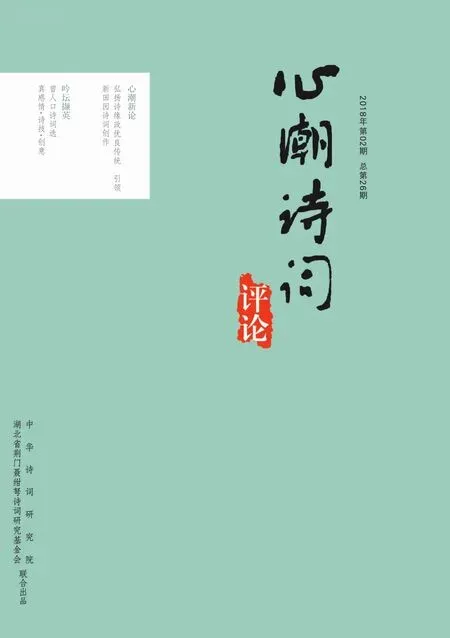浅谈诗词中化实为虚的语言表现手法
2018-11-14
化实为虚,是诗词中比较高的一个境界。具体来说就是把景物化为情思,从而达到虚实相映,情在景中,情绪自然饱满的目的。
化实为虚在于恰当精准地使用谓词,有时一字可生奇效;高明一些的诗人则善于使用通感语言;更高明的,莫过于“不类为类”,突出语言的自我表现力。我们看下面几个例子: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刘长卿《新年作》)
今朝春意薄,去岁故人稀。
(雪野《冬日咏梅》)
冢上已深三宿草,人间始重万言书。
(杨启宇《挽彭德怀元帅》)
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
(甄秀荣《送别》)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王维《过香积寺》)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商山早行》)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李白《送友人》)
以上皆化实为虚之范例。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意思是说早晚陪伴自己的,只有岭上的猿猴;和我一起领略风光烟雾的,只有江边的柳树。写得具体,其中不难看出作者所处的环境,和内心的单调寂寞。用“同”“共”二字(谓词)化实为虚。
“今朝春意薄,去岁故人稀。”“薄”和“稀”也是谓词后置的写法,也是化实为虚。“今朝春意薄”句看似写梅花,实则暗含人生感慨,世态炎凉,有情在内。“去岁故人稀”,则是说早年的那些故交早已随着世事变迁,大半零落,已经少之又少了。
“冢上已深三宿草,人间始重万言书。”是以“已深”“始重”这两个词组化实为虚,含蓄深沉,给人以无限沧桑、悲凉和沉重之感。“已”“始”这两个虚字和谓词的结合非常重要,起到突出强调和加深语气的作用,是此诗之眼,不可或缺。
“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这里是以“如”“写”两字化实为虚。“如”“是”“似”“像”等字在古诗里往往是做动词用的。这里的夕阳——红豆,绝不是简单的大和小的关系,这里有长时间伫立遥望因而看朱成碧的意思在内。“写”字,是把“夕阳”人格化的写法,“相思”是“夕阳”层层写出来的,绵绵密密,千丝万缕,辉煌壮丽,弥满天空。其实不是夕阳在写,而是人心在写,是送别者的心在写。此诗境界深沉辽远,色彩壮美绚丽,感情深挚、热烈兼而有之,情景交融而格调甚高,可谓奇情壮采,是当代诗人采用化实为虚手法的典范之作,也是该诗得以广泛流传的真正原因。
王维的表现似乎更高明些,使用了通感语言,用字比较“活”。“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咽是呜咽,幽咽,声音比较低沉,“咽”字表现出山的幽静,咽于危石,泉声因危石而咽;冷,说明山的深僻,日光稀薄,所以说“冷”,或者说日色使松树的颜色看起来发“冷”似的,这是感觉范畴(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
这里“咽”“冷”,是典型的通感语言,把泉声和日色都赋予了人的感情。是化实为虚。人们常说“意象”,不是指某种简单事物的表象,要有“意”在内,要赋予某种事物以人的特殊情感,才可以称之为“意象”。
上面讲到的几种,应该说是一般情况,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也是更高明的手法,就是根本不用谓词,只是把某些相关联的景物排列在一起,靠语言本身来自我表现,也同样能产生化实为虚的奇妙效果。我们看温庭筠的这首《商山早行》: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这是把六种事物排列在一起,中间不用谓词,这是靠语言本身来表现情思。这个排列的顺序不能乱。鸡声是天亮前鸡叫,鸡一叫,客店的人起来赶路,天上还有月亮,人的足迹印在板桥的霜上。这说明客人起的很早,霜意很浓,天气很冷。——写得很凄清,从而透露出旅客赶路的寂寞和辛苦。这就是从景物见情思。
再看李白的这首《送友人》: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首先说明这不是比喻。浮云是浮云,游子意是游子意;还有落日、故人情。它的一种是具体的景物,一种是抽象的人的情感,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作者不过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起来,使语言自己产生效果。
我说先后顺序,是说浮云、落日,是作者首先看到的,而游子意和故人情,是作者随之产生的。这里要说的是事物之间某种相近的特性。浮云,是飘荡不定的物质;游子意,是一种飘零恍惚的情感。这里共同的意味在于“漂泊”。
如太白之天资,加之性格放旷,也可能信口吟出,自然绝妙,又另当别论。但其写诗从不刻意做作,从不拘泥古人成法,一向主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理念,所以才能融情入景,深入人心,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要说的是,如果想学习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必须即情即景,选择事物或情感最相近的共性来表现,不可勉强为之。如果东拉西扯,胡乱效仿,则很容易画虎类犬。
这样把某些相关的语言排列起来,让语言自身来充分表现情感,并不加入人为因素予以叙述和说明,含蓄深邃,意境绝佳,这是诗人修炼很高的一种境界。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语言表现方式,例子很少。这说明即便古人,会这样使用语言来表现的人也不多。
我也曾偶然写过这样的句子,比如“烟霭村前树,斜晖雨后墙”(秋兴);“鸡啼窗纸白,日落远山红”(农夫);“雪霁东山白,峰悬夕照明”(初冬微雪并观柳)……这些都是用景物来表现情思的。“烟霭/村前树,斜晖/雨后墙”,是写身处乡村之中,悠然自得的心情,也是把几种景物进行排列;而“鸡啼/窗纸/白,日落/远山/红”,写的是农人闻鸡即起下田耕作,直到日落西山才肯收工回家。这里写的是乡村的农民生活,是农民早出晚归的劳作辛苦之情。当然这些都不是刻意的,而是灵感闪现时的意外之笔,是细心观察和平日的生活积累,是客观事物和内心情感的某种相互观照。
著名国学大师钱钟书说过:诗以不类为类,为美(大意如此,非原句)。其实他所说的不类为类,就是指语言的自我排列,句子的词或词组之间并没有比体和喻体的关系,突出语言的自我表现力。我们前面讲的李白的句子,就是不类为类的典范。但是像这样的语言手法很难学,一是要作者必须认真观察事物,二是要认真学习揣摩前人的经典手法,还要有悟性和生活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