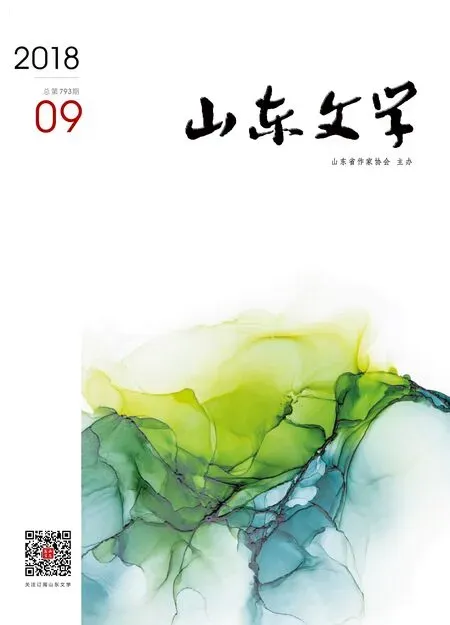试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
2018-11-14张馨
张 馨
“‘五四’时期散文的革故鼎新,如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相当自觉和彻底的。散文自此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并迅速地造就了一个既与古代散文媲美又为后世提供典范的繁荣期。自“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其中“新散文”的发展承袭了“五四”破旧立新的模式,为散文文体丰富和更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众多以创作“新散文”为主的“第四代”写作作家中,作为理论倡导者的祝勇无疑是“新散文”创作实践最坚决、最彻底,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散文家,“把历史放在偶然化和欲望化的天平上重估历史本源的价值”,并以此出发进行的历史散文的跨文体写作,是近年来祝勇所竭力追求的。这些历史散文在写作形式、语言结构、文体风格、作家立场、篇幅体量等方面都有力践行了他所谓“新散文”的创作观,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一、跨文体叙述:祝勇“新散文”的破体与创新
“‘新散文’的理论核心强调的是对传统散文的文体反叛。”早在2002年,祝勇便以《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完整表述了他的“新散文”创作观念。在这一长文中,他强调:“散文急切需要一场革命,在革命中,所有的陈规陋习都应当打破,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应当排除,所有的陈年老账都应当重新审视。既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对散文的样式进行规定,那么,所谓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咏物抒情、以小见大,都只能被认为是散文界的自我禁锢,或者别的什么界对散文的成见。”为了打破这种“成见”,他挥刀破斧,摒弃传统的散文写法,实现跨文体叙事,以达到“综合写作”,这种追求最直观的映象便是对“故宫”系列散文的书写。
祝勇对故宫的书写始于2003年的《旧宫殿》,之后他相继推出《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作品。从单纯地以故宫为背景揭露宫廷内部隐秘而又惨绝人寰的阴谋手段,到走向宫廷深处,细致地描摹紫禁城内的书画作品、建筑群落、历史人物,祝勇新作《故宫的古物之美》在延续以往历史散文写作的手法和观念的同时,又展开了对古物之美的探索,构筑了祝勇对故宫书写的完整性,并以此深化了他的历史散文观。在祝勇看来,“传统的散文对叙事采取单一化原则,只讲一件事情,而且为了区别于小说的叙事,尽可能地简化一件事情的血肉,也很少细腻地描绘,只给出一个事件的轮廓,或者几个细节,然后将其指向某种情感,或者某种思想和道理。这种叙事法则,过滤了事实本身的丰富性,也弱化了散文的魅力。”因而,以《旧宫殿》为开端的历史散文,决心破除传统散文的局限,“在散文文体中普遍渗入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类因素,抹去文类的疆域,使之成为文体杂糅、偏离传统散文审美期待的文本创作。”这种“破体”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祝勇的《旧宫殿》俨然成为一本叙事小说,他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等散文作品将大量的诗歌、在新闻中才常见的“高清详图”大胆地融入文本书写。这样的写作方式虽有历史的深度,但并非历史学术的著作,而是谈人论事的历史散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历史叙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自身研究与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正如前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说:“祝勇很早就把关注点聚集到明清历史,特别是紫禁城上面来,他不仅沉潜于史料,而且对紫禁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这种扎实稳健的风格,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难能可贵。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视角,这刚好有利于发挥它的特点,对紫禁城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阐释,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本。”
真实性先于艺术性是传统散文的基础,也是用以区分散文与小说界限的准则。“事实上,散文界所坚持的所谓真实,本质上却只不过是组接、利用、想象,甚至……虚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祝勇为代表的“新散文”家们试图用“虚构”来还原散文的真实,用以打破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祝勇认为,“散文的虚构不是整体性的,而只是技术性的,是为了表达存在的真实。小说里的虚构可以‘无中生有’,而散文里的虚构则是‘有中生有’,是对素材的重新组合、修剪、利用,因此,散文的虚构是有限制的虚构,不是像小说那样,可以无限制地虚构。”比如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中》便大胆地引入了虚构等想象性的小说因素,在“夜雨西山”一章中,祝勇这样书写受“乌台诗案”牵连的苏轼:“苏轼踏着残血走出监狱,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旧历除夕之前。他的衣袍早已破旧不堪,在雪地的映衬下更显寒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渍,要被阳光晒化了。”回到家中的苏轼在当天又写下了两首诗,“写罢,苏轼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诸如此类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与第一人称主观叙述相结合的方式,在书中比比皆是。《故宫的古物之美》亦是如此,祝勇笔下的商周青铜、秦俑汉简、唐彩宋瓷、明式家具、清代服饰,不再是冷冰冰的文物,而是充满灵性的“古物”,那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物”在祝勇笔下再次复活:“九鼎”化身为埋藏得最深的种子,在地面上结出花朵与果实;“钟鸣鼎食”背后是人间的灿烂与淫糜;“莲鹤方壶”寄托着那个时代的生命诉求、时代美学……“这都与善于虚构叙事的小说书写相去不远。”祝勇的历史散文便是借助这种虚构的手法,给读者提供解读历史的另一种策略和视角。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方法向余秋雨进行艺术上的挑战。在祝勇看来,“他的许多篇章,都在重复一个主题,就是权力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压迫,看似尖锐,实际上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判断历史人物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更新,没有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新的尺度上衡量,在余秋雨的文章里,他们安全地保持着原有的身份……”而祝勇融入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情感体验、利用虚构的手法阐释历史的散文创作,正是对与历史保持距离、书写僵硬历史的散文写作模式的有力搏击。
二、存在的复杂性:祝勇“新散文”的丰富与深化
秉承古人写作遗风,现代散文的创作讲究短小精悍、结构精巧,无论是周作人还是林语堂,抑或是朱自清,他们皆惜墨如金,很难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看到长篇大论。言简意赅似乎成了现代散文书写约定俗成的规定。为了打破这种约定,祝勇等“新散文”家们进行了众多的文本创作,最为表层的变化便是不再言简,犹如滔滔江水般,文脉绵延。祝勇的《旧宫殿》有15万余字,《故宫的隐秘角落》有18万余字,《故宫的风花雪月》有20万余字,像《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均10多万字。诚如祝勇所言,长度并未对作品的艺术水准构成了损害,它们的存在是对“既然诗歌有长诗,小说有长篇,甚至多卷本长篇,散文为何不能写”的质疑。大容量的散文无疑更有利于“新散文”家们充分地表达。“就散文文本而言,散文篇幅的膨胀,势必使得文本蕴涵的信息量更为丰富,情感表现更为杂,意象更为纷繁。”
“存在的复杂性,要求文学必须接受、呈现这种复杂性。”散文篇幅的膨胀,势必带来散文内涵的复杂。在祝勇看来,“过去的散文,总是试图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明一个道理,这不是散文,是童话,是骗小孩子用的,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的,有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于是,他的长篇或曰大体量散文,尽可能地回到和直面世界本质,呈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故宫寻找苏东坡》里,为了寻找苏东坡独特的生命印记,祝勇既描绘了苏轼与苏辙、苏迈、苏迨等家人之间的日常,也写了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朝廷大臣,还记录了苏轼与张方平、马梦得、李常任等好友之间的往来。从与郭纶的交往开篇,接连详细记录了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几代皇帝对苏轼的态度,中间穿插了沈括对苏轼的陷害,苏轼对吴道子绘画技术的慨叹,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技艺的推崇……这些人物不再是史书上记载的历史人物,而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人类向来是最复杂的存在,为了打开苏东坡的内心世界,祝勇用众多复杂的人性内涵构筑了历史的纵深。在《故宫的古物之美》中,他写道,“在庞大的世界面前,写作是那么微不足道。”正因为“物是无尽的。无穷的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消失的)。无穷的物里,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情感、盛衰、哀荣。”在这里,祝勇已经超越对人性的书写,又与物进行平等的对话。在“踏雪寻梅”这一章节中,祝勇用一件件剔红笔筒、圆盒、圆盘,红底描黑漆诗句碗,表达了他写作的初衷,“日子,其实可以过得很美,美不是奢华,不与金钱等值。美,是一种观念——一种对生命的态度,是凡人的宗教,是我们为烟火红尘里的人生赋予的意义。”只有懂得什么是美,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古物之美,就这样,他用文字,串联成故宫里又一部艺术史。至此,在祝勇的故宫艺术史里,他的写作立场更加坚定、思想观念更加成熟,已经完全摒弃当代散文写作曾一度呆板奉行的“形散而神不散”的观念。
祝勇等“新散文”家们认为,传统的散文表达简单、透明、没有任何弹性,是因为它的语言是透明的,且这些透明的语词与它们的含义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新散文’写作中,写作者们拒绝对思想的直接呈现,而是致力于恢复了语言自身的价值。”于是他们的语言在传递既有的含义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含义,呈现一种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动态关系,使整个作品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比如,在《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祝勇将故宫中的这些文物,称为“古物”,更好地凸显了其时间的属性。在第一章“国家艺术”里,为了还原商州青铜本来的颜色时,祝勇把那些我们熟悉的青铜的青绿色称为“岁月的颜色”,并称这种“岁月的颜色,就是青苔的颜色。因此,它们表面的铜绿斑驳,是岁月强加给它们的。”可以想象,当青铜器上长满了斑驳的青苔,那沉睡了千年的器皿瞬间变成了生生不息的活体。继而,祝勇又说,“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而是熟铜般的颜色,在黄河与黄土之上,发出一种灿烂的金黄。”这样阐释,打破了传统的比喻里,我们所说的金色的阳光、金色的秋天中的金色。正如当一个人从一群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王,他便不再是普通的人一样。“金色是一种迷人的颜色,也是最能烘托出权力的富贵和威严的颜色。它令人肃然起敬,又目眩神迷。因此,金色是一种充满魅惑的颜色,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颜色诱发的。”通过类比,祝勇将“金色”描绘成了权力、富贵、欲望的颜色,且这种颜色的含义,不是“金色”本身所具备的,而是由人的欲望赋予的。不仅仅只是“国家艺术”这一章节,在祝勇的构词中,每个词语都有着无比广阔的意义空间,且词语的排列组合,又使意义空间以几何级数剧增。在他看来,恢复了词语的活力,便是恢复了散文的活力,他利用语词的复杂性,不断创造词语的组合的新方式、开发新的词义,寻找散文书写的新的可能性,也借此丰富和深化他的“新散文”创作的实践。
三、先锋性的追求:祝勇“新散文”能否长久保鲜
祝勇挚爱散文,钟情于那文字里所透露的生命温度。“因为我们热爱生命,所以我们热爱散文。感谢上帝,感谢阅读和写作,赐给我们幸福。倘若有一天,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散文,我们仍旧可以活下去,因为散文会告诉我们如何在时间的河流里摆渡生命,告诉我们生存的目的,以及世界上简单朴素的奥秘,为我们传播福音。”他沉浸在散文的世界里,将千载历史酿作一壶浊酒,把万里江山化作一尺丹青,在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回旋往返,穿来梭去。从散文家的立场出发,祝勇写下了许多文字,在他看来,这些文字无论对世界有用或者无用,对他自己而言,都不可或缺。祝勇早期散文里满是青春的观感,1993年,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与梦相约》出版,以沉静温雅的文笔,表现出超乎年龄的智慧。从“人生小语”到“青春笔记”,从“如是缘深”到“与梦相约”,从“天涯短歌”到“艺术走廊”,祝勇将诗意的名字赋予了每一个章节,分享着生命中的欢乐和伤感、丰盈和平淡。如今的祝勇,致力于“新散文”的创作,不再仅仅是文字优美、清韵雅致,与诗意的梦相比,多了几分深沉与凝重。他不断扩大散文的篇幅体量,突破散文和小说的界限,寻求更具辐射力的材料,做出了许多促进“新散文”发展的先锋性的实验。
还需看到,祝勇在“新散文”的写作中似也存在着某些缺陷。首先,“无论是‘新散文’的理论倡扬还是创作实践,都建立在传统散文特别是‘体制散文’的批判之上,”这种批判确有偏激之处。我们理解,“每一代的文人学者,在其崛起的关键时刻,普遍担心被上一代的光环所笼罩,隐约都有弑父情结——或谈论时刻意回避,或采取激进的反叛姿态”(陈平原语)。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文化思考散文纵有缺陷,也是从全新的角度出发观察社会,构筑自己的散文体系,是建国后文化寻根散文开始的标志。对他全盘否定,实有不当。其次,祝勇的历史散文过于强调个人主观经验的融入,纵然他是在对史料系统的研究后才进行书写,但是像身受牢狱之灾的苏东坡,在出狱后,真的会觉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渍,被太阳晒化了吗?这种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势必也会带来历史写作的空洞与抽象。最后,当小说与散文真正实现了“跨体”,我们是将二者合二为一还是舍弃一方的存在?“新散文”家们在沉浸于自己创作的喜悦中之时,是否应该反思,“这种过于专业化、过于先锋性的书写很可能在自娱自乐的同时,流失了大部分阅读者的兴趣,从而重蹈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黯淡收场的覆辙。”(陈剑晖语)
结语
刘心武认为,以祝勇为代表的“新散文家”们,虽意接续“五四”文人的传统,却不是述旧的一派,而精研古典却不沉迷于“古色古香”,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冯骥才说,“一大群站在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中东张西望的作家中,终于有人回过头来瞧一瞧西边天际将灭的晚霞。”祝勇们对“新散文”的执着追求的背后,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是尊重历史、敬畏生命,张扬民族个性。由于工作的原因,在庞大的故宫里,祝勇度过了生命中最安静和沉实的岁月。面对浩瀚的文明,他深入历史细节、收敛历朝风雨。无论是风格的转变还是思想的深化,祝勇始终推广“新散文”,坚守文化阵地。这位温文尔雅、风采清秀的散文家,怀揣着对先人创造的虔敬、对祖辈惊魂的追寻,为我们勾画一幅幅历史画面,助我们深入传统文化的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