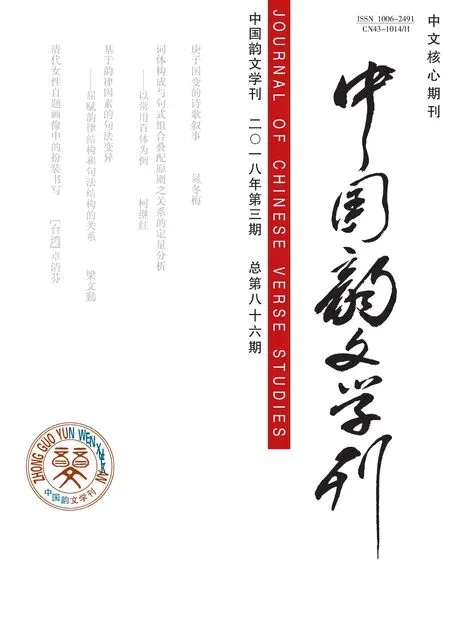“遗民门客”纪映钟与清初京城诗坛
2018-11-13白一瑾
白一瑾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清初遗民诗人以幕府门客身份活跃于京城诗坛者,首推纪映钟。
纪映钟(1609—1680后),字伯紫,又称伯子、蘖子,号戆叟,世为江南上元(今南京)人,生前著有《真冷堂诗稿》《补石仓集》《蘖堂诗钞》多种,多已佚失。今传《戆叟诗钞》四卷,散乱汗漫,已非其原作旧貌。
纪映钟在晚明时代的南京士林中,地位颇为崇隆,与顾梦游并称南京诗坛的两位职志。按郑方坤《国朝诗名家小传》:“金陵为陪京重地,山川姘淑,风物清华,钟鼓声闻,衣冠都雅。是时扶质垂条,星奔川骛者,则必以纪伯紫、顾与治二君为职志。”入清以后,隐居不仕,号钟山遗老。诗作亦多故国之叹,尤以《金陵故宫诗》名闻大江南北。龚鼎孳《纪伯紫金陵故宫诗跋》:“中山一老,徘徊吟眺,麦秀之感,苞桑之惕,凛乎有余恫焉。”
一 “共事十年寄腹心”的“遗民门客”
纪映钟于康熙二年应龚鼎孳以“总角交”名义之邀,赴寓京师,在京生活达十年之久。直至康熙十二年龚氏卒,次年春,纪遂南还,其后隐居南方,再未赴京。施闰章《别纪蘖子》系施氏于康熙十年离京时赠别纪映钟所作,注云“时客龚宗伯宅”,说明当时纪映钟客居京城,是住在龚鼎孳的寓所。其诗云:“白头重别暮尊前,桂树风凉八月天。作客可能忘草阁,移家闻说买江田。贵游每结王生袜,诗品群推记室篇。长忆钟山存一老,十年风雪滞幽燕。”即可见当时纪映钟以南京遗民身份,长期客居京城,且寄居于龚鼎孳幕下的生存方式。
纪映钟入幕后的生活,首先是作为普通幕僚,为龚鼎孳代作文书笔札,处理各种官场应酬事务。阎尔梅在《赠纪伯紫》中写道:
尚书当代之山斗,容众怜才工诗酒。天子亦心慕其名,垂问公卿不置口。登其堂者号龙门,顾厨争附宫墙走。伯紫独为长揖客,正大相规一无苟。笔札应酬意思闲,五官并给不停手。俄顷挥毫千百言,如人意中所夙有。周历宪台三尚书,声誉赫然赖此叟。共事十年寄腹心,脱略形骸称耐久。
阎尔梅与纪映钟交期极密,将纪氏称为“四十五年一良友”;而且,阎尔梅在康熙时代频繁往来于京城龚氏府邸,必然熟悉纪映钟的生存状态。在他的记载中,纪映钟不但作为龚氏的幕僚担任文书事务,而且很可能参与了某些重要政务的处理,因而极受龚氏信任,故云“共事十年寄腹心”。《赠纪伯紫》诗提到阎尔梅与纪映钟的相识,是在天启七年:“有明天启岁丁卯,石头城下秋风早。”末句又云“四十五年一良友”,则此诗必作于康熙十年,阎尔梅最后一次离京之时。因而诗中所谓“共事十年寄腹心”,必在纪映钟正式成为龚氏门客的康熙时代。
其次,龚鼎孳作为京城诗坛“职志”,除政务之外,还有大量的文坛应酬事务:“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即使龚鼎孳确是一个好士爱客之人,如此大量的谒见者也令他吃不消。而这些事务也为纪映钟所分担。在《赠纪伯紫》的记载中,纪映钟甚至担任着对这些“挟诗文游京师”的后进文人进行“把关”的工作:“游京师者纷纷如,鸡鸣早曳侯门裾。……伯紫视之惟一笑,小设匏尊慰客居。谒尚书者旁午至,先向伯紫投空刺。往答天街款段劳,须眉斑点黄尘腻。”龚鼎孳在京城诗坛的显赫声名,纪映钟功不可没。
除了笔札政务和文坛应酬这类“合法”事务之外,纪映钟还参与了不少龚鼎孳援救开脱遗民的秘密事务,这极有可能是龚鼎孳对其“共事十年寄腹心”的真正原因。《清诗纪事初编》:“(龚鼎孳)官刑部尚书,宛转为傅山、陶汝鼐、阎尔梅开脱,得免于死。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又颇振恤孤寒。钱谦益所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吴伟业谓‘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而为龚鼎孳所开脱免死的“长安三布衣”中,纪映钟至少参与了其中两位遗民的援救:
首先是傅山。《傅青主先生年谱》“顺治十二年”条目记载:“金陵纪伯紫映钟、合肥龚尚书鼎孳力救之,事白,释归。”顺治十一年,傅山以南明总兵宋谦策动河南抗清事受牵连被逮,押于太原府受讯。太原府初以逆案上报,被刑部会同都察院驳回,复审后太原府以傅山无罪结案。当时龚鼎孳正是都察院左都御史,且系三法司会审的主要负责人,这一判决显然是他从中回护的结果。傅山之子傅眉在随父系狱期间所作《与古度书》中提到:“囚眉愚见,以为恳边老爷作一申文至都老爷处,将囚眉及叔暂保在外。”信中“都老爷”显指龚鼎孳。而纪映钟当时正在山西巡抚陈应泰幕中,且与傅山系至交好友,在其间起到了周旋联络的作用。《清诗纪事》:“世传(傅)山叛案得纪映钟、龚鼎孳而解,……然则果有其事矣,映钟盖为之周旋者。”
其次是阎尔梅。他因参与榆园军反清事,长期被清廷追捕,流亡四方。康熙四年因乡人出首,复为朝廷所缉,处境危急,阎尔梅不得不携次子秘密入京向老友龚鼎孳求救。龚鼎孳遂慨然应允:“刑部龚尚书,山人故友也,辄力为解,自矢曰:‘某岂恋旦夕一官,负天下豪贤哉!夫以忠义再罹难,吾不能忍矣。’乙巳十二月十一日特书题释。”其间,纪映钟百般设法,不仅为阎尔梅代作辩章,且利用清廷自首宽免的刑例,假报阎氏年岁,在阎氏获释过程中出了极大的力量。鲁一同《白耷山人诗选本·七言律》有《纪伯紫白仲调为予草辨章小僮贞宁持诣刑部上之僮十四岁》。孙运锦《白耷山人别传》记载更详:“适纪伯紫白仲调崔兔床皆在龚处,因时有诣狱放还之例,为作辩章,增其年十岁,使小僮上之刑部,龚司寇据以老病入告,得谕旨放还。”
纪映钟虽入清廷“贰臣”之幕多年,但颇能自重身份。他不但终身不仕清,且除龚鼎孳本人外,并不与其他清廷大僚轻易结交,更无干谒权门希求出山之意。这使得他与一般门人“清客”之流,有本质上的区别。郑方坤《国朝诗名家小传》:“伯紫以青云白雪之身,皭然不滓,少与庐江龚宗伯友善,宗伯既贵,招至京华下榻,岁且十稔,此外未尝轻谒一人,轻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因而时人对纪映钟依附龚鼎孳为门客之事,多持宽容态度;对其名节问题,也大多无甚异议。若同系遗民人士的方文有《赠纪伯紫》:“但得贤主人,何须悲道路。顾念长干里,父祖有丘墓。多积买山钱,仍回旧京住。”
二 纪映钟入清后的数次入京
纪映钟正式的幕客生涯,虽然是始自康熙二年,但入清后纪映钟与京城的渊源,却早在顺治时代即已开始。顺治十年夏,赵开心起用入京待命,纪映钟受其聘一同入都。纪映钟《真冷堂诗选自序》:“今夏浪游燕市,汇思姜子论诗甚欢。欲予出其所有以丽于姜子及圣秋韩子、凫盟申子之间,而予野处久,敝帚尘积,杂乱潦草,未尝携之游笥中,仅记忆数十章以应之。至燕市近篇,乃十留二三焉。”纪映钟到京的时间,或在顺治十年五月。他作于京城的《姜汇思侍御置酒歌》云:“侍御置酒苍藤悬,五月六月如秋天。”
《真冷堂诗稿》附录韩诗《戆叟诗选序》中,还记载纪映钟有这样一段议论:
壬辰春,余以师命再游长安,明年夏,叟亦受御史大夫赵公聘,相遇于京洛。客有讶之者,叟曰:否否。独不见圣予、景熙乎?圣予往来故京,画马自给,景熙教授泉州,其诗凄婉沉郁,有唐余音,独不能与二君子上下千古乎?
身为遗民而入清廷大僚之幕,在清初士人讲求名节的环境中,不乏可议之处。而纪映钟遂以遗民龚开、林景熙自喻,以示自身虽入幕而不改节。
此次纪映钟在京城与龚鼎孳多有唱和,龚鼎孳有《送陈行五之登莱和伯紫彦远韵》等。纪映钟《真冷堂诗稿》亦有《雪中书所见呈龚少司寇并简见未在辛燕友三郎中》。龚鼎孳任刑部侍郎事在顺治十年四月至顺治十一年二月,此诗必作于顺治十年末。
此次纪映钟在京一直逗留到顺治十一年五月,方赴山西巡抚陈应泰幕。龚鼎孳有《送伯紫之晋阳》,其五云:“数子林中侣,同时邺下游。龙潭初珥笔,河渚竟归舟。雨湿啼莺路,人分战马秋。最怜挥手罢,蓬迹感淹留。”注云:“伯紫西行,彦远南返,而吾与圣秋踯躅京洛,人生何能长合并也。”提及纪映钟赴山西,以及另一位遗民人士胡介启程回乡之事。胡介回京时间,以王崇简《赠别胡彦远》诗,收录于《青箱堂诗集》卷九,注明“甲午”,显然是顺治十一年春的作品。纪映钟也参与了送别胡介的唱和,在胡介回乡之后离京。离京之时系十一年端午,龚鼎孳有《纪伯紫午日过别留宿小斋是夕大雨》:“旅雁愁闻度太行,檐花偏落故交觞。别逢五日丝堪续,雨过三更话渐长。军府文章推建业,中原人物问明光。射雕跃马吾真懒,他夕重连薜荔床。”
顺治时代纪映钟的第二次入京,在顺治十五年秋。龚鼎孳有《喜伯紫至都门和长益洞门韵》,按龚鼎孳于顺治十三年南下使粤,过杭州时曾与纪映钟见面。纪映钟《过岭集序》:“客岁秋冬之际,孝升先生将有东粤行,时予适寓武林,轺车至,迓之北关,先生留予宿舟中。”次年龚氏使粤归来,途经南京,包括纪映钟在内的诸多南京遗民俱来相送,多有唱酬,参看《伯紫招集孝侯台秋眺》《秋日偕澹心伯紫子翥过寒玉郊园小饮竟日》《于一伯玑苍略子翥秋我杓司伯紫澹心绮季诸子别于燕矶》等。《喜伯紫至都门和长益洞门韵》其一云:“隔岁同登周处台,菊花寒共鬓毛摧。”其二云:“万事江湖惭计拙,一年灯火似君来。”则纪映钟此次入京,必在南京送别的次年,即顺治十五年秋。其后,纪映钟在京参与龚鼎孳多次唱和,如《同伯紫赋送绮季之晋阳》,事在顺治十五年冬。此诗之前有《送李琳芝侍御察荒中州》,李森先河南查荒事在顺治十五年十月。《元夕雪后伯紫绮季过集和空同韵》系顺治十五年元夕。又如《正月六日伯紫友沂过集》、《立春前二日谈长益纪伯紫姜绮季赵友沂陈子寿同鲍子云夜集》二诗。以其下《送严颢亭都谏假归虎林》诗,严沆请假归乡葬亲,事在顺治十六年。则此次纪映钟与龚鼎孳的在京唱和,必在顺治十六年正月。又如《韩大令叔夜将之永嘉值其初度同伯紫赋赠》,按《晚晴簃诗话》:“韩则愈,字叔夜,鄢陵人,贡生,官永嘉知县。”光绪《永嘉县志》:“韩则愈,字秋岩,鄢陵人,顺治十六年以恩贡来知县事。”可知龚纪二人此次酬答,也在顺治十六年春。
本次纪映钟在京居住数月,于顺治十六年春前往福建。《送伯紫从金陵之闽中》:“纪叟临岐但一醉,赠诗不羡姑山多。纵无佳句代谖草,应有清梦随烟萝。闽南荔子五月熟,舍东桃叶三春波。暂归远游亦快意,安能尘土长婆娑。”以其上《三月廿三日见西山积雪》及其下《闰三月十二日张司空招集慈仁寺看海棠余与洞门先至》,可知纪映钟此次离京,在顺治十六年春。而以作于顺治十六年秋的《九日同圣秋与可绮季园次宗来玉少登毗卢阁复饮松下仍叠前韵》:“却怜纪叟闽山麓,刺促钟鸣与鼎食”,可知此时纪映钟身在福建。
纪映钟在顺治时代的第三次入京,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只可确定顺治十八年他在京城,参与了龚鼎孳送陈祚明回乡的唱和。《定山堂诗集》有《集慈仁松下送无称胤倩同圣秋灏亭伯紫峻度和胤倩韵》。陈祚明回乡事在顺治十八年八月。
不过,纪映钟最后在京城的定居,还要到康熙二年应龚鼎孳之约入京,直至康熙十二年龚鼎孳去世以后离开京城。他也正是在这十年间,成为京城文化圈的长驻成员。由龚鼎孳在这十年间的诗作可以看到,龚氏在京召集的大规模文人集会,大多活跃着这位“钟山遗老”的身影。若康熙三年重阳的黑窑厂之会,《定山堂诗集》有《九日招崔兔床吴岱观姜绮季朱鹤门王望如纪檗子白仲调项器宗阎秩东纪法乳姜孝阿沈云宾王公远黑窑厂野集用重阳登高四韵》。黑窑厂是京城宣南地区风景胜地,生性好游而又宾客众多的龚鼎孳,极喜在此地登高游赏。程可则《题合肥龚大司寇祝册》其七:“岁岁重阳节,高丘此地登。”注云:“右龙爪槐在京师宣武城南最高处,公每岁九日与同人吟眺其地。”而这些登高游赏活动,纪映钟几乎皆有参与。若龚鼎孳作于康熙六年春的《花朝春阴同伯紫兔床椒峰法乳孝阿集黑窑厂分赋四首》:“岁岁长安陌,暄迟负柳条。萍逢惟数子,花发又今朝。杂坐侵芳草,狂呼倚碧霄。台空尚萧瑟,相劝酒如潮。”《九日黑窑厂登高同方虎国子康侯青藜纬云榖梁仲调伯紫湘草次康侯西山韵》:“彭泽卑栖也弃官,肯因马栈负烟峦。天连野色浮空阔,人坐秋阴爱薄寒。餐菊饱应骄五斗,振衣轻不让千盘。兰皋延伫游将远,讵必高予岌岌冠。”此次登高,事在康熙九年重阳。
其余若康熙五年春,阎尔梅入京,龚鼎孳召集京城多位士林名流与之唱和,这其中也有纪映钟参与。《定山堂诗集》有《春夜集慈仁海棠花下同古古伯紫限韵》、《上巳后一日招同古古兔床伯紫仲调集慈仁寺海棠花下是日晨雪》。到康熙六年冬,阎尔梅再次入京,纪映钟也曾参与龚阎二人的唱和活动。《定山堂诗集》有《古老过集拈空同马上城中见雪山之句同作》及《雪后古古檗子础日子寿方虎荆名遥集康侯锡鬯湘草武曾纬云竹涛青藜仲调糓梁武庐同集小斋古老限杜韵即席四首是日稚儿初就塾》,均是阎尔梅于康熙六年冬入京时所作。次年六月,陈维崧入京,纪映钟又和龚鼎孳一起与陈维崧聚会唱和,《定山堂诗集》有《雨夜伯紫其年小饮春帆即席分韵》。
三 “独为长揖客”:纪映钟入幕之生存状态
在龚鼎孳幕下的文人唱和活动中,一方面,纪映钟作为龚鼎孳的门客身份而出席,但仍能保留一种嶙峋傲骨,有别于俯仰随人的“清客”之流。而这一点也得到龚鼎孳的充分尊重,《集仲调寺斋》其四云:“怪他龙性异,对酒不能驯。”注云:“为檗子先归。”龚鼎孳性格豁达,又有好士之名,对于这位钟山遗老的不驯之性,具有相当宽容的态度。
另一方面,纪映钟的布衣身份,和超然名利场外的立场,也是龚鼎孳这位文人气息浓厚的高官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他在《琉璃厂眺月同伯紫孝阿》中写道:“不识鸣驺地,林塘意外幽。晴沙初吐月,高树总浮秋。官事听蛙减,寒星带雁流。平生丘壑兴,倦眼一时收。”与布衣友人游赏京城胜地琉璃厂,自然难免会引起龚鼎孳那一种文人气的“丘壑之兴”。
而纪映钟作为遗民的名节无亏的生存状态,更能引发龚鼎孳这位名节丧尽、处境尴尬的“三朝元老”的慨叹与羡慕。龚氏《与纪伯紫》:“铜驼萧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胜林惭涧愧之至。悔此小草,困倍飘蓬,惟时咏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句,以自忾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时能去于怀。尘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在抒写自己与纪映钟深挚友谊的同时,自己身为贰臣的凄苦,也展露无遗。这也正是龚鼎孳平生好士成癖,且特别乐于结交与接济遗民的隐秘心理动因。
从纪映钟本人的心态来看,他虽浪游京城、托身龚氏幕中,亦不免与其他清廷大僚有诗文往来,但他始终不忘自己身为“钟山遗老”的志节。他在顺治十年入京后的当年冬天,有《喜稚恭至》云:“小草非初意,长安且漫游。”已明己不愿出仕之意。《西家女》一诗,出言更为激烈:
西家女,未出阁。东家女,三易夫。东家貌肥黑,西家艳芙蕖。蹇修大都来,手持双璧鱼。一见东家女,载以鸾铃舆。西女闻,笑且吁:我宁守我纺缉车,不愿易夫如蘧庐!
此诗笔墨相当辛辣,也可知纪映钟对挚友龚鼎孳的“贰臣”身份和身为“三朝元老”的历史,其实也是颇有看法的。
在龚氏幕下时,纪映钟对自己的定位,颇类于战国时代诸侯宾客的角色。他自称“决不可为郗参军,亦不甘为陈书记。择主择宾各有伦,男儿心耻曹桓辈。以是名震诸王侯,雅有推扬无谗忌”。他不但要求来去自由,而且坚持自己为人处世的底线。所以,他在与龚鼎孳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以敢于规劝的诤友面目出现:“伯紫独为长揖客,正大相规一无苟。……周历宪台三尚书,声誉赫然赖此叟。”
而龚鼎孳对他以平等的友情相待,无疑也是纪映钟能够泯然彼此身份立场之界限的原因。他在《立春次日孝升奉尝北发置酒高会紫淀长歌送之依韵倚和》中,回忆龚鼎孳丁忧南归以后,在南京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诸多遗民诗酒唱酬的往事:“日偕诸子坐香幢,声宣金石商歌发。曹刘沈宋才各展,古钗脚注冰文茧。”在纪映钟心目中,他后来在京城客居时与龚鼎孳的往来,也不过是南京诗酒唱酬的延续。同时,纪映钟给自己和龚鼎孳的定位也颇耐人寻味:“孟郊倔强尊韩愈,山谷钦岐事老坡。”他以孤高寒士孟郊、黄庭坚自喻,而以好客爱士、提携寒士的高官文人兼文坛领袖韩愈、苏轼喻龚鼎孳,这种定位,显然是强调彼此文人身份,而尽量虚化彼此出处立场的差异。
不过,纪映钟对自己的幕僚生涯也并非没有慨叹乃至痛苦。他在《感兴》一诗中写道:“我生山泽儒,经年事柔翰。胡为频远行,风霜切陶坂。只怜骨肉孤,屡犯湖海澜。贫贱自危苦,因风发浩叹。”身为“山泽儒”而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流寓他乡、依人门下,即使是龚鼎孳那样的“贤主人”,他的内心也是苦涩的。这种苦闷,显然来自于他虽然身为遗民,却以幕僚身份在清廷大僚的圈子中活动,因而不得不采取一种谨慎乃至于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伯紫恂恂法圣贤,沈潜不露英雄气。携家北从尚书游,绿水芙蓉何其丽”,“来往燕京辄聚首,我每纵横君杜口。至慎有如阮步兵,玄言清绝无臧否。蕴藉闳深不可方,珠秘精华剑隐铓。明哲保身诵山甫,大智若愚贾深藏”。
这也就可以解释,纪映钟在对待另一位曾经一度流寓京城,来往于仕宦高官之门,却终于白衣还山的遗民人士胡介的态度。顺治十一年春,胡介南归钱塘故里,包括龚鼎孳在内的大量京城文化名流有诗相赠,纪映钟亦有《彦远别我南归》一诗。他先是回忆自己在顺治二年即得悉胡介之名,“记昔乙酉岁,断发出奔走”。当时的胡介“既道姓名罢,行藏更非苟。淡比松下禅,坚类柏舟妇。一家河渚栖,梅花带左右。入林恐不密,数峰当户守。内子亦苦吟,研山间井臼”,是一位隐居故里、清苦自守的遗民。“此语今十年,梦魂未尝负。荦荦千秋名,沦落同敝帚。投刺长安道,错愕辨真否。烧灯韩子庐,浊醪倾几瓿。平生性命欢,独此堪不朽。长歌贻骞修,再歌示良友。环堵生烟霞,真怀动星斗。何意超古初,只不落人后。”虽然他与胡介在京城相处颇为投契,但对胡介入京以后来往于权门的生活,还是略有不满的。是年春,胡介归乡,“春到理归鞍,故人备粮糗”。纪映钟十分欣喜,于是反复叮嘱胡介,归乡以后务必谨守遗民的生存方式,勿再轻易出外干谒权门:“离合固难期,□归毋回首。湖上多桃花,涧中赢南亩。莫带长安尘,轻点溪□酒。”这对于本人尚在寻求入幕机会的纪映钟来说,实在是一种颇为苦涩的慨叹。
值得注意的是,龚鼎孳在与入京的遗民文士进行聚会唱和时,往往同时邀请纪映钟出席。其中以龚鼎孳与阎尔梅的往来尤其明显。阎尔梅于康熙后多次入京,与龚鼎孳往来,而龚氏几乎每次都同时让纪映钟出席。其中可考者如下:
康熙四年,阎尔梅与次子阎焸因狱事入都,求救于龚鼎孳。龚氏时为大司寇,职掌刑部,为题疏得免。阎尔梅本人于康熙四年九月入京,直到康熙五年春方离开京城。其间曾与龚鼎孳多次唱和,而纪映钟皆在座。其中可考者包括康熙五年元旦,阎尔梅有《丙午元旦孝升招饮与伯紫仲调炅儿同赋》。康熙五年元宵节,阎尔梅有《元宵与龚孝升纪伯紫白仲调同用钱牧斋灯屏旧韵》,是年春还有一次唱和聚会,有《春夜集孝升斋中偕魏子存刘公勇程蕉鹿王西樵王贻上崔兔床伯紫仲调限韵》。直至阎尔梅离开京城,龚鼎孳在西堂为之送行,纪映钟也在其列。纪映钟有《送古先生还沛上》诗。
康熙六年冬,阎尔梅再次入都,寓真空寺,一直在京城滞留到次年三月。其间的唱和活动,纪映钟也大多参与,包括康熙六年冬的《雪后古古檗子础日子寿方虎荆名遥集康侯锡鬯湘草武曾纬云竹涛青藜仲调谷梁武庐同集小斋古老限杜韵即席四首是日稚儿初就塾》。康熙七年人日之会,《白耷山人诗集》卷六有《戊申人日孝升招饮与周鄮山陆冰修朱锡鬯纪伯紫分韵》。直至康熙七年三月,阎尔梅离京,龚鼎孳招集众友于真空寺为阎尔梅饯行,纪映钟也曾参与。《白耷山人诗集》卷六上有《戊申禊日诗》十四首,序云:“余久客燕京,戊申春将南去,大司马龚公以三月三日饯我于城西之真空寺。……同席有金陵纪伯紫,武林吴兴公,长洲文与也,嘉禾吴佩远,龚伯通,龚禹会,龚雪舫暨二儿焸。”其十下自注云:“纪伯紫时在司马幕府中。”
康熙九年春,阎尔梅复入京城,立春后二日,周在浚携具过饮龚鼎孳寓斋,阎尔梅亦在座。龚鼎孳有《嘉平立春后二日雪客携具过小斋招同古古条侯平子湘草谷梁檗子饮中限韵》二首。四月初一,龚鼎孳和纪映钟、曾粲、何昭侯在真空寺为阎尔梅饯行。《白耷山人诗集》卷六有《孟夏朔日宗伯偕伯紫青瓈昭侯饯余真空寺限韵》。
可以看到,龚鼎孳与阎尔梅在康熙时代的整个交往过程中,纪映钟几乎每次唱和活动都参与其中。这一方面当然与龚鼎孳在宽免阎尔梅案件时,纪映钟曾从中相助有关;另一方面,龚鼎孳实际上也是藉由纪映钟之遗民身份,拉近自己与其他遗民士人的心理距离。龚鼎孳虽有好士之名,毕竟大节有亏,因而在与遗民文人交往时,双方都不免尴尬。而纪映钟这位身份特殊的“遗民门客”的出席,对于此种尴尬情形,则是一种有力的化解。以《云中古檗二老仲调小集花下叠韵》为例,其诗云:“四海双蓬鬓已银,艰难身许故交真。一枰棋局浮云过,依旧南枝逗眼新。”两位渡尽劫波的前朝遗老,再加一位同样是渡尽劫波的“贰臣”,三位老友于尊前共话陵谷沧桑的情形,宛然可见。
由于纪映钟具有前朝遗老与龚氏门客的双重身份,他往往能在龚鼎孳与遗民士人交往的过程中穿针引线,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传达彼此囿于身份而不能明言的复杂内蕴。仍以阎尔梅为例,他本是在明亡后破家养士、抗清复国的志士,半生奔走四方,遭受清廷通缉。龚鼎孳出于友情义气,为其解脱狱事。以龚氏的心态而论,他是真心希望这位心如铁石的老友能从此放弃反清之志,回归故里安分隐居以终老天年;但却又囿于双方政治立场,不能直接相劝。而纪映钟则正可充当这一角色,他的遗民身份,更容易被阎氏视为自己人。所以,纪映钟在《送古先生还沛上》诗中,既盛赞阎尔梅“不为蹈海不封留,剩水残山蹑屩游”的坚贞志节,也颇有善意的规劝:“不死还应重此生,老年作别自心惊”,“却袖剸蛟驯鳄手,澄江如练好投纶”。这样入情入理的规劝,想来阎尔梅也不会十分排斥。
纪映钟不仅善能斡旋于龚鼎孳与遗民士人之间,而且在遗民友人与京城其他新贵士人发生冲突时,也能善加斡旋保护。按阎圻《文节公白耷山人家传》记载,阎尔梅于康熙五年春离京时,京城众友人在慈仁寺为之送行,时有新贵在座,在席上冒失地劝说阎尔梅仕清:“客有官太史者,顾谓山人曰:先生不仕。先生仕,愿以明史任先生。”性格刚烈的阎尔梅当即峻拒,并引用靖难之役时拒燕兵于金川门外,其后又拒仕永乐朝的龚安节为例,称“我仕,于义则无害,如有愧龚安节。”由于阎尔梅言辞过于激烈,还差点提到“某初与诸同志者起”的反清往事,考虑到他刚刚获赦不久的“前政治犯”身份,纪映钟担心横生枝节,马上在席间大呼“先生是也!止勿复言。”化解了一场风波。
四 纪映钟与京城文化圈之互动
由于纪映钟长期随龚鼎孳生活在京城,他也得以在京城文化圈扎根,并且结识了不少京城文化名流。其中较著名者有:
与宋琬。纪映钟和他订交,系在顺治十年入京之时。《赠宋玉叔》:“宋家世出斵轮雄,熹烈二朝玫与琮。……琬也连枝呼小宋,嵁岩气骨霞丰容。总卯读书万破卷,捉笔横扫千人锋。真辨阳虚探鸟迹,挥斤迁固卑衡邕。浩如东海势回薄,峻比泰岱封长松。……长安瘦马行蹉蹉,归掩双扉侧弁哦。意立皎然行已决,随情赋物篇尤多。”是年冬,宋琬补官为陕西陇右道佥事,纪映钟又有《送宋荔裳佥宪河东》一诗相赠。
与杨思圣、魏裔介。杨魏二人皆系河北籍仕宦诗人,又是京城士林名流,时有“杨魏”之称;而身为南方遗民的纪映钟得以与他们结识,也得益于他寄寓京城并客于龚鼎孳幕下的生活状态。他在顺治十一年离京赴山西之时,作有《二君子行别杨犹龙学士魏石生都谏》:“巨鹿栢乡下,君子予所钦。巨鹿破万卷,闭户如深林。鸿文出枕闷,古调弹幽襟。栢乡富谠论,杰立明堂琛。经纶资庙算,旷思悬峰阴。……予见二君子,山高而水深。忽发三晋辙,将访首阳岑。”后来,纪映钟虽然一度出京,但仍与杨思圣等人保持着书信往来与诗文唱和。《圣秋至自蓟门得杨犹龙方伯书兼有所贶赋谢》:“杨子寄书汴水头,致之者谁韩荆州。开缄朗朗见秋雪,新诗千百惊心眸。温然尺素语真切,兼损清俸双精镠。我知杨子作吏如冰蘖,亲从学士领藩臬。……却忆悲歌在燕市,手披韦素忘金紫。朝罢元亭闭竹阴,诗成海淀看流水。”魏裔介亦有《复纪伯子书》书信一札,回忆纪映钟顺治十年在京城与他的往来:“素心晨夕,良晤在怀,忽而迈征,咏采葛之章,为之三叹。足下高怀不羁,真气迎人,每向长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足下嗜痂之好,乃比之于昌黎,仆诚愧死矣。若乃东野之达,则足下实足以相后先也。”
与申涵光。申涵光是著名的直隶籍遗民,也是北方最知名的遗民诗人团体“河朔诗派”的主将。纪映钟与他结识的时间,应也在顺治十年夏秋时节,是时纪映钟随赵开心入都,而申涵光以请父恤事入京。申涵光有《偶过韩圣秋寓值纪伯紫姜汇思快饮时汇思将南归》,其一云:“下马闻高会,开帘尽所亲。秋花盈小院,京市有闲人。老向何方好,交怜我辈真。十年江左梦,风雨念西秦。”“十年江左梦”句,显指申涵光在甲申之变以后,一度南下避乱,到本年正好十年。
另一首《社集金鱼池柬韩圣秋纪伯紫姜汇思邓叔奇》系在京城风景胜地金鱼池与纪映钟等聚饮:“南郊宫殿锁遥空,今古凭栏感慨中。故里秋花三月别,天涯词客一罇同。朱鱼就日冲寒藻,白雁呼群度晚风。世事安危公等在,疏狂应任鹿皮翁。”味其诗意,也是在顺治十年秋。纪映钟《真冷堂诗稿》则有《题节愍申先生册应凫盟请》。后来纪映钟南归,申涵光还有《寄金陵纪伯紫》回忆自己在京城与纪映钟订交之事:“昔在金台侧,逢人问酒徒。黄花吟入寺,白眼卧当垆。狂任公卿怪,清寻霜月孤。园陵看蔓草,血泪几同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