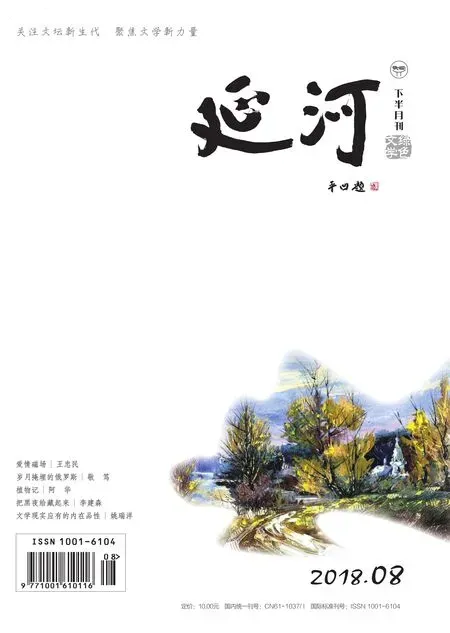文学现实应有的内在品性
——以鲁迅、格非、余华、苏童等作家作品为例
2018-11-13姚瑞洋
姚瑞洋
俄国理论家尤•迪尼亚诺夫在谈论何为“文学事实”时说:“并非在文学的中心有一条固有的、连续的溪流在运动、在进化,而在其两旁则只游动着新的现象,不,这些新的现象代表的正是中心本身,中心则成为周边。”他指出进入文学领域的“事实”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位移”和“进化”,这对我们审视当下的文学现实仍为可取的观点——哪些现实内容可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这需要作家作出兼具时代特征和个人感悟的甄别。但不妨把文学现实比作一条大河,一条寓于时空、流变不息,时刻与人的存在相伴随、且相互作用的大河,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最佳距离介入现实,以便一睹它的汹涌壮丽。还要指出的是,文学现实虽一直在流变,但其流变绝非毫无规律可言,读懂了它的内在品性:自然、宽度以及深度,或许它会自然流淌而来。
一、自然:当代语境下人性真情的流溢
文学现实的第一个品性就是自然,文学表现现实大忌生搬硬套,需使现实“随风潜入夜”。要承载流变不息的现实素材,文学首先要具备与之相符的形式,而文学形式的演变又受自然与人为两方面力量的影响。当代文坛持续的迭代更新值得我们思考,这可能是过度人为导致的结果。晚生代、新写实紧跟先锋文学的步伐,于此之后又是什么?急于树立新的叙述标杆的后遗症就是容易忽略文学其他方面的建构,形式实验退潮后先锋作家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和意义的苍白就是其中一例。格非的《褐色鸟群》可谓玄奥至极,但它所表现和隐喻的现实却几乎空洞无物,它赖以生存的就是玄奥难懂本身。现在返观之,难免存在故作惊人的问题,连格非本人都笑称:“我也看不懂”。中国当代文学磕绊至今,应该可以更从容地栽培一种混融、恰切、有力的叙述来支撑现实。格非《人面桃花》的古色古香在新世纪文坛足以独树一帜,那为何《褐色鸟群》可能是过度人为,而《人面桃花》却是自然生长?因为格非作《人面桃花》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表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加之独处异国他乡,寻根的潜在冲动易于涌现,中国文学的古典气脉才自然流淌于字里行间,这才是文学自然应有的唯一逻辑,混夹其它杂念则必定损害文学自然。拥有充足的历史耐心,让形式自然自由地发育生长还只是现实自然的第一阶段。
现实自然的第二阶段是语境自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特定的语境,对的人出现在错位的语境,怕是什么人物都无用武之地;而如果对的人出现在深度吻合的时空,意境便水到渠成了。我们谈论文学自然,应回到文学现实,回到真切的生活体验,唯其如此才可能在读者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可以被看作当代生活体验开始的里程碑,它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一脉相承的。微信、支付宝、共享单车等时代新象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基础,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但是这里还隐含了一个更内在的问题,是不是找准了当代的界标就达到了语境自然的效果?其实还不能在这里下肯定的判断,客观的当代现实要进入文学的语境自然还需转化处理,并非非虚构性描写可以胜任。一个可供言说的文本是余华的《第七天》。应该说,当时学界和市场都对余华《兄弟》之后七年之久的最新长篇力作持有一定的期待,他将如何续写绝望与荒诞?可是《第七天》的绝望与荒诞似乎给人一种错愕感,既没有从前血淋淋的犀利,又难言其它惊艳之处。问题可能出在当代语境的建构、氛围的营造太过真实,给读者省去了隐喻和象征的美感。虽然《第七天》全书充斥魂灵虚幻的叙述笔法,但所描绘的无疑是高度还原的当代现实,不少地方直接就是新闻记录般的挪用。可见语境自然并不以真实为唯一标准,还需对生活现实进行隐喻和象征的艺术化加工,是一个真实与艺术的动态平衡。
有了形式自然和语境自然的加持,我们就可以谈论现实自然的最高阶段——人性自然了。换言之,人性真情的自然流溢。长久以来,笔者有一种隐约的阅读感受,在对人性的书写上,中国文学不及西方文学那么勇敢、透彻、深刻,不敢或不愿揭露最丑恶的内心,从而也就无法呈现人性最深处的善恶博弈。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人也貌似普遍比中国人开放,这里所指的开放,即以经济基础为核心的个体性与不可侵犯性。目前来说,文学史界的一个共识是,西方文学始于史诗,中国文学发于《诗经》,这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西异古,并产生出两套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西方史诗,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诸神有着强烈的人情世性。史诗既活在社会的上层,又活在民间,它的世俗性使它容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声音,而且具有集体性的表演娱乐性质。它贴近听众的趣味,目的就是赚取利益,表演者与观看者双向的、以金钱为核心的经济意识便早早凸显在西方文化心理结构里了。这种乐于表露自身情欲哀乐、价值取向——尤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的文化心理不妨称之为资本世俗。发端于《诗经》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包含政治功能、实用主义以及抒情传统,不妨称之为政治世俗。政治世俗和资本世俗最大的差别可总结为:资本世俗强调盈利性和个体性,政治世俗重视抒情性和集体性。所谓集体性就是说政治世俗不以个体为中心,不以自我实现为最高追求,甚至说政治世俗有生以来就自带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属性,平民百姓的欲求在一定程度上被约束了起来。这解释了上文所述的中国文学作品不及西方那么“放”的原因,再加上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及浪漫主义运动的催化促进,中国迟到的五四和改革开放若能力挽狂澜,那也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想象了。
回到人性自然的讨论上,认识到中西异古的思想资源和人性传统后,我们应该如何透析当下社会的人性?笔者以为,中国正在经历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就是政治世俗与资本世俗的糅合重塑,当下社会涌现出来的众多乱象都是人们在资本世俗面前把持不住造成的,这是人性的自然乱象,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现实,是当代文学最渴望书写的灵魂素材。
二、宽度:历史长河中人间万象的海纳
文学作品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厚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也是文学现实内在品性的题中之义。何为现实的厚度?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之现实,现实的厚度意味着作品不能只表现自身亲历的单一时代之现实,还应通过打通单一时代之现实与其它时代之现实的关联,把多时代之现实的深刻关联看作一个整体来全貌式地呈现。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实包容一定比现实自然更深一层,精准地找到多个现实自然之间的深层内涵关系,现实包容才有可能被探索。
要在能够写出现实包容的作家群里挑选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非鲁迅先生莫属了。其作品蕴含的思想高度与承载的现实厚度都足以让诸同仁望洋兴叹,这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解读时说时新的原因,甚至还有跨学科研究的介入。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学界依然对鲁迅先生保有持续的热情和敬畏,但是我们不从当下对鲁迅先生的解读谈起,让我们回到那个激扬的年代,让现实的厚度自然流淌出来。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钱理群等有过这样的论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并充分肯定了《呐喊》《彷徨》成熟的现代小说艺术,还援引严家炎对《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的评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从形式的现代化来看,现实的形式自然做到了。鲁迅先生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和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借鉴都服从于他表现民族精神顽疾的深切愿望,形式和内容相辅相成。从内容的现代化特征来看,现实语境与现实人性的自然效果达到了吗?鲁迅先生深刻地剖析了当时的语境,哪怕在短篇小说的篇幅里也能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愚昧气息,与现时代语境的距离感不言而喻;进而,人性的顽疾开始显现,如封建的“吃人”本性和灵魂的沉默麻木,重铸国民性一直是鲁迅先生书写的驱动力。以上是现实自然,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自然才进入了现实包容?鲁迅先生批判的愚昧麻木和“吃人”的封建传统只是清末民初时期的问题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往前看,中国的封建传统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尔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强化。往后看,鲁迅先生痛恨的国民性被启蒙打倒了吗?启蒙在五四时期就像惊鸿一瞥般珍贵,很快就被救亡图存全面压倒,后又被特殊时期意识形态所管控,如今又受后现代主义的钳制。现代性的很多结构尚未完善,即刻就要面对无情的解构,启蒙已经成为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话题。最重要的,不是文学引导了现实,而是现实催生了文学,哪怕是借鉴,也要有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已不容申辩,文学必须跟上。被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到了后现代主义这里,只剩下一条干瘪且若隐若现的尾巴了,但毕竟它是渗透到了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原本就是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现代启蒙的后续产物,到那时候,鲁迅先生的发现或还能继续往下延伸。从西周延宕到当下,这就是容纳人间万象的现实包容。
上文谈过,不是文学引导了现实,是现实催生了文学,那么文学现实的包容就必然源于现实生活的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经历过三大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其一,汉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以及内化;其二,近现代时期对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的模仿学习;其三,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价值、观念等微观方面的普遍东渐。作为唯一一个绵延千年不断的古文明国家,中国社会在生活现实的包容、内化上有着辉煌的历史。今天这个薪火相传的大熔炉已前所未有地膨胀,古今中外所有的信息、资源在这里冲撞,变革的社会、矛盾的人性和新鲜的事物在这里混搅,这样丰富饱满的现实理应成为培植文学的沃土。但令笔者遗憾的是,当代文坛还是喜欢写历史、写乡土,或者说,书写当下现实的时候常常会表露某种苍白无力,或许这也是当代难出像鲁迅那样的大家的原因——无法抓住当下现实。回到当下现实,抓住当下现实,以当下现实为主导再辅以历史源流,这才是生活现实和文学现实的开拓,是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三、深度:生命本质里存在意义的发掘
现实的深度,即在现实包容的审视下发现事物的规律、生命的启示——我们为什么活着?文学的现实包容隐含的一个道理是:为人为事、立言立物最后都归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换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但这只是功利性的思考逻辑,难道不得天下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吗?显然不是,那我们苦苦追寻的生命更为本质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问题还是得让鲁迅先生领路。刘再复在本世纪曾两度谈起鲁迅先生的灵魂维度,第一次说道:“阿Q只能视为中华民族古旧灵魂——集体无意识的图腾,而不能视为个体生命的图景,在阿Q身上,没有明显的灵魂的对话与论辩。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法庭门前站住,然后退出……鲁迅的退出说明了即使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并解剖过国民集体灵魂的最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也没有向灵魂的最深处挺进,明知‘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必须同时也是‘伟大的犯人’,但终究没有兼任这两个伟大的角色。”这当然是在用世界文学史上伟大作家的标准来要求和看待鲁迅先生,受制于民族大义的呼唤、社会环境的动荡、写作寿命较短等诸多因素,他确乎没有在小说中成熟地叩问生命个体的灵魂维度,但这不代表他没有关注,恰恰相反,鲁迅先生把个体生命灵魂的存在意义付诸其一生的实践。刘再复第二次评论时言道:“由于他摆脱当时流行的、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极中作选择的做法,因此,他既继续启蒙,又超越了启蒙,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叩问个体存在意义的维度,达到对个体存在的把握。”这里的“集体主义”意指当年众多新文化先驱陆续投身救亡革命运动、文学沦为救亡和革命工具的现象;“个人主义”意指另一部分作家逃遁至纯文学的世界以安身立命的现象。鲁迅先生明显异于这两股潮流,其实他已经意识到先前自己曾批判的所谓旧传统、旧文化早已不是外身于我的他者,而是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潮头上鲁迅先生显得惊人地清醒,就像他怀疑自己也曾“吃过人”一样。在矫枉过正的声浪中保持意识的清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何鲁迅先生能逆流而上,发同仁所不发,见时代所未见?
鲁迅先生从未止步于某一样事物或某一种思想,他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行,通过否定自我来更新自我。所以他能看到层层纵深的景象,在他的思维中永远有一个等待追寻的真知——萨特的“欠缺”,这个“欠缺”可能就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人生来就自带“欠缺”,这“欠缺”是生命存在的无形部分,赋予人的行为以意义,直到死亡把生命变成命运,人的自在存在才与“欠缺”引起的自为存在完全重合为一个完整的人。鲁迅先生在《墓碣文》中所言的“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就提醒我们要整体性地看待他的思想,“欠缺”引着他纵横于历史转折处,他的小说虽未能充分表现生命个体的灵魂博弈,但以他另外的文字作为补充。整体观之,其激昂奋进的一生和厚重深刻的思想力透纸背地书写了生命个体的存在意义——永不停息地追寻“欠缺”。
与之相反,如果人的自为不够强大,“欠缺”不够清醒,虚无化的过程过于模糊,不足以把握自身的行为,意识沦为本能的奴隶,那生命很可能会在死亡到来之前变成命运。苏童《黄雀记》中的保润可能是当代文坛中最欠缺“欠缺”的人物之一。“在《黄雀记》中,作为主体的作者和小说人物都无一例外地迷失了自我,整个小说由此陷入一种混乱、模糊、嘈杂和浮光掠影的叙述”。保润自始至终都处于迷失自我的生命状态。纵观整部小说,保润不是极具城府之人,做不出口是心非之事,相反他的行为被本能的情感支配着,如果他真想通过捅刀子的方式复仇,一出狱就应该行动;再次,保润身上的刻字“君子”与“报仇”并不能充分证明保润有着坚定的执行计划,因为这只是苏童惯用的象征、隐喻手法,又是宿命论和神秘主义在作祟。这样的叙述在苏童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不能证明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保润是因为衬裤的偶然刺激才捅了柳生,可怜的保润看不到“欠缺”微弱的灯光,再次迷失在命运的捉弄中。虽然说“欠缺”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人人生而有自为,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坐以待“为”,如果可以的话,存在主义哲学就变成宿命论的注脚了。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欠缺”?这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回复,有的只是多样化的获得,把握“欠缺”的力度不一,就是存在意义的精彩纷呈。
从文学现实的现实自然(包括形式自然、语境自然和人性自然)、现实宽度以及现实深度三个内在品性来看,鲁迅先生在当代文坛仍无出其右者。我们应该在这座丰碑上再出发,让文学现实的大河更为汹涌壮丽,目前最为紧迫的就是洞见政治世俗与资本世俗糅合、变异出的新鲜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