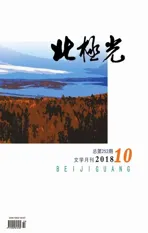疏影
2018-11-13刘爱武
⊙刘爱武
一
三月里来,杨柳儿抽条,铜钱草忘我地生长,青黄中零星出现的蓝色小花惊了伏龄,柳絮儿还没飞起来,面部似有无数小虫蛰过一般,辣辣的,红点由内而外地冒出来,春天蠢蠢欲动,伏龄对镜,竟生起气来。
贴片面膜,窝在沙发玩手机,也没什么好玩的,千篇一律地打开微信和QQ,叫个没完的是四五个工作群,那些行政坐班的,有事没事发些图片工作汇报,好像工作只是为了汇报,烦躁死这些,再看又是心灵鸡汤和人生感悟,伏龄基本不点,停留在此却不知自己究竟想看到什么。这跟伏龄的状态接轨,整天魂不守舍,一直没梦想又一直走在梦想的路上。
伏龄喜欢把家收拾得干净,衣物拾掇有序,阳光正好,晾出的衣服有股子清香,地板抹得比大桌子干净,然后傻子一样不穿鞋来回穿梭,一个人的家真叫自由。灶台上水开了,茶炊子吹哨般地叫,伏龄看着它叫偏不关火,偏不关火,它偏叫,这屋子一下有了情趣。
伏龄想起在云南喝普洱时,一浙江人说这也叫茶,旁人说当然叫茶还是名茶。她不屑地说,我家就种龙井,还有比龙井更好的茶?这就是爱与不爱的道理,你爱了它便是天下最好的,你不爱它名头再大也与己无关。龙井到底是天字辈的,只有配上红楼里的陈年雪水,只有配上雪小禅那样的清雅之娴,方可品之。这样一来对浙江人看不上普洱倒也能解释得通了。看王志文演的《天道》,主角落得个吃整箱方便面的境地,却仍然对茶与音乐十分讲究,现在似乎明白了几分。老北京,遛胡同串子的京片们,始终以提个鸟笼,长衫撩起茶馆喝茶为雅兴,这种雅兴和扬州人早起吃小汤包有些类似。
二
伏龄在茶的氲氤下,微眯着眼,人上了年岁喜欢假寐,半梦半醒,沐在阳光下,腿上摞本书,说在看书,思想飞得老远,有时挻佩服自己的,睡着了都在看书。美好时光里的伪装者。
三寸金莲的小脚姨奶奶是裴氏食府的正室夫人,膝下无子女,恶毒的婆婆用笤帚赶着吃食的母鸡,含沙射影地骂着:“给你吃有什么用啊,连只蛋都不会下”。小脚姨奶奶撩起衣襟试泪。
“伏龄小囡,你大大真鬼呢,他看上了你的嗯姆,扁担头上捎个麻布袋做样子,人家问,大喜子去瞧相好的,他回,去五里观收谷子去”,小脚姨奶奶看中了这个黑黑的大喜子,把娘家侄女说给了他。“日头下山的时候,大喜子扁担头上又捎个麻布袋回来了,人家问,大喜子没收到粮呢,他回,价钱没谈拢,隔几天再去。”姨奶奶说这些时,夕阳的余晖照在她安祥的脸上,小囡坐在矮凳上,双手托腮望着姨奶奶,似懂非懂的。姨奶奶手上抓着一把韭菜,竟是忘了择。“你大大一次复一次的去收粮,结果就把你个小不点收回来啰”,她用手指括了下伏龄的鼻子,哈哈笑着,颠个小脚奔披厦做韭菜煎饼。
三
伏龄工作台上各类报表等着归并,年假刚过,事多。
OA提示,一季度营销方案已出,各项指标任务让人不敢懈怠,伏龄电话联系了一些客户,报表归并完结后松了口气。窗外,许多的女孩手中捧着玫瑰,瞄了一眼桌上的台历,哦,2.14,她浅浅笑了笑。桌上的手机在台面上不停地打转,来信息了,是一条消费信息,伏龄一怔,自已的信用卡今天并没有消费啊,是不是信息有误,她查了下明细记录,才想起她用自已的主卡为平凡申请办过一张附属卡,一年多了,平凡一直没用过这张卡,今天他消费了五千多元是买什么了呢?她打了客服电话又查了下消费出处:金伯利钻石,一阵喜悦漫过,她少女般飞起了红霞,拨通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号码,旋际又关了。情人节,该不会是他要给我制造一点浪漫?她又浅浅地笑了笑。
下班了,平凡早她回家,做好了晚饭,二人还喝了点红酒。橘黄色灯光下,二人靠在一起看综艺节目,平凡说在超市买了汤圆,当宵夜吃。夜深了,平凡侧头睡去,伏龄对着这条信息发了呆。她的眼前,雪白的汤圆像死鱼的眼睛,令她作呕。“他制造的浪漫不为我”,那一夜就这么过了,她不问他也不说,也许平凡一直不知道,附属卡的消费信息主卡人知道。伏龄再清楚不过,平凡在外面为她这个做大老婆的也配了张附属卡。洗澡和喝茶是伏龄认为最美的享受。在烦恼和理不清思路的情形下洗澡,喜欢仰面迎着水流,闭目世界消失,大知闲闲,小知间间。
迟到的春天,别着悠长的阴雨期,像婰着七月的孕妇,眼不见底的姗姗来迟。有生命力的一草一木,会在沉睡中醒来。跟它们一样,伏龄在一呼一吸之间活着。
下得楼来,萌生一个人看风景的念头,刚步出小区门口,见一小男孩张大嘴要哭,他的妈妈离他两米开外,不回头,蹲下来,这孩子的表情变化太快,破泣为笑,趴上了妈妈的背。伏龄和这位妈妈相视一笑,孩子的目的性很强,达到了就不伪装,这点比成年人诚实,这位妈妈很是聪明,没等孩子伎俩实施就先行满足,她一定没有听过柏拉图的这句名言:“对一个小孩子最残酷的待遇,就是让他心想事成”。
湖堤岸边,那些残虐的芦苇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抢战先机的永远是紧贴土地的小草和闻风而动的杨柳。南湖边垂钓的人很多,微波不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皇家别墅,雍容华贵,临湖居上,是有钱人的温柔乡。一双男女依偎,面朝湖心,一群民工铺草坪,一身泥泞。生活就是这样,有人活情调,有人忙生计。
小径两旁绿化带,春风和煦,打碗花开得白灿灿的。这个本不是园林范畴内的,但它依然自顾自地开着,不平分春色,以独特的方式华芳一隅,你看与不看,都在。想起鱼玄机之于温庭筠,就如打碗花之于春天,卑微中矜持。
行至过街天桥,能片景的看这个城市,看得最清楚的依然是天天能看到的那个着白色塑料薄膜外衣的乞丐,他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没有,接着下一个垃圾桶。“在饥饿面前,人最先吃掉自尊”。李碧华的这句话蹦出来。我吓一跳。
四
小城不大,深究到多少平方公里,伏龄不知晓,她所熟悉的小城,是最繁华的商业街以及上下班回家的那段路。
旺季攻坚战,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天桥,桥上许多赏景的人,他们和她们很有闲趣地街拍,有多久没有驻足,好好地看看这座城了,站在桥上的那一间歇,注目这座城市,瞳孔里什么也没有,这城市那么空。
伏龄的眼里只有最后一辆回家的班车,车上坐着三三两两的人,风从车窗灌进来,她的心跟着车奔跑。
那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小街道,是伏龄的故乡,说故乡有点矫情,那就论着是出生地吧。
清明,祭祖,在爷爷墓前哭了良久,还能长睡家乡,爷爷很幸福。
聚月小楼午餐,问老板娘,儿时小伙伴的名字,她惊喜地问,你是伏龄?对,是伏龄,不停地说着谁谁谁,谁谁谁,临了,她不肯收饭钱,并送了一些土特产。
有些情感是指甲,剪了还会生长。
五
一场秋雨,银花家男人又卧床不起了,田地里稻草乱七八糟地躺着,遇了些雨,粘耷耷的。银花想把它们堆成个小伞形,湿淋淋的稻草怎么也立不起来,银花想起自已的男人,就和这稻草差不多,病秧秧的好多年。
“姨奶奶,给五分钱,买个草鞋底吃”,“小囡,到街东头去买,尼姑家的不要买”。“为什么呢,我和冬梅要好,我去她家买”。姨奶奶没有回答为什么,七八岁时她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冬梅和她差不多大,她和她一起上小学,她的妈妈从伏龄有记忆起一直戴一顶灰色的尼姑帽,她没有头发,常年脸色灰暗。大人们说她有麻风病,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到她们家玩。但银花婶待人非常和善,对自家有病的男人也照顾的很好,她家有当街的门面,婆婆帮衬着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她有俩闺女一小子,如果不是男人早早地死了,一家子也散不了。
死了男人的银花,更加地诚惶诚恐了,有时倚门发呆,有时坐门坎捡豆。下学了,几个混不吝淘气包,冷不丁掀了她的帽子,“麻风病,麻风病”,冬梅正好站在眼前,她的豆撒了一地。冬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她的话越来越少,上学放学也再不跟同学一起。下雨了,其它同学都有妈妈送伞,她就一直淋着雨走,小小的身躯倔强地前行着。冬梅有个叔叔在外地,一直想接济大哥一家,她奶奶也有带着孙子孙女投奔小儿子的意思,冬梅一直不肯。“我连给女儿一把伞的能力都没有,一直让女儿淋着雨上学放学吗”?银花婶去了一趟县里,回来后就打定主意要离家出走。
几天后,突突突的拖拉机开到了冬梅家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
冬梅妈围了一条大红的三角巾,拎了一个布袋出了门,突突突的拖拉机冒着烟开走了。门口一位老人抱着一个男娃在抹泪。
冬梅不知道妈妈去了哪儿,后来政府上来人说她的妈妈去了几千里开外的麻风村,那儿是政府办的麻风病救助站。
冬梅随奶奶和弟妹去了外地,那年冬梅二年级。
好多年过去了,没有银花婶的消息。街上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早点摊喝豆腐脑时向村官打听,后几经周转才知晓,银花婶在麻风村自给自足,种点小菜,过与世隔绝的生活,麻风村里另一个男人心疼她,俩人搭伙过日子,她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已的孩子。
斑驳的老墙体,疏影离离。像这个故事一样留在伏龄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六
大雪湮城,才有冬天的气势,那是一望无垠的肃穆,是飞飞扬扬的小确幸,寻常人家里堆个雪人,陪孩子打场雪战,都是冬天的恩赐。
红砖黑瓦高门楼,半人高的围墙内,扫出小块空地,在鸡罩下立根五六寸的木棍,放根长线栓住鸡罩,人走得远远的,几颗小脑瓜子凑一起,大气不敢出,紧紧抓着那根线。觅食的小麻雀来了,啄罩内的稻谷,待两三只进来迅猛地一拉,欢天喜地,这是从少年闰土那儿学来的游戏,乐此不疲地开心了好些年。
红泥小手炉,四块瓦棉鞋,炭炉上雪里葓闷狗肉,25瓦的电灯泡来来回回地晃,这一晃一晃的人就软了。父辈们爱执着酒杯咪口小酒,吃几粒花生米,也偶有拿筷子头蘸点酒让孩儿们舔,辣得伸舌时,他洪钟般的笑,醉在迷朦的有雪的冬天。
一窗白雪,数枝寒梅,心上雪似梨花,几起几落。“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重觅幽香,每经一场都会笑对,这样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