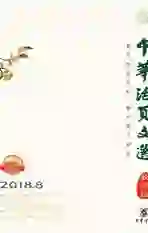宋学背景下苏轼的文化性格
2018-11-12宋颖
宋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称: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苏轼正处宋学产生的阶段。汉学重道德伦理而疏于哲学论证,元气论和天人感应论相对粗糙;又坚持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无法跟随时代发展和创新,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的佛道思想相抗衡,特别是难以应对富有精致的思辨哲学和超凡成佛的新型修养方法的佛学的挑战,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宋学应运而生。
宋学产生在疑经惑传的基础上。陆游论述宋代学风的转变时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引)此时,儒释道三家思想已经历了相当时间的相互激荡和影响,儒学在时代的要求下开始形成改造旧经学的新风,入佛道之室而操其戈,寻找形而上的根据。理学是宋学中对后世思想和教育影响最大的派别,此外还有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和当时其他讲义理的儒家经学各派。
苏轼的文化性格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他与其弟苏辙作《古史》,质疑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苏辙《古史·序》),一样富有质询和怀疑的精神,秉承儒学,“旁资老聃释迦文”(《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浸淫三家,创造性地融汇三家最有合理性和最富活力的核心精神,铸造出历史上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性格。尽管其学术的影响不如理学,但他通过其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创作,将其文化性格中的核心精神展现出来,对后世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价值追求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潜在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苏轼的人格精神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与理学核心精神完全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而这一潜在影响实际并不逊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在传统学术上有重大影响的理学。
一、苏轼文化性格的特质及原因
苏轼文化性格最引人注意的特质,就是精神上表现出的空漠感和行为上积极入世的尖锐矛盾。李泽厚在《苏轼的意义》一文中说,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关键所在”,并非“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而是其“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敏锐地指出了苏轼的特质。但李泽厚又用“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解释这一空漠感,并认为这不仅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这一说法只流于表面,并未看到要点。
苏轼的空漠感并非那么简单。厌倦、感伤、退避固然在每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苏轼空漠感的精神实质。只有深入这一空漠感的精神实质中去,才能真正看透苏轼的文化性格,并透过苏轼的文化性格看到宋学中哪些因素与传统精神核心更加相近、哪些与传统精神核心背离;也能更清楚地提炼出那些以潜在的方式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中国士人性格和心理塑造发生着重大影响的因素。
首先看苏轼空漠感的表层原因:佛老思想的影响。
在苏轼之前,虽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过人生空幻的感慨,但没有哪个人如同苏轼一样表现出如此前所未有的巨大空漠感:“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南歌子·带酒冲山雨》28岁),“聚散交游如梦寐,升沉闲事莫思量”(《浣溪沙·长记鸣琴子溅堂》38岁),“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45岁),“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南乡子·霜降水痕收》46岁),“笑劳生一梦”(《醉蓬莱·笑劳生一梦》47岁),“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56岁)……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的感慨虽然是晋代之后士人常见的意识,但苏轼相比前人,这一感慨的确尤其频繁与持久:“東坡词中的梦凡八十二处,表示一般意义上的睡梦不在分析之列”,单从词中就有这么多人生如梦的感慨,见于人生的各个阶段。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如梦意识在二十八岁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这显然不能说是个人经验,而是文化经验在士人心理结构中的累积,是文化心理。
人生如梦的思想最早来自于先秦道家。“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庄子·齐物论》)人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做梦,自以为是醒着,只有醒来才知道原本是在梦中。人生也是一样,愚昧的人毕生费心竭力追求着,殊不知全是一场空幻,只有死后才是真正的解脱。
这种如梦思想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是人生在本质意义上不具备现实性,是一场空幻;二是人并不具备自己所认为的认识真理的能力。当庄周梦见自己是蝴蝶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其周也”,当醒来后,“遽遽然周也”,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到底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庄子·齐物论》)怎样才能判断自己的知道不是不知道,不知道不是知道?从整个宇宙来反观人类本身,渺小“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庄子·秋水》),短暂似“白驹过隙”(《庄子·知北游》)之忽然,如此有限的人生怎能穷尽无限的宇宙?所有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相对的,而非终极真理。由此看来,没有终极可信的标准,也没有可信的判断。那么建立在人类认识基础上的一切文明,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失去了其坚实可信的基础。那些音乐、绘画、哲学理论,相对于大化流行的天道自然,不都是些多余的“骈拇枝指”“附赘悬疣”(《庄子·骈拇》)吗?人类文明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相对于儒家以文化证明人的价值的乐天主义,道家对文明和人类本身的反思不能说不深刻。自此,这种迹近价值虚无的观念和心理体验就深深植根于传统知识分子心中,多用作现实失意的抚慰剂:当功业不成时,便以在大化流行中人生只是瞬间一梦的想法来超脱具体得失。苏轼也以真诚的心理经验,承继了这一对人生和文明价值的反思的思维模式:“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个人的种种人生经历犹如一梦;“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历史上的英雄事业终究成空;甚至“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前赤壁赋》),连存在本身都是微渺苍茫、不足一道。
两汉佛教传入后,其思想通过和玄学“比附”的方式,与道家思想同类相附开始传播,“电光”“石火”之说就来自于佛教,与“白驹过隙”等相似的思想流传开来。从陶渊明到李白,诗中都不乏人生如梦的思想,到苏轼,二者已无比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行香子·述怀》)至“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道家空幻与释家无常的观念已水乳交融:人生就像飞鸿驻足在雪上留下的爪印,一旦鸿飞雪化,就了无痕迹,一切皆属偶然,并无意义。
苏轼少时读《庄子》,就认为深得己心,自称“某龆龀好道”(《与刘宜翁书》)。他早年任杭州通判时听海月大师惠辩宣讲佛理,也“百忧水解,形神俱泰”(《海月辩公真赞》)。虽然对佛教思想接受有一个过程,但最终还是深入其中,得其精要。佛老对人生和文明进行反省的自觉精神,在长期的文化心理累积之下,逐渐渗透于所有对具体人事的观照之中,普遍的无意义和无价值蔓延出来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空漠感。
但这一空漠感在苏轼独特的文化心理作用机制下,其心理走向和解决方式和佛老有着根本不同。
对于无价值意义的人生,老子主张“为道日损”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损除文物、典章、礼仪乃至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恢复到“为腹不为目”(《道德经》第十二章)的基本需求当中去;庄子则更主张“忘”,忘记主体意识,浑浑噩噩,同于草木,禽生兽死(《庄子·马蹄》),以“无乐之乐”为“至乐”(《庄子·至乐》),换言之,也就是从精神上取消人与客体相区别的意识,以达到与万物“齐一”,无所挂碍,则可“逍遥”。释迦则更主张“无我执”“无法执”,放弃对人本身主体性的执着,放弃对思想、价值和物的执着。总之,无论是释家还是道家,都在价值的虚无中走向了自我放弃。
苏轼对此明确反对:“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弗售也。……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议学校贡举状》)他还批评过禅宗“废学而徒思”,造成“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饱食而嬉”,无异于“为大以欺佛”。(《论修养帖寄子由》)
苏轼的价值建构方式,是在面对价值之空时毅然崛立,在反思和质疑中重新建立起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在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开篇第一句就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人生的悲剧真相,将人抛到虚空之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伟业、王侯将相都已湮灭成空,人生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直接提出了人的价值空虚。
面对根本意义上的价值空虚,人只有两条选择道路:一是干脆放弃自我的主体意识和生命,或向彼岸世界寻找救赎;二是价值的自我贞立,向空而有,依据人类最根本的生本能重新建构起新的价值,彰显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因为人想要生存延续,就必须明白:“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在没有意识到人生的虚无时所坚持的价值追求,有可能是盲目乐观、经不起考验的价值追求;而在面临彻底的虚空后去建立的价值,则是建立在对人类悲剧性存在彻悟的基础之上的、充满自觉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价值,是反思之后的、更有力的、更高层次的价值。由此,反思才显示出它的必要性和意义。
中国文化之所以存在这么久,就是因为放弃或向彼岸世界寻找救赎从来都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苏轼向空而有的新价值的建构方式,有其文化精神源头。在原始儒家处,人的价值完全源于内在价值的自我贞立,这一价值的自我贞立既不依赖于外在价值的评判系统,也和鬼神等彼岸世界完全无关。
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外在的名利、功业、寿夭都有“命”和“天”的客观因素,并非完全由人所能把握,当然也就不可能成為评判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根本标准;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鬼神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因为人的内在修养与价值的提升不是因为惧怕鬼神的监督和评判,而是为了自我成全,是“为己之学”,只需要假设祖宗的神灵在,以便通过祭祀的礼仪培养人该有的恭敬肃穆之心。所以子罕言“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甚至再进一步,无论成败,“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都不必埋怨外在环境和他人,只需要将之纳入内心,使其成为成全自我境界、提升自我修养、磨砺自我的资源即可。
总之,人之成为人的根据,不在外在的成败,也不在鬼神的评判,完全在于内在的价值的自我贞立,这一内在价值不依待任何外在因素。这一价值贞立的方式,正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苏轼承继了这一精神。此词开篇,江水虽然淘尽了当年的英雄伟业,但反思后,激起的是对历史合理性的更高层次的认同,英雄的风采和生活细节却使人重新感受到了一切存在的必要和意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在对英雄的还原之中,使人体会到了栩栩如生的鲜活的生命。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到底何在?就在这种人所共有的生命体验、鲜活的情感、永恒相似的追求之中,在于生命本身的存在之中。功业虽已成空,但对事功和责任的担负、对伦理情感的眷恋,却通过人类所共有的体验,凸显出永恒的意义。向空而有的这一过程,就是通过对具体的功业价值的否定的空,激发了人类最富有合理性的、最真实的总体意识。从否定到建构,从对具体的背离到对本质的贴近、对恒久合理性的追求,弥合了个体无法在终极意义上征服世界的悲剧意识。这一新的价值建构,完成了否定、追询、重新构建的心理历程。
原始儒家向空而有的价值贞立,立的是血缘伦理道德。而对文明反思的空漠感必然促使人对一切权威真理包括儒家所立的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反思。面对这一根本性的意义虚无,显然,任何受到历史性局限的简单、固有的理念,都势必显示出它的脆弱性,不足以成为强有力的支撑和依凭。例如道德这一概念,本身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当不符合一定时期主流具体道德准则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占据群体大多数时,就意味着具体道德准则需要根据时代变革了。任何外在的具体价值观念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不可能永远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成为一成不变的终极价值依据。如果把任何固定的理念或标准作为终极依据,那么随着历史阶段的推移,它就会极大地显示出它的有限性或反动性。
而反思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使人不得不彻底摆脱具体的观念束缚,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建构,保持这一价值建构的最大合理性。那么,重新判断和建构的依据,推之于极处,只能是人类总体意识。所谓的人类总体意识,是“指在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有利于人类总体的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历史合理性不受具体价值观念和个别历史阶段的价值评判系统的束缚,而是以人类总体的存在与发展为最终依据,导向人类价值观念上的自足”。
显然,人类总体意识是开放的、生动的,它超越具体的价值观念和历史阶段,要求人本于“诚”去体验、把握、建构价值;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僵化的标准,因此每次的价值建构都需要人进行完全独立的、无所凭依的思考和判断,经历怀疑、迷惘、质询、建构这一过程。
这也是苏轼空漠感的一个深层原因。当既有价值甚至人类存在本身都遭到质疑,当没有任何权威和现成的观念可以给予帮助,当必须独立于天地之间,进行痛苦的重新思考和认证、选择放弃或承担,追询以何种依据和理由去放弃或承担,随时用全部的生命去体验、辨别之时,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向着宇宙时空发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不断追问,和“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无所栖、缥缈清冷却又有所持、苦苦质询的孤影。这不是所谓的孤芳自赏,这是精神上的独立所面临的无所凭依。
二、传统文化核心精神与苏轼文化性格的生成
可以说,依据人类总体意识建构新价值,不但是苏轼文化心理中空漠感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关键所在。他在进行哲学思考和人生实践的时候,从不为任何具体的权威或僵化的观念所束缚,一直是用独立、批判的审视和真诚的生命体验去辨析和建构。“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中庸论》)苏轼本人这一说法,正是其能动地思考的佐证。也可以用于对他和理学根本区别的概括。
在这样的一种否定—寻找—肯定的心理过程之中,所建构的新价值必然保留以往价值的合理内容,同时有新的变化。苏轼本于“诚”而进行的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中,无疑他的核心价值仍然不离儒学的“道”,但这个“道”的具体内容和原始儒家、理学相同或不同的细微之处,则非常有考虑的意义。
宋学的根本任务,其实就是为儒学的道德或者说“善”寻找一个形而上的根据。在这个逻辑中,理学发展得最为极致。二程接受老子和《易传》的思想,认为“道”是哲学最高范畴,是“善”。“孟子言性之善,是言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秉受处不相远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到朱熹,建立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把“理”“性”“善”归为同一,此后,“理”上升为终极标准,并逐渐与“人欲”发展到“不容并立”的程度。它一方面把儒学发展成一个理论严密的系统,从而大大加深了它的影响力,在使之成为传统社会教育和思想的主流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又以一个先验的不可移易的“理”代替了人类总体意识,使富有主动性的弘道的人变成了被道所奴役的人,丧失了儒学中最人性化、最有活力的部分,在这一点上与孔子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
孔子圆融得多,孔子的道就是“仁”。但孔子从未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针对不同的人问“仁”,孔子给出了许多描述,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等等,对仁的含义进行过多方面的点拨。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到,这个“仁”是指从血缘亲情的自然感情出发,由情而理、推己及人地去爱他人,为了成全他人而部分地克制自己的私人欲望和要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个“仁”发端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自然情感,不是来源于某种外在观念的强加和逼迫。夫子罕言“性与天道”,并非没有理由。
在孔子这里,“仁”是道德,但是又时刻不离情感,它发于自然情感,归于自然情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道德的培养要从引发人的自然情感、吟咏性情的《诗》出发;然后用礼来约束引导各种情感,使内在的情有合理的外在表现方式;但礼是外在强加的,所以要用乐来熏陶,使得外在的礼在更高层次上内化为内心的情感需求。理始终蕴含着情,情理相融,难分彼此,敦厚自然。
孔子之所以不为“仁”做生硬的概念界定,是因为“为仁由己” (《论语·颜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活生生的人弘扬的是有利人类总体发展的“道”,而不是刻板僵硬的“道”主宰人。这个核心价值“仁”或者“道”在此时是开放的、生动的。孔子并未把它变成一个僵化不变的具体的价值概念,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以人类总体意识为根据、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的理念。
苏轼承继了原始儒家中这一开放的核心精神,坚持以“诚”的原则去认识哲学的根本命题—— “道”,认为“道”无善无恶,“善”不过是“道”的派生物。这就为事物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基础,留下了空间。他又在《扬雄论》中明确地将“才”排除在“性”之外,认为“善”是“性”之效,而非“性”所固有。“情”是“性”的自然表现,现实中的自然之情就是“性”的显现和生发(见《东坡易传》卷七)。这些观点,既符合原始儒家情理相融的出发点,又破除了先验的外在规定性。或者可以更清楚地说,破除了某种高高在上的外在价值评判准则或权威。
可见,苏轼的“道”的精神,与孔子在某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依据都不是某种形而上的或独立于人之外的某種观念和理念,而是基于最有利于人的群体延续的人类总体意识。除此之外,在反思、否定和质询中,针对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苏轼还对于如何重新解决“道”的内在情理关系,有了新的、非常有意义的创造。
极空必须生有,人必须在至大的虚空中确立自我的价值。确立价值,就不可能不沉入于生活中一切的具体现实;但在至大的价值虚无之中,执着于一切具体现实又显得那么无意义而可笑。
于是,苏轼创造性地把文艺审美的态度彻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但把生活中的一切当成审美的对象,把审美的体验当成生活的主要内容,更把担负社会责任的“道”的义务,转变成审美的心理体验和审美需要,这样,外在的义务变成内在的需求,担负的痛苦转化为生活本身的愉悦。生活中的凡尘俗事、功业上的成败得失,都变成了一场审美心理体验,结果如何不再重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苏轼成功地将生命倾情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以全副的热情和积极拥抱生活,不须离群索居、退避枯坐,“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在充沛的生命意识中,万物相即,天风鼓荡;又得以保全身心的纯粹,不为成败利钝而戕害本真,获得“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书》)的澄明境界,不会起坐戚戚、难以自已。
以往的儒家,虽然基本精神是价值的自证,但担负社会责任和义务依然是其最为重要的追求之一,“治心”和“修身”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尽管内在坚持可以不为得失所夺,但喜怒哀乐依然不免为得失所累:“始学也既累于仕,其仕也又累于进。得之则乐,失之则忧,是忧乐系于进矣。平旦而起,日与事交,合我则喜,怜我则怒,是喜怒系于事矣。耳悦五声,目悦五色,口悦五味,鼻悦芬臭,是爱欲系于物矣。”(《江子静字序》)苏轼在前人的文化资源基础上,成功地把审美的态度移植到实践和生活的态度之后,不但保留了儒家深入生活、积极进取的行动,而且将人无待于外的价值的自我贞立彻彻底底地付诸了实现。“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深入其中,而又超脱其外,“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宝绘堂记》),审美的意义彻底代替了功利的占有和追逐的意义。
这样,责任必然需要担负,这是拥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对结果则“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观棋》),这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执着而超越的态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有了审美沉入,所以这一担负不再显得那么沉重,这一超脱也不再那么艰难。苏轼之所以欣赏陶渊明的诗,也是因为陶渊明在空漠中并未走向空漠的流弊——精神胜利法、弃世或油滑,而是把意义寄托在当下的生活、感受和作为中。但陶渊明相比较于苏轼,还没有用审美来完成对功利生活的彻底转化,在现实的偃蹇中时有无法解决的不平和痛苦,没有苏轼这种圆融的审美人生境界。
这一审美的人生态度,并非凭空而来,也有其思想线索。孔子曾经向往的最高人生境界,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审美境界(《论语·先进》),而不是积极奔走、治理国家的功利人生。庄子的“心斋”“坐忘”“逍遥”,佛学的“空”“幻”等也为传统文艺提供了具有超越境界的审美范畴。儒道内在超越的方式,更根植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苏轼把内在超越的方式、文艺体验的方式和人生的境界相结合,创造出了非常富有文化特色的审美生活态度和践履方式。孔子所谓“六十而耳顺”,成败得失都能纳入内心,成为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资源,在这一审美人生态度下,从苦苦的自律修养而得,转化成了真正简易可行的自然功夫。
这一方式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极彰显传统文化特色的哲学:理性是建立在感性体验之上的体味与超越,理性经由审美积淀为心理本体,从而达到高度的统一和一致,理由情生,情由理出。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原始儒家倡扬的伦理道德的情理相兼、圆融无碍的传统自然地发挥到极致的,也就非审美而无他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向着宇宙进行“明月几时有”的价值追问之后,人的意义,最终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上来。这个伦理道德不是观念上的伦理道德,而是通过寻找的具体的、充满了生活意味的、鲜活生动的伦理道德,是审美心理化了的伦理道德。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审美的人生态度下,获得了一种本体的宁静。正因为寓意于物又不留意于物,才能做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可以说真正把握了儒家的“五十而知天命”的精神与老子顺其自然地“为”才是“无为”这两种精神根底处的相通,既坚持了儒家刚健有为的人生践履,又因为有了对无法超越的人生、天命的洞彻烛见,而可以待之以心无挂碍、自然而然的通脱潇洒。苏轼的文化人格,在精神上超脱,在行动中却没有走向混世遁世,而是更为执着,秉承了文化精神中刚健有为和超越自我的这些部分,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的精髓。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苏轼的空漠感乃是苏轼最重要的特质,这一空漠感来源于对生存真相彻底的洞彻,和独立思考的无所凭依。但苏轼的空漠感所激发的,是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是人对更高层次的价值的追求和确立,最终,苏轼通过审美实现了道德和情感的圆融,精神自由和现实自由的相通,从而从根本意义上确立了以全副热情融入生活,又以极大智慧超脱于具体功利和世俗观念束缚之外的生活方式。纵观苏轼的一生可知,他到过好多地方:四川眉山—开封—山东密州—苏杭—彭城—黄州—广东—海南……几乎走遍当时的中国,阅尽人世风云,历遍江河山川,早年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积极从政,处处留下实实在在的政绩,始终秉持着儒家“弘道”的坚持,完全不同于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消沉、感伤、退避”。当然,至大的空漠感流弊的确也能导致阿Q 精神、逃避责任、油滑退避,这就要视乎个体灵魂是否足够强大,能否将传统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核心精神承继、积淀、向空而有地创造了。
总之,苏轼之“道”,是在对文化和人的生存进行彻底反思、直面人生虚空的悲剧性存在之后,以人类总体性为原则,重新铸建的“道”。它承继了传统文化中最具开放性、最富有活力的核心精神,通过独立的思考将传统文化中最合理的内容彰显出来。而这一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无疑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强健生命力、最有价值的部分。
儒释道三家思想深度交融,这是宋学的特点。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三一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佛老。”宋代的统治阶级也提倡三教合一,宋真宗曾说:“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八十一)苏轼自己也说:“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庄子祠堂记》),认为他们“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他说,苏辙的《老子解》如果“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具体说来,在方式上,苏轼承继了传统文化中“人的自证”的这一最有价值的价值建构方式,在悲剧性存在中崛然而起,于明知不可处毅然相信、在无价值处追寻并创造价值;在精神上,苏轼将佛老的思辨、怀疑和反思的精神,与儒学中“人能弘道”、以人类总体为依据的活泼能动的精神相融合;在内容上,用佛老的审美原则协调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协调哲学思想中伦理道德的情理关系,形成了极其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人格。苏轼的文化性格,是儒释道三家最富有活力的文化精神的融會贯通,是宋学最具有意义的现实结果。
审美本体化是这一创造的核心。这一创造,在应当出情入理的观点上承继了原始儒家,但审美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内容,这一文艺心理在哲学和生活实践中的推广,使得审美心理本体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