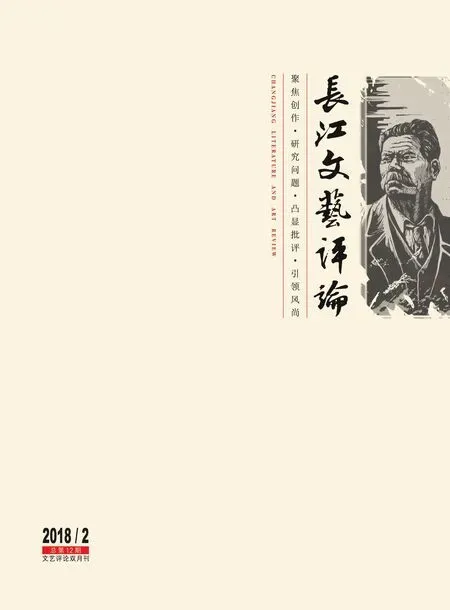从“黄飞鸿”到“冷锋”:中国当代影视英雄形象核心话语的嬗变
2018-11-12◎盖琪
◎盖 琪
一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关英雄的话题和故事总是经久不衰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而言,英雄的“在场”都是维护集体认同、确认核心价值的必要条件。虽然在历史的某些特殊阶段,“英雄已死”的慨叹可能会暂时风行,但是从共同体发展的长线趋势来看,人们对英雄的需要却始终是深层的,不可替代的。
英雄所承载的,首先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连贯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文化“源代码”。即对于我们这个共同体而言,什么是最应该受到尊敬乃至崇尚的,什么是最应该遭到鄙夷乃至痛恨的,什么是值得我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所有这些有关认同与价值的根本性问题,都可以从一个共同体最为推崇的英雄形象中,得到最直观的回答。
英雄所联结的,更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不同时代最为深切的期待与渴望。在时代语境的更迭中,一些类型的“英雄”可能会遭到疏远以至淡忘,而另一些类型的“英雄”则会受到传颂甚至膜拜,而其中起作用的,正是英雄身形样貌下所潜藏的深层文化逻辑;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英雄形象所指代的“核心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会建构出不同的英雄,这一点在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艺样式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无论是在古典时期的史诗、戏剧、戏曲、绘画和雕塑中,还是在现当代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英雄形象的核心话语一直是在随着时代语境的更迭而进行嬗变的。就中国影视艺术场域而言,最近二十年来,最为广大受众青睐的典型英雄形象及其所联结的核心话语,也一直在发生着有意味的变化——而其中所蕴含的,正是当代中国人对理想自我、对自身与世界关系、以及对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多重想象。
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的转型作用于大众传媒场域,突出体现为受众审美期待与文化旨趣的相应位移,以及由此发生的媒介审美文化形象的深入变格。其中,就能够引发全民接受热潮的影视英雄形象来看,其核心话语:
(一)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就是以“武林高手”面貌示人的黄飞鸿,而其所蕴涵的核心话语则是一套兼具民族主义情感热忱与民族文化反思视角的复合符码——这也是非常符合彼时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化心态的。这样一种充满两难意味的编码任务之所以落在“黄飞鸿”肩上,主要是因为其媒介形象历史谱系格外丰富,所以显得别具优势:纵观中国当代影视文化史,黄飞鸿是被反复书写次数最多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而即使是在世界影视文化舞台上,黄飞鸿形象谱系所跨越的时间、涉及作品的数量,以及不同时期形象之间千变万化的程度,也都远远超过了英国的詹姆斯·邦德、法国的佐罗,或者日本的寅次郎等。
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地区引发接受热潮的,是由香港导演徐克所推出的系列武侠电影中的黄飞鸿。虽然早在徐克的首部黄飞鸿电影《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上映之前,中国的黄飞鸿电影就已经高达104部之多,但有所不同的是,徐克之前的黄飞鸿多是作为典型的传统英雄出现的,“他是社会仁义道德的保护者,正义凛然又带有封建色彩,属于‘古典主义’英雄,很符合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的社会心态。”但到了徐克这里,黄飞鸿则在更大程度上被塑造成了一个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一方面,他仍旧秉持儒家的仁义观念,对于江山社稷抱持深切的责任感;但另一方,与十三姨之间的爱情却又使他与东方的伦理纲常发生了某种无法化解的龃龉,并与西方现代文明具有了某种暧昧复杂的关系,而这也正是徐克的黄飞鸿电影中所潜藏的文化反思意味的根源。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深层文化意味的处理上,其后风行的叶问形象表面看似与黄飞鸿形象一脉相承,但实际上却要简薄许多。
(二)第二个阶段是2005到2010年左右,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是以“江湖做派”为特质的李云龙,其所蕴涵的核心话语则带有鲜明的民粹倾向,可以说是一套充满江湖智慧与市井活力的符码系统。而从传媒艺术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2005年前后几年正是中国电视剧的鼎盛时代,所以彼时最受欢迎的“大众英雄”也多是出自电视剧场域。其中,《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大宅门》中的白景琦、《铁梨花》中的赵元庚、《狼毒花》中的常发等一系列“江湖英雄”形象,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场域的主要审美文化旨趣。应该说,这些英雄形象的风行与彼时市场经济环境上升期,人们对崛起的财富阶层的整体印象与复杂心态是息息相关的。
以李云龙为例,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的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为一种对江湖道义和江湖智慧的推崇。从形象话语所连接的深层价值来看,一方面,这类“江湖英雄”往往着力奉行并维护一套通行于底层游民社会的伦理规则,表现出仗义疏财、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等“人格楷模”特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源自游民阶层的消极文化观念,包括好勇斗狠、轻视生命的暴力倾向,肆意妄为、无视法治的破坏倾向,蔑视知识、蔑视教养的反智倾向,只问敌我、不问是非的帮派倾向等等。而这些消极文化观念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所强调的民主、文明、公正、和谐、法治等关键概念都有着潜在的消解作用。因此,对于这类“江湖英雄”,最值得回望与提炼的,即是如何在尊重相关民间审美惯性的同时,对于其中的负面因素加以化解与引导的问题。
(三)第三个阶段是2010到2015年左右,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是以“现代精英”格调取胜的余则成乃至梅长苏,而其所蕴涵的核心话语则转向知识性的、崇尚格调的、善于权谋的符码系统,因而与上一个阶段形成了格外有趣的反差。总的来看,反差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糙汉子”的审美疲劳之外,这一阶段也正值“谍战剧”与“宫斗剧”最受追捧的时期,而在这两种商业类型中,主人公自然都是以权谋心计见长的人物,而这也恰好在深层文化心理上迎合了社会转型瓶颈期日益弥漫的职业压力与路径困惑。
除了《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琅琊榜》中的梅长苏之外,《黎明之前》中的刘新杰、《悬崖》中的周乙也都是这类“精英英雄”谱系中的翘楚。而后来风靡荧屏的“大女主剧”——《甄嬛传》中的甄嬛和《芈月传》中的芈月,以至于今年《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周莹,则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上的女性变体。但不论性别还是年代,这类英雄究其实质都带有明显的中产阶层文化想象:在生活细节上讲求品位,在事业领域中充满智慧,在价值观念上具有自由左派意味,在关键时刻可以有所腹黑,但在人生大势上又能清醒把握原则——这正是日益庞大的中国中产阶层面对当代纷繁局势对理想自我的期许与描绘。显然,这一阶段的英雄及其核心话语是更富于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因而其流行能量至今仍然堪称巨大,也仍然有可能生长出新的变体。
(四)第四个阶段则从2017年开始初露端倪,而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就是被称作“新时代硬汉”的冷锋,其所蕴涵的核心话语则可以用“青春热血+强国想象”八个字来概括。换句话说,《战狼2》中的冷锋是一位脱胎于互联网时代独特文化生态的“新大众英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在冷锋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浓烈的“互联网青春民族主义”的特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相比,它的符号和文本都更为年轻化、趣味化,更有网络亚文化色彩,少见悲怆情怀与反思诉求,多数情况下洋溢着一种自信的狂欢情绪。由此甚至不妨说,冷锋就是一只由真人扮演的“那兔”。而另一方面,冷锋形象又吸纳了“大国崛起”论述框架下逐渐盛行于民间的国族身份界定方式。不同于曾经的“受害者想象”,这种新的界定是以“领导者想象”作为主轴的,展现出崇尚经济与科技等物质文明优势的倨傲色彩。
冷锋形象及其核心话语的当下意义在于,通过上述两方面的融合,“很好地解决了军事题材电影中个人服从于国家、组织的叙述难题,冷锋的行为既是个人主义的,又具有国家身份。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走向新的认同,意味着一种新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所改造的利益共同体。”但与此同时,其带来的尴尬性也不容规避: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跳出旧有的“强者/弱者”、“拯救者/被拯救者”、“先进/落后”、“现代/前现代”的二元对立表述模式,没有新的价值创造,只不过将自身由劣势一极放到了优势一极而已。
综上,我们看到,从“黄飞鸿”到“冷锋”,从弱国反思到强国想象,中国当代影视英雄形象的核心话语在二十年间经历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嬗变过程。既然当下,以“冷锋”为标志,我们的“大众英雄”已经开始尝试以更具主体性的姿态,亮相于更为纷纭的后全球化媒介舞台,那么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承担起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化身份、表达当代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职责,就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创作者和研究者自觉探究的课题。
注释:
[1]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2]张慧瑜:《〈战狼 2〉“奇迹”的背后:大众文化工业系统与主流价值观的契合》,百家号“媒介之变”https://baijia.baidu.com/s?id=1579321138350733834&wfr=pc,2017年9月23日。上网日期,2017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