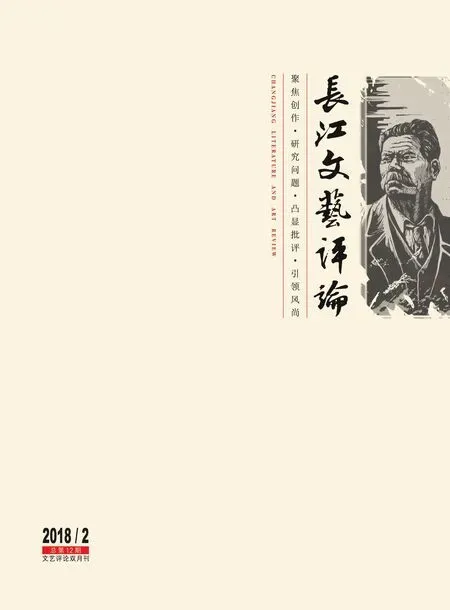金粉泡沫中的谅解、契合与求真
——论夜鱼的诗
2018-11-12◎盛艳
◎盛 艳
一、谅解的力度——从灰色到透明
夜鱼的诗是有烟火气的。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位诗人。她的诗性不是与生活抗衡得来的,而是同生活交谈与理解得来的。在此无需使用妥协这个词语,妥协而引发的哀怨、无奈或者是水仙花般的情愫,在夜鱼的诗中你是要扑个空的。
夜鱼的诗呈现了一个个或动或静的生活场景,她擅长将生活的灰色铺陈开来,用温柔的笔将它调和,最终使之成为一抹着色的透明,浓淡相宜。在水墨画中,你明明知道那是山,却又望得不真切,得到了意,形式就不那么重要了,夜鱼的诗同理。
《苦夏》写的是送女儿,然后打车而返的经历。在诗中,有着“培优学校”“导航”“学费”“二手出租车”“争产的官司”这些标志着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词语。两个原本陌路的女人偶遇于同一时空,相互审视彼此的生活状态,短暂交汇,随后各奔西东。诗的焦点是“一小会儿意犹未尽的停驻”,“停驻”既是女司机自我审视的瞬间,也有折射出我对于彼此不同境遇的思考。“让我尴尬的”是“我忍不住问她家里是否有人帮衬/她摇头一笑:婆婆为房产要和她打官司”。正是对于“他者的不可说的生活”的触痛,使得我“走出很远才敢回头”。这短暂的停驻提醒着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囚徒。
正如在《我想搬到楼间距大一些的房子去住》一诗中,诗人带着一丝揶揄的口吻,用“玫瑰战争”比喻夫妻之间的冲突:
去年夏天
我从敞开的窗户
见过他们搂抱亲吻
女人纤细天真
丝毫看不出
肺活量惊人
我不能确定
他们的玫瑰战争
还要持续多久
写作的视角同样也是由他者的生活回转到“我”的生活,最终进入了交叠的灰色领域:“我的持久战/安静之极”。每个人都在承受生命之痛,而在夜鱼的诗中可见的只有淡淡一抹灰色,但这灰色并不让人绝望,在夜鱼看来,这也许就是生命本来的面目。
从旁的,引到自身,最终归于虚无,这在夜鱼的诗中是常见的。诗人未奋起抗争,却也并不妥协,灰色地带在诗的语言下变得逐渐透明,触手可及,让人有可能去更换视角,审度不同的生活,最终使得“他者的不可说”成为诗中对城市生活描述的常态。
在《湄南河》中,诗人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一条河流,镜头是动态的,仿佛一帧蒙太奇。顺着湄南河缓缓而下的是金闪闪的佛塔寺庙,华夏高楼,破烂棚子,而“看起来并无不适”,彼处与此处,相处得安然。这一切似乎源于“河水丰盈得像另一种宗教/黏合安抚着一切所托之物”。异域的诗因为独特的景物、风情甚至是声音,大多是吸引人的。而《湄南河》最让人动心之处却是这条河流的共生和包容。不同的生态、人群、不同的面目都在这曲水中得以记忆,这一瞬间,“被万千游客养肥了的腻水/在东南亚阳光强烈的摩挲下”被定格成影像。这一影像不是刻板的,它在波涛中涌动,周遭亦是波涛般的诵经梵音。此时你不能知道究竟让你眩晕的是湄南河之水,还是湄南河上的吟咏之声。整首诗亦真亦幻,却又在现世金粉的泡沫中撕开了一角,让人窥见一丝生活的真实面目。湄南河承载众生,是无悲无喜的大地之母的形象,不同的是,河水的流动与移步换景使得这种隐喻不真而幻灭,诗歌结尾处的悖论感在诵经般的吟咏中不断地被放大,诗的指向归于虚无:“内心全是金粉般的泡沫”。
夜鱼对此处与彼处的世情的掌握是游刃有余的。诗人试图深入到个体境况的深处,去探个究竟。然而彼处与此处终究是不同的,虚幻的和不可说的那部分成了夜鱼诗中飘忽不定的一抹咏叹。夜鱼在表达充沛感情的同时,试图在节制这种情感的力度,一方面这种节制使得“他者的不可说”透明而不黯淡;另一方面,这种节制在审美与情感上所具备的力量使得语言完成从日常到诗歌语言的转化。
二、契合的智慧
对某一场景的把握,并通过精准的语言将其具体化的能力,展现了诗人对语言的控制力。《开桥时分》选择的是零点十分,诗人选择“桥断然洞开/滞留了一整天的巨形货轮”作为世态万情的载体。视角是从透过圆顶教堂的彩玻向外看,借助教堂的高度,诗人呈现了万能的上帝视角:男人们是醉醺醺的,仿佛“烤熟的醉虾”,“岛屿上女人们的窗子则由红变蓝”,色彩的转换映衬出从过桥前等待的焦灼到过桥后的宁静的心态的变化。《开桥时分》的动作意味强烈,用巨型货轮瞬间的移动,隐喻了现实生活的蓄势待发,以及其后的宁静:
飘出的轻鼾
如一串银色的小鱼
正赶往固定的区域繁殖产卵
在这几行诗中,声音与意象在真实与虚幻中衔接,转换,形成意象的变形与幻化,“一串银色的小鱼”将鼾声的轻与梦境的延绵衔接得恰到好处。通感孕育着巨大张力,“赶往固定区域”不仅仅是“一串银色的小鱼”,又恰好映照了巨轮本身。诗歌首段提到的“圣彼得堡每到深夜都有一次/新鲜的分裂”,“分裂”和“繁殖产卵”构成了巨大的生殖隐喻。圣彼得桥的分裂,涅瓦河一阵悸动,滞留了一整天的巨型货轮都出发赶往固定的区域,男人和女人的影像的浮动,这一切亦真亦幻,似乎是在说真实的巨轮起航,又仿佛是把人类繁衍的巨大冲动呈现于深夜的断桥开启与河流悸动之中。诗中的符号反映了诗人潜意识中的创作主题——“孕育”,而孕育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契合之力,这亦可被视为夜鱼创作的母题之一。从《湄南河》到《开桥时分》,都可以看到诗人对于水有着融会贯通的理解,代表着阴柔之水的河流也成为母性的最好载体。
如果诗能呈现某种中性的状态,当然是好的,创作中的“安能辨我是雌雄”使诗人能跳脱出既定的性别局限来观察世界,但这并非说不倡导女诗人从女性视角出发。恰恰相反,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和生活经验正是她们写作的优势。夜鱼似乎对于自己的性别有着得天独厚的理解与接受,在诗中,洋溢着女性气息的描画将读者带入一重又一重属于女性独有的精神世界,譬如《猎杀》中的“游牧民族的忧伤/均匀涂抹下去”,你都以为就要这样忧伤下去了,但是忧伤“很薄,薄得像一层米皮”。这忧伤也是不能够的,它最终被平庸的日常解构:“高压锅里的鸡,电饭煲里的饭”,诗中没有危险与猎杀,但日常生活就像一把刀子“慢慢地猎杀我们自己”。生活是猎杀之刀,也是天荒地老的刀子。夜鱼的诗呈现了女性的真实生活,可以看到现代生活对于女性精力的蚕食。在诗中,可以看到诗人虽知晓生活的平庸,仍淡然处之的通达;虽无激烈的挣扎,却有着与生活和解的智慧。
男人则多以“醉汉”的形象出现在诗中,譬如《西街之夜》中,“我看见渐老的时间/爬上了你醉意醺醺的脸”;《胭脂路》中“路中段教堂的十字架下/脱光了衣服的醉汉/惊得灰雀呼啦啦从尖顶掠过”。醉汉的出现又常伴随着十字架,罪与救赎的同时出现,表明了对于男性不绝望也不偏激的态度。清晰可见的男性的面目在夜鱼的诗中不多见,《购镯记》中有一位卖玉镯的小伙子,这是位多与女性打交道,也偏向于女性化的男性角色:“脸越发白皙/且透着急切的红晕”。小伙子急切地向女顾客推销着玉镯:
这裂纹不要紧
不会断,不信你掰……
裂纹并不影响玉镯的坚固,但在诗人的笔下“和田玉镯虽碧如春水,但瑕疵明显/一道裂纹,使身价低廉如无望的人生”。玉镯疤痕的外化正是“我”伤痕内化的映射:“嗯,好吧,不致命。我戴在腕上/忽然发现玉上瑕疵与我手上的疤痕/非常合契”。“我”对疤痕态度的转变似乎没有经过激烈的内部思想的挣扎,对于玉镯的瑕疵“我”虽然觉得不妥,却有着接受与包容的态度。这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诗人对于“瑕疵”生活或者“伤痕”自身的态度,即契合。平静河流下的暗涌人生莫不如此状。
除了在《蝴蝶斑》中一次对男性语义模糊的描摹,男性在夜鱼的诗中大多语焉不详、面目模糊。《蝴蝶斑》中,诗人将“青蛙”和男性的意象叠加,模糊而陌生,怪异得让人有丝不舒服。从幼年时“你握一把无色无瑕的小刀/对一张被你完整剔下的青蛙皮,沾沾自喜”,到“我曾扯脱过一个男人的袖子/那只裸露的胳膊,像极了剥皮青蛙”,最终到“但我预言了你的青蛙/他将挣脱你的手指,跳到野地上蜕皮”。夜鱼在此处用坚定的笔触将男性的世界一分为二,“青蛙”与“蜕皮”将男性的生理层面刻画得丝丝入扣,而诗的结尾写到:
在扑扇扑扇的阴影下
那上蹿下跳的青蛙,显得多么滑稽
我们懒得描述,不仅是因为
我们都有疲倦得稀薄的嘴
在夜鱼的诗中,这是唯一略有疲态的收梢。大多数情形下,夜鱼的诗是一杯妥帖的睡前红酒,是一味生活柔化剂。《过汉口六渡桥施工现场》则以施工现场这一特定场景,通过视角的转换与上升来实现现实和虚幻的融合,雕琢了瞬时的一刻。诗歌开头处写到:
说拆除就拆除
温柔通达了三十年的六渡桥
不再渡我
这是女性的娇嗔——对于六渡桥的拆除虽然不喜,却也并无多大的埋怨,知道说出来也于改变现状无补。“施工现场”这一场景的选择使得对往昔的追忆、今与昔的对比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找寻味道的瞬间衔接了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过渡句隐藏在诗的中央,似乎是隽语,却又点醒了诗的真正主题:
我想要找的
和吃有点关系,又似乎全无关系
通过对六渡桥花岗岩桥面的回忆,诗人将视角升高,高一点的视角更接近全能视角,可以综述宏观场景或对某段经历进行综观。从铜人像到“人像的脚底下/熙熙攘攘的广场南侧/民生、民权、民族三街汇集处”,再到“生意不好也不坏的冷饮店”,“我”站在钢筋水泥的工地,穿行过记忆中熙攘的人群与街角,最终抵达记忆的落脚点——给我“点红豆沙冰,靠窗坐等的人”。诗人通过陌生化的延宕的叙述方式将现实一幕一幕地柔化。
可以看到,夜鱼的诗具有温柔的特性,对于狰狞的苦难不是退缩与排斥,而是选择坦然相对,其中有种与宗教共通的特质与美感。基督教与佛教都是直面苦难的,譬如在基督教中有“原罪”说,佛教中又有人生八苦。基督教对于苦难是接受的态度,耶稣本人就是苦难的标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对于苦难显得异常平静,以血为救赎,后又复活,展现了承受心灵的苦难,最终超越苦难的历程。佛教对于苦难的态度则更积极,直面苦难,不作回避状。夜鱼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契合”,就是对于苦难的一种接受与包容,近似于宗教中的安然与平静。
三、在馥郁中抵达本真
《归》是一首有梦的特质的诗。《归》中的院落不似在真实世界,更像是在梦境中隐约出现的。那么幻化是如何得以实现的?真实的场景是如何携带记忆最终进入意识的深处,以断片式的絮语被呈现出来?这正是《归》要展示给我们的。
“对一座呈现事物本性的院落/我的闯入显得突兀”揭示了《归》的主旨。诗人用细致的笔墨来展现如何“呈现事物本性”。从“屋顶覆着/几个世纪厚的茅草和葵叶”“蓝花瓷碗”“疼痛的牙”“木桌”“纺线”最终落脚于“我失去的那部分重量”,可以看到成年人对童年追忆和入梦的感受是相似的,事物在这二者中都是模糊、柔软的。弗洛伊德认为梦是对潜意识的凝缩与伪润,带有很大的思考性和目的性。《归》似乎长出藤蔓,延绵细腻,枝丫缠绕,从现实到记忆,从错觉到梦境,细节的刻绘和情绪的转合丝丝入扣,而诗的落脚稳定、安然。
从诗歌的第二节,以“木桌”为中心的写作,呈现了完美的“语晕”结构。刘洁岷在《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中指出语晕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在变化中获得的,由多个词晕排列组合的语晕就构成了诗歌。词晕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是单个概念的符号。每个词都是有“晕”的,即“词晕”,它是对于词语意义的一种隐喻性的理解。
《归》这首诗体现了夜鱼敏锐而独特的词语选择能力。纺线与纺车这些常常进入古代诗歌的词语,在现代诗中却是凤毛麟角的。纺车的嘎嘎声,母亲和姐姐坐在树下纺织时的絮语,落下的槐花,所有词语交织在一起,在模糊与朦胧中开启了记忆之门。在诗歌创作中,对特定词语的选择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这些词语的具体感受和态度,同时释放了在语晕推进中诗歌语言的巨大潜能。《归》这首诗的语言中心是院落中家人围坐晚餐的一张木桌。晚餐并非是讨论的关键,但是“院落”“晚餐”“香樟树”“槐花”“落叶的簌簌”和“狗的轻鼾”这些词语的勾连,就已经丰满地呈现出了院落的生活的温暖恬静。
说起围坐晚餐,我不能不提到院落里的木桌
经常落满细碎的花瓣、树叶甚至鸟屎
我的童年匍匐其上,咬着笔杆走神
作业本因此添加有笔墨之外的复杂成分
冲淡了红色叉叉带来的刺鼻气味
从木桌,过渡到木桌上的落物,包括“细碎的花瓣,树叶甚至鸟屎”和作业本上红色笔墨的味道。从“作业本”到“注意力”的转换合乎逻辑,却又有着较大的跨度,将诗向虚幻处不断拓展——注意力“被她们手中缠绕的纺线分散”,纺线的绒絮到她们的絮语,到槐花,最后到“香樟、牵牛花和桂花树,簇拥着院落/交织出的奇异香气”整个过程宛如意识流般流畅,全方位地调动了读者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与嗅觉。诗歌的高潮最后落脚于情不自禁的发问:“我有些晕眩,这到底/是回归还是从未离开?”梦的形象性、象征性、模糊性都在《归》中得以实现。“呈现事物本性的院落”究竟是什么?事物的本性又是什么呢?无需多言,诗中所呈现的画卷已经给出了解释:
旧光线一圈圈如纺轮般懒洋洋地晕开
我失去的那部分重量,正稳稳地贴挂在
粗壮的树干上
可以看到,《归》是一首谈及重振元气,获得力量的诗。成年人从白日梦般的童年汲取温暖,这就是家的本性:柔和、绵软,是记忆中“童年匍匐”之所在,唤回了“我失去的那部分重量”。
夜鱼的诗节奏柔缓,不激烈,不刺激,虽然是对熙攘世界的描绘,却让人暂时摆脱了紧张与喧闹,进入了安静而模糊的世界,内心得到缓和、安慰与放松。正如诗人在《迷路》中写的“自从我写诗,就越写越安详/允许自己迷路、走神、虚掷、游离/譬如他们在正确的方向争分夺秒的时候/我正和某段路基下的麦子和鱼,重叠着魂魄和颤栗”。
《归》的长处在于基于事物本质的纵向之探索,词晕的不断叠加,抵达记忆深处的童年,最终捕获了“事物的本性”。探寻事物的本质,并用诗的意义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呈现诗歌本真的过程。与此类似的探索还出现在《西湖吟》中。夜鱼突破了状物时的征引和感物,直接劈入事物的本质,“要写这片湖太难了”,因为湖水“被赋予了太多虚拟意义”。诗人要做的是剔除外部的,发现内在,是为了湖水本身而去写湖水。在写的过程中用一把剃刀将与本真无关的一一剔除,正如奥卡姆定律中所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湖边的木质长椅在我起身离去后
很快,坐上了一对恋人
临别一瞥,水
还是我来时的那个样子
在这首诗中,夜鱼没有通过陌生化的隐喻去吟咏或描绘,而是做着诗的减法,把一层层西湖被人工赋予的面具摘下,试图剥除司空见惯的意义,还原湖水的本真。在诗歌创作理念上,这是首超前的、具有实验性的诗。如果说《西湖吟》做着减法,诗人在《馥郁》一诗中则做着加法,通过调动灵敏的感官和纷繁的记忆来描述追求本真之路。这首诗的表象是描述辨认植物的味道,本质却是揭示认识事物本真的历程。
《馥郁》中的“晾晒冬装”这一短语本身就具备“收藏”与“冥想”的意味。秋桂盛开的树下,“空气越发醇厚”,在松散的,模糊的语言指引下,诗聚焦于“那个分发桂花糖的下午/在最小的手掌放入最大的一块”,谈及了老人对于孩子“那些带点偏袒的呵护,其实是/堆叠在皱纹里的稀有金属”,难能可贵的是孩子们对于物质的易满足感“说起桂花糖、桂花糕/想起我们曾经一勺便足矣,杯子也适中”。成熟则是在“甜味越来越淡,香味若有若无”的成年经历中“学会了辨别/所有生长的气味/便无所谓杯子的大小,我们被馥郁包裹/尝出清水里的甜,内心柔软得可以/容下任何一粒种子的萌动”。植物的宁静一如既往,秋日的馥郁桂花香味中的冬衣晾晒,使得人们在冥想中学会了认识事物的本真。由此可见,夜鱼创作的潜在动力在于对事物本真的探寻。诗中所呈现的对于生活的理解与契合,交流与对话,对于他者不可说的灰色地带的描摹,都来自于对于其本真的追寻与了然。夜鱼的诗柔和,熨帖,有着植物天然的纯粹与馥郁,正如她在诗中写到:
好在植物的宁静一如既往
它静静地凋零、发芽、抽枝,开花、结果
这一系列过程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