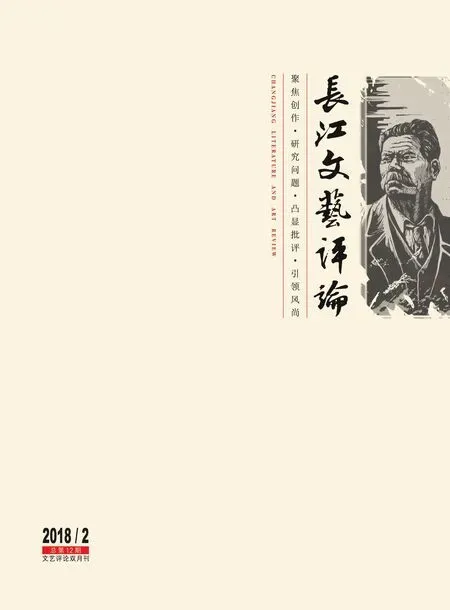文学的认知不止于文坛
——秦岭访谈录
2018-11-12◎王彬秦岭
长江文艺评论 2018年2期
◎王 彬 秦 岭
王彬(以下简称王):
作为考察当代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载体,《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在学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地位,其权威性和参考价值被广泛认可。该丛书纳入对你作品的集中研究,我认为是有眼光和远见的。秦岭(以下简称秦):
客观讲,走过盲目和率真之后,创作上反而不那么自信了,有愧学界和读者的期待。我始终把学界对我创作的观察和研究视作鞭策和鼓励。我的作品并不多,累计也就出版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也就几十篇。尽管骨子里也笃信“一本书主义”和“文贵精不在多”的箴言,岂敢拎来当作自勉自慰的挡箭牌。好心的编选者给了我一大堆儿编选的理由,让我以文学的名义给予积极配合。我想,那就权当学界给了我一次全面审视自己的机会吧,假如它是一面镜子,我愿意用它来照自己。王:
你的作品给学界提供了研究你的所有理由,这就像我们组织的“中国文学论坛”,其中有多届邀请你担当嘉宾一样,全国有成绩、有经验、有想法的作家很多,我们之所以选择你,一是你的作品既与众不同又符合文学精神的呈现,二是你的一些想法非常适合论坛讨论和交流,这两点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同时具备的。你的加盟,让论坛少了一些积习和匠气,多了一些本真和元气。我想,《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和我们论坛对你的选择殊途同归,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秦:
这次由您来主编关于我的研究资料,似是巧合,也似是注定。您主持的“中国文学论坛”对我的厚爱和选择,是我创作生活中的一件幸事。我借助这个论坛反思我的创作,发出我的声音,同时感受到了与体制内、学院派完全不同的思想交锋和观念争鸣。这使我在借鉴中外文学创作经验方面,在寻求自我突围和坚守方面,在传统和时尚的判断方面,仿佛豁开了另一种渠道,有了存储和释放的感觉。很多朋友认为我这五六年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我都羞于面对五六年前的过去。要说改变,论坛的作用力不容小觑。我这些年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也多是论坛中的发言,与其说是给同行和读者,毋宁说是留给自己。王:
我曾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教学管理、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有机会接触过很多全国一线的青年作家。应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成绩斐然,都有各自的创作追求和文学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但创作方法同质化的情况在一些范围内也是存在的,这也是文坛的共识。你曾是鲁院高研班中的一员,也曾作为优秀学员代表参加过鲁院近些年的一系列活动。身处其中,你如何理解自己的创作路子?秦:
在我看来,作家与作家的区别,完全在于个体特征的凸显。我不好说自己是否有这种明显的特征,但我抱定一条。绝对不能拾人牙慧,不能重蹈覆辙,不能瞻前顾后,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随行就市。即便是在十字路口,也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当然,这样的判断绝对要避免盲目、盲从和盲动。话说回来,我十年前做得并不好,因为“悟道”的局限,也曾随波逐流。王:
你的几个系列的确构成了当下文坛独特的、无法复制的特殊风景。比如你的“皇粮系列”“乡村教师系列”“地震系列”“水系列”等等,这些系列小说仿佛异峰凸起,成为我们频频回首的景观。小说里既有反思又有批评,既有悲悯情怀又有觉醒意味,多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和社会、自然、土地、权力、情感层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能巧妙地把政治、经济、文化元素融合进叙事的经纬之中。有些题材别人也曾表达过,而在你的作品里,总有新的思考和向度。秦:
我并没有刻意让创作服从系列的路径,这个系列的客观存在,应是自然形成的,比如以水为背景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完成后,突然发现水这个东西与人类的关系真是太神奇了,生态背景下的水,可谓命运多舛,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脾性有着与生俱来的相似性,包括中国农民的命运,于是难以遏制地有了《吼水》《借命时代的家乡》等。至于如何认识自己的创作,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断不会孤芳自赏,但也不是心中无数。有意思的是,我的自我判断有时也与编选者、文学专家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比如在我的“地震系列”里,我自己比较满意《阴阳界》《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在“教师系列”里,我比较满意《杀威棒》《不娶你娶谁》,在“战争系列”里,我比较满意《幻想症》,在“计划生育系列”里,我比较满意《一路同行》,但学界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偏重于《皇粮钟》《心震》《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绣花鞋垫》《透明的废墟》《寻找》等小说。也就是说,有时候,个人满意度与读者比较接近的小说,反而在专家那里打了擦边球;自己心中没底的小说,反而一时间会众说纷纭。好在我更在乎写什么和怎么写,而对于别人的评价,我更在乎其中有启发意味的部分。王:
的确这样,作家、读者、专家的兴奋点不完全一致,这种现象有正常和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一部作品问世,各方态度可谓千姿百态,既与文学的社会属性和各色人等不同的感受力有关,也与当今人们多元化的文化选择有关,当然,也不排除社会的浮躁和复杂性。秦:
您这个话题对我是有启发的,当今文坛和当今社会,谁才是作品的裁定者。注意我特别强调当今,当今和过去对文学的态度和认识的确不一样。这让我想起最近随长春电影制片厂剧组西部行的经历,他们要把我的“皇粮系列”中的小说《皇粮》搬上银幕。影片顾问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刘守英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行还有长篇纪实文学《南渡北归》作者岳南,那晚,农业专家、文化学者、地方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不约而同地对我的小说《摸蛋的男孩》展开了讨论,争鸣的焦点是中国城乡“二元化”对立最尖锐的供应制时代,忍饥挨饿的农村孩子通过把手指探进母鸡屁股摸蛋的方式试图把握母鸡产蛋的时间,便于确保把鸡蛋上缴国家,保证城市供应。这一惯常的农家生活细节,到底和中国历史是什么关系,与民生是什么关系,与中国城乡居民的命运是什么关系。我在这样的热议中发现了另一妙处,他们的讨论与当下文坛的讨论方法完全不同,他们的讨论根本上是把文学纳入历史、社会和哲学范畴来讨论的,而文坛始终抵达不到这一层面。所以,我有时候和搞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的专家聊文学,反而比在文学理论家那里获得的启发要多得多。就像易地搬迁,听起来好像仅仅是换个地方盖房子,地质、水利、农业、生态、土地专家给你提供的信息会使你茅塞顿开,而你如果一味听信泥瓦匠的话,极有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王:
是这样的,文学终究要被社会来认知而非止于文坛,否则就是画地为牢。文学是人学,文学中的人物是文学立足于世的根本,这本应是一以贯之的古老话题,而今反而变得陌生和新鲜了。一方面,都在对文学中的“人”千呼万唤,而另一方面,又都匆匆忙忙在故事、人、情节之外翻弄叙事的方式。很多作家不敢在“人”的问题上下功夫,唯恐不够时尚,唯恐在追逐西方叙事模式的道路上不够超前。我发现,你的小说中对“人”的呈现多有出彩之处,在《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借命时代的家乡》《杀威棒》《吼水》《一路同行》《幻想症》《寻找》等小说中,那一系列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让人过目不忘。我注意到,你近年的一些小说被有关省市成功改编成了评剧、晋剧等各种戏剧,而且囊括了戏剧界的诸多奖项。我要说的是,戏剧是非常中国化的传统艺术形式,其强大的民族性、民间性特征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在全社会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量,也是这个原因。我想,他们之所以青睐你的小说,正因为你的小说中有“人”存在,记得当年中国作协研讨你的《皇粮钟》时,有人提出“在秦岭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中国农民”,这是十分可贵的。秦:
很难想象小说中假如失去人物形象和故事内核的支撑,这样的叙事是否能够仍然有资格归于小说这种文体。曾经某个时期,文坛打着所谓先锋的旗号热衷于散文化的小说,或者有意让叙事在故事外往复循环,甚而以淡化故事和人物为能事。我一般不会参与这方面的争论,我也读过大量欧美国家的小说,我欣赏先锋,但我更在乎“先锋”中对人物命运的切入,更注重对人物与社会关系脉络的考察。欧美作家普遍把“人”的元素做得非常活,非常到位,这点对我启发不小。当然我也关注欧美作家讲述故事的技巧,在我看来,国界、地域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而魅力恰恰就在这样的迥异里。芭蕾是芭蕾,京剧是京剧,我绝对不会干那种用芭蕾包装京剧的蠢事。文学的技巧必须与本土的生活质地、文化原色和审美习惯结合起来,如果剥离了这一层,技巧支配下的“人”必然成为怪胎。王:
从你的创作视野看,似乎农村题材居多,实际上你长期在天津这座大城市生活,将来是否仍然要坚持写农村。秦:
我对农村充满莫大兴趣,当年在老家天水农村生活、工作时积累了很多东西,而今农村的变迁与变革,与这些东西无时不在发生剧烈的碰撞,我在这种碰撞中难以自拔,至少今后一段时期,我将仍然把视角投放到那里。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认为小说只是小说,而是给予了更为深邃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是通过故事,当然主要是人物表现出来的,祝你创作出更多鲜活丰盈的形象,从而无愧于时代与社会,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留下浓重的笔墨。秦:
谢谢您!我不敢奢望自己有多大能耐,但文学作为我的生活方式之一,我倒是希望把油盐酱醋调配得有味道一些。啥是好味道?我唯有且调且品,且品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