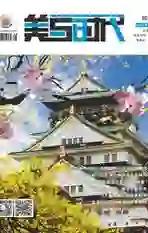福建文化背景中的朱子文学思想之继承与变异
2018-11-09宋红宝
摘 要:朱子文学多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其受福建文化影响甚深,同时其对福建文化的影响也颇巨。魏了翁、真德秀两人对朱子文学思想多有继承,但也因为理解有别,以至未能全面发展朱子“文道合一”的思想。而朱子文学中的艺术成分逐渐被遗忘,相反说教竟成为共识,这其实是对朱子文论的误解。
关键词:福建文化;道艺互轻;真德秀;魏了翁;朱子文学思想
朱子是孔子以来,兼备理学与文学集大成的学者,其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文学成就,是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朱子有很好的家学渊源。其父朱松“喜诵古人文章,每窃取其书,玩之矻矻而不知厌”。朱子也曾说过其父“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诗高洁而幽远,其文温婉而典裁。至于表疏书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吕思勉也曾指出:“南渡以后,理学家能为歌诗者,以朱子之父乔年及刘屏山为最著。”其次,即使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朱子依父嘱而跟随“三先生”学习时,其也不忘留心于文学。在很多人看来,朱子的诗文受刘屏山(屏山、白水和籍溪三先生,对朱子或有再造之功)的影響或许比朱松更深远。虽然朱子师事屏山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这段时间无疑是朱子学习诗文的关键时期。
有学者指出,朱子文学多有浓厚的地域文学色彩,事实上这自然还是闽学的底色不自觉地呈现而已。然而,如果要说朱子文学与新安文化没有关系,恐也不确。徽派的艺术风格实际上也因其父的言传身教,而流入其思想状态之中。或可说,朱子文学思想既有新安文化的基因,又多受道南一脉的影响,更与八闽大地浓郁的风俗和秀美的风光熏陶有关。更有学者指出,朱子弟子后学中,尤以福建学者受其影响最深。
宁宗庆元年间,朱子、元定等人遭党禁罢职,朱子之文章、学说一度也被禁绝。待权臣韩侂胄败亡伏诛后,朱子之思想、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在此期间,有多人为了朱子学的重新流布而奔忙。其中,功劳最著之后学,尤以真德秀(号西山)、魏了翁(号鹤山)两人为最。真、魏两人同年出生,也同年考中进士,更同朝为官,可谓志同道合。两人虽谨守道学家所宣扬之义理,但对于文学思想之认识以及朱子文学地位之评价则多有不同。
据《宋元学案》记载,“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而已。”魏了翁承学于张栻弟子范荪,受朱子和南轩学问影响颇深,可谓“私淑”;真德秀则问学于朱子弟子詹体仁,其对诗文的主张也自认与朱子一脉相承。在梨洲父子看来,鹤山远见卓识,能力更超西山之上;西山对于学问只知墨守成规,不敢变通,惟门户之见是从。我们不妨也可以说,鹤山与西山两人不同籍贯和履历,或也影响了他们对朱子文学思想的选择。
魏了翁年少时即“喜记诵词章”,相对而言其并不反对文辞,而是反对不根无实之文、不本于道之辞。其指出,“人之言曰:尚词章者乏风骨,尚气节者窘辞令。某谓不然。辞虽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鹤山并不认可时人所谓“尚词章者乏风骨,尚气节者窘辞令”。在其看来,文辞虽是小技,但确是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的,无本之人显然不能胜任;东坡以辞章自成一家,后人也以其为辞章之宗,然而后人并不真正了解东坡所以为文的缘由,言外之意自然是东坡的文章也有气节,故而更有存在的意义;词章、风骨、气节和辞令可以完美结合于诗文之中,但评价诗文优劣,应以大节为标准。毫无疑问,这一所谓的“大节”即是理学家所坚守的“道”或“理”。
鹤山可谓很好地继承与发挥了朱子关于诗文的某些正确的主张,这自然也是与其“能文”有相当之关系。如果仅从“能文”的角度而言,西山或也不如鹤山。
真德秀指出,“国朝文治猬兴,欧、王、曾、苏以大手笔,追述古作,高处不减二子。至濂洛诸先生初,虽非有意为文,而颇片言只辞,贯综至理。若《太极》《西铭》等作,直与六经相出入。又非董、韩之可匹矣。然则文章在汉、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为盛尔。”
在西山看来,西汉和唐代实为文章的辉煌时期,然而在那么多的文学家中却只有董仲舒、韩愈等少数几人的文学作品才能发挥义理,有利于世道人心的弘扬;宋代文治斐然,欧、王、曾、苏等古文大家更是造诣非凡,成就并不在董、韩两人之下;濂溪、横渠、二程等人纵然不是有意作文,但即使是片语只言,也能贯彻道理,《太极》《西铭》等著作更可以媲美六经,这是董、韩等人的文章所不能比拟的;文章在汉唐,虽多有成就,但真正可以称为鼎盛的,惟有宋代而已。西山对于“国朝”文章的赞许,并非仅是一味地偏袒,而是立足于自身思想合理的识见。真德秀编有《文章正宗》一书,文集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然选录标准及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轻于论文。在西山看来,明理义的文章,才能视为正宗,也只有这种“正宗”的文章,才可以流布天下,挽救世道人心。西山十分注重《大学》《中庸》等理学著作,其认为只有涵养其中,用心体会,才能深达其旨,进而仔细研习《太极》《西铭解》《近思录》等书,才能契悟义理之精微。惟有理学家的文章才能避免空虚无实之病;华而不实的诗文只是哄骗工具,自然也非贯道之器。可以说,真德秀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当时颓废、闲散的文风,但未免矫枉过正,反而抑制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梁启超指出:“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于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在梁氏看来,气候山川对于个人或者地域文化多有潜移默化之影响,环境对于当时当地甚至某个人的影响或有不可思议的作用。或许,我们也可以猜测真、魏两人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选择与信守也多与当地文化有关。身为福建后学的真德秀对于朱子的“忠贞”与维护或也与文化有关。
文治天下,是艺祖定鼎以来的“国是”,有宋自太宗以来历朝帝王皆能遵守右文政策。无论是古文还是骈文,诗抑或词,在宋代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若论“诸公率崇性理,卑艺文”,显非事实。且不说宋初所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未曾崇性理,庆历以来古文大家未有卑艺文之举,就算是理学家也不完全都是崇性理,卑艺文,最多也只能说是伊川和西山等人而已,我们知道朱子也并非如此,其只是坚守“文道一贯”罢了。程颐是朱子之前理学家中宣称“作文害道”论的主要代表,而真德秀又是朱子之后理学家中阐扬“文以载道”论的重要代表。而同样是阐扬“文以载道”,真、魏两人也多有分歧。
“道”“技”问题,实为“道德”与“艺术”的问题。艺术必然要表达内心,内心最可珍贵者即是道德,而能把内心道德完美展示出来的技巧可称为艺术。一切道艺皆由心生,而人心若合于天意,则为天人相应,如此则道理的圆满得以彰显,艺术的美感也得到体現。文艺固然不能轻视,以免失去主体性而沦为理学的附庸,但性理之学由于涉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根本问题,所以必须得信守。朱子在阐发性理方面精义时“主程抑苏”也是无可厚非,毕竟东坡并不以性理著称或也不屑为之;而在诗文方面,朱子对于东坡并非全然否定,对于二程兄弟,也非一味袒护。
钱锺书指出:“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越来越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不管道学家是无能力而写不好诗或者是有原则地不写好诗,他们那种迂腐粗糙的诗开了一个特殊风气,影响到许多诗人。”这些诗人中,除了相对著名的黄庭坚、贺铸、陆游、辛弃疾等大家以外,还包括一些文学史上不太显耀的小人物,诸如:吴锡酬、吴龙翰、陈杰、陈起等人。据钱钟书介绍,反对道学是周密家里祖孙三代相传的门风,而周密本人所取“草窗”的笔名更是来源于濂溪与明道等道学家“不除窗前草”的典故,从周密身上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可知道学家的文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实远在祖宗时期,柳开、王禹偁等人即反对五代以来诗文的庸俗化,已发北宋古文运动先声。庆历以后,欧阳修、曾巩等人进一步倡导古文,继而濂溪、横渠、二程等理学家也力辟西昆体或四六骈文的缺失,这无疑也从侧面声援了古文运动,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遂蔚为大观。这种盛况空前的文艺繁荣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朱子提倡“文道一贯”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朱子以前的理学家轻薄文艺,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但不管如何辩解,这确实影响了当时的诗文创作。朱子非但没有墨守之偏见,而且其还能利用自身的兴趣,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这些诗文,无疑可以成为艺术的典范。同时,朱子还根据理想准则,评判了诸多文学作品。虽然也曾引起不少争议,但朱子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评论,确实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朱子所提倡的文道一贯之理念,更应该成为理学家或者文学家共同遵守之型范,然而,事与愿违。后世学人无论胸襟还是识见都不如朱子,理学与文学的分歧也逐渐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朱子之建议原本对于理学中人或者骚人墨客皆有助益,怎奈双方竟不以为然。其实,这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就算文人学者认同朱子的某些文学主张,以道统自居的理学家们也不一定能谨守朱子合理之构想。
朱子门人后学只知道墨守成规,而不知灵活变通,再加上他们不具备朱子的才气,所以他们所作之文章越益忽视、否定文学的艺术性,更带有浓厚的说教气息。同时,一般的文学家也不具备朱子的性情,因而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误解甚至歪曲朱子的文学思想。当然,朱子虽然主张文道一贯的思想,但是其有时不免也有重道轻文的想法或者做法,而这些“重道轻文”思想,不断地被某些后学特别是政治地位或者学术地位比较重要的后学所宣扬和阐释甚至利用,以至以讹传讹,最终形成“一犬吠形,万犬吠声;一人传虚,百人传实”的局面。涌现文道相轻的景象,并非是朱子本意,然而又不能不说与朱子有一定关联。
参考文献:
[1][清]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96:2696.
[2][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3][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4]钱锺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45.
作者简介:
宋红宝,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