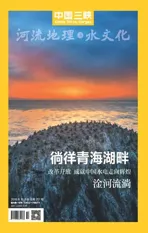海南:唐蕃古道上
2018-11-09耿占坤编辑田宗伟
◎ 文 | 耿占坤 编辑 | 田宗伟
我不是随意参赛的骏马,
假如你非让我参赛的话,
请备上一套精致的鞍子吧!
谁说我不跟你比赛呢?
我不是随意对唱的男儿,
假如你非让我对唱的话,
请说一句心底的话吧!
谁说我不跟你对唱呢?
——海南藏族民歌

青海地图 制图/ Hleeow
在青海湖南岸的青海南山和黄河之间,形成了几个宜农宜牧的盆地,恰卜恰镇就位于其中最大的共和盆地中心。据说,“恰卜恰”是蒙古语,意思是切开的山崖。我相信,同青海中西部地区所有的蒙古语地名一样,它还应该有一个更为古老的吐谷浑语或古羌语名字。从历史上看,这里一直是古羌人、吐谷浑人、吐蕃人以及蒙古人所追逐的理想游牧之地,恰卜恰正处在唐蕃古道上,无论它当年是一个小镇还是一个驿站,它都显得非常重要。今天,从这里出发,远方前往青海南部高原,近处可以达到黄河龙羊峡。
山重水复的唐蕃古道
率侍臣、宫女、匠师、僧人及随从护卫两万余人,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登上了这道山岭。在这里她受到吐蕃王朝松赞干布特使的恭迎敬拜。
站在这个叫做赤岭的山岭上,公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起伏的山峦和茫茫无边的土地被翠绿的草覆盖着,草原上缀满各色的鲜花,一群群的黑牦牛和洁白的绵羊撒满草原,从远处,传来牧羊女断断续续的歌声,几顶黑色和白色的帐房立在草原深处,充满了神秘。在草原与蓝天相吻处,一团团白云不停地涌动、变动、犹如千军万马。风强劲地吹来,携裹着新鲜、幽凉而芬芳的草原气息,这气息美妙而又陌生。
公主回望一眼东方,然后平静而亲切地对迎接她的使臣说:起程吧,我们回家。
在大唐文成公主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道路。
这是一条贯穿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道路,它在汉藏交往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这是一条通过联姻而得以拓展的充满传奇的道路,因而这条古道上一直弥漫着温馨与和平的色彩。
一千四百年前的长安无疑是世人注目的中心,大唐帝国的强盛、繁荣和开放,使得从君王到文人骚客都确信一切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一时期大唐天子有精力和实力考虑去开拓更加高远广大的疆域,这是此前历朝帝王所不能想象的。
通往高原的道路并没有经过太多的征战或曲折便打开了,这取决于吐蕃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双向需求。
追逐着文成、金成两位大唐公主的步履,精于算计的茶马互市的商人、巧于周旋应酬的使臣和无数心怀虔诚的僧侣香客奔波往返于这条道路上,汉地的丝绸、工艺、宗教及某些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传入高原,高原的马匹、牛羊等同时运往内地。一些唐代诗人甚至在传闻与猜测中对高原神奇的文化产生了诗意的热情。可以说,在这次规模空前的交流中,得到更多实际利益的当是吐蕃,丰富的物质和先进的文化使吐蕃受益匪浅,使长期封闭的高原在对中原地区的大开放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强大唐王朝的联姻,使吐蕃王朝在没有受到更大抵抗的情况下尽据诸羌之地,包括统治了青、甘、川地区达300多年的吐谷浑王国,从而统一了青藏高原。而对于唐王朝,除了获得马匹、牛羊、高原奇珍和来自印度的文化之外,它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高原产生的重大政治与社会影响以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为青藏高原最终在元朝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唐蕃古道几乎畅行无阻地延续了二百多年。当然,这条道路上走过的并非全是友好的使者,官兵西进征讨和吐蕃势力东扩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如是说:“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杜甫更为我们描述了塞外高原、青海湖畔这样一幅景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风啾啾。”这个苍凉得近于恐怖的场面使我们明白,和平的代价并非只是茶叶与马匹。唐蕃之间最大的一场战役是文成公主和亲之后三十年发生在青海湖畔切吉草原上的大非川之战,在这次战役中十万唐军全军覆没。“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走下高原,向东推进,控制河西走廊一带达100多年,并曾一度进入长安。
唐蕃古道随着唐王朝的覆灭和中原地区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而阻断,吐蕃王朝也随之而衰落,此后数百年间,辉煌一时的唐蕃古道被掩没在牧草与风雪之中,直到元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统辖之后,这条古道才被帝国的马蹄重新踏出痕迹来。至清代,随着王朝对蒙藏事务的重视和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古道再现昔日的繁忙。钦差、大臣、士卒、商人、香客、汉地高僧与藏地活佛奔波于高原上下,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不同的角色,也取道河西走廊、经青海试图进入西藏。然而这条古道对西方人并不开放,他们在这条古道上付出了时间、金钱、装备甚至生命的代价。
唐蕃古道从长安到拉萨,全长达3000多公里之遥,沿途穿过富饶的秦川、沟壑深切的黄土丘陵和祁连山峡谷,然后沿湟水而上进入雄伟广阔的青藏高原,从赤岭向西南,穿越茫茫草原和无数沼泽湖泊,渡过黄河与通天河险阻,翻过一座座雪山,一路有看不尽数不清的壮丽风光;从中原到西羌再到藏地,汉、回、蒙、藏等多民族的生活与文化迥然有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农耕游牧、神鬼贤圣、土风俚俗,大相径庭。一路有说不完的故事,听不完的歌。
唐蕃古道像一道夕阳下的影子,被创造、被晕染、被吞没,又一次次地被朝阳映现出来。
赤岭的记忆
日月山是进入海南的大门。无论在地理、文化还是人们的心理上,并不高大的日月山都是无法忽视的。它是严格地理意义上的青藏高原门户,是外流的黄河水系和内流的柴达木盆地水系的分水岭,也是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唐代以前称为赤岭,是唐王朝与吐蕃王国的界岭,也是和亲、交战、茶马互市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它因为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在此摔碎了日月宝镜而得名日月山,人们以这山岭和众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来怀念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修建了日亭和月亭,分立于山口道路两侧的山丘上,并在日亭内绘制了公主和亲故事的壁画,尔后又在山坡下修造公主塑像和其它建筑。山口海拔3520米。站在日亭眺望,天地空阔,气象磅礴。起伏跌宕的山岭东侧,是镶嵌于山坡和谷地中的片片农田,每到夏天,金黄色的油菜花与翠绿的青稞麦苗交替排列,伴着鸡犬之声从小山村里升起阵阵炊烟;而山岭的西边却是坦荡的山间牧场,草原上牛羊成群帐房点点,马背上的牧人悠然高歌。作为一个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大概很难有其它地方能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概念阐释得如此一目了然。
日月山与南北两侧的青海南山和大通山绵延相连。群峰之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即使到了五六月间,山下一场大雨过后,群峰上依然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这些属于祁连山脉的高大山岭以一种顶礼赞颂的方式环绕着圣洁的青海湖,它们手挽着手,犹如草原舞会上一群英武矫健的男子汉,将美丽的牧羊女置于它们宽厚有力的怀抱,从而使青藏高原在与人们相遇之初就充满了动人的柔情和神奇的豪迈。
从日月山向西一路下行,经过整洁美丽的草原小镇倒淌河时,整个小镇清新扑面的藏式建筑风格让人顿生喜悦。弥漫于空中的异域气息告诉行者,我们已经进入了真实的青藏高原,你将经历的是与此相关的环境、人物、事物、生活与文化。
小镇与流过它身边的小河拥有同一个名字。这是一条奇流,它以逆天下流水而只身向西的个性和诸多美丽的传说闻名。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全长不过数十公里,流水涓涓,隐藏于草丛之中,乘车路过的人很难注意到它。有人说它是西海龙王的一根倒须变成的,也有人说它是文成公主在日月山停留时流出的思乡之泪,因而更多的人相信它是一条柔美而充满感伤的女性之河。

日月山 摄影/殷生华
这个小镇最早诞生于何时已无从考证。至少从元朝时期,这里就应该是通往西藏和青海西部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而且作为进入青藏高原的第一个驿站,它存在的意义非同一般。官差在此换马,香客在此歇足,或许也偶尔有一两个远征的商贾在此借宿。旅人们受命运的驱使而踏上这苍茫高原,他们谁也无法预知明朝置身何处,前途吉凶,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个驿站就是第一个幸运的终点。那么,是谁第一个支起帐篷独守这无边的寂寞?又是谁第一个在此告别黎明一去不返?在这块土地上,哪里还掩埋着征战者的白骨,哪里又遗落着情人们的碧玉?作为时间的驿站,又把多少英雄和传奇送进了历史,而又一次次地看着它们重演;作为人生的驿站,它为多少行者接风送行,却从没有许诺为他们再度洗尘!倒淌河,也许这个名字就已经向行人暗示了一切。
今天,由这个小镇向西偏南,将会进入黄河流域的共和盆地,那里是海南州首府所在地,也是通往玉树州的必经之路。而跟随着清澈神奇的倒淌河继续向西偏北,青海湖就像一幅巨大无比的蓝色绸缎迎风铺展在天地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江西沟:高原上的典型小镇
高原上这小镇之小,让都市人以及中国中东部地区的人们难以想象。我之所以能够注意到它,并不仅仅因为它在一比三千七百万甚至更小的中国地图上占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圆点,还因为它同样是高原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以及旅行中不可忽略的载体与内容。在整个藏区有许多这样的小镇,江西沟应该属于比较大的一个,因为它拥有三个条件:处在109国道青藏公路上、位于青海湖畔、是一个乡政府所在地。
在沿公路两侧一百米多的范围内,集中建有一些房屋,这些房屋面对公路一字排列,建筑风格和门面的装饰具有鲜明的藏族风格,看来是特别规划的,因为大部分房屋并非民居或藏族人所有,而主要是由来自青海东部或内地的回族、汉族开设的餐馆、商店等,它们构成了小镇的主体。

日月亭壁画 摄影/殷生华
仅仅十几分钟,我便从西到东又从东到西把小镇溜达了一个来回。我看到,小镇上大约有四十几家餐馆(其中2/3以上是清真饭馆),二十几家小商店,三四家可以停车住宿的旅社,三四家汽车、摩托车修理铺,两家录像放映室。我漏掉什么了吗?对了,还有一个乡政府、一个农业银行、一家信用社、一所寄宿小学,一个工商所,一个卫生院,一个公安派出所,一个邮政所,一个草原畜牧服务站,一个养路道班,一间理发室。噢!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不过并不见什么贸易,院内的主角是十几张台球桌。如果我还漏掉了什么,我请他们原谅。
这样一个小地方拥有四十多家餐馆看上去是太奢侈了。实际上除了进“城”来的牧民和那些单身的公职人员外,主要的客源还是途中客:往返于西宁-格尔木-拉萨之间的汽车司机、观光者、商人、打工者等等。餐馆一般都不大,少则两三张桌子,多则三五张桌子,比较干净、整洁,尽管地方很小,许多餐馆还是挤出一席之地放一台电视机,并配有录像机或VCD,这实际上成了招揽顾客的一个条件,特别是并不急于赶时间的牧民,他们乐意一边慢慢吃饭,一边欣赏一场免费的录像节目。精明的商人之道处处可以体现出来。

日月亭碑文 摄影/殷生华
小镇上的商店同样规模很小,大多是单间,少数有两间,供销社有三间铺面。商店中的商品大同小异,都是综合性的百货,多是服装鞋帽、烟酒食品、牙刷电池等,比较有特色的商品是那些藏族牧民喜爱的用品和饰品,包括各式藏刀,金属、石质、木质、骨质的装饰、首饰品,还有价格昂贵的水獭皮。乡长曾太本带我去看一家当地藏族人经营的商店。商店有十多个平方米,所售商品同其它商店无甚差别。店主是一位大约近五十岁的男子,个子不高,一脸憨厚,乡长用藏语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省里来的记者,想采访你。没想到他竟像女人似的用手捂住脸,夺路逃到外面去了,这个几十岁男人的举动实在让我吃了一惊。我笑着对他喊:你再不进来,我就在这里当老板了!乡长告诉我,这里藏族人经商的很少,即使有,效益也都不太好。我想,见了生人就羞得吓跑的经商老板,要想生意红火怕还真是难呢。可见就藏族人而言,传统的文化与心理、传统意识与现代商业活动之间,依然矛盾重重。
同许多既偏远又“落后”的地区一样,这里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产业——工业。在不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第三产业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尽管规模小而原始,这里单一的经济成份产生了有价值的调节,也给生活注入了一些新鲜和活力,它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几乎不停地下了一夜的雨,清晨起来,雨丝依然在织着那张有经无纬的梦中之网,冷风仿佛也在寻找温暖似的直往衣服缝里钻。小镇还没有醒来。青藏公路那醒目的黑色柏油路面横贯草原,蜿蜒而去。公路南侧是大片尚未成熟的青稞和油菜田,远山已披了一层积雪。空气清凉,雨使得空气更加纯净了,一尘不染,但雨也给庄稼带来了灾难,阴雨使气温降低,随低温而来的寒冷可能会让这些庄稼再也达不到饱满和成熟的辉煌。公路北侧,掠过草地可以看到湖水发出一片银灰色的光,从小镇到青海湖边还要穿过大约4公里的牧场,但看上去却近在眼前,那粼粼的波光和超然的幽静把草原和小镇都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国度。
随着一家家餐馆升起炊烟,夜泊的旅人和车辆相继醒来,过往的车辆渐渐多起来,早起的牧民也开始进城了。在灿烂的朝阳下,小镇再次担当起联系社会、沟通文化和创造生活的历史责任。
跟随牧民迁徙
像候鸟一样,仍然有一些族群在为生存而追逐着大自然的脚步。春夏秋冬,风霜冷暖,他们世世代代听从神灵的指引和呼唤,完成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使之生生不息。湖畔的牧民们把逐水草而居的古老生活方式保留至今。我相信这是人类所具有的与羚羊、斑头雁、麋鹿或白天鹅相同的本能与智慧,这是一种生存的艺术,也是一种传统和文化。
在江西沟乡,我赶上了牧民的一次转场。这次向湖畔牧场的转移极其短暂,他们在这里放牧大约8到10天。湖畔是冬春牧场,这个短时间的停留完全出于对牧场的保护:通过牛羊把尚未干枯的牧草踏得坚实严密,贴向地面,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冬春季节的大风给牧场带来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牧民还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赛马会。因此这次短暂的游牧生活富有意义。十天过后,牧人们将再次从这里搬走,到偏远的深山去放牧,直到山里雪封冰冻,在最艰难而漫长的严冬与荒春,他们会再次回到这里,一直坚持到第二个夏天。牧人们像候鸟一样在大自然中探索着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可能,漫长的岁月和严酷的环境,使牧人的生命力和生存的智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青海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山,赛宗寺则依山而建。 摄影/夏都/东方IC
经乡上干部的介绍,我加入到了小伙子角巴家的转场队伍,同他们一起吆喝着牛羊向湖边走去。角巴的队伍很庞大,有800只羊和100多头牦牛,他带领着妻子、小儿子和两个妻妹负责这次转场,老人们同样留在定居点。羊群似乎没有什么负担,一路轻快地向前跑,而牛群却不然,它们绅士般地迈着方步,哼哼叽叽地磨蹭着,几头调皮的小牛犊一边走一边相互挑衅、打斗,常常给队伍中制造混乱。四头大牦牛理所当然地担任搬运工,它们毫无怨言地背着一个个大包裹,金属器具随着它们的行进不停地发出极有节奏的叮当声。一只高大的牧羊犬跟在队伍中,但很快它发现草原上有一位女友叫它,于是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日月山。是唐蕃分界岭,也是农耕牧业区分水岭。 摄影/殷生华
下午两点,我们到达牧场。同许多人家一样,角巴家在这片属于自己的牧场里建有一间简陋的小土房,他们不需要再支帐房了。土房前用土块围了一个院子,院内种了一片燕麦,草也和燕麦长的差不多高,绿油油的,一直长到门口。土房很小又很低矮,墙是用土堆起来的,房顶平平的,在很细的木椽上铺一层篱笆,上面再抹一层泥完事,房内大约有十平方米,其中里面的一半被一个贯通的土炕占据了,连炕有一个灶台,屋内没有任何家具。因为房子的门窗都是洞开的,在不住人的大半年时间内,这房子是鸟雀、野兔和老鼠的宫殿,炕上地下布满的鸟粪和老鼠屎就是证明,土炕上还有几丛野草,长得很高。
几头驮牛搬来的东西包括被褥、毡毯、锅、碗、盆、茶壶、挤奶的木桶、背水的塑料桶、炒面、酥油、羊肉、大饼和油炸食品、牛奶分离器、一捆牛毛绳以及其它生产用具,当然还有姑娘们用的香粉、润肤膏、准备节日用的盛装和首饰,这些东西在草地上摆放了一大片,看来准备很充分,不过角巴有一辆摩托车,如果缺什么他可以随时回“冬窝子”去取。虽然省去了支帐房的工作,但房子需要大扫除。角巴的妻子得勒和妹妹花保开始用芨芨草扎成的扫把打扫房间,一瞬间尘土弥漫,炕上和墙根的杂草也被拔下来同鸟粪一起扫了出来,尘土还没有散去,得勒已经在灶膛里生起了牛粪火,烟雾大极了,房子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不得不从里面逃了出来。
姑娘们像变魔术一样把这间刚刚还是野雀之巢的小屋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家,环顾房内,我不禁惊奇和感慨,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可一切又是那么充足,衣食住用都不缺少。我发现,获得一种自由的、既不会挨饿受冻又不会孤苦寂寞的生活竟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对于一种自然纯朴而又轻松愉快的生活,所有的奢侈品和贪得无厌的奢望都只能给它增加不和谐的累赘。于是我对自己、对我永远也不能适应的那另一个环境中的人们怜悯起来。
湖畔的牧场是牧人们所拥有草原中最好的、最重要的、也是面积最小的牧场,它是畜群安全顺利越冬度春的根本保障,因而牧人都十分重视对湖畔牧场的保护和利用。每家的牧场都用铁丝网围起来,这也给放牧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畜群不再需要专人时时看守。对羊群只需晚上赶进羊圈,早上放出去就行了,牛犊每天晚上要赶回来拴在屋旁的草地上,以防夜里走失,对成年牛可以不管,但每天早上要给母牛挤奶。
在得勒和花保两姊妹干活的时候,我到湖边闲逛了一个多小时,在紫外线毫不留情的威胁下,我终于放弃了在湖畔等落日的打算,捂着火辣辣的脸走回牧场。“家”里空无一人,我倒了一杯奶茶,走到草地上用大衣支起一片阴凉,坐下来休息。一杯奶茶,一阵凉风,使我浑身的倦意全消了。
夕阳靠近山顶,得勒背着满满一桶清水回来,从她额头上滚落着汗珠。她说背水的地方很远,在湖边有一股泉,是淡水,走捷径来回有三公里路,但中间还要翻过好几道铁丝网。这个塑料桶能容50斤,我感到它在花保的背上有如一块巨石。她放下水桶,嘱咐我吃喝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然后又匆匆去湖边赶牛了。
当姑娘们赶着牛羊牧归时,生活仿佛又成了一支歌,一幅画。这时候,夕阳正从地平线上最后一片云朵里半隐半现地放射出光芒,晚霞烧红了天空,气象万千。草原上的光线暗下来,被一层充满神秘气氛的色彩笼罩着,牧草在微风中低吟着古歌,姑娘们的身影映在草原上,一直向远方投射过去,鸟儿在羊群上空飞来掠去,迎接着它们的归来。一切都充满了生活的自然诗情。
晚饭后牧人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我和他们一起遵循早睡早起的习惯。牧场人家只有一间房、一张炕,老少都在一处就寝,只是按次序分开,客人也不例外,特殊待遇是炕的最上方,即面对炕的最左边属于客人。于是这个位置理所当然地留给了我,依次是角巴、他的妻子、孩子、两个妻妹。在我的铺位上,放了一床崭新的被子,看着这土炕的灰尘,我久久不忍心把这被子展开。在挨近我枕头部位的墙根,有一个老鼠洞,望着它我忧虑重重,我问角巴:晚上会不会有老鼠出来?角巴看了看洞口说:会。于是得勒出去找了一个土块把它堵上(结果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那土块早已无影无踪,洞口清晰地留有老鼠爬过的痕迹)。终于,我还是同角巴一家五口在这张大炕上一起进入了梦乡。
夜里,我被屋外的响声惊醒,是风和雨的声音,还伴有沉闷的雷声,天气变化真快。房内的气温明显下降了,我强烈地感觉到冷风从洞开的门窗拥进来,一股一股地直往被窝里钻,雨点打在房顶上的声音时急时缓。我将被子拉到脖子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清晨6点多钟,我听到炉膛里的火在燃烧,热腾腾的气流从炕上透过脊背来,花保已经在烧炕、烧开水。屋外的风仍然在呼呼地刮着,天色阴沉。我穿上大衣走出屋外,空气像是被过滤了一样清澈纯净,但风雨仍然没停。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国家地质公园 摄影/杨顺丕/视觉中国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湖二郎剑景区 摄影/耿玉和/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