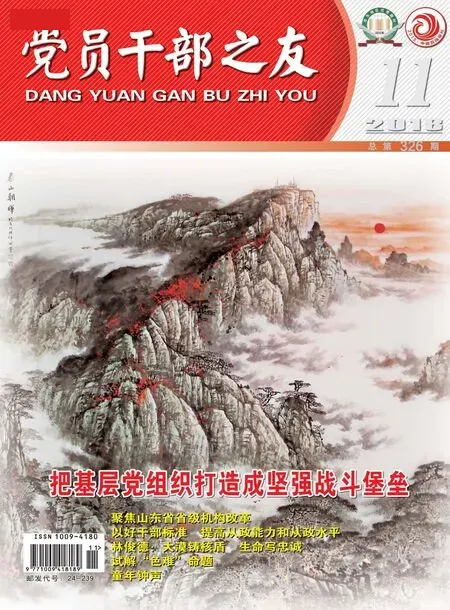试解“色难”命题
2018-11-06

黎 青 /图/
“好与贤己者处”的子夏问孝,孔子回答他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对“色难”的理解,众说纷纭。我觉得钱穆先生讲得比较到位,他说:“色难:此有两解。一,难在承望父母之颜色。《小戴记·曲礼》有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能在无形无声中体会得父母之意,始是孝。一,孝子侍奉父母,以能和颜悦色为难。《小戴记·祭义》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人之面色,即其内心之真情流露,色难仍是心难。前说指父母之色,后说指孝子之色。既是问孝,当直就子言。且前解必增字说之始可通,今从后解。”
侍奉父母,以能和颜悦色为难。面对老人,能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因为难能,所以可贵。
在孔子看来,能养、能服、能先,都不是孝。犬马喂饱了,就是“能养”,不关乎敬;“有事,弟子服其劳”,你干不了的,我帮你干了,为长者折枝,这是“能服”,不掺杂太多感情;有座位,让给老人先坐,有好吃的,让给老人先吃,这是“能先”。在孔子眼里,这都不是孝,或者不是大孝。真正的孝,必须要有“敬”。和颜悦色,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临时的表演。“色难”是心难,“色难”是态度难。
在当今社会,却出现了一些不孝敬老人的怪现象。如,有些子女对老人做不到“能养”,有的为了房产,对簿公堂,房产显然比父母重要,典型的重物轻人。有的人,对宠物的态度超过对父母若干倍。不能养,就谈不上能服。服,服侍、服务,都做不到。老人一有事,晚辈互相推诿,不愿意干,躲得远远的。能先,就更谈不上了。我曾听说过一件事,孙子在大酒店结婚,当奶奶的满心欢喜,早早地打扮好了想参加期待了多年的隆重仪式,但儿子、儿媳妇来了一句:还是在家给我们看门吧。奶奶只好噤声。辛辛苦苦把孙子看大的奶奶心里能好受吗?人心不古,以至于此。
看到这些不孝敬老人的怪现象,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敬老方面可否分步走,第一步要做到:能养、能服、能先。这是物质层面的,要让父母有获得感。做晚辈的,要舍得给父母花钱,为父母提供必要的保障,衣食住行,都要考虑;要舍得花精力去服侍父母,服务父母;有好事先想着父母,比如有好吃的,好喝的,先让父母品尝,别自己偷偷地独享。第二步,解决“色难”命题。这是精神层面的,就是要让父母精神愉快,让父母有幸福感、安全感、自豪感。
我曾跟好多晚辈交流过,他们说,第一步不难做到,能舍得,能付出。难的是第二步。就是解不开一个疙瘩,觉得老人认识问题的角度、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标准等等,很难沟通。比如一个苹果烂了,扔掉就是,但是老人非要将好的那点挖出来吃了,才算心安。比如处理剩菜,再比如不停地唠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等等。看上去,这些都是小事,无关其他,但是相处起来,就特别难,有时就是因为这些小细节而引发矛盾。这些矛盾看似不起眼,但很尖锐、很难调和。“色难”命题,的确是个不好解开的难题。
难题解不开,主要是人有了傲慢之心,觉得自己无论从体力还是从能力、智力上,都高于老人了,就产生了一种高傲,而这种高傲呢,自己很难觉察。反思我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农村考上大学,有了城镇户口,那时叫吃上了“国家粮”,身份就变了。一眨眼离开农村到城市三十多年了,自己没有觉得有啥变化,其实已经变了。比如回家,我没有了扫院子的习惯,但我弟弟就很习惯,看到院子不干净了,就立即清理,可我却感觉不到。闻着驴粪、马粪味道,就受不了了。小时候的玩伴找我玩,我有些不耐烦,觉得他们见识浅。我能按时给母亲养老费,但没有给母亲端过饭,没有给母亲捶过背,甚至好久都没有给母亲打电话。总觉得自己很重要,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这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而把老人看轻了。有时候,母亲固执于一件事的时候,我会很蛮横地改变。这不是傲慢吗?是,我不能做到和颜悦色。我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我怎么能弯腰扫地呢?我怎么能道歉呢?南怀瑾先生说:“人都有自我崇高的心理,讲得好听一点就是自尊心,但过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结果就会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
傲慢之心,需要放低姿态纠正,跪下来纠正。我们有个好的家风,就是年除夕子时,我带着弟弟们煮完饺子,然后到灶台下、院中、大门口,在灶王爷、祖宗牌位、财神爷等面前供奉,敬拜三界诸神 。然后,在院子里放烟花爆竹。进屋的时候,我跪下来,给母亲磕头,我弟弟还有儿子、侄子辈们也跪下来给我母亲磕头。磕头的时候,我会大声说出来:“给俺娘磕头。”当你跪下来的时候,那一刻是谦卑的,是对母亲感恩的。那一刻是敬的。等天明了,我再领着晚辈们,给全村里的长辈们磕头拜年。这种仪式,就是在呼唤一种敬。
跪给老人的姿势,是打掉自己的“贵”,准确地说是“娇贵”,也就是要打扫一下一年来的尘埃,让自己轻装上阵。我现在想,我之所以还能清醒地立在世上,就是这样的家风浸润的结果,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自尊,但不能自贵。
我知道我们的好多家庭都传承着这样的风俗,这个风俗,是数千年来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文化基因。人人膝下有黄金,不能随便下跪,但是给父母下跪,是温暖的姿势。
“色难”命题,钥匙是敬。何谓敬?朱熹解释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就是心无旁骛,专心无杂念,有杂念,就是不敬。杂念,就是私心、私念。做到敬,不容易,很难。正因为其难,所以要克服之,把一切都当成修炼,克己而敬老。
“色难”命题,其实曾子也有自己的体悟,他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大意是,要调整容貌,摈除愠怒之色、狰狞之姿,要和颜悦色,这样可以避免粗暴、放肆、粗鄙。怎么“动”?用学问修养熏陶,一点点化出谦和安详的气质。怎么“正”?使自己的脸色、神情、态度端正,所谓“正颜色而不妄”,这样就接近于诚信、实在;怎么“出”?言辞和语气谨慎小心,把握分寸,这样就可以避免粗野和悖理。
敬爱长辈、孝敬老人,需要正身,“正身而不外求”。而这一切,都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一生之功。“色”是变的,要以不变应万变,就要磨练,练内功。
敬老,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叶芝的名诗《长久的沉默之后》中有一句,我爱反复咀嚼:“肉身衰朽乃见智慧。”这是台湾诗人杨牧翻译的。其实从老人那里获得智慧很简单,只需我们年轻人转向他们,深情地注视、耐心地倾听。说白了,关心老人的过程,就是获得智慧的过程。解决好“色难”命题,就是在获得智慧。获得智慧,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的洗礼。
与老人一起,和颜悦色,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