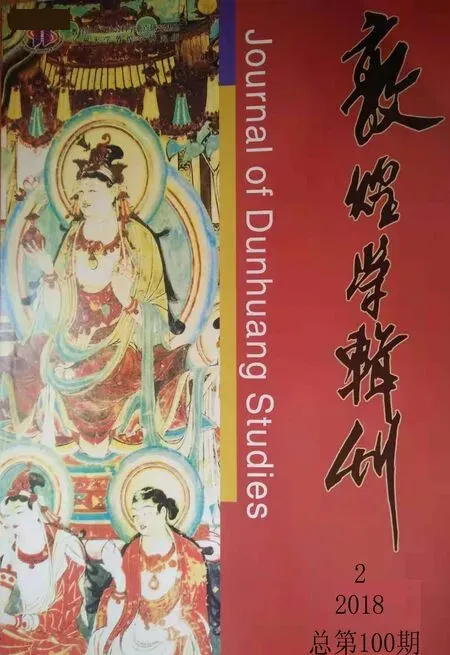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
2018-11-01郑阿财
郑阿财
(1.四川大学 中古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5;2.台湾南华大学 敦煌研究中心,台湾 嘉义 62249)
一、研究旨趣
“赞”作为一种文学作品,一般研究大抵从文体学的视角出发,近年较多从中国文学与佛教文学赞体的比较入手,进而论述汉译佛典赞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多是单一作品的考论,或据校录的文本进行内容析论;但对于中国佛教文学中赞的性质、功能及其运用等问题,因传世典籍可资探究实况的文献不足,以致相关论述大多缺如。
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赞体发展的关键期,其时正值纸本卷轴盛行的写本时期。基于佛教弘传与仪式赞的运用,不论是僧人创作或法会用以宣唱的范本,还是僧人私下传写备用的抄本,均以写本形态呈现。唐以后印刷术发达,进入刻本时期,其时图书大多经过整理刊刻印行,写本渐趋消退。今传世文献典籍写本实不多见,唐前写本尤为稀少,写本文献呈现的文化现象也因此而逐渐无由得知。今敦煌藏经洞数万件不为流传而流传的唐前佛教写本文献,其中有不少佛教赞颂写本,保存了晋唐佛教文学文献的原生态,提供当时佛教赞体的样貌以及考察寺院活动僧人使用的实况,是研究中国佛教赞体性质与功能的一手数据。
敦煌文献中的佛教赞,内容众多,如:《太子赞》《辞阿娘赞》《辞父母赞》《出家赞》《西方净土赞》《大乘净土赞》《父母恩重赞》《十恩德赞》《五台山赞》《五台山圣境赞》《金刚经赞》等,其赞颂主题包括赞佛成道、赞佛子出家、赞西方净土或佛教圣地、赞颂佛典等等。
前贤对此文献的的整理校录、内容的分类探讨,已不乏成果,如赵立真《敦煌赞文研究》[注]赵立真《敦煌赞文研究》,“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5月。、上山大峻《敦煌出土〈淨土法身讚〉について》[注][日]上山大峻《敦煌出土〈淨土法身讚〉について》,《真宗研究》21,1976年12月,第62页-71页。、陈祚龙《新校重订敦煌写本〈十空赞〉表隐》、[注]陈祚龙《新校重订敦煌写本〈十空赞〉表隐》,《东洋文化论集: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8页-318页。川崎ミチコ《佛母赞管见》[注][日]川崎ミチコ《佛母赞管见》,《东洋学论丛》41,1988年3,第119页。、杜斗城《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注]杜斗城《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1页-401页。、《关于敦煌本〈五台山赞〉与〈五台山曲子〉的创作时代问题》[注]杜斗城《关于敦煌本〈五台山赞〉与〈五台山曲子〉的创作时代问题》,《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50页-55页。、程正《法照撰〈淨土法身讚〉の依據文獻について》[注]程正《法照撰〈淨土法身讚〉の依據文獻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3卷第1号,2004年,第175页-177页。、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の紙背文書について》[注][日]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の紙背文書について》,《佛教学研究》5,1951年,第71页-72页。、《法照和尚念佛讚——文本並解說》[注][日]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文本並解說》,《龙大图书馆山内文库庆华丛书》,京都:京都庆华文化基金会,1951年。、《法照和尚佛讚について》[注][日]佐藤哲英《法照和尚佛讚について》,《佛教史学》第3卷第1期,1952年,第42页-64页;《佛教史学》第3卷第2期,1952年,第38页-48页。、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注]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年。后收入《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89册,高雄:佛光出版社,2003年。、王志鹏《敦煌佛教歌辞研究》[注]王志鹏《敦煌佛教歌辞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徐铭《敦煌本讚文類小考――唱導、俗講、變文との關わりより》[注]徐銘《敦煌本讚文類小考――唱導、俗講、變文との關わりより》,《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七号,2013年,第333-346页。等。
敦煌佛教赞的相关研究,除了强化敦煌文献研究的内容外,也激发了学界对中国赞颂文学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研究者对于中国佛教经典与文学中赞颂文学的论析,如陈明《汉译佛经中的偈颂简要辨析》[注]陈明《汉译佛经中的偈颂简要辨析》,《南亚研究》2007年第2期,第52-54页。、孙尚勇《中古汉译佛经偈颂体式研究》[注]孙尚勇《中古汉译佛经偈颂体式研究》,《普门学报》第27期,2005年,第181-220页。、黄毅洁《汉魏六朝佛典佛教赞研究》[注]黄毅洁《汉魏六朝佛典佛教赞研究》,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硕士论文,2010年。等。
检视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大多抽离赞体使用的现场而集中在个别文本的研究。个人由于近年关注敦煌写本的原生态,结合佛教仪式轨范,并将之纳入赞体文学发展来考察。今欣逢《敦煌学辑刊》“百期纪念专辑”出刊之际,特以敦煌《高僧赞》作为研究对象:从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及中国佛教赞体文学的流变入手,尝试探究赞体文学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不同文体、不同文类同一题材的文本性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同时也能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藉以表达《敦煌学辑刊》长期以来提供敦煌学研究发展学术平台及影响的庆贺之忱。
二、敦煌文献中的佛教歌赞与高僧赞
敦煌乃佛教圣地,莫高窟藏经洞是佛教石窟,其中所发现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的敦煌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与佛教有关。除了经、律、论等佛教典籍外,比较珍贵的是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初期禅宗史料、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同时还有为数可观的唐五代寺院文书,呈现佛教传播发展的实际面貌,可说是当时敦煌佛教寺院活动的全纪录,提供了研究唐代寺院文化具体而宝贵的一手材料。因此,学界每每称敦煌文献为中国中古社会生活的活化石或时空胶囊。其主要即在突显敦煌文献不为流传而流传的特性,具有反映实际生活面貌的珍贵价值。
唐五代宋初,民间佛教普遍,赞颂作品大量流传,僧人文士多参与创作,然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任其流散。敦煌文献中保存为数可观的佛教赞颂,正可弥补此一缺憾;同时也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赞颂在中土传播与实际应用的种种实况。

佛教继承印度赞颂传统,初期佛教有赞佛,随着佛教发展,高僧大德辈出,佛教宣教弘法过程,乃有赞僧。赞扬高僧的赞文,逐渐增多。形成赞颂佛法僧三宝具足的赞颂文学。内容包括皈依顶礼三宝,颂扬佛德之赞叹歌曲;歌咏佛法甚深微妙之诗文;以及传达高僧作为。在佛教弘传的发展历程中,佛陀及其弟子的赞颂自然最为风行而深受瞩目。敦煌文献中的佛教赞颂文学,内容主题呈现的也是以赞佛成道、赞佛子出家等最为丰富。其中赞佛成道最为主要,内容包括佛陀生平之事迹,例如:诞生、出家、苦行、降魔等,这些作品在赞颂佛陀的同时,也成为另类的佛陀生平传记文学。敦煌文献中《太子赞》《悉达太子赞》《太子修道赞》的写本丰富,种类也多,可以证明。
就文学体类论,佛教传记文学的发展,初期以佛传文学为主,随着汉传佛教的发展,开始有僧传文学孳长,晋魏隋唐以来,僧传文学更是蔚为大宗。赞扬高僧的赞文,当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后所衍生的佛教传记文学奇葩。今敦煌文献保存有不少此类作品。其中原卷题名有“赞”的,计有:佚名《佛图澄罗汉和尚赞》S.0276V、P.2680、P.3355,释金髻《罗什法师赞》S.0276V、S.6631V、P.2680、P.4597,《南山宣律和尚赞》P.3570,释利济《唐三藏赞》S.6631V、P.2680、P.4597,释金髻《义净三藏法师赞》S.6631V、P.2680、P.3727、P.459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P.2104V、S.4036、《稠禅师解虎赞》P.3490、P.4597,《寺门首立禅师赞》S.1774V、P.2680、P.3490、P.3727,《故法和尚赞》S.0276V、《吴和尚赞》P.4660、《禅和尚赞》P.4660等。1985年金冈照光在《关于敦煌本高僧传因缘》[注][日]金冈照光《关于敦煌本高僧传因缘》,《古典文学》7,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21-140页。一文中较早关注到S.1625《佛图澄和尚因缘记》,以为是概括佛图澄的神变故事,与“变文”同样也是作为讲唱的。现今留下的抄本虽短,但实际上讲谈时大概讲得很详细,主张应另起“高僧传变文”一类,来进行分析研究。
唐代佛教发达,赞颂作品曾经大量流传,释徒文士多所创作,惜受正统文学观念影响,此类作品大多散亡。所幸敦煌文献保存有此类作品,提供我们了解僧赞文学发展演变具体的实物材料。
三、从写本原生态看敦煌高僧赞的功能与性质
所谓“原生态”是从自然科学生态学科的“生态概念”借鉴而来新生的文化名词。原生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敦煌文献中的文学写本“原生态”则是指没有经过整理改变,保存于敦煌文献抄写的原始状态,包含了作者的草稿、修改、定本、抄录、转写﹔抄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编纂、汇录、丛抄、散篇、涂抹改写、乃至习文练字等原始的样态。
敦煌文献中的佛曲歌赞,写本形态有卷轴、册子、单张散页,抄写情况有佛教歌曲集、丛抄、散篇,及曲文合抄,反映了抄者身份,呈现出佛曲文本的使用功能。其中高僧赞以写本形式流传,形态多样,有汇抄,有散抄,有卷子,有册页,大抵为敦煌地区僧人所抄,保存敦煌地区佛教高僧赞抄写的原生态,可反映文本的性质与使用的功能。敦煌僧诗、全敦煌诗等一类整理研究[注]如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诗校释》,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作品文本辑录或研究,基本均以单一作品立论,罕有关照作品抄写的原生态,使用者对作品的运用与功能也未能有所析论。我曾于《从敦煌文献论灵验故事在唱导活动的运用》[注]郑阿财《从敦煌文献论灵验故事在唱导活动的运用》,《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2-148页。一文中根据六种因缘记抄写于八个卷子的原生态情况,从抄写者、使用者、编撰者等视角考察高僧因缘记在佛教弘传的运用,探究其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表现的功能性。以下谨就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进行简要叙录,以便从其写本原生态窥探其功能与性质。
详检前举《佛图澄罗汉和尚赞》《罗什法师赞》《南山宣律和尚赞》《大唐三藏赞》《大唐义净三藏法师赞》等敦煌高僧赞写本,其中S.0276、S.6631、P.2680、P.2775、P.3355、P.3490、P.3570、P.3727、P.4597等九件,均为卷子本,呈现着与其他佛教文书汇抄的形态,其抄写情形如下:
(一)S.276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抄有长兴四年癸巳岁(933)的《具注历日》。背面分抄:1.《阿难陁总持第一》《摩诃迦叶头陁第一》;2.《第一代付法藏大迦叶》;3.《灵州史和尚因缘记》;4.《佛图澄罗汉和尚赞》;5.《罗什法师赞》;6.《第廿五代付法藏人圣者舍那波斯抄》。按:除《灵州史和尚因缘记》《佛图澄罗汉和尚赞》《罗什法师赞》外,均出自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中印度传法世系二十八代之中。
(二)S.6631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背面分抄:1.《归极乐去赞》;2.《四威仪》;3.《卧轮禅师偈》;4.《香赞文》;5.《游五台山赞文》;6.《辞父母赞》;7.《义净三藏赞》;8.释利济《赞》;9.《九想观诗》;10.《和菩萨戒文》;11.《罗什法师赞》;12.《维摩五更转十二时》等。
(三)P.2680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分抄十六种文书,分别为:1.《唯识论师世亲菩萨本生缘》、2.《唯识大师无着菩萨本生缘》、3.《寺门首立禅师赞》、4.《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号增忍以节度使李公度尚书立难刺血书经义》、5.《第廿三代付法藏人圣者鹤勒那夜奢》、6.《第廿四代付法藏人圣者师子比丘》、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8.榜书底稿[注]有“佛告目连:汝是天竺辅相之子,其母好食豆,子因而豆也”“妻子寝卧迦叶行道时,迦叶寝卧金色女人行道时”“迦叶往□□□□女庄一会像从黄色□愿□夫妻金色女时”等。按:叙事图像与讲唱变文,在画面或讲唱情节发展的关键,每每有“……时”“……处”等指示套语,藉以提示阅听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高潮。因此敦煌壁画变相往往存有榜题,而敦煌文献中也出现有壁画绘制前置作业的榜题文稿,或称简子目号。参樊锦诗《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华学》9、10合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1-1004页。、9.《大唐义净三藏赞》、10.《佛图澄和尚因缘记》、11.《大唐三藏赞》、12.《罗什法师赞》、13.《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14.《远公和尚缘起》、15.《三威仪》16.《杂写》等十六种文书。背面分抄:名录、便粟历、绢帛历、练绫历、声闻唱道文、转帖、社司转帖、丙申年四月十七日慕容使军请当寺开大般若经付经历、疋段历。按:《第廿三代付法藏人圣者鹤勒那夜奢》、《第廿四代付法藏人圣者师子比丘》出自《付法藏因缘传》印度传法世系二十八代之中。
(四)P.2775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抄:《付法藏传》,背面接抄《付法藏传》外,分别抄有:1.《义净三藏》;2.《大唐义净三藏赞》;3.《白草院史和尚》;4.《刘萨诃和尚》;5.《惠远和尚》;6.《佛图澄》;7.《第十四圣提婆》;8.《第十五罗睺罗》等。
(五)P.3355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抄北魏昙摩流支译《信力入印法门经》卷第二,卷背抄有《十大弟子赞》《付法藏传》等。《十大弟子赞》《阿那律天眼第一》《付法藏传·第七代付法藏人圣者伏陀难提》间夹抄有《弥天释道安第一》《佛图澄圣僧赞》,文字与S.276《佛图澄罗汉和尚赞》大同小异,而无赞末附诗。
(六)P.3490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为财礼凡目、油破历、辛巳年破历等,背面分抄:1.《寺门首立禅师颂》,文末题记:“先天二年(713)十二月廿五日清信弟子张文爽述,比丘智照书”。2.《稠禅师解虎赞》;3.《于当居创造佛剎功德记》文末题记:“于时天成三年岁次戊子九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题记。”4.敬绘文殊、圣贤、万回、观音等愿文四篇,文末题记:“天成三年戊子岁九月十七日题记。”
(七)P.3570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七十》。背面分别抄写:1.《南山宣律和尚赞》;2.《隋净影寺沙门慧远和尚因缘记》;3.《刘萨诃和尚因缘记》;4.《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号增忍以节度使李公度尚书立难刺血书经义》。
(八)P.3727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付法藏传》及其他禅宗史料、沙洲官吏及僧人来往状牒数通。《付法藏传》行间夹抄或接写有十多种文书,分别为1.《内亲从都头之常乐县令罗员定状》;2.《都知兵马使吕富延、阴义进状》;3.《第八梦、第九梦》;4.《国清父母给瓜州吕都知、阴都知状》;5.《沙门道会给瓜州吕都知、阴都知状》;6.《圣者泗州僧伽和尚无念因缘》;7.《寺门首立禅师赞》;8.《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号增忍以节度使李公度尚书立难刺血书经义》;9.《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10.《刘萨诃和尚因缘记》;11.《大唐义净三藏赞》。全卷抄者非一,其中赞与因缘记字体相近,当同一人所抄。
(九)P.4597号。卷子本,正背书。正面分抄:1.《和菩萨戒文》;2.《西方乐赞文》;3.《散华乐赞文》;4.《般舟梵赞文》;5.《香汤赞文》;6.《四威仪赞》;7.《卧轮禅师偈》;8.《受吉祥草偈》;9.《大乘中宗见解要义别行本》;10.《香赞文》;11.《花赞文》;12.《游五台山赞文》;13.《辞父母出家赞文》;14.《义净三藏赞》;15.《罗什法师赞》;16.《唐三藏赞》;17.《稠禅师解虎赞》;18.《菩萨十无尽戒》;19.《金刚五礼文》;20.《五台山赞文并序》;21.《寅朝礼》;22.《九想观诗》;23.《佛母赞》;24.《出家赞文》;25.《菩萨安居息解夏法》;26.《辞道场赞》;27.《请十方贤圣赞》;28.《送师赞》;29.《劝善文》;30.《入布萨堂说偈文》;31.《受水说偈文》;32.《声闻布萨文》;33.《布萨文》;34.《十二光礼法身礼》;35.《破酒历》。
从这些写本汇抄的情形可以推断当是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僧徒实际使用的佛教文书,大抵为佛教寺院法会活动中庄严道场、赞颂高僧之用。根据以上各件写本简要叙录所呈现的抄写状况,其性质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二种:
(一)属画像赞性质之高僧赞
上述九件写本中,S.276、P.2680、P.2775、P.3355、P.3727等五件,都是出现高僧赞、高僧因缘传与《付法藏因缘传》抄写在同一写卷的情况。
高僧赞主要为《佛图澄罗汉和尚赞》《罗什法师赞》《唐三藏赞》《义净三藏法师赞》,其中《罗什法师赞》《义净三藏法师赞》《唐三藏赞》同为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金光明寺僧人所撰,前二赞为释金髻所撰[注]释金髻,俗姓薛,吐蕃时期出家于敦煌金光明寺,后为释门副教授。,后赞为释利济所撰[注]释利济,俗姓姚,吐蕃时期敦煌金光明寺僧人,据S.1520《法门名义集》、BD01046《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下等写卷,知是当时敦煌地区重要的写经僧。。是此写卷出自敦煌金光明寺,极可能为金光明寺佛教活动所使用。
按:《付法藏因缘传》,又作《付法藏传》,或《付法藏经》,历代经录记载不一。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著录云:“《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注]《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见[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岀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2页。)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有《付法藏传》4卷、《付法藏因缘传》4卷[注]《历代三宝记》卷9:“《付法藏传》四卷(见《菩提留支录》)。和平三年昭玄统沙门释昙曜译”。同卷又云:“《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或四卷,因缘广,昙曜自出者)西域沙门吉迦夜延兴二年(472)为沙门统释昙曜于北台重译,刘孝标笔受(见道慧《宋齐录》)”。同书卷10又云:“《付法藏经》六卷(见《李廓录》),凉州沙门宝云译。”。唐道宣《大唐内典录》、智升《开元释教录》著录承袭《历代三宝记》。
《付法藏因缘传》列举从佛灭度时以最胜法咐嘱大迦叶起,至师子止,印度传法世系二十四人,依次为:大迦叶、阿难、摩田提、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弥遮迦、佛陀难提、佛陀蜜多、胁比丘、富那奢、马鸣、比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僧伽难提、僧伽耶舍、鸠摩罗驮、阇夜多、婆修盘陀、摩奴罗、鹤勒那、师子。隋、唐时,天台、禅宗的法统说,均以本传为依据。禅宗要籍敦煌本《六祖坛经》更依《付法藏传》,略加增减,构成二十八祖之说。即在“师子”后加舍那婆斯、优婆崛、僧迦罗、须婆蜜多,下接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六祖惠能。[注]法海问言:“此顿教法传授,从上已来,至今几代?”六祖言:“初传受七佛,释迦摩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弘忍第三十九,惠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见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202-204页。)加上同卷汇抄的还有其他禅宗史料,这除了说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禅宗流行之外,也显示这些高僧赞、高僧因缘传在当时寺院佛活动中被广为运用的具体情形。
再者S.3074《高僧传略》(拟)残存有康僧会、鸠摩罗什、竺道生、法显、佛图澄等部份,内容大抵节录梁慧皎《高僧传》以成篇,其中竺道生部份前题有《宋扬都龙光寺法师竺道生图赞》,鸠摩罗什部份,前题有《罗什法师译经院》,据此推测此盖配合高僧画像节录高僧传文字作为图像解说的赞文﹔由此可见这些高僧赞也是配合高僧图像的说明,极可能是在寺院道场悬挂诸佛、菩萨、历代高僧及祖师画像以供法会礼拜时,由法师进行一一礼拜赞颂。因此可结为一体,书写于画像下,也可抄录以备法师歌咏赞颂之用。
寺院与石窟是佛教僧徒日常修行、说法及进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等需求而产生的建筑。因此,石窟除了安置佛像,绘制经变画外,也会绘制诸佛、菩萨、历代高僧画像,以供法会礼拜之需,并庄严道场。上举九件中P.2680、P.3355均抄有壁画榜题文字稿,其中P.3355六则榜题子目旁分别标有“托经”“拄杖”“念珠”“香炉”“托意仗”“啮枝”等画像人物形象的标志特征。无疑是高僧壁画、图像绘制的明证。从写本榜题文字稿与高僧赞、高僧因缘传、乃至高僧传略抄合抄的情形,又说明了高僧壁画、图像与高僧赞的密切关系,既可独立阅读,又能依据法会活动的实际需求结合使用。又P.2971“壁画榜题底稿”性质相同,其中部分圣者或高僧名字旁后加有画像特征的标示,也可供作有力的佐证。
P.2971
录文:
东壁第一须菩提(把香铃无弟子)、第二富楼那(把经无弟子)、第三摩诃迦旃延(把如意□有弟子)、第四阿那律(坐□床无弟子)、第五优波梨(把杨枝于瓶无弟子)、第六罗侯罗、第七阇夜多、第八婆修盘陁、第九摩奴罗、第十鹤勒那夜奢、第十一师子比丘、第十二达摩祖师、第十三惠可禅师、第十四璨禅师、第十五信大师、第十六弘忍禅师、第十七能大师、第十八无着菩萨(无弟子)、第十九世亲菩萨(无弟子)、第二十罗什法师(写经无弟子)、第二十一佛图澄、第二十二刘萨诃、第二十三惠远和尚。
敦煌写本《高僧传》与将写真肖像与撰写赞文相结合,藉以供作后世子孙缅怀先人之用的《邈真赞》[注]邈真赞,又称“真赞”“写真赞”“真仪赞”“图真赞”“邈影赞”“邈生赞”,是依托画像以阐述主人公生平行迹的赞体。时贤整理得92篇,参见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同样配有图像。这应是承袭中国传统画像赞发展而来。只是唐代《邈真赞》是运用于丧葬文化中的赞体,对象为当代往生者,有僧人,有俗人。《高僧传》则用于寺院道场法会仪式之间,赞颂对象为历代高僧或寺院的祖师。基于此一功能特性,“高僧赞”的内容表现,基本上沿续着刘彦和《文心雕龙》《颂赞篇》所指出应用性文体功能的轨辙:“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简单交代人物生平之时,注重轮廓性的赞美夸誉,其文本内容主要呈现褒赞称美平生的要旨,以简笔勾勒来彰显仪容,并细选行事,以抒写性情,因此显示出较强的纪传功能指向。
(二)属法会仪轨之高僧赞
又九件中,S.6631与P.4597二件,基本上都是同卷抄录有《义净三藏赞》《罗什法师赞》《唐三藏赞》等高僧赞与《西方乐赞文》《归极乐去赞》《散华乐赞文》《香赞文》《佛母赞》《出家赞文》《游五台山赞文》《辞父母》等佛教歌赞,及《和菩萨戒文》《布萨文》等法会仪式文书。在在说明都是当时寺院法会活动仪式进行过程中僧人实际使用的写本。其中P.4597保存较为全面而完整,S.6631也是同一性质,只是因不同法会,且规模也有大小的差别,仪式程序除必要的套用外,节目自然有所增减改易,以配合实际需求,然无论如何,其性质总归属于法会仪轨使用之佛教赞颂艺文。这种情形就像P.2130《法照和尚因缘传》(拟题)后接抄:《西方道场法事文》(内容包括:《念佛法事次第》《散花乐赞》《宝鸟赞》《回向发愿文》《念佛偈赞》《西方十五愿赞》《十愿赞》《西方念佛赞》《净土乐赞》《西方礼赞偈文》《忏悔文》等)、《佛说观佛三昧海藏经本行品第八》等三部分。除了说明这些写卷文书的使用者盖为敦煌地区佛教僧人或寺院外,且可窥知当与净土五会念佛有关,显为法照门徒持有之写卷,作为净土念佛法会进行时的参考仪轨。[注]参郑阿财《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第59-69页。徐俊也对敦煌佛教赞颂与佛事活动关系有所关注,他说:“敦煌赞颂作品本身的内容、形式、作者、时代及流传情况等都比较复杂,就功用和流传方式而言,赞颂与宗教仪轨如礼忏、布萨、宣讲、化缘、劝俗等佛事活动有关,幷由此而在广大僧俗民众中间流传,与敦煌佛教的消长和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见《敦煌佛教赞颂写本叙录——法藏部分六种》,《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9页。)
从功能性来看,赞颂文学最初以“佛赞”为主,之后发展乃有“僧赞”的出现;若从佛传文学的视角来考察,先是作为赞颂的“佛赞”“佛弟子赞”,之后才发展到兼具赞颂与弘传的“僧赞”,进而扩展出具弘传性质的高僧“因缘记”一类僧传文学。
“高僧赞”赞颂的对象、“高僧传”记叙的传主与高僧“因缘记”记叙的主人翁,同为高僧,其内容多涉高僧的行迹,“高僧赞”,多采五言、七言或四言的韵文形式以赞扬高僧或祖师之功德,篇幅简短,概括典范性强;“高僧传”多以散文体记叙人物生平事迹,以表彰高僧在弘扬佛法过程中的行迹,塑造高僧德行高远、法力深厚,强调佛教史地位与评价为主体,篇幅较长,具史传性、全面性、史料性强;“因缘记”多以散文、偶有骈文,讲究文采,篇幅短小,具传奇性书面性强。所以“高僧传”“高僧传略”“高僧因缘记”“高僧赞”可说是同质而分用。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唐开成五年五月五日五台山竹林寺斋礼佛式述:
阁院铺严道场,供养七十二贤圣……便赴请入道场,看礼念佛法事。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宝幡、宝珠,尽世妙彩张施铺列,杂色毡毯敷洽地上。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贤圣。黄昏之后,大僧集会。一僧登礼座,先打蠡钹,次说法事之兴由。一一唱举供主名及施物色。为施主念佛菩萨。次奉请七十二贤圣,一一称名……其奉请及赞文,写取在别。[注][日]释圆仁原著,[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2-273页。
圆仁所见唐代五台山竹林寺诸斋礼佛式中提及堂中傍壁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后奉请贤圣、唱赞贤圣,奉请七十二贤圣,之奉请及赞文,写取在别。敦煌写本P.4597、S.6631二件,会抄《义净三藏赞》《罗什法师赞》《唐三藏赞》等高僧赞与《西方乐赞文》《归极乐去赞》《散华乐赞文》《香赞文》《佛母赞》《出家赞文》《游五台山赞文》《辞父母》等佛教歌赞,及《和菩萨戒文》《布萨文》等法会仪式文书,正是唐代敦煌寺院斋礼佛式文书实物的遗存,相互印证,此类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也得以了然。
四、敦煌高僧赞与高僧因缘记等文本性析论
所谓“文本”,盖指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实体,是具有完整、系统的篇章。“文本性”除依托文本所表达的意涵外,还包括不同文类与具体文本间互文或差异所所呈现的关联性意义。[注]参陆扬《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专号导言》,荣新江主编《唐研究》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页。本人在研究敦煌文献与俗文学时,对此也多所留意,更有感于佛教文学乃佛教弘法布教的主要媒体,不同体类,每每因传播的主体、环境、对象的不同,为求效果,而选择适当的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同一内容题材,在不同的体类也会因不同的功能需求、不同的传播形式、传播对象而有所取舍、变衍。[注]参郑阿财《史语所藏〈鹦哥宝卷〉研究——兼论同一题材在各类俗文学的运用》。2006年12月“俗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主办。
近年有鉴于高僧传乃至敦煌写本高僧传略、高僧因缘传、高僧赞等各类僧传文学,盖同属佛教传记文学的范畴。这些文本虽然在文体上有散文与韵文的不同,在文类上也有史传与颂赞的差别,且内容各有侧重,功能也不尽相同,然其本质却同归僧人传记文学。同一高僧每每出现在高僧传、高僧因缘记、高僧赞等不同的文学体类。历代高僧作为佛教典范人物,除了为高僧传所记述外,高僧的事迹也往往被用来作为道场、法会讲唱的题材;也有图写高僧形象庄严道场时,以赞来颂扬高僧,因此高僧因缘记、高僧赞的出现也是极其自然的现象。不过其间存在的文本性相当鲜明而凸出,无疑是中国佛教传记文学中值得关注的议题。以下谨以两晋南北朝佛教东传关键阶段极具影响力的高僧佛图澄为例,尝试析论敦煌高僧赞与高僧因缘记等文本性。佛图澄,西域人。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佛教高僧辈出,很多高僧从西域、印度来中土,他们讲经说法,教授弟子,翻译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兴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佛图澄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除了深入经藏,深明佛理,又擅长方技咒语,弟子众多,如僧朗、首尼、道安等,都是当时中国佛教重要的弘教人才,影响深远。
佛图澄入东土传法时,适值五胡乱华之世,化导后赵二石,泽润苍生,流名千古,垂范后世。有关他的事迹在中国佛教史上深受瞩目,尤其是他展现诸多神通教化世人权巧方便的种种行迹,使其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受称道的神异高僧。梁慧皎《高僧传》将当时在佛教传播与实践具重要表现的高僧,分别立传。分作“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神异传”主要记叙高僧的神通事迹,《佛图澄传》即被安置在“神异传”的第一传。
佛教最初弘传时期传播的手法往往取决于所处的环境与遭遇。神通为佛教宣传取信于人的方便手法,也是六朝神异之谈盛行的原因之一。因此,梁慧皎在《高僧传》“神异”下肯定了佛图澄显神通的意义与贡献,说:
论曰: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至若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石参烟,则力士潜伏。当知至治无心,刚柔在化。自晋惠失政,怀愍播迁。中州寇荡,群羯乱交。渊曜篡虐于前,勒虎潜凶于后;郡国分崩,遭屠炭。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骋悬记于襄邺。藉秘呪而济将尽,拟香气而拔临危;瞻铃映掌,坐定吉凶。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萠,固无以校也。[注][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8页。
慧皎这段说明,既彰显佛图澄的神通为当时僧俗大众所喜闻乐道;同时也据以作为僧人神异事迹立传之张本。
高僧因缘传又作高僧因缘记,为佛教叙述因缘的散文体传记文学作品[注]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因缘记”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3-524页。。所谓“因缘”本是佛家观念里“因”和“缘”的合称,是佛教用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它们生起变化现象的用语,所谓“因缘和合,诸法即生”。佛家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因果联系、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之中;众生皆在善恶因果的严密关系中,只有皈依佛法,虔诚修持,才能脱离苦海,获得解脱。敦煌说唱文学中的因缘,就是讲述佛弟子或善男信女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故事。
佛教原始经典十二分教,其中第十为“因缘”Nidana,音译为“尼陀那”。是佛说经、律的事缘,《大毘婆沙论》卷126:“因缘云何?谓诸经中,遇诸因缘而有所说,如义品等种种因缘。如毘奈耶作如是说;由善财子等最初犯罪,是故世尊集苾刍僧,制立学处。”因缘是各佛法的缘起,有如诸经之序。可从律和经两方面来说。在律的方面以制律因缘为主,如善财子因初犯戒而制立学处,可知戒律是随着违犯而制定的。在经方面则是叙述引起说法的因缘,如义足经先叙因缘——佛化作一苾刍,向佛请问,而后由世尊答说。小部经和本生经有序偈和交待各种因缘。因缘记一般篇幅短小,有的直接撷取《高僧传》以成篇,书面性强,讲究文采;有的以骈文写成,且多具故事情节与传奇色彩。显然与当时寺院的说因缘之风密不可分,是寺院用以配合俗讲而使用的佛教文学。敦煌文献中保存有S.1625、P.2680等《佛图澄和尚因缘记》,以下谨将《因缘记》与《高僧传》对照表列,并略加说明:

《佛图澄和尚因缘记》《高僧传·佛图澄传》佛图澄者,中天竺国人也。幼年入道,而求出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诵此土儒史,论辩而无疑滞。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若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鬼神,以麻油涂掌,千里事彻见由掌中,如对面焉。又听铃音,便知万事。志弘大法。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劾验。石勒、石虎尊之甚重,虎诏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位不受,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绵,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澄身长八尺,风姿详雅,妙解深经,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大德诣澄讲说矣。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圆四五寸,通彻腹内,或时肠从中出,辄以絮塞之。夜欲诵书,拔去其絮,则一室洞明。又于斋日至水边引肠洗之,已洗还内。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肠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长八尺,风姿详雅。妙解深经,傍通世论。澄死之日,有人见在流沙南行。中天竺国人闻知,不信,遂开棺验之,全不见尸矣。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见在流沙,虎疑不死,开棺不见尸。
从上表对照可知《因缘记》的内容可说完全剪裁自《高僧传》。慧皎《高僧传》是佛教的史传,其本质是佛教的历史,编者与编纂的目的乃基于佛教,其内容与取材自当本于佛教传播的视角出发,因此《高僧传·佛图澄传》,篇幅长达5000多字。
《佛图澄和尚因缘记》叙述的重点有:幼年出家,善解文义、论辩无疑滞、具备预知之神通、深受石勒、石虎的尊崇、异于常人(乳旁有孔)、开棺不见尸等,篇幅短小,极具概括性。其中,有关佛图澄显神通的记述则有:善诵神咒、能役鬼神、掌中见事、听铃知事、腹中洞明、水边洗肠、开棺不见尸等。内容、文字大抵取自《高僧传》,或摘录,或裁剪;有些片段甚至一字不差地抄录搬用。
同样佛图澄的事迹也见载于《晋书》。《晋书》为是正史,系官修的史书,其出发点与视角当然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编纂。相对而言,宗教性应该较淡,而历史性较强。二者自是有同有异。唐房玄龄等撰的《晋书》也有《佛图澄传》。一为僧传,一为史传,专博有别,撰写立场不同,因此内容多有详略、异同。《高僧传》具僧传的文体性质,对于神通事迹的叙事,叙述神通事迹时,力求叙事的主体能具真实感,故多清楚交代事件发生的人时地,带有可稽考之史学性也是其特色之一。
《晋书》为史书,其人物传记的叙事无论文本结构,或叙述的语气口吻、观点立场,基本多具历史视角。其编撰年代后于《高僧传》,记述佛图澄事迹,当多参阅《高僧传·佛图澄传》;只是二者编撰目的有所不同,内容各有所重。慧皎为高僧立传,应是真实记载高僧生平、事迹[注]《高僧传·序录》:“(前之作者)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逮乎实时,亦继有作者。然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辞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第524页。。房玄龄等编撰官修的《晋书》以政治史事为核心,除求纪实外,有些编撰者好采诡谬碎事,且广纳异闻[注]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从贞观十八年(644)开始,至贞观二十年(646)完成,距慧皎(497-554)逝世已约90年之久。《旧唐书·房玄龄传》云:“《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然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43页。。因此,自然也就有所差异。如佛图澄于永嘉四年(310)到洛阳弘法,未投石勒大将军郭黑略前的情节,《高僧传》中叙述得比较详细。另有部分内容如佛图澄欲于洛阳立寺未果、佛图澄谏石勒、襄国人薛合二子恼怒鲜卑奴、石斌欲僭位事、佛图澄劝谏石勒毋杀生、游民麻襦预石虎之死等情节,则是《晋书·佛图澄传》所未见。
赞颂与记述的对象同为西晋来华传教以神异见称的名僧佛图澄,篇幅短小的《佛图澄罗汉和尚赞》与《佛图澄和尚因缘记》,文类不同,一为赞颂,一为因缘﹔文体有异,一为韵文,一为散文。然终究为相同文本,其间存着差异与互文的文本关系,以下特将二者对照表列,标示其内容故事情节异同如下:

《佛图澄罗汉和尚赞》《佛图澄和尚因缘记》异哉释种,作用难量,洞兴旨奥,默识否臧。以油涂掌,探腹洗肠;尽还谋塞,夜抽出光;自在生死,示现无常;葬石而起,后赵知亡。载《高僧传》,后代腾芳。又诗曰:权实应无方,临流每洗[肠];腹[孔]明照室,掌里现兴亡。示灭无□□,名常则不常;世人思贱迹,犹想觉花香。佛图澄者,中天竺国人也。幼年入道,而求出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诵此土儒史,论辩而无疑滞。若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鬼神,以麻油涂掌,千里事彻见由掌中,如对面焉。又听铃音,便知万事。石勒、石虎尊之甚重,虎诏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位不受,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澄身长八尺,风姿详雅,妙解深经,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大德诣澄讲说矣。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圆四五寸,通彻腹内,或时肠从出,辄以絮塞之。夜欲诵书,拔去其絮,则一室洞明。又于斋日至水边,引肠洗之,已洗还内。澄死之日,有人见在流沙南行。中天竺国人闻知,不信,遂开棺验之,全不见尸矣。
《佛图澄罗汉和尚赞》为韵文,计96字,含四言赞体14句56字,及五言诗8句40字;《佛图澄和尚因缘记》为散文,计250字。由于二者同样是穿插于法会活动中使用,所以篇幅均较为简短,而赞体为画像赞,图赞一体,篇幅自然尤短。尽管篇幅短小,然对所赞颂的对象与记述的人物事迹仍极具概括性。赞为唱诵,因缘记为讲说,所以韵散有别。又二者虽均属法会活动仪式中所运用,然其功能与属性各有所主,各有所重,因此,出现同题异文的作品乃极自然的现象。
虽然《赞》《因缘记》乃至《高僧传·佛图澄传》均以佛图澄神异事迹的为叙事核心,然《赞》属唱诵高僧的赞体,《因缘记》为可阅读兼供讲唱的纲要文本。《赞》不求情节的完整,侧重整体印象,故人物刻画较为概括;《因缘记》则故事情节叙述面向相对较为完整,以利提示,方便讲说者之铺陈演绎。至于《高僧传》的记述因篇幅较长,叙述力求完整而详尽,且对相关情节的因果始末多所诠释,展现了佛教历史传记的本质与特色。
六、结语
高僧传记是结合佛教、历史与文学三方面元素,将高僧个人的宗教历程,提供后世信众学习的修行典范。然而,作者运用史料裁剪与改写,积极建构高僧的典范与形象,史传的编撰往往承载著作为僧史身份的宗教使命。
佛教的弘传,人物事迹的宣扬与讲说最为主体。其人物自是三宝中的佛、僧,从核心的教主佛陀,到佛弟子、佛菩萨、众多的罗汉;乃至更为接近现世信众的高僧,其生平事迹从出家、学佛、证道、传法,其间故事性、传奇性、神异性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手法。
高僧传、高僧赞、高僧因缘传的主体人物都是高僧。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端赖其在戒、定、慧三学的实践,可为信众修学的典范;因此,佛教寺院或法会之中每有绘制高僧图像以供瞻仰,并收庄严道场之效。或于法会唱导活动之中,用以广为宣说,藉此彰显高僧的德行懿范。高僧赞、高僧因缘记,主要记叙高僧的事迹,内容虽与《高僧传》《续高僧传》相似,也有直接撷取或改编《高僧传》以成篇,主要均以凸显高僧典范与神异事迹为主,相同的文本,不同的文类与文体,呈现差异与互文的文本性。敦煌地区僧人抄录此类文献,具壁画榜题与图像赞之功能,又为法事仪轨与宣讲颂赞之提示与参考之用。
汉代开始佛教随着印度及西域高僧的弘传,佛教快速的发展,晋唐胡汉高僧倍出,在中国史传传统的影响下,记述高僧大德行迹典范的僧传应运而生,《名僧传》《高僧传》一类僧人传记著作一时蜂出。有唐一代,纪传人物赞与图像赞的发展下,高僧因缘传与高僧赞是另一形式与不同用途的僧传文学。
赞颂文学最初以“佛赞”为主,之后发展乃有“僧赞”的出现;若从佛传文学的视角来考察,先是作为赞颂的“佛赞”“佛弟子赞”,之后才发展到兼具赞颂与弘传的“僧赞”,进而扩展出具弘传性质的高僧”因缘记”一类僧传文学。“高僧赞”赞颂的对象、“高僧传”记叙的传主与高僧“因缘记”记叙的主人翁,同为高僧,其内容多涉高僧的行迹,与高僧传文本关系密切。就文体论,“高僧赞”为韵文体,多采五言、七言或四言的韵文形式,以赞扬高僧或祖师之功德,篇幅简短,概括典范性强;“高僧传”为散文体,其记叙人物生平事迹,以表彰高僧在弘扬佛法过程中的行迹,塑造高僧德行高远、法力深厚,强调佛教史地位与评价为主体,篇幅较长,具史传性、全面性、史料性强;“因缘记”以散文体为主,偶有骈文,讲究文采,篇幅短小,具传奇性,书面性强。“高僧赞”“高僧因缘记”可以说是佛教传记文学的特殊成员,“高僧赞”“高僧因缘记”与“高僧传”相同的文本,具强烈的文本性,三者同质而分用。既丰富了中国僧传文学的多元性,也展示了僧传文学发展上,形式、体裁的特色及其在寺院法会仪轨的运用与功能,极具佛教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价值。
附记:交稿前获睹日本京都大学新刊《敦煌写本硏究年报》第12号,内有杨明璋《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抄及其用途》[注][日]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硏究年报》第12号,2018年,第27-44页。一文,此文检视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抄,关注高僧赞与其他佛教文书合抄的情形,藉以探讨写本性质及其用途,部份论述与个人此文有异曲同工,相互辉映之妙,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