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那个让世界理解中国的“老外”
2018-10-30张健
张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变化非常了不起……有的美国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也有人很担心这种超越,但不管是哪一种人,他们都开始关注中国”
1979年1月,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里,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酒会正在举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于现场发表演讲,距离他不远处,站着一位斯斯文文的美国学者,正安静地聆听他的发言。这人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在傅高义的生命里,这是在物理空间上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当时的傅高义肯定不会想到,在21年之后,他会因缘巧合,投身到一项浩繁的写作当中,这场写作会花掉他10多年的时间,而书写的对象,就是此刻站在他面前演讲的邓小平。

“中国先生”
说起来,傅高义与中国结缘,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费正清曾于二战前,在清华大学短暂地学习了一年中文,回到美国之后,费正清主张美国大学要培养出更多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傅高义是费正清亲自物色并着力培养的学者之一。在1961年至1964年的三年间,傅高义被要求集中学习中国历史。而实际上,傅高义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一些传统的中国小说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似乎
更感兴趣。
傅高义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3年,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一两次。除了身临其境,傅高义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很多途径,比如哈佛大学有不少中国人,包括中国学生与访问学者,这些人都成为傅高义的交流对象,在与他们的聊天中,傅高义不断地“抵近”中国。在中国之外,傅高义对日本也拥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曾出版了《日本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等著作。
2000年,在韩国济州岛,傅高义问他的一位朋友,如果要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的未来发展,应该做点什么?这位朋友告诉他,那就应该认真地研究中国,研究邓小平。那次谈话后不久,傅高义下定决心不辞劳苦,要以70岁的高龄,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
他花掉了10多年时间,终于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2013年年初,《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傅高义表达了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他写道:“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与‘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在新书发布会的当晚,我作为记者,对傅高义做了一次采访。那次采访是在傅高义下榻的宾馆房间,邻近北京三联书店。当我们推门而入的时候,一个瘦小的美国老头从沙发上起身迎接。他西装革履,面容清瘦,头发已经花白。他的眼睛很小,脸廓狭长而线条分明。他用流利的中文与我们打招呼,声音很轻,语调
舒缓。

那次訪谈之前,我其实并不了解傅高义,而且我猜测,国内熟悉他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但是没有谁会想到,这位美国老头会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出版而在中国变得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为哈佛大学鼎鼎有名的“中国先生”。他在北京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面对听众与学者潇洒陈词,在高校的礼堂里与教授及学生谈笑风生,在飞来飞去的间隙里,接受一家又一家媒体的邀约采访……如果你仔细阅读那本砖头似的《邓小平时代》,你可能会产生与我一样的感觉:傅高义是实至名归,他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与处世方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风俗、民情,显得如此富有心得。
傅高义谈吐严谨,常常会在交谈中停下来思索,这个时候的他,两只手习惯不停地搓动。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变化非常了不起,只用了32年时间,就超越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速度举世罕见。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国会在未来不久,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有的美国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也有人很担心这种超越,但不管是哪一种人,他们都开始关注中国。”
这种巨大变化,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傅高义谈到,当下的美国学者,对中国启动的这场改革、对于启动这场改革的领导者,认识有些不足。这也是傅高义写作《邓小平时代》的一个缘由,他想告诉美国读者:需要重新认识邓小平。傅高义评价说:“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坚定地搞改革开放,没有前路可循,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实验一边推进,这是需要胆略的。中国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展现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
在写作之初,傅高义翻阅了不少别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书。但到后来,他感到,历史事件容易梳理,而了解邓小平的想法却最为困难,因为邓小平没有留下日记,傅高义又无缘与他当面交谈,所以一切只能依靠间接的材料与采访。《邓小平年谱》的出版,曾给傅高义的写作带来不少方便,但也仅限于帮助他了解到,邓小平在某个时间做了什么事情。至于邓小平为什么那么做,当时的考虑是什么,他却不容易搞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以后,70多岁的傅高义开始频频奔波于中国大地。他去过邓小平留下了足迹的很多地方,包括四川广安、江西瑞金、太行山,还多次奔赴成都与重庆——那里是邓小平任西南局领导人时的办公场所。每到一个地方,傅高义都尽量去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从中找寻过往年代的气息。他还通过种种渠道,与那些熟悉历史情况的人交谈,这些人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家人、秘书,也包括研究历史的学者。10年来,受访者粗略估计有300多位,这个名单里还有李光耀等中外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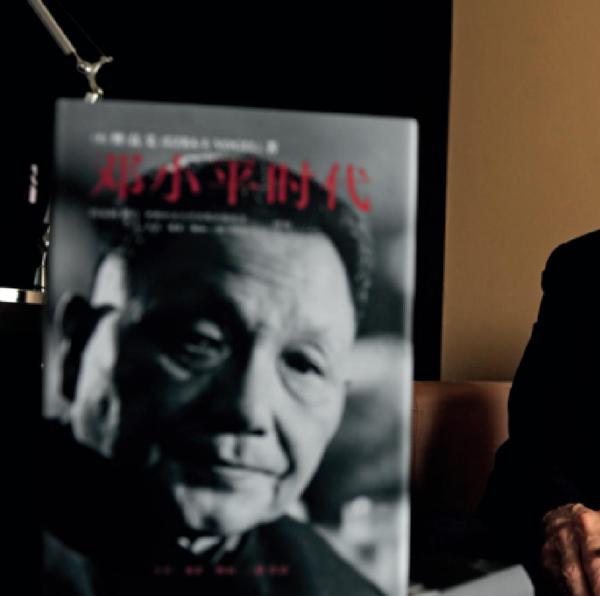
有时候,被采访者会言说各异,但这正是令傅高义着迷的地方,他会兼收并蓄,然后自己慢慢去揣摩产生差异的原因。写作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他不断地发现新课题,反过来又促使他去了解更多的人。比如,在开始写作的一两年,他发现陈云对于邓小平的作用很重大,他们有着奇妙的互补关系。于是,傅高义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研究陈云,阅读关于陈云的资料,并且采访了他的秘书朱佳木。这本书虽然命名为《邓小平时代》,但傅高义要写的远远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傅高义要展示给读者的是,19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
那是一次将近3个小时的访谈,傅高义坦诚,平易,充满学者风范,说话也不艰涩难懂。他对“邓小平时代”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因此一旦话题进入到他的研究领域,就尤其显得健谈。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满足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因而主动地设置话题,以便于阐述自己的看法。临结束时,傅高义意犹未尽:“那就最后再问两个问题?”——然后,他却一口气回答了我们五六个问题。
再一次见到傅高义,是在那次采访的一年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云集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优秀的专家学者,可谓星光熠熠,高朋满座。在开幕式之后,傅高义作为最先发言的专家,登上了演讲台。那一天的傅高义西装革履,步伐矫健,比一年前在宾馆接受采访时,更显得神采奕奕。他脱稿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言辞依旧谦谨,却充满智慧,既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祝福,也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他还谈到,从古典中国到当代中国,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转向,也代表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我们外国学者,基本的工作、基本的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我们应该用我们能用的努力,跟很多的学者一起向中国学习。”傅高义表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难免会有误会和错读,暂时也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长期的方向是好的。他说:“我们的交流有好处,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太多了,但是没有基本的互相了解就没办法解决。我觉得外国学者在中国也好,中国学者在外国也好,都有责任去实现这个梦。”
了解这个时代的中国
最近一次采访傅高义,是在北京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一次聊了更多生活中的事情。生活中的傅高义十分珍爱他的家人与朋友,他认为自己最为享受的事情,就是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以及与老同学们聊天。除此之外,他的时间依然给予了工作。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退休以后,除了每周几次的骑行锻炼,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邓小平的研究中。他的太太埋怨说,傅高义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退而不休,对家务从来不搭不理。说到这里,傅高义的脸上涌起了幸福的笑容——他并不为这种埋怨而感到烦恼,反倒似乎自得其乐。
从交谈中,基本上可以判断,傅高义属于那类比较传统的学者,他并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新理论与新概念,也比较反感过于琐碎地开展学术研究。他所秉持的研究方法,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讲究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山川地理等各个因素切入,逐步地接近研究对象。这也是他所强调的“全面的眼光”“对历史背景与时代氛围的充分了解”。正因为如此,傅高义的写作并不过分依赖纸上的材料,而是倚重实地的采访与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研究方式使他的写作充满了艰辛,因为他得满世界去寻找那些可以为他提供有效信息的交谈者,但同时又充满了收获,因为他总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捕捉到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

“对于这本《邓小平时代》,您心中的第一读者是什么人?”我问他。
“我心中的第一读者,是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美国普通老百姓。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当时跟我一起念书的小镇上的同学,后来大多并没有成为专家,也没有成为知识分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有兴趣来阅读我的书,并且喜欢它。因此,我不大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也不想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太复杂,因为我必须保证如我小镇同学一样的读者能够读懂这本书。我曾经把《邓小平时代》拿给我的那些同学们看,他们读了以后告诉我:‘你写得太精彩了!这样的反馈令我感到非常幸福。我自信比其他的大学教授更为了解美国社会的底层,如果他们不乐意为这些底层人士写一点东西,那么,我却非常
乐意。”
《邓小平时代》在美国出版以后,傅高义说,社会评论方面,90%以上都是积极的评价,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而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至于一些美国的中国学专家,他们之中既有人对这本书并不“感冒”,也有人真诚地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2012 年,《邓小平时代》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这个奖专门授予那些以英文写作的非虚构类著作。在颁奖典礼上,携《论中国》参与角逐的基辛格博士对傅高义说:“你赢得这个奖是对的,你写这本书不容易。祝贺你!”
无疑,傅高义对他的《邓小平时代》十分看重。他说,哈佛大学同年出版的100多本书中,《邓小平时代》在销售业绩方面是表现最突出的。按照傅高义所言,这本书本来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但事实上却让他在中国变得知名。谈到这里,傅高义笑了起来:“有更多中国读者喜欢我的书,我当然更高兴了!”
《邓小平时代》因为涵盖了丰富的中外資料与研究成果,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探究与评论,被认为是国外邓小平研究的重要著作。除了摘得莱昂内尔·盖尔伯奖之外,2013年,在上海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傅高义又被授予了“世界中国学贡
献奖”。
对于这本书,傅高义坦承:“我的看法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以后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我将要不断修订与补充这本书。我的一个愿望是,几十年后,那时的人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改革时代,了解这个时代的中国,他们会觉得读我的书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就是“中国先生”傅高义的中国雄心,他对于中国的求索与书写显然不会停止,他与中国的缘分仿佛是一条汩汩溪流,将随着漫长的时间一起流淌。
来源:2018年09月0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