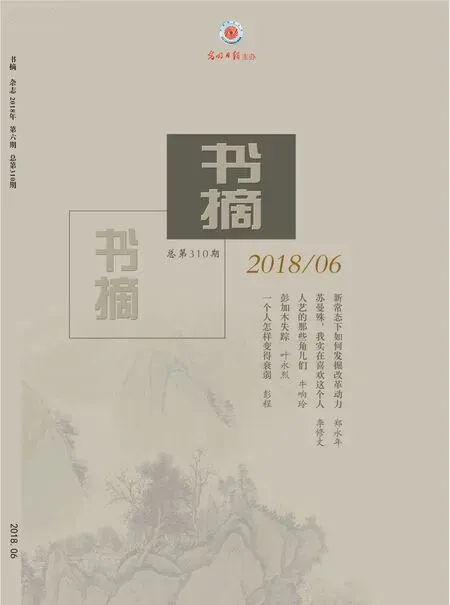书话二则
2018-10-25周振鹤
☉周振鹤
一册只有四页的书
其实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份价目表,但它恐怕比一般的书更为难得。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但在洋务运动中起了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在翻译西书方面也远远走在前头。以傅兰雅为主的洋人和以徐寿、华蘅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科技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方面早已有人做过全面介绍,毋庸词费。
宣统元年(1909),曾有人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译西书写了内容提要,并予以出版。这部名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西书提要》的书在较大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它让我们得以了解那些西书的基本内容,从而理解当时国人最迫切需要懂得的是哪些知识。但对于那些中译西书的实际流通情况,我们就知道得有限,而这一点对于那些书在当时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面前这册只有四页的《翻译各种西书价目单》,在这方面或许可为我们提供点信息。这份价目单共列出了五十四种翻译书的售价,并且还附有翻刻其他十五种书籍的价目。当时出版的书籍篇幅是以卷计算的,但售书的价目单上却是以本或部计价。譬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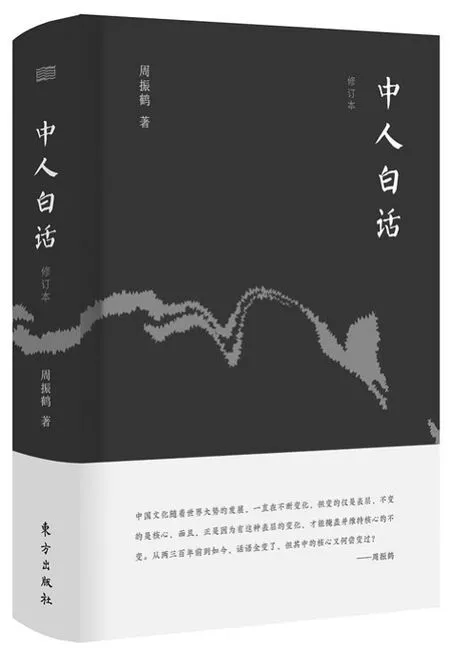
《制火药法》一本,价二百八十文,《开煤要法》(贰本)每部四百文,《测地绘图》(肆本)每部一千文,等等。五十四种书平均看下来,每本在二百文上下,多不过三百文出头,少不低于一百七十文。最贵的一部书是《水师章程》,有十六本之多,售价达三千二百文。书的价钱不但与篇幅大小直接相关,自然也与纸张好坏有关,上述价钱是指连史纸本,如果是以赛连纸印刷,则以上述价格的八折计。
这个价目单未标年份,很难确知是什么年代的标价。只有两条线索:一是《西艺知新》在本价目单中注明“现成十卷,尚有续刻”,而在上述《提要》中该书已有续编十二卷,显见《价目单》要比《提要》早出好一段时间,至迟是光绪年间所印。第二条线索是《西国近事汇编》在价目单上共出了癸、甲、乙、丙四种,而该书是和今天期刊相类似的连续出版物,从同治癸酉年起至光绪己亥年止(1873—1899)。这个期间含有癸甲乙丙的年头有癸酉、甲戌、乙亥、丙子(1873—1876),癸未、甲申、乙酉、丙戌(1883—1886),及癸巳、甲午、乙未、丙申(1893—1896)三组,但既然价目单上对年份只标天干,而不标地支,则很可能是第一组期间所出版的,否则会与其他年代相混淆。所以价目单很可能是1876年以后不久所印。
我们关心的主要还不在于《价目单》的印刷年代,而是要依据这个年代弄清当时一百文钱能买多少东西,看看书价到底贵不贵。但手头没有1876年的物价材料,难于直接对比。顷阅清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有几个物价数据可作参考。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二十一日,记山西太原当时因受旱灾影响,粮价上涨,白面每斤六十文。同年十月二日记,“即以麦较,去年每斗六百文有零,此时每斗一千三百文有零”。翌年五月八日记其途遇一教书人,“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脩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
以这几项数据和上述《价目单》相较,则其时书价不菲。一个教书匠,教学生一人,一年只能有一千六百文的收入,而一部《水师章程》就要三千二百文,哪能买得起?何况这种书与乡下的穷知识分子究竟没有什么关系,不大会有人去买它的。
但是,一斤白面在涨价时卖到六十文,则便宜时按麦价之涨幅推测只得三十文,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译西书平均每本只得三四斤或五六斤白面价钱,似乎又不能算太贵。如果对城市里稍有余裕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书价是负担得起的,因此推测这些西书在清末科技启蒙方面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末民初到底出了多少小说?
有时我们真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做学问的认真劲。在中国许多智者不为之事,如编索引、做目录之类,日本学者,甚至是大学者都照做不误,然后倒过来,中国学者再援用日本学者的成果,做自己本国的学问。怪不得要引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就以一个不算复杂的问题来说,清末民初到底出了多少小说,我们就一直闹不清楚,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去彻底弄清楚,只能人云亦云数十年。
阿英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估计清末民初的小说有1500种以上,到50年代又修正为1000种出头。据此估计,阿英在其《晚清小说史》中称,清末小说是翻译多于创作,并说翻译小说要占到总数三分之二。但实际上,在阿英所举的千种小说中创作小说有420种,翻译小说有587种,翻译小说虽多于创作小说,然仅占总数的58%,并未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阿英以后的研究者一直祖述其说,从不加以验证,从未对翻译多于创作的估计表示过怀疑。直到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的《翻译文学集》,其序言仍援引阿英之说而不改。事实果真如此吗?经过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等人的穷尽式的研究,不但发现晚清自1840--1911年,共出小说2304种,超过阿英的统计数一倍有余(当然阿英的统计起于1875年,而不是1840年,但1840-1874年的小说数量极少,不影响基本结论),而且其中创作小说1288种,翻译1016种,创作明显多于翻译,推翻了原来的定论。
日本学者这些个数字从何而来呢?一篇篇数出来的。即以20世纪初的四大小说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小说林》)所载小说篇目而言,阿英数出来是46篇,前不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典》算出来是110篇,而樽本他们算出来是133篇。这是对大家都较熟悉的文学期刊进行计算,难度不大,而中日双方已有如许差距。难度稍大的,则只有日本学者的成绩而不见中国学者的努力了。晚清的许多小说是发表在定期刊物上的,而大量的刊物已为时间所湮没,首先就得去发掘它们,然后才能计算其中所刊登的小说数量。因此日本学者在做小说数量统计前,先做了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工作,那就是统计中国到底出了多少定期刊物,然后才能得出上列的小说数目。本来计算小说数量已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目的是根据这数据做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判断。但因为中国没有现成的期刊总数的资料,日本学者不得不从更为基础的工作做起,算出了中国在晚清时的定期刊物有672种。而据我所知,在中国的新闻史著作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尽管这个数字并非不可修正)。至今我们已经出版了够多的新闻史专著,从全国到地区性的都有,但你若想在其中找到某一时期的全国或某地的报刊的具体数量,你一定要大失所望,因为这些新闻史重要的是论而不是史。
以上所说似乎有点长他人志气,但其意并不在灭自己威风,而是希望我们有真正的进步。中国非无做学问的人才,只是心急气浮了些。也许有人要说,统计小说数量这种事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笨功夫罢了,谁不会?可恰恰就是因为这智者不为的事耽误了我们的正确判断,原来晚清并不是翻译小说多于创作小说,而正好是相反,这一来对近代文学史的一些解释就该有点不一样了。钱杏邨(阿英)先生当然是了不得的人物,即使他误认翻译小说多于创作小说,也不失其筚路蓝缕之功。多少珍贵的小说资料由其保存下来,他所写的《晚清小说史》《晚清小说目》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有其重要地位。问题是后人不应躺在他的成就上睡觉,而应该不断有所超越,做出更新更好的成绩。1988年,《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已在一衣带水的彼岸编了出来,但他们并不满足,现在仍在继续修订增补之中,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一事实有点触动,而不要仍旧漠然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