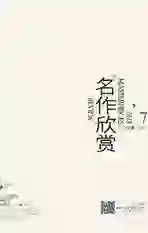“一带一路”背景下《四书》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与影响
2018-10-20孙施昕
孙施昕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四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成为热点问题。17世纪初《四书》传入欧洲后,英国早期自然神论学者以儒家学说为理论依据,抨击启示宗教。此后,英国学者将对《四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大多呈现赞同和批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汉语语言方面,《四书》成了英国学者研究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材料。
关键词:“一带一路” 《四书》 传播
一、早期自由神论中的《四书》
《四书》传入欧洲最早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时期,即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首批进入中国内陆的罗马公教传教士,为了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率先开始翻译拉丁文版本的《四书》用于学习中文。1662年,耶稣会教士郭纳爵和殷铎泽也由于相同的原因合译出版了以《大学》《论语》(前五章)为底本的中拉双语刻本《中国智慧》。殷铎泽在不久后又翻译出版了《中庸》相对应的中拉双语刻本《中国政治伦理》。1687年,柏应理将近年出版的三种《四书》拉丁文译本在巴黎进行重版,结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般英国读者阅读的英文译本《孔子的道德》直到1691年才得到发行。至此,欧洲关于儒家学说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此背景下,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爵士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四书》的杂文。
坦普尔是在1685年的一篇关于园林布置的文章中开始直接提到中国,而在其更久之前的文章里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孔子,却处处有儒家学说的影子。在1671年发表的《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中,坦普尔谈到世界上的政治组织可分为君主政府以及民主政府,二者都来源于家庭组织,是“父权”的直接体现。这与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a的性质十分相近。除此之外,其1683年撰写的《英雄德性论》详细论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府学说,并且在白应理等人的《四书》拉丁文译本的理论支撑下,进一步阐释了“为政在人”的学说。坦普尔论述儒家学说是基于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四书》等典籍资料,难免会受到翻译者的影响,因此,在介绍儒家学说时并没有脱离当时关于《四书》的一般看法,但他的文章更适合普通民众的阅读。
早期欧洲关于中国的论述侧重于政治和道德,17世纪末“中国人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引起了欧洲人的思考,以廷德尔为代表的18世纪英国早期自然神论者开始引用《四书》作为例证阐释英国的宗教问题。廷德尔在其1731年发表的《创世纪以来就有的基督教》中指出:“我并不认为孔子和耶稣基督教的格言有何差异,我甚至认为前者的简单朴素的语录可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的比较晦涩的指示。”b主张运用圣经与儒家学说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要将理性作为处理一切事物的准则,反对神的启示,而儒家学说恰好可以作为他证明自己主要论点的理论依据。廷德尔甚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学说显得更为合理,对圣经的彻底批判导致其有将圣经完全转化为中国式儒家学说经典的趋势。廷德尔广泛地涉猎了中国的书籍,他将中西两大道德体系对比进行道德研究,将儒家学说与耶稣学说提升到同一高度,同时,尝试运用儒家学说批驳圣经中的不合理成分,在批判宗教角度上进行了形式的创新突破,为后继的宗教学批评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范式。
英国政治作家博林布鲁克在长期的政治失意時期,对《四书》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思想也有过深入的思考。在1714年6月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通讯中,他将孔孟的学说分为个人对自己、家庭和国家的责任,与《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谋而合。同时,博林布鲁克也从柏应理等人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以及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寻找佐证中国存在原始宗教的资料。他认为中国存在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信仰自然的规律,顺天而行,用理性引导人性,与之相比,欧洲宗教故弄玄虚的成分占据极大的比例。他以此作为宗教批评的理论根据,挑战圣经的权威性,高扬理性,反对神学。博林布鲁克在廷德尔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中国原始宗教为基础,用自然的道理,即“天道”,驳斥追求神秘主义的神学家,从而达到以理性反抗神学的目的。
博林布鲁克关于儒家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754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影响了欧洲一大批研究儒学的学者。英国诗人蒲柏的《论人篇》体现了明显的自然神论倾向,被认为是根据博林布鲁克的散文稿而写成的。法国启蒙主义的领军人伏尔泰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上,与博林布鲁克立场保持基本一致,认为儒学对“天”和“天道”的信仰是与孔子的道德结合而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同时,18世纪中叶的自然神论倡导者,大多延续廷德尔、博林布鲁克的学术思路,以《四书》展现的儒家学说的理性主义为理论指导,抨击启示宗教,质疑教会存在的价值。在此层面上可以说《四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解放思想、破除教会迷信提供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是欧洲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四书》研究方向的转移
18世纪30年代,法国人杜赫德编辑出版了《中国通志》,英国《君子杂志》的出版人凯夫和当时伦敦的另一出版人瓦茨随之展开了英文译本的翻译工作,并就翻译的准确度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同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为《君子杂志》撰写历史人物和当代名流小传时,也依据《中国通志》为孔子写了一篇小传。这样《论语》就有了主要的三个英文译本。在语言二次转译的过程中,一些重要内容会流失,同时,三位初版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不自觉地增添自己的想法,使得《论语》英语翻译的准确度又下降了一个层次。但是,关于英译版本的争论在客观上也传播了《论语》内涵的思想。在三个版本中,根据翻译的按语对比中文原版,约翰逊的翻译更贴近原义,侧面也体现了约翰逊的哲学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内核有相近之处。他在孔子小传最后总结孔子学说中谈到,孔子整个学说的重点是在于宣扬道德性,并使人性恢复到它原有的完美状态。当然这种说法受到当时法文译本注解者和翻译者的影响。
18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系列假托他国人而创作的信札,最具代表性的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英国诗人哥尔斯密在此文学创作潮流下创作出了《中国人信札》(后更名为《世界公民》)。
哥尔斯密在创作时参考了郭纳爵等人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以及杜赫德的《中国通志》。因此,《中国人信札》中有一部分关于儒家学说的论述。例如第7函中提到:“我们要恪守那中庸之道,既不是无动于衷,也不宜悲伤自损;我们的企图不在灭绝性情,而在节制情性;碰到悲伤故事,不是默然无动,而在使每一灾祸化为有利于己的条件。”c这里的中庸的英文译法正是根据《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d得出的。另外,第33函中举例中国历史上的贤臣明君,为证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提供事实依据,隐喻英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腐化和锈化。除此以外,《中国人信札》中也存在以中国哲学思想抨击教会的观点。例如,书中的中国哲学家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式的人物,哥尔斯密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来发表自己不便直说的对英国宗教的观点。但是,哥尔斯密对儒家学说的看法存在单一、片面和过度赞扬的缺陷,因此儒家学说中落后、保守的部分削弱了对英国社会的批评力度。
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可以称作是英国第一个汉学家。他关于中国哲学思想的论述较为松散、零碎,不成体系,但是在教育学方面,其学说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琼斯在首次阅读《大学》后就写成了论述教育的文章。文章已经失散,存留的《大纲》开篇引用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后文的论述中,琼斯强调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善”,而“至善”是个人推广至全人类的一种博爱精神。为了能够有推而至全人类的善,必须进行知识的普及,提高知识学习的能力。虽然琼斯见到的《四书》材料已经是三四次转译后的材料,对《四书》不可能有透彻的理解,但是对这段话的阐释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琼斯对儒家学说有着个人独特的见解,并且准确地抓住了原作者议论的重点。
之后琼斯对中国的宗教和伦理道德的论述,一方面《四书》的原来含义受到中文到拉丁再到英文转译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偏差,使得琼斯对相当一部分孔孟之道的理解误差较大;另一方面,琼斯开始注重比较东西方思想理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推崇孔子的言论,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异教”的称呼实质上是“狭隘的心胸与粗鄙的态度”e。
三、对《四书》的批评言论
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法国学者的研究,但是与法国学者在18世纪形成对中国文化过度狂热的情况相反,英国学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入了冷却期。在18世纪赞扬、推崇《四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大氛围下,以笛福为代表的另一部分英国学者有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二者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宗教方面。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大多为主教、传教士等教会人士。
正如上文所说,英国早期自然神论者引《四书》为例证阐释、抨击教会,反对者的主要反驳点也集中在此。1737年,佚名撰写的《自然神教的救药》认为,中国人对孔子的推崇是一种偶像崇拜,也就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信仰,从这个角度出发,即使中国人自称不信仰宗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感召。宗教人士对《四书》之类的儒家学说的批评性论述,大多围绕着“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展开。
猛烈抨击中国哲学思想的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其观点充分体现在了《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三部《真诚的感想》中。在书中,笛福借鲁滨逊之口称孔子学说将政治、道德和迷信混为一谈,三者毫无关系,也没有说出有意义的道理。孔子学说使得传教士在中国进展缓慢,异教徒无法领会神启。此外,他还认为17世纪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狂热仅仅是因为发现中国文明化程度高于预期,中国唯一值得称赞的只有瓷器。笛福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大量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蔑视和大量的虚构,然而,笛福为什么要对中国进行彻底的轻视和诋毁,学界并没有定论。
18世纪中叶对中国诽谤程度最高的是1753年至1754年在《君子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的无名氏。中国人推崇龙,当时有将龙指代中国的说法。《新约》中记载了一种十角七头的怪兽是基督的敌人,无名氏提出龙就是这种怪兽,即中国是基督的敌人。在后续的文章中,无名氏更是认为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是邪恶、阴险的豹子,它们蛊惑、麻痹了欧洲人,并且声称许多有学识的人赞同这种说法。虽然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但也从侧面反映对儒家学说代表的中国文化,许多欧洲人还持怀疑的态度。
四、语言著作中的《四书》
出于生活和传教的需要,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选择翻译《四书》来作为学习中文的手段。由此導致《四书》拉丁文译本、英文译本流传到英国后,也长期作为汉语语言学习教材。耶稣会士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翻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汉语学习的一般材料和参考用书。在此基础上,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编写了《汉语札记》的拉丁文本,以《四书》作为阐释汉语基本语法的实例,减少了汉语学习以及用汉语写作的难度,长时间作为欧洲各国的汉语语言教学范本。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士曼也编写了以《四书》作为底本编写的《中国言语》,被选用为伦敦皇家学院的汉学专业教材。该书以中国的文言语法为核心,大量的《四书》原文作为语料,同时也有选择性地摘录了朱熹等人的注疏,以及晚清文人关于《四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汉语的本质,使得汉语更容易被接受,引发英国人学习、研究汉语。同为伦敦会传教士的马礼逊在英国下层读书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华英字典》。这本工具书以《康熙字典》为基础,分为《汉英字典》《五车韵府》《英汉字典》三部分。同时,以《四书》为语料来源,灵活地运用《四书》解释字词含义、阐发相关文化。《华英字典》的普及让英国的普通民众也有机会自学中国文化,增加了两国人民交流的机会。威廉·琼斯爵士在研究汉语语言方面也颇有建树。在欧洲人普遍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的时代,他已经发现汉字其实具有图画性或表意性。同时,也观察到了汉字符号,即偏旁部首,组合形成的新的效果,揭示了汉语书写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自己对印度语言的理解,琼斯还深入考察了汉语中的佛教用语的来源和意义。例如,阿弥陀佛在中国佛教徒的概念里实际上是对佛的称呼,“阿弥陀”意为“无量”,是用来修饰“佛”的。此外,琼斯对《四书》名称的翻译至今是通用的称呼方式。
《四书》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四书》最初以拉丁文译本的形式传入英国,因此在英国学界和上流社会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学者的研究推动英文译本《四书》的出版发行,使得英国的一般读者能够以《四书》为基础材料学习汉字、了解中国文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英国学者的研究角度也从中国的政治、道德,扩展到哲学领域,并且溢美之言和溢恶之言相互争执。这种情况的产生从侧面反映出《四书》代表的儒家学说具有深层的内涵和极强的可读性,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这一点也是现今学者研究对外文化传播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四书》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研究如何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进行沿线国家的中国文化传播。首先, 根据其他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典籍采用中文直接翻译至其他语言的形式,避免由于再译导致的信息误差、遗漏。其次,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注重求同存异,从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思考研究的新角度、新思路。最后,需要认识到《四书》一类的中国典籍不仅可以作为汉语语言学习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其中蕴含着的人文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a 张燕婴译著:《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7页。
bcd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第170页,第201页。
e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 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2] 罗莹.十七、十八世纪“四书”在欧洲的译介与出版[J]. 中国翻译,2012(3).
[3] 陈树千.《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J]. 孔子研究, 2016(1).
[4] 陈满华.威廉·琼斯的汉语研究[J]. 语言研究, 2007(1).
[5] 钱钟书.钱钟书英文文集[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