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外交辞令
2018-10-04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程念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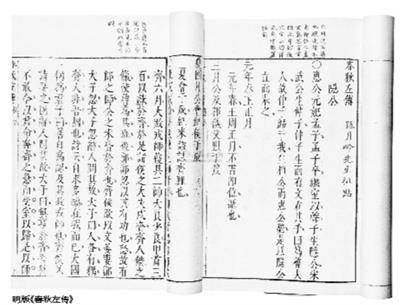
《左传》所记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甚多,充满着机智与雄辩,但总体上却是委婉、含蓄而文质彬彬。尊王的大历史之下,仁义总是要维持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仅是一种风度,也象征着一种力量。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冲突,变得你死我活。列国外交,无非以相互损害和吞并为目的。《左传》上的那种辞气委婉、含蓄而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君子人格与风度,已然遥不可及。
程念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是非常讲究辞令的。
《左传》有烛之武退秦师,事在前630年。其时,晋、秦大军围郑,要灭掉郑国。形势危在旦夕,郑文公就派一个叫烛之武的人去劝秦穆公撤兵。烛之武发牢骚,说自己壮年时都没派上用场,到老了还能有什么用。郑文公连忙道歉,说过去是自己不对,但郑国若亡了,对大家都不利呀。
出了一口怨气,烛之武便连夜去见秦穆公。他对秦穆公说,郑国知道自己要亡,如果这事对秦国有利,哪里还敢来讨饶;问题是秦与郑隔着晋国,何苦这样劳师远征,灭掉郑国,而使晋国受益;不如让郑国成为秦国的东方与国,将来总有机会为秦国效劳;再说当年晋君(重耳)借道秦国,回国争夺君位,事先说好了要用焦、瑕这两个地方来回报秦国的,但早上渡过黄河,傍晚就在那两个地方驻军设防;这样不守信誉、贪得无厌的人,在东侵郑国之后,必然也会向西扩张,觊觎秦国的边疆;这种于秦有害而于晋有利的事该不该干,作为秦国的国君,难道不需要好好掂量掂量吗!
上面这段话,《左传》的原文,真是漂亮极了:“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烛之武会讲话,不仅仅是文辞,道理尤其讲得好!他给秦穆公分析利弊,都是从秦国的角度出发;讲晋国之不可信任,举的也是晋国对秦国不起的例子。讲得头头是道,句句触人心境。他态度谦恭,辞气委婉,说理清晰,分析利弊虽说是从大处着眼,却具体、实在,丝毫也没有先声夺人、强词夺理的味道。
《左传》王孙满对楚子,事在公元前608年。楚子就是楚庄王。他率军北上,讨伐陆浑之戎。陆浑地在秦、晋之间。陆浑之戎,就是被秦、晋强迫迁居此地的戎人。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获胜,军队直抵周的边境,要在洛水边检阅军队,向周定王展示武力。那时候,秦、晋的霸权已衰,楚庄王的霸权正盛,问鼎中原的志气大张。周定王当然不敢怠慢,派了王孙满前去犒劳楚庄王。楚庄王问王孙满,周的“鼎之大小轻重”。鼎是天子权威的象征。夏、商、周易代,鼎亦随之转移。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可见其处心积虑。意思是说,周的天子地位,如今还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是,他问得很巧妙,也就是问鼎有多大多重,人家似乎抓不住什么把柄。
王孙满对楚庄王的无礼提问,当然很气愤。但诸侯争霸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言辞往来,也不是儿戏,分寸必须把握得好。王孙满态度内敛,口气温文尔雅,说:朝代的盛衰,取决于德而不是鼎;夏朝有德,而知天下何善何恶,并铸之于鼎上,使人民知道,入川泽山林就不会遇到魑魅魍魉,所以上下同心,能得到天的庇佑;夏桀失德,鼎就转移到了商,承天命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归之于周;总之,德之美好光明,鼎哪怕很小,谁也拿不去的;如果奸邪失德,鼎就算很大,谁也保不住;而且,德与不德,取决于天命;成王当初定鼎于郏鄏(洛邑),卜辞说周要传三十代、七百年;现在周德固然已不如从前,但天命未绝,还不是问鼎之大小轻重的时候。
这段话,《左传》原文,辞气甚健:“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我们知道,按周的国力,是不能与楚平起平坐的。然而,周在政治上仍有号召力,尊王是当时诸侯交往的通则。楚庄王明里问鼎之大小轻重,暗里是在挑战周在政治上的号召力。王孙满避实就虚,以一句“在德不在鼎”,反过来抓住楚庄王的要害,于是引经据典,借题发挥,雄辩地将“鼎之大小轻重”的问题信手一转,变为对有德无德的讨论。诸侯争霸的世界,政治上必须“尊王”,是当时的大历史,也就是不可移易的“天命”;“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的说辞,正符合当时历史的实际。但是,在回敬楚庄王时,王孙满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态度,不去责问楚庄王提这样的问题是何心肠,只是在讲清楚“在德不在鼎”的道理之后,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一句,轻描淡写地把楚庄王的挑衅化解于无形,没有让楚庄王老羞成怒。
《左传》所记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甚多,充满着机智与雄辩,但总体上却是委婉、含蓄而文质彬彬。尊王的大历史之下,仁义总是要维持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仅是一种风度,也象征着一种力量。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冲突,变得你死我活。列国外交,无非以相互损害和吞并为目的。
《战国策》上说,秦国想得到周鼎,直接派军队去索要。周使颜率就跑到齐国去,说与其把鼎给秦,倒不如给齐;如果齐国肯出兵,可以名利双收。齐国一出兵,秦军果然就退了。齐国于是要周兑现诺言。颜率又对齐王说,鼎有九个,运送需要大量人力,且无论途经魏国还是楚国,都会被扣留;鼎又不像禽兽那样,自己会飞会跑。这样的话,真是一点诚意也没有。齐王认为上了当,颜率却说周是真心想把鼎给齐国,随时等齐国去取。作为周的使者,颜率的确很机智,而且话也讲得滴水不漏,就是缺少诚意。事或出于不得已,毕竟让人不堪。
《战国策》上还说,秦王嬴政想吞并安陵君的土地,说要用五百里换安陵君的五十里。安陵君说,祖上受封于魏国先王,自己不敢见利忘义。他派唐雎去向秦王解释。秦王对唐雎说,韩、魏大国,说灭就灭掉了;安陵君算是长者,自己才愿意以十倍的土地换安陵五十里;但他居然敢不领情。唐雎说,安陵受封于先王,增广百倍,也决不敢换!秦王问唐雎,知道什么叫“天子之怒”吗。唐雎倔犟地说不知道。秦王说,那可是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唐雎问,那你知道什么叫“布衣之怒”吗。秦王说,无非就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嘛。唐雎说,那是“庸夫”,自己说的是“士”;以前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当他们“怀怒未发”,天象已经示警,有“慧星袭月”“白虹贯日”和“苍鹰击于殿上”;而今“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就是自己要步他们的后尘。两人的言辞都咄咄逼人,充满杀气。最后是秦王“色挠”,向唐雎让步。在《战国策》所记载的列国交往中,这样咄咄逼人的言辞,是很普遍的。
战国的大历史,就是喻于利,而不能喻于义。所谓“合纵连横”,无非是出于君王吞并天下之志。所以,一切都不过是“诈”与“力”的体现。诈有诈仁、诈义、诈诚、诈信、诈忠,等等,等等。而所谓“力”,就是强与暴的结合。所以,天下虽多“口辩”之士,《左传》上的那种辞气委婉、含蓄而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君子人格与风度,已然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