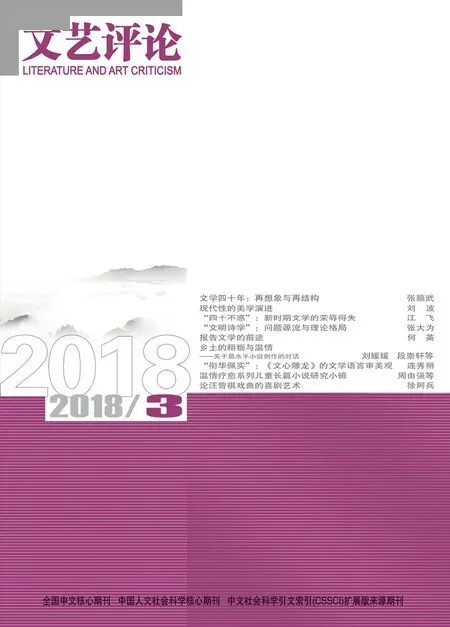乡村归来者与自我认同危机
2018-09-28苏沙丽
○苏沙丽
一、遭遇乡村及身份尴尬
对原乡的书写,不管是建构,还是解构,我以为沈从文的乡土文学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先大略梳理一下他有关湘西的书写。如果说在沈从文早期的写作生涯,也即困守在“窄而霉”是书斋靠回忆来聊以乡愁的慰藉,大多集中于对湘西风物民情的描摹;到接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边城》的写作,他自觉为之的文学世界的构建更为明显,这里面倾注了他对生命现象的倾心,如他所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①。他构筑的湘西世界最重要的价值及意义也就在此。《边城》的写作完成于1934年前,而在这年年初,因母亲生病,沈从文一路舟行南下回湘,这也是他1922年离乡北上后的第一次归来。在这一行程达二十多天的日子里,沈从文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书信,附上图画寄给夫人张兆和,而这些书信的内容及透露出来的情绪、隐忧也在慢慢影响着他日后的创作,尽管在1936年发表的散文集《湘行散记》里依然可见一种书写的明朗,言语间掩饰不住对一种边地性情民风的激赏之义。这之后的1938年,因战乱,学校南迁,在这途中沈从文经过湘西短暂停留,发表未完成的小说《长河》,同一年出版的还有散文集《湘西》。前者正如王德威所说,已构成与《边城》的“双声对话”,那份妥帖于天地之间的自在自为终归是要与现实对峙,变革的异质力量也不由分说地侵入边地山城。后者对边地人的惰性,地方自治的混乱,包括知识者毫无用处的悲悯都一一清算在内,批判与担忧无不彰显。两次回乡,现实力量的介入和重新装置的现代意识终归改写或结束了那些诗意的想象,沈从文的回乡亦是对湘西这一地域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其创作旨归的一次调整,这与他20世纪40年代对生命的抽象抒情及冥思并不能脱开干系,在现实的境遇中沈从文为之努力建造的关于“生命”的世界已然坍塌,来自于自身内部的纷争也就在所难免,自我的精神分裂看似隐晦,其实早已显露裂隙和端倪。
回乡的经历及对创作的影响只是隐遁地存在于沈从文的作品里,而在更多的小说中,知识者往往就以回乡的经历来窥看乡村及自我的角色或身份。这在鲁迅的乡土小说里早已形成了被后来者不断效仿的叙事模式:离开——归来——再离去。这一叙事模式是与作者对乡村的惯常情感相一致的,也是与知识者自身对家园的寻觅与归依及精神处境相照应的。
在早期的乡土文学中,周作人和鲁迅都为乡土文学的发生发展做过理论或实践的贡献,但是二人均极少在文章中直接表达过对乡村的爱恋,乡愁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极为隐晦的情感,于周作人来讲,“乡愁”大概都隐遁到对风物的热爱;对于鲁迅来说,他的性格里像是在压抑这样一种感情,要么是被一种对传统文化及下层人物的悲悯与批判、忧心所替代,要么是被一种知识分子的彷徨无依所掩饰。在他的小说里不止一次写过那种归来时却无家可归的心情,《故乡》自不必说,《祝福》里也是以回乡的模式开始叙事,“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②。《在酒楼上》也是如此,“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③。故乡的凋敝、冷清与作者压抑不悦的心情是相谐和的,故乡风景的暖意不再,或者说陌生化,也直接将归来者置于过客或外来者的境地。
对于大多数乡土作家而言,故乡或许只是停留在年少时的记忆中,当作家们回溯过往时,很多时候也是一味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故乡》中对闰土今昔之间的对比,他对“我”叫的一声“老爷”将一切拉回到现实语境,身份的隔阂,“我是谁”的问题由此衍生。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④
……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⑤
“我”也曾是乡下人,与闰土是幼时的玩伴,那时他的生活是“我”所向往与不知的,而今“我”只是一个乡村的归来者,过客而矣,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外来者。因为卖掉祖屋以后,“我”在这里也将无所托寄,这是小说的开头作者就已经表明的回乡目的,在闰土眼里“我”就是以前的“老爷”,尊卑已显,距离已生;在杨二嫂及众多乡邻的眼里“我”是达官贵人,而在自我的意识里,“我”又是谁呢?除了有种侵入乡村的异质感,无法再与儿时的小伙伴和乡亲对话的悲凉感以外,对自己的身份是否有种自觉?没错,是知识者,也即启蒙者。因而,“我”的归乡除了对故乡时过境迁的失落,更是无处托寄的启蒙的失落。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⑥
具体地说,也就是知识者一直凭藉的现代性启蒙话语找不到与乡民们对接的方式,这其中就包括知识者本身对启蒙的怀疑,而启蒙话语则是众多的知识者在抛却了传统后,相信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现实的力量,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我”在与杨二嫂对话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来不及辩解;在与祥林嫂的对话中,对她提出的有无魂灵的问题更是无从作答。知识者的形象,或者说归来者的局促是在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中再次显现。
中国的知识者并非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他们不是像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以不依附于任何群体的独立身份来发言,他的身份及意识往往也是通过另一群体来陪衬和彰显的,而所谓的启蒙或现代思想往往也是在与传统的对接张力中得以凸显,知识者自身的精神困境与关于“我”的身份纠结也是在这一境遇中更加显明。而这一困境也是可以视之为当时知识者的普遍之情状,它在乡土文学中不断地轮回,回转。
1985年,韩少功发表过一篇小说《归去来》,或许可以很好地诠释乡土作家的那种身份迷失的迷茫和失落。小说中“我”“马眼镜”和“黄治先”三个人重叠在一起,“我”去一个地方仿佛似曾相识,而那里的村民也把“我”当成是一个叫“马眼镜”的回城知青,与“我”一起回顾了许多以前的事情,而“我”只不过是那个叫作“黄治先”的人。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还有自身意识中的“我”,三者混淆融合一体,正像是乡下人、知识者和外来者这几种身份重合在众多的乡土作家及知识者的形象塑造中。“我”的归来常常并不能寻得乡情温暖,恰恰相反,虽然对记忆有所感知,但终归还是无法更加深刻地融入进去;“我”是再一次确证自身身份的模糊及格格不入,与乡村生活及价值理念的渐行渐远,还有终将离开的宿命。
也是在1985年,莫言也发表了一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同样是一个回乡的故事。“我”和暖青梅竹马,“我”19岁,暖17岁那年,一队解放军从村里经过,蔡队长看到“我”和暖都有文艺特长,就说明年过来招我们去部队当兵。而在这不久,有一次“我”推暖荡秋千,秋千的绳子断了,暖落入刺槐丛中,刺瞎了右眼。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暖嫁给一个粗俗的哑巴,并生了三个同样不会说话的孩子。两人的再次重逢也就从作为大学老师的“我”在回乡的路上碰到暖开始。
知识者的身份仍是刻意张扬的,只是他不再是一个背负着启蒙意识的时代先行者,而是对乡村生活有着天然体恤之情,内心还有走出乡村的那么一点轻松与得意。
我在农村滚了近二十年,自然晓得这高粱叶子是牛马的上等饲料,也知道褪掉晒米时高粱的老叶子,不大影响高粱的产量。远远地看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心里为之沉重。我很清楚暑天时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我为自己轻松地叹了口气。⑦
莫言写作这篇小说的时代,走出乡村的知识者是让乡下人无比羡慕的,意味着可以逃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做一个可以享受诸种待遇的城里人,因而当“我”矫情地说很想念故乡的时候,暖的话可以说道出了众多乡民的心声:“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她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⑧也许也就不难理解暖心中的怨怒: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⑨
10年后的暖无疑只是这样一个普通又粗俗,内心还带着怨气的农妇:
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脖子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⑩
而我是一个即将提拔为讲师的大学老师。即使“我”的话语里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我”的身份已经将两者隔之千山万水,知识者再次失去与乡民对话的机会和可能,犹如《故乡》里的迅哥。小说的末尾,被王德威称为“当代文学里,再没有比这场狭路相逢的好戏更露骨地亵渎传统原乡情怀,或更不留情地暴露原乡作品中时空错乱的症结”⑪。
好你……你也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⑫
与其说这是情与理的冲突,不如说是现实乡村的困境和乡民们无法言说的悲伤与逃离了乡村的知识者看似了无牵挂的情感之间的冲撞。“我”终究只是过客,既无从再重温故乡的温情,也无法再在乡村面前彰显一个知识者的形象,后者对于乡村来讲正如启蒙话语对乡村来说都是无效的,而且是隔阂冷漠的。
确认自我的身份,“一种方式是在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有本质作用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种是在与那些对我持续领会自我理解的语言目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的关系中”⑬。很明显,“我是谁”的问题并不能在回乡的经历中得到清晰的答案,身份的纠结,想要再次融入乡村,却又无从再像过去一样自然地出入,这或许也是现代知识者无法避免的悲剧,终归知识者与乡村之间有着难以填补的沟壑。
二、现代与传统间的彷徨“一卒”
身份的尴尬或许只是走出乡村的知识者最为表象的症候,更深层的是隐藏于意识深处两种思想的相互咬啮。以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高老庄》和新世纪阎连科的《风雅颂》这两个文本来看,更能清楚地知晓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彷徨“一卒”的精神思想状态。
《高老庄》发表于1998年,以大学教授高子路携城里的妻子西夏返乡为父亲做三周年祭奠为主线,铺陈开了一个鲜活的乡村世界,一面是外在的肌理,即变动着的乡村社会及人事,蔡老黑的葡萄园、王文龙的地板厂都在搅动着乡村的安宁,利益相争在所难免,带来了乡村生态的变化,也影响着人心的流动。一面则是子路与菊娃、西夏、石头等等之间的情感纠葛。其间还穿插着子路搜集地方方言以作为研究的素材,西夏对远古石碑的发现,从而对高老庄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
子路作为大学里教古汉语的教授,有学识也有名望,理应也是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熏染的,小说也讲到他想要以现代文明的方式对曾在农村的妻子菊娃进行“改造”:
当他在省城里开始研究古汉语的时候,菊娃那几年老是害病,手脚浮肿,眼圈发青,他三天两头地写信要她好好治病,菊娃的来信却是说:医生认为没有病,只是脾气不好,肝湿气过重所致。他又在信里反复指出她的脾气固执急躁,由此又数说她的无故爱叹气,舍不得花钱,不注意打扮,太照顾她的娘家,他是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改造得尽善尽美。⑭
“改造”的失败也就直接导致子路与菊娃的离婚,而他后来婚姻的目的也就变成:“回到省城发誓要找一个老婆,一个自己最满意的让外人企羡的老婆,而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心态思维及族种。”⑮说到底,他与菊娃婚姻的失败不全是各自性格的不相融,深层的原因仍是一种农民式的自卑、自负与虚荣心在作怪,有着一种都市文明的矫情,他对自身身高的自卑,对西夏漂亮的容貌和长腿的迷恋则将这样一种心理推向极致,但是他的身上又未见现代文明的理性、明智、通达、正义,反而在回到高老庄之后他农民式的习气一览无余。另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前妻菊娃的感情上,优柔寡断,自私狭隘,他们虽已离婚,复婚无望,且自己又已娶西夏,在内心也希望菊娃能有一个好归宿,但是每每听到或见到菊娃与其他男人相处,子路往往又觉得气闷。二是在对待蔡老黑的事件及其他的乡村事务时,子路往往表现出来的又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的心态,一直纠结的也是私人感情,他对蔡老黑、王文龙的冷淡也完全是出于他们与菊娃之间皆有关系。相比之下,来自于城市,受现代文明影响更深的西夏,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去融入乡村的人事纷乱,以包容温和的态度去处理与菊娃和石头之间的感情;她仗义执言,热心帮助敢爱敢恨的蔡老黑,想要为受辱的苏红打抱不平;她对远古文化的好奇与热情也远远超过一种功利的目的……
通过子路与西夏的对照,在贾平凹这里或许并非一定要显示出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乡野文明的对立冲突,我以为,他想要展示的仍然是一个走出乡村的知识者的困境——未曾完全开化的现代文明与积习渐深的传统心理之间的相互矛盾。这之间还夹杂着变异的乡村如何成为精神归处的问题,现代生活及意识一点点侵入乡村,搅动乡村经济及生活常态的王文龙、苏红、蔡老黑这些人也很难以正面的形象出现。《高老庄》毕竟还或多或少地有他自己的经历在里面,正如在后记中所透露的那么一些中年人的疲惫:
在世纪之末写完《高老庄》,我已经是很中年的人了……中年是人生最身心交悴的阶段,上要养老,下要哺小,又有单位的工作,又有个人的事业,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脑袋,而身体却在极快地衰败。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也开始相信了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在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⑯
诚然,子路对乡村有牵绊,亦如他内心深处想起菊娃母子时灵魂的不安;他所收集的方言古语也是他研究的内容,但是牵绊也好,这些与工作相关的素材也罢,除了给他增添心灵的负累,不复提供他一种前行的力量,我们除了从他身上看到那些农民性格的劣根性,也无从追溯一种传统文化的深厚给养。与此同时,现代文明也没有给他一种关照这种生活的眼光与魄力。换句话说,他常年经现代文明的浸染或规训,也失去了对乡村更复杂也更琐屑人事的应对能力。这也让人想起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所说的,“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⑰。我想这不是一味地在说自己的关注点仍然停留在乡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仍然是农民的,当贾平凹说自己是农民,骨子里仍然剔除不掉农民性的时候,也正是对农民性的警惕和省思。当然,我们在讲这样一种农民性的时候,也并非一概所指的落后、愚昧的一面。
小说的结尾,子路撇下西夏一个人先回城,离开时他到父亲的坟上磕头,说了声:“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⑱他的累或无奈无助,也许皆源于一种知识者的失语。子路回到城里,也许会很快地恢复那种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彬彬有礼、现代人的情趣与嗜好,只是在回乡的日子才真正将内心的卑怯与不堪暴露出来。子路的精神状态或许也不仅仅适应于他。
与高子路一样,《风雅颂》里的杨科也是这样一位从乡村走出来,但身上还依然保留着很深的农民性格及习气的知识分子。小说是以他在京城里的一系列挫败开始,有来自婚姻家庭,也有来自事业工作的;接着因带领学生抗击沙尘暴,有损名校形象,被校委会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精神病院;后又逃离出来,回到故乡,几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辗转,最后找寻到诗经之城,与众多逃离现代城市的教授、妓女共同生活。小说的原名就是“回家”,阎连科对现代文明及制度的抨击,对知识者内心病态的批判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以“回家”来逃离现代文明,也就是要回到乡村及传统文明,回到思无邪的淳朴与至尚。
主人公杨科这一人物“自我”及人格的分裂其实也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固然城市文明及制度营构了改变命运的严苛氛围,但是作为知识者性格的弱点却也值得警醒。杨科是第一个从村里考上京城名校的乡下人,后又顺利地读完硕士、博士,并留校任教,杨科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独立人格形象,反而是对权利的崇拜、屈服,甚至是不顾及尊严的懦弱、委曲求全。还在读书时,他对导师关于婚姻的安排言听计从,是因为他看到这一切背后所指代的现实利益;当他耗时5年完成诗经的研究著作《风雅之颂》回到家,看到妻子与副校长偷欢时,他的反应却是极度地卑怯、猥琐:
然就在我将要泪流满面时,心里蠕动一下子,我鬼使神差(也计从心上来)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跪下看着他,也看着惊怔在一旁的妻子赵茹萍。我重复地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⑲
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这一行为的理由,就是杨科仍然想以自己的委曲求全来维护一个乡下人在城里得到的一切,包括事业与爱情,尽管看上去并不那么美满。他在妻子赵茹萍面前的卑微也是可见的:他虽是研究和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但是他所开设的关于《诗经》的课程在学校并不受欢迎,远远不及妻子赵茹萍在课堂上大肆宣讲明星的私生活那样受到追捧。他在城里的境遇是可以视为人文知识者在以经济利益为运筹社会的遭遇,更确切地说,他的经历里也有着作为乡下人的辛酸奋斗史。也正是基于在城市爱情与事业的挫败,他想到的唯一一条出路便是回家。
在乡下,作为大学副教授的杨科是受欢迎的,至少这里还有着对读书的尊重,尽管很难说乡民们是出于对读书本身这一种行为的尊重,还是对由读书所能升迁达致的道路的企羡,但是杨科在给孩子们摸头以示鼓励和运气的活动中,找到了一种自我的满足及虚荣。“那一天,我在前寺村感到的温暖和信任,如我最终在天堂街上产生的爱情一样,把我和世界都浸泡得神魂颠倒、志昏意迷,使我再一次错过了由那些刻字的石头给我带来的惊人的发现与成就。”⑳他的自满和虚荣还表现在对于回家原因的隐瞒,过年时假借校长之意打电话让村里人知晓他在城里的地位。除了想要获得这样一种身份的认同及尊重,乡村还有他往昔的恋人玲珍,而他却在关于玲珍的种种传言中失去了与之复合的机会,最后又移情于像其母的女儿小敏,并在小敏新婚之夜杀死了她的丈夫。这时,杨科无异于一个真正处于精神分裂的病人。
然而,乡村又是杨科的心灵归属吗?这里也有如城市里一样的“天堂街”,当杨科试图一个个劝说女孩子回去读书时,并没有人听信于此,尽管那些女孩们依然尊敬他,听他讲《诗经》。但是很明显,他的作为知识者的清高,对知识与传统的一种维护和信仰难以再打动任何人,亦如他在精神病院为一群所谓的精神病人讲课受到欢迎那样,本身是一个悖谬和反讽。这也是知识者无从改变的社会现实,无法与变动中的乡村社会对话的悲剧。杨科最后找寻到的诗经之城,看似是远古文明的发祥地,看似可以归遁,他所意欲建构的乌托邦无非是没有权力、众生平等、性爱自由,从他与众多人近乎狂欢淫乐的状态,除了让我们看到这个乌托邦的虚妄与虚空,更加清晰呈现的其实是作为知识者的杨科的精神现象——无法弥合的自卑与软弱——这或许来自于乡村,阎连科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㉑
阎连科将主人公置身其乡村成长的背景,其实也是在拷问这样的成长环境对其性格的影响和塑造,他在城市及权利面前表现出来的懦弱不堪也许正是乡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阎连科所说的,“大学”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或许可以视之为那些并没有“现代”起来的思想及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或城市文明并没有赋予杨科相应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他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也没有真正浸润到他的内在人格里。回家的失败,或者说无从归依,在于“家”本身的破败,更在于知识者本身建构“家园”的无力。
基于此,我以为《高老庄》和《风雅颂》都是从知识者的视角来审视一种内在乡村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怎样的实质内涵?我想,可以归结到长期农业社会所积习下来的心理,还有现代以来城市文明对乡村长期压制下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的扭曲与形变,既有来自制度的规约,也有来自异域文明的诱惑,如子路一直以来对自己容貌身高的不满,杨科对城市及权利的崇拜……现代文明在他们身上恰似一个伪装,在一定的时候内在的惰性及丑陋就会显现出来。
从知识者所体验到的身份的尴尬,到对自身内在性格及意识的审视、剖析,看似走出乡村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未真正走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那么调和甚至是对立的境遇。走向城市,并不意味着现代文明就能够长养一代人的现代品格,关于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能够放之四海皆准。回到乡村,也并不是像古时的游子那样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并能寻得一处净土的慰安,共享的文化背景在一点点逝去,乡村本身也在变化,尽管更为矛盾的是那些固守于性格深处的乡土性的东西在作祟,毕竟知识者大多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乡土依恋,耳濡目染的农民性并非能轻意褪去。因而,在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的内在结构时,赵园在《艰难的选择》中也发出这样的感叹:“该按照何种‘模子’来改造一下中国人,使我们自身,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性格更臻完善呢?我们多余的是什么?‘常识’?‘经验’?农民性?少的是什么?哲学思辨?理论的彻底性?现代意识与世界眼光?”㉒
乡土,不仅是现实的境遇,一种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它浸润于国民性格中的东西仍然要经历无比漫长的进化和蜕变期,而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始终在这样一个境地中徘徊,甚至煎熬,一次次冲撞着自我认同的困局。
①沈从文《水云》[A],《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②③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第25页。
④⑤⑥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第481-482页,第485页。
⑦⑧⑨⑩⑫莫言《白狗秋千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第226页,第227页,第226页,第238页。
⑪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页。
⑬[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⑭⑮⑯⑱贾平凹《高老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7页,第48页,第357页,第356页。
⑰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514页。
⑲⑳㉑阎连科《风雅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140页,第327页。
㉒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