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中国文明的积聚,是政治手段实现的
——读《美术、神话与祭祀》
2018-09-28龙梆企
□ 文·图 / 龙梆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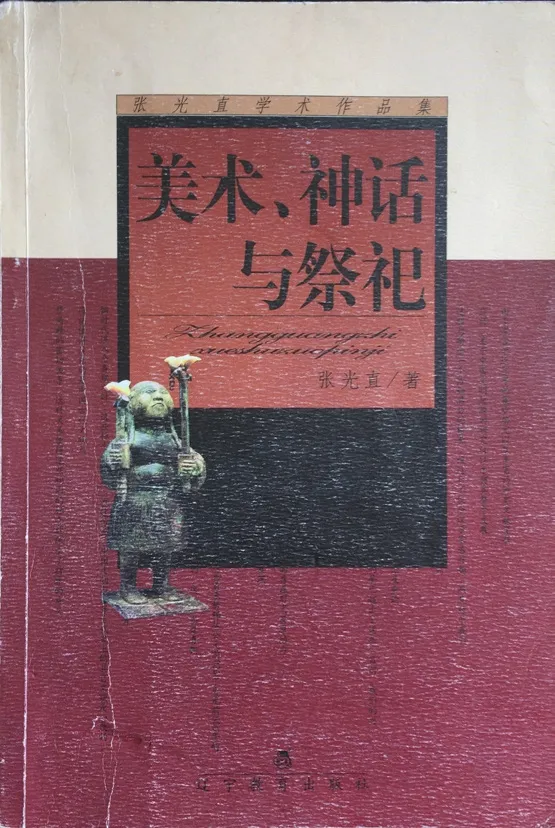
张光直(1931年—2001年),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开创聚落考古的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蔚为风潮,并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古代中国的考古》是迄今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著。
1933年,鲁迅在他的杂文《电的利弊》中,对中国技术进步作这样的描述: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鲁迅的本意,显然是要嘲讽一下中国的“旧文化”“旧文明”。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辛辣的批评是一种普遍的潮流。中国的“旧文化”,被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视为落后,而再造文明的梦想和行动,则建立在对这种“旧文化”“旧文明”的批判之上。
半个世纪后,晚清以来对中国文明的这种忧思,又再度成为热潮。但与晚清或者民国不同,新的时代语境和学术积累,使这个问题开始呈现出比过去更深入的探讨,以及更为多样的理解。
考古学家张光直1983年出版的Art,Myth,and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就是对这一热门话题比较权威的研究之一。在这本小书里,张光直几乎肯定了(并非有意)鲁迅对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差异的区分,但是不同的是,张光直并不认为中国是例外,反倒认为起源于两河流域的西方文明(鲁迅眼中的“外国”)才是例外。
张光直出生于北京,是已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在这本书出版前,他已先后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商周考古,对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及中国早期文明(新石器时代),有很权威的研究。
张光直1983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他在哈佛大学本科生课堂讲义基础上改成,对于繁琐的考古研究而言,这本书虽然算不上大众读物,但也算通俗易懂。几年后,这本书被云南省社科院郭净先生翻译出版,书名叫《美术、神话与祭祀》。此后,多次再版,俨然成了一本畅销的学术著作。
文明的界定与研究取向
《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探究的主题是:“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个问题,可以归入文明起源的范畴。但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张光直在书中,并没有对中国文明的时间、空间,以及模式等诸多宏大问题,提出多么惊世骇俗的看法。他的着眼点,反倒是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比如,政治权力跟巫术、艺术、文字的关系等等。
要理解张光直的逻辑前提,有必要回顾一下对文明起源的诸多探讨路径。文明起源的探讨,通常有一种思维模式,通俗点概括,就是:“×××的出现,标志着×××地开始进入文明时代。”而被视为文明标志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单选或者多选项:城市、国家、文字等等。
举个例子,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王朝是夏,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中,夏经常被忽略,甚至认为它只是传说。原因在于,夏还没有文字出土,而随后的商却有文字,于是商就成了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这种简单粗暴的判断标准,如果理解不当,通常会弄出一些惊世骇俗的结论,从而一定程度导致今天对于中国文明,以及各少数民族历史的认知的一些乱象。
《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对文明一词并没有特别新颖的界定。在并不显眼的地方,张光直提到他对文明的理解:“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这个界定,特别强调了文明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因果链条。简单推演下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文明才能出现,而文明的出现,又进一步促使了人类的财富增长。
这个界定对理解《美术、神话与祭祀》很重要,因为财富积累问题,跟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关:财富是从生产技术进步中获得,还是从政治权力的变革中获得。
这两个不同的路径,代表两种文明类型。前者是西方文明,后者以中国为代表。中国早期文明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资源(文明)的最初集聚,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
中西文明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不同文明的对照,近百年来一直是很多思想交锋的逻辑前提。但作为一本提纲挈领的小书,《美术、神话与祭祀》的原文里,倒没有刻意比较这两种文明的不同。不过,我们读到的简体翻译版里,无论是译者序,还是后来作者同意加进去的“后记”,都强调了中西文明之间的“比较”。大概文明这种宏大叙事,只有比较的视角,才容易跟当下形成共鸣。
郭净先生在译序中,援引张光直先生的其他著作,把这种比较出来的差异做了简要概括:
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前一个就是以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为代表的文明,这种文明就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其文明的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等等。”概括而言,这种文明演进的特征是破裂性的,即技术导致人与自然分离,文明与前文明(野蛮)两种不同时期的断裂。
对照而言,中国文明的特征是:青铜器等金属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是被应用于农业,而是被应用于祭祀,以及表达政治上的象征含义;文字也主要被用来占卜,和跟死去的祖先(也是神灵)交流;政治上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稳固的统治集团。而这种文明,总体的特征是连续性的。
而且,特别要强调的是,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张光直认为,中国文明的演进方式,“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特点,反倒是西方文明,才是例外。
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的迷茫,更不像晚清、民国初年的自卑。所以,也更加需要平心静气地审视两种文明的性质与结构。而且,文明和文化的比较,不能为了比较而比较。今天很多比较研究垃圾的地方,就在于只为比较而比较。
血缘、功德与礼法
《美术、神话与祭祀》全书七章,有非常清晰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张光直对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心得(毕竟这本书是讲义基础上改成),其价值必定不限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探讨,也启发我们认识民族史、古代史。
我们不妨来梳理下这本书的逻辑结构。核心问题是,导致政治权力集中在某个统治集团手中的各种条件。所以,该书第一章就围绕氏族、城邑展开,而最后一章(第七章)则回到考古材料中,观察这些条件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过程。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介绍。氏族是人类文明演进中,最有普遍性的组织。在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后,氏族政治得以延续。血缘是氏族的纽带,通过血缘的认同,本氏族得以跟其他氏族区分,氏族内部,血缘的亲疏远近又决定了权力的再次分配。
权力的继承者,理论上只能是血缘最近的男性成员,而且通常是长子。至于其他血缘同样亲近的兄弟,则会被分封到国都之外的地方另建他个人的宗族和国家,而被选定的地方,就会因为这种政治需要,而逐步发展为城市。
城市是文明起源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城市起源,张光直比较认同于李约瑟的说法,城市“不是人口自然集中,资本或生产设备自然集聚的结果”“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中心”,而是“古代封建领主的据点”。
血缘只是给权力的攫取提供了一个先天资格,但除了血缘,还需辅之以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张光直概括为三种:“道德权威(胡萝卜);强制力量(大棒);以及通过对神灵世界交往的垄断来占有知识(宗教与仪式)”。道德权威和强制力量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第二章集中讲述。至于第三种攫取权力的工具,则最为复杂,张光直用了三章的篇幅加以描述。
道德权威是统治集团内部,或者他们对外部需要树立的形象,所以,统治者的事功和德行,一直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甚至被描述成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我们看到先秦时代的神话和古史传说中,几乎每一位古代的君王,都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进步方面留下了功绩。最早的那些氏族部落的王,他们不是发明这样,就是发明那样,有的甚至是百科全书式的发明天才。比如黄帝,会造车,造船,制铜镜,盖房子,蒸饭,作弓,甚至连足球也是他发明的。夏商周时代,很多文化发明都已经被前辈抢注,所以,他们在功德方面,更加突出的是德。比如舜孝敬后母、亲近兄弟,商汤为了求雨,不惜以身投火,雨神可怜他,降雨把火给灭了,等等。
获取权力和维持权力的强制力量,除了我们知道的军队这样一些有组织的暴力,张光直还把它扩展到宗族组织,以及祭祀和礼仪。甲骨文里的“族”字,上面是一面旗帜,下面是一支箭,本义就是军事组织。族长也是军事首领,冒犯要被重罚。而族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汇编成礼,实际上它就等于法。比如,《礼记》规定,王者要定期去巡守,看领主们的祖祭,是否行之无误。如果发现不符合规定,领主要被贬黜。
天地神人的沟通
政治权力的获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那就是沟通祖先或神灵,从祖先或神灵处得到知识与认可。这种政治活动,充满巫术色彩。
跟祖先或神灵沟通的方式,主要通过巫觋来完成。巫严格指女性,觋指男性,他们能够将神附体,帮助统治者实现与天地、神灵的沟通。张光直指出,商代的甲骨文提示我们,商王是巫觋的首领,甚至商王本身可能就是巫觋的一员。
与神灵沟通的重要性,从甲骨文身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文字,是我们今天汉字的源头。但它最早的功能,可能并非日常使用,而是用于巫术活动。
3000多年前的商代,流行用烧灼牛肩胛骨的方式占卜。这个方式,在云南彝族他留人中过去还有保存,只是他们用的是羊肩胛骨。占卜的结束,商王或者商王的助手——巫师,有时要在裂纹旁边刻下所提的问题,偶尔还要刻下所得到的答案。显然,这些文字是活着的商王与死去的祖先的“聊天记录”。他们所聊的内容,也就是商王想要占卜的事项,以及通过卦象(裂纹)得到的“回答”,上至祭祀、战争,下至牙会不会痛这等麻烦事。
张光直还指出,商代喜欢喝酒,这可能也跟巫术盛行有关。因为喝酒让巫师们更容易找到迷幻感觉。而那些精美而昂贵的青铜器则正好用来当酒杯。
沟通天地、神灵的仪式,还涉及到其他辅助要素,这些要素也都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内容。张光直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标题就是“艺术——攫取权力的手段”。所谓艺术,主要是指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为主题的装饰纹样。张光直很熟练地列举了这些纹样的类型,并具体分析这些纹样的象征功能。他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作为牺牲的动物的象征,而这些动物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
同样的逻辑,张光直还认为,文字本身也具有某种沟通天地的神秘力量。他分析了中国古代对汉字神话描述,并结合考古材料,对文字的起源也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
文字的出现,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认为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在古代还有这样一个剧情夸张的神话。公元二世纪的《淮南子》里记载,当仓颉造汉字时,天地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文字的诞生,为什么会如此惊心动魄?可能因为古人认为,文字的出现,解释了某种世界的秘密。
对汉字起源更实证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族徽……演变而来。”张光直进而推断,文字具有内在的力量,或者权力。这种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因为知识由死者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显示于后人。这就是文字拥有权力的逻辑前提。
从“三代”文明特征,推演史前文明
沿着上面的逻辑,我们接着介绍这本书剩下的内容。
权力的角逐中当彼此的差距并不明显的时候,如何让权力的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呢?
张光直在第六章中给出一个答案:“以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首先是青铜器)的方式”实现对权力手段的独占。古史上最有说服力的是“九鼎”的故事。
传说大禹和他建立夏朝的儿子启,铸造了九鼎。九鼎上绘有各方国的动物图案,其铸造的金属也来自各方国。这个传说给九鼎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味。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象征国家,象征王权的正统性;其次它还象征财富,以及财富的荣耀;再次,它象征着统治者对金属资源的垄断。总之,独一无二的九鼎,象征着王权对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
王权对技术与资源的垄断,还表现在玉器方面。《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对玉着墨比较少,但实际上玉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要性不容忽略。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有玉的礼器出现。玉同样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稀缺资源。而和青铜器等金属不同,玉在宗教方面的重要性,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史。而玉矿的采集,也伴随中国文明的扩散而逐步从中原向西部扩展。
对这些内容,当代的中国文明史研究,已经又比30多年前的张光直的论述更进了一步。
从《美术、神话与祭祀》的文章结构来说,最后一章(第七章)最不容忽略。它是全书逻辑上的完善。前面说的都是一些很理论的推演,而这一部分,结合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材料,具体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张光直的著作,再次证明,文明起源问题是很难被说清楚的问题。不过,结论如何,对于这本书来说,已经不太重要。张光直的这本主张多学科融合的小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些可能的研究路径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从先秦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推演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是否可行。再比如,他围绕政治权力问题,列举的各种文明的要素之间,能否像张光直希望的那样,构成一个动力系统,并能够用于史前文化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