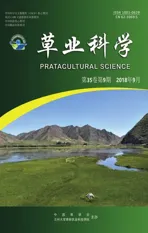养殖业的农业伦理学之度
2018-09-19董世魁任继周方锡良杨明岳祁百元
董世魁,任继周,方锡良,杨明岳,张 静,祁百元
(1.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5; 2.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3.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4.青海省铁卜加草原改良试验站,青海 共和 813000)
中华文化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还包括南方的海洋文化或渔业文化)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混血”凝结而成。尽管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但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系统中,豢养类(畜禽养殖)在汉代以前居于重要地位,绝大部分土地用作草地畜牧业。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以耕地农业占主流地位,畜牧业转变成为种植业服务,养牛为耕田,养猪为积肥,豢养与农耕结合,其所具有的特定的家畜饲养方式,仍不乏伦理元素[1]。在中国漫长的农业历史发展过程中,以豢养(包括草原放牧和农区饲养)文化为主导的畜牧业,尽显了“帅天地之度以定取予”的农业伦理学特质,从“时宜性”、“地宜性”和“尽地力”3个维度反映了农业伦理学之度。
1 畜牧业伦理观的时宜性
在漫长的牧业生产历史中,“时宜性”一直是中国草原区牧民和农耕区家畜饲养者十分珍视的伦理学原则,这种“时宜性”的原则体现在家畜饲养、保健、育种管理等多个方面,如“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暑伏不热,五谷不结;寒冬不冷,六畜不稳”、“春放阴坡,夏放东西,秋放近坡,冬放高坡”、“先远后近,早阳午阴”、“春不啖(喂盐),夏不饱;冬不啖,不吃草”、“牲畜看季节,膘情看经由(管理)”、“春放一条鞭,夏秋满天星”、 “夏天给庄稼追肥,冬天给牲畜加料”、“与其冬天干熬,不如夏天抓膘”、“夏天赶着放牲畜,冬天拴着喂牛羊”、“秋来追膘冬不愁,春天羊羔满山游”、“春不吃盐羊无力,冬不吃盐饿肚皮”、“冬不吃夏草,夏不吃冬草”(藏族民谚)、“春天牲畜像病人,牧民是医生;夏天好像上战场,牧民是追兵;冬季牲畜像婴儿,牧民是母亲”(藏族民谚)、“开春羊赶雪,入冬雪赶羊”(哈萨克族民谚)、“夏抓肉,秋抓油”(哈萨克族民谚)、“早晨在向阳坡放牧,中午天热在背阴处放牧”(哈萨克族民谚)、“春来剪毛两头落,冬来剪毛落两头”、“霜降配羊,清明分娩”、“马配马,一对牙(二岁就可配种)”。这些基于时宜性的伦理学之度的把控,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畜牧业生产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当前中国的可持续畜牧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古今畜牧业生产所强调的诸多伦理观中,“逐水草而居”是草原牧民高度凝练、概括和全面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原则,对维系中国国土面积40%以上的草原区的畜牧业生产和民族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历代的民族史或传记中可得以印证,诸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2],《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酪,以毛毳为衣”[3],《南齐书·河南传》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4],《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其兽,牦牛、名马、犬、羊、彘,……,其宴大宾客,必驱牦牛,使客自射,乃敢馈,……,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5]。古人所指的“逐水草而居”就是草原游牧,实际上“逐”是循自然规律所动,按照牧草和水源的季节变化(时间节律)来移动放牧(家畜)。当下以人类生态学的观点评价可得,游牧是人类适应自然并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结果。从生态学观点看,游牧是牧民、家畜和草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自然资源管理系统(图1),具有移动性、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有效保护和共同支持的特点。通过迁徙来适应水、草的季节变化就是草地畜牧业“顺天时”的伦理学最佳诠释,“逐水草而居”一方面满足了夏秋季畜群对食物和水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冬春季家畜繁殖和保膘的需求[6]。
在中国西部和北方地区,以牧业为生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和裕固族等草原民族具有悠久的游牧文化,形成了基于草地畜牧业“时宜性”的游牧生产方式,具体按照迁徙方式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多次迁徙,一年搬迁10次之多,这样的搬迁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而现代只有少数地区存在。
2)一年之中搬迁4次,即春、夏、秋、冬四时营地,牧民迁徙各地营地的规律、时间的分配、路线和范围的划定,一般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也要依水草是否充足而定。一般来说,春牧场为5-6月,夏牧场为6-8月,秋牧场为9-11月,冬牧场为12-2月。传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哈萨克族都有四季牧场。
3)一年之中迁徙2次,即冬营地和夏营地。哈萨克族的一些游牧群众,夏天到布尔加尔地区伏尔加河流域放牧,冬天到巴拉沙兖过冬。
4)按照三季转场轮牧。在青藏高原地区,11月-翌年4月为冬春季节,牧民在各地避风定居;5-8月夏季转入高山牧场;9-10月秋季,畜群逐渐下牧,为秋季牧场。在高原东部的湿润和半湿润草原也是按照夏秋―冬春―春秋三季划分牧场的。
5)走场游牧,除了季节固定的牧场之外,还选择其他的牧场放牧,目的是为了抓膘。
从古至今的实践表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不仅保护和维持了草原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而且传承和发扬了悠久的草原民族文化。基于时宜性原理的移动和适应是草原民族在脆弱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前提与基础,不论是生产、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传统,都充满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正是由于“顺天时”的游牧传统和生态伦理,才使得这片神奇珍贵的土地得以保留至今。这也是我国现代放牧管理学原理之一——“草原季节畜牧业”诞生的基础,它对科学利用草地资源、提高草地畜牧业生产水平具有指导意义。当前,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应该摈弃以“超载过牧”、“垦草种粮”为代价换来的GDP增长,其导致草地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水资源减少、沙尘暴频发等恶果,此时古老游牧文化的伦理观愈加显示出了其重要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更加彰显了其传承价值和持续发展的意义。

图1 游牧草地畜牧业的组成要素(家畜、草地、牧民)及其特点Fig. 1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livestock, grasslands, and herdsme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storal husbandry
根据文献[6]制作。
Modified by [6].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在牧区推行草地家庭承包、牧民定居、草原围栏、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区草地牧业生产、生态和生计功能的良性互动发展[7]。这些政策的影响在草原区已经显现,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干旱半干旱草原区的土地荒漠化与草地承包到户、牧民定居、草原围栏建设等密切相关。正如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8]所讲:“人类社会由游牧到定居,到农业,到工业,到城市化,好像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草原也不应该例外,其实这是偏见,小农的偏见;游牧呢,就是它当地来讲,经过多年选择,利用草原最经济、最实惠,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一种经营方式,却被我们消灭了”。同处干旱半干旱草原区的蒙古国牧民达娃[9]认为:“对于牲畜来讲,逐新鲜水槽而牧是非常重要的。放牧的草场是要精心选择的,为了给牲畜提供最好的采食条件,我们会经常更换草场,……,不以移动来更换饲养环境,牲畜是不会健康繁殖的,……;只有健康的牲畜才能提供健康的肉食和奶食,所以牲畜的健康是所有的前提,……”。这些观点正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现行的草原畜牧业政策的拷问,也是激发公众对强调“时宜性”伦理观的畜牧业进行重新审视和理性呼唤。
2 畜牧业伦理观的地宜性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传统思想之一,也是指导农牧业布局的基本依据。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的真实描述[10]。另据《周礼》记载“职方氏变方圆六畜以识物情,便其豢牧。但鬣有鬣之养,角有角之牧,毛有毛之刍,羽有羽之饲,畜于水者须知水,畜于山者须知山,飞着得其动,潜者得其动”[11]。这些论述都是“因地制宜”的伦理思想在古代农耕区畜牧业(养殖业)生产中的具体反映,对发展区域特色畜牧业具有指导意义。这种“因地制宜”的畜牧业布局思想,对当今草地畜牧业生产的空间优化格局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主要优良家畜品种的空间分布和畜牧业区划便是最佳例证,如产自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川牛、山东省西南部的鲁西牛、河南省南阳地区的南阳牛、山西省西南部的晋南牛、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延边牛、内蒙古地区的蒙古牛、甘肃省天祝县的天祝白牦牛、湖北省恩施地区的恩施水牛、宁夏地区的滩羊、山东省南部的小尾寒羊、山东省西部的大尾寒羊、新疆地区的新疆细毛羊、山东省济宁地区的济宁青山羊、内蒙古地区的内蒙古绒山羊、山东省崂山地区的崂山奶山羊、广东和广西的两广小花猪、湖南省宁乡猪、江苏和浙江省的太湖猪、浙江省的金华猪等。
从古至今的“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文化则更体现了草原区“地宜性”的畜牧业伦理观,根据地形、气候、水源、牧草(生长情况),合理放牧家畜,有效利用草地资源,提高畜产品产量[6]。“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态智慧,其地宜性的伦理观在草地资源利用、家畜品种搭配、农牧生产耦合的空间格局优化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当今草原区的可持续畜牧业/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青藏高原牧区、蒙古高原牧区、西北内陆干旱牧区的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和裕固族等典型的游牧民族草地畜牧业生产实践,可以诠释“逐水草而居”的地宜性伦理观的重要性,并可以为中国草原区可持续畜牧业发展提供借鉴。
在青藏高原牧区,以藏族为主体的草原民族世代传承着依自然规律而动的游牧生活,每年按牧草和水源的季节性变化在不同区域游动放牧家畜,这是一种典型的既能高效饲养家畜又能有效保护草原的生活方式[12]。每年春末夏初(5月底到6月初),高寒草地牧草完全返青,牧民开始“出圈”(从低海拔或河谷地区的冬季草地开始向高山或高海拔地区夏季草地移动),此时高海拔地区(一般在3 000 m以上)的高寒草地返青的牧草可以满足家畜采食,喜凉怕热的牦牛和藏羊等家畜适宜高山或高海拔地区的凉爽气候,可以充分采食牧草资源。夏季(6月中旬至8月中旬),牧民在高山或高海拔地区的夏季草场(俗称“夏窝子”),早出晚归的游走式放牧(早晨和傍晚气候凉爽时一般在高山沼泽草地或灌丛草地放牧,白天气候炎热时一般在高山山顶上或湖畔、河边、泉水处放牧),让家畜充分采食快速生长的牧草。秋季(8月下旬至10月中旬),高山或高海拔地区气候逐渐变冷,牧民开始驱赶家畜进入中山地段的秋季草地(或春秋草地),此时高寒草地的牧草已经结籽并成熟,家畜充分采食进行“抓膘”(育肥)。冬季(10月下旬至来年5月),牧民驱赶家畜继续向下移动进入平地或山沟的冬季牧场(俗称“冬窝子”),在离家较近、海拔较低、避风向阳的地段放牧,冬季牧场的牧草枯黄晚且经过半年多的累积,能够满足家畜的冬季生活维持需要。在放牧实践中,青藏高原的牧民总结出了“夏季放山蚊蝇少,秋季放坡草籽饱,冬季放弯风雪小”、“冬不吃夏草,夏不吃冬草”、“先放远处,后放近处;先吃阴坡,后吃阳坡;先放平川,后放山洼”、“晴天无风放河滩,天冷风大放山弯”等丰富的放牧经验。这既是青藏高原藏族牧民传统的生态智慧,又是朴素的草原畜牧业伦理。正是这种“地宜性”的伦理观所使,人畜都循一年四季按照气候与植物生长周期而移动游牧,成为自然规律的执行者、维护者[12]。与藏族一样,生活在青藏高原北缘-东祁连山的裕固族也世代传承着游牧生活,主要采用冬春、春秋、夏秋3类牧场进行季节游牧,饲养牦牛、藏羊、蒙古羊等家畜。目前,裕固族的游牧方式由原始的“逐水草而居”的大迁徙改为季节性循环放牧。在游牧过程中,常常采用“先放远,后放近;先放山,后放川;早放阴坡,后放阳坡;公放远,母放近;公放山,母放川”等原则进行草地轮牧。在家畜饲养和保健管理上,一般在2-3月冬季牧场(冬窝子)完成接羔、育羔;5月中旬进入春秋牧场进行春季羊牛驱虫,紧接着开始拔牛毛、给牛羊去势,剪羊毛;6月中旬又进夏季牧场开始抓膘和育肥[13]。正是“因地制宜”的伦理观支撑下的游牧文化,使得裕固族年复一年进行着草原畜牧业生产活动,续写着千年的游牧历史。
在蒙古高原牧区,以蒙古族为主的草原民族世代以游牧为生,与畜群朝夕相处,积累了丰富的草地放牧管理经验,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下,牧民根据一年四季的气温、降水和牧草资源的变化而进行移动放牧,即选择春、夏、秋、冬4个营地轮换放牧家畜。春季营地一般选择在避风遮寒、气候暖和的低山丘陵地带,从而使畜群(主要是羊群)保存体力并有利于接仔(羊羔、牛犊)和育幼(畜);夏季营地一般选择在山阴、山丘、山间平川的细嫩草地分布区,这一区域气候相对凉爽、牧草丰富,有利于放牧牲畜抓膘和保膘;秋季营地是低山丘陵地区以豆科、半灌木、蒿属类牧草为主的荒漠草原,牧草营养价值较高,有利于家畜固肥保膘;冬季营地主要以低山丘陵或山阳地带半灌木为主的草地为主,避风性很好,为保护家畜安全过冬奠定基础,冬营地一般特别注重牲畜的卧地(圈棚)建设,蒙古族牧民常说的谚语“三分饮食,七分卧地”,说明冬天保膘的重要环节是卧地。在漫长的游牧历史中,蒙古族牧民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逐渐确立了基于“地宜性”原理的四季牧场划分和利用原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14]。
在西北内陆干旱牧区,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草原民族牧民世代以家畜饲养和狩猎为生,形成了在山地、平原、盆地间随季节变化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这些草原民族逐渐掌握了牧草生产随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据此积累了什么时候进行转场、什么时候对羊群进行配种等等知识。一年四季中,牧民按照游牧区地形地貌、植被分布及气候特征的差异性(春旱、多风,夏短、少炎热,秋凉、气爽,冬季严寒漫长、积雪厚等特点),把放牧草地划分为四季牧场进行流动放牧:春季牧场一般分布在避风遮寒的低山丘陵地带,主要在3-5月放牧利用;夏季牧场一般分布在高山地带,主要在6-9月放牧利用;秋季牧场一般分布在低山丘陵地带,主要在9-10月放牧利用;冬季牧场主要分布在平原或绿洲地带,一般在11月至来年的2月放牧利用冻干的牧草,辅以补饲少量储备的干草[15]。这一区域的草原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总结出了高山-低山-平原-绿洲等不同系统间游动放牧的形式,甚至在一年之内游走上千公里进行放牧,以保证草地牧草和家畜的供需平衡资源供给和家畜饲草料需求的平衡。正是这种基于“地宜性”伦理观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才使该区的草原文化延续至今,经久不衰。
近年来,随着草原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逐渐得到重视,以草原禁牧为主的草原保护和恢复政策措施在牧区推广,包括“游牧民定居”、“围封转移”、“退牧还草”等工程。但是,多数草原和畜牧专家认为,完全禁牧并不是科学的决策,应“考虑民族习惯和人民生活,依据自然规律,遵循客观事实,不要轻易宣布绒山羊是草原罪人”、“生态建设不许养羊是错误的,……,是人破坏生态,不是羊破坏生态;农田种草,减轻天然草地压力,支持生态建设,对羊开刀大可不必”[16]。从草地畜牧业发达的国家——新西兰的经验来看,草地生态保护应该是“人管畜,畜管草”,建立了人-草-畜和谐共处关系;他们根据草地生长状况,决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放牧多少家畜;不仅获取经济优良的畜产品,也靠家畜放牧来控制杂草,改良草地,就是靠放牧来维护草地的健康。科学的放牧系统中,有不禁牧的“禁牧”,长期轮牧就是把草地分为若干轮牧分区(放牧单元),某一轮牧分区(单元)有一年到几年休牧;还有短期轮牧,在一年的放牧季内,按牧草在不同季节的生长状况,分区轮流放牧[16]。这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实践的集成、延续和发展,如《蒙古史》曾记载“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17],说明蒙古各部的牧场大体划分区域,以一个区域为基本核心构成游牧空间,季节迁移、转换营地基本限于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哈萨克族的游牧也是以部落和阿吾勒(牧村)为单位进行的记载“轮牧区域由部落和阿吾勒头人、元老和比官会议协调划分,因而他人不能插手更不能随意改变,是固定的”。可见,中国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强调放牧的时宜性和地宜性原则,体现了“季节畜牧业+划区轮牧”的原始思想,其伦理学价值应在重视生态文明的今天得以珍视。
3 畜牧业伦理观的尽地力
对于畜牧业生产,尽地力就是通过合理养殖实现单位土地面积的最大牧业产量。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土地承载容量或承载能力,即土地承载的家畜数量不会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限值[18]。对于草原牧区的草地畜牧业,这个限值就是家畜放牧不会导致草地退化的载畜量;而对于农区的舍饲畜牧业而言,这个限值就是养殖业不会导致面源污染的环境容量。显然,畜牧业生产潜力是有限的,必须保持在土地的承载力之内。尽地力的思想不仅强调土地的生产潜力和环境容量,而且强调人对自然的伦理关怀,可以理解为伦理学容量。古今草原民族尤其珍视草地畜牧业生产中的伦理学容量。汉代晁错在《守边劝农疏》中对匈奴游牧生活的描述“(胡人)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18],今天的蒙古族等以畜牧业为生的牧民经常强调“牲畜熟悉草场才会长膘”、“放牧牛马草地好”、“没有草场就没有畜牧”。这些都是尽地力的伦理学思想在草地畜牧业生产中的完美体现。
在生态学、畜牧学、草业科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草地畜牧业“尽地力”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载畜量的制订和实施。载畜量的概念最早在1923年由植物生态学家Sampson提出,认为在草地牧草被(家畜)正常采食而不影响下一生长季草地产草量的条件下,一定面积的草地能够承载的一种或多种家畜的数量。1964年美国草原学会规定了载畜量的标准,即每年最长放牧时间内,一定土地面积上存活的最大家畜数量(并不意味着持续生产),在草原管理学中,它与载牧量的含义基本相同。1985年我国草原学家任继周提出了载畜量的综合概念:单位时间内单位草地面积可以正常养活的家畜数量,并由此提出了载畜量的表示方法,即时间单位法、面积单位法和家畜单位法[19]。针对草地国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的管理,野生生物学家提出了平衡生产和生态关系的载畜量核算方法。1979年Caughley给出了不同放牧密度下植物和草食动物的图示关系[20](图2):当植物的生长量和动物的采食量相等时,受食物供应量的限制,动物种群的数量不再增加(动物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此时植物和草食动物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草地的承载力最大,达到了生态载畜量(点D)。从生产角度讲,放牧系统达生态载畜量时,草地承载的草食动物数量最多,但其体况并非最好,生产力并非最高;同时与未放牧系统相比,草地植物的群落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此,1985年Bell在此关系图中引入了草食动物出栏率的变化,并强调指出,草食动物的数量应以动物健康状况和草地稳定程度而定,当草地载畜密度达生态载畜量的1/2或2/3时,草食动物的可持续出栏率最大,生产力最高(点F),此时的载畜量为草地经济载畜量(点E)。当草地经济载畜量向生态载畜量增加(草地放牧率增大)时,草地资源的退化趋势也会随之增加[21]。

图2 草地生态载畜量和经济载畜量的关系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apacity of grasslands and economic capacity
草地载畜量是“草畜供求关系”的测度标准(阈值),但是实际生产中由“供求关系”估算的生态载畜量无法准确反映草地的实际载畜能力,且不能明确判定草地的超载程度,因此,必须监测草地的放牧率(实际载畜量),根据放牧率与载畜量的平衡关系,结合草地植被、土壤和动物的表观特征说明草地的放牧利用程度。放牧草地的土壤状况、植被组成和动物产量的变化与草地的放牧率密切相关,草地超载与否取决于放牧率与载畜量的平衡关系。从放牧率与载畜量的关系可以看出,载畜量是放牧率的额定标准(阈值)。当放牧率高于载畜量时,放牧压力和植物再生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破坏,草地超载过牧,草地基况变差或出现退化现象。因此,放牧适宜度理论是牧场合理利用和高效管理的基本原则。放牧率过高,草地没有特殊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出现退化现象;放牧率过低,草地收益不抵成本,导致经营者破产,只有基于草地载畜量调控放牧率才能实现草地的合理利用和健康发展[21]。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草地管理策略违背了放牧适宜度理论。解放初期,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政策误导下,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放牧草地被大面积开垦,造成了家畜数量较多、放牧草场面积较小的草畜“供需矛盾”,引发了北方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改革开放后,随着家畜和草地的“双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头数观念”驱动牧区群众盲目扩大畜群数量,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草畜矛盾”,加速了放牧草地的退化进程。退化草地的经济载畜量和最佳放牧率降低,草地的经济收益并未随放牧家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随草地生产力的下降而下降。当前,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为主导的政策背景下,“草地禁牧即为保护”的极端做法与草地畜牧业“草畜协同发展”的伦理观相左。因此,草地管理者和经营者应根据放牧适宜度理论对草地管理策略进行调整,实现放牧草地的最大经济收益和生态功能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广大牧区草地畜牧业生产的伦理学容量扩增。
尽管从面积来看,草地畜牧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产量来看,农区畜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主体。统计数据表明,98%以上的猪肉、鸡肉、鸡蛋,95%以上的牛肉和80%以上的羊肉都是由农区提供的[22]。由于农区的家畜饲养方式主要为舍饲,因此农区畜牧业的发展并不受制于耕地及草地资源,而主要受制于饲料的投入水平。从生产潜力或尽地力的原则来看,只要有市场需求,饲料、兽药等投入品供给充足,农区畜牧业的规模及家畜饲养量就能迅速扩大。尽管农区畜牧业规模化和家畜数量增加满足了人们对动物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高度集约化的家畜饲养容易造成养殖空间不足、环境容量超载的问题,进而产生动物福利受损、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集约化畜牧业生产往往在有限的空间内圈养成千上万只单一的畜禽,并将大量动物装在拥挤车厢中从饲养场长途运输到屠宰厂,动物不得不忍受严重的饥饿和其他病痛,这严重损害了动物福利或对自然生命内在价值的尊重。另外一方面,集约化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污染经常超过环境容量,在处理设施和技术落后的状况下容易产生环境污染。据农业部统计,中国畜禽粪污年产生量约38亿 t,40%的畜禽粪污未得到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给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已经成为农村的突出环境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压力下,不少地区实施了“一刀切”的畜禽禁养政策,甚至将已经纳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的各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保种场和保护区等也列入禁养和关停范围。这种为防止农区家畜畜禽粪便污染而“一刀切”的“禁养”政策和为防止牧区超载过牧引发草地退化而“一刀切”的“禁牧”政策一样,严重违背了尽地力的农业伦理学原则。
事实上,从古今中外的农区养殖业生产实践来看,种养结合、发展生态农业是保障动物福利、解决畜禽粪便污染等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先民们就有爱护家畜、保障动物福利的意识,据《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畜养篇第十四·养牛类》记载“夫农之于牛也,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视牛之疫疠,犹己之有疾,视牛之子育,若己之有子也”[1]。这种爱惜家畜、重视家畜福利的农业伦理观对今天的养殖业生产具有启示作用。将耕地作为畜禽粪便消纳场所是解决农区养殖业畜污染问题的根本之出路,因为畜禽粪尿等废弃物既是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新陈代谢产物,又是种植业所必须的有机肥资源。中国先民早在商代就已经开始给农田施用厩肥,西汉《氾胜之书》记载“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23]。当时,农户为了给农田积肥,对家畜进行舍饲并收集家畜粪肥。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集约化畜禽养殖场产生的富含氮、磷养分的固体粪便和液体粪污作为有机肥料还田利用,是一种最为经济有效的资源化利用和粪污治理方式。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荷兰、丹麦、德国等,都建立了基于氮、磷养分管理的畜禽场粪污还田利用、匹配农田面积的规定。然而,近年来集约化畜牧业迅速发展导致了农牧分离问题凸显,具有种养结合、农牧并举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农业生产系统,畜禽粪尿作为有机肥的还田率仅有40%~50%,其余部分损失到环境中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和空气质量下降。因此,基于“尽地力”的农业伦理学基础,根据粮食、蔬菜和果树等农林作物生产模式的不同需求,按照养分循环利用过程中的供需平衡原则,确定单位面积土地氮、磷输出与输入量,建立不同种植模式下单位养殖规模匹配农田面积,为实现农牧结合、粪污与土地养分平衡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 畜牧业伦理学之度的优化——生态畜牧业
从时宜性、地宜性和尽地力3个维度来看,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畜牧业伦理学之度的最佳体现,千百年来这一伦理观维系了草地畜牧业的永续发展。中原农耕民族一直践行“地力常新”的农业伦理观,建立了农牧结合的生产模式,如《三农纪·畜属·羊》中记载“南方有草鱼塘,宜修羊栈于塘岸上,每晨以羊矢扫塘中以饲鱼,草鱼之粪以饲鲢鱼,此一举而羊鱼之利两收。将羊系于处所,煮豆拌盐合草,日日饲之,勿多饮水,一月即肥”[24]。纵观中国农业发展史,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一直秉承畜牧业生产的“相宜”和“适度”的原则,保持了畜牧业的旺盛生命力,这些思想对当今的畜牧业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当前,在生态环境退化带来的挑战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机遇的背景下,如何继承传统畜牧业的伦理思想,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促进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矛盾中,探寻解决畜牧业发展困境的出路和途径,是关系农业伦理学容量扩增的重要命题。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生态畜牧业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
生态畜牧业是指运用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等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吸收中国传统的种养结合、农牧并举的农业生产方式,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和技术体系,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农、林、草系统结合的生态畜牧业生产体系。生态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动物养殖业、生态畜产品加工业和畜禽废弃物(粪、尿、加工业产生的污水、污血和毛等)的无污染处理业。生态畜牧业包括如下几大特征:
1)以畜禽养殖为中心,同时因地制宜地配置其他相关产业(种植业、林业、无污染处理业等),形成高效、无污染的配套系统工程体系,把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
2)生态畜牧业系统的各个环节和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如果某个环节和要素受到干扰,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波动和变化,失去原来的平衡。
3)生态畜牧业系统内部以“食物链”的形式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转化,以保证系统内各个环节上生物群的同化和异化作用的正常进行。
4)生态畜牧业具有完善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系统的经济值增加,同时废弃物和污染物不断减少,以实现增加效益与净化环境的统一。
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畜的发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典型代表;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这种模式以日本和韩国为典型代表;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自然畜牧业,这种模式以英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为典型代表。中国草原区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以第二种为主,即草畜平衡的草地畜牧业模式,农区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以第三种为主,即农户小规模饲养的生态畜牧业。另外,也有学者按照畜牧业的空间布局将其分为草原生态畜牧业、城郊型生态畜牧业、农区生态畜牧业和山区生态畜牧业等类型。但是,无论何种类型的生态畜牧业,其目的都是综合考虑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科学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牧草和饲料资源),生产优质、高产、安全的草畜产品,减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