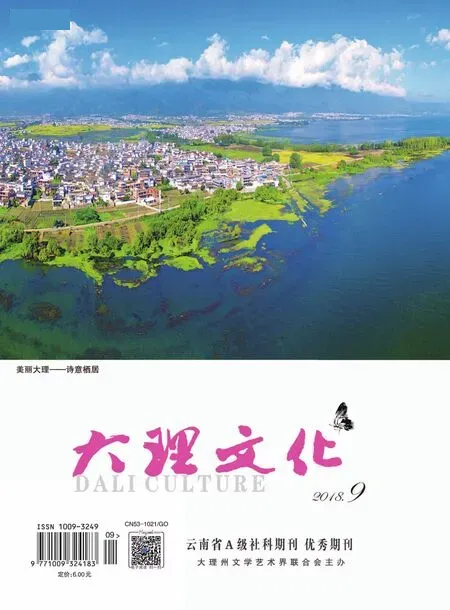深藏在记忆中的民族节庆
2018-09-18
责任编辑:张琼斯
岁月的流失,也难将珍贵的记忆忘却;
历史的变迁,总是将自信的文化弘扬。
洱海流域的大理坝子地区,气候温暖、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是一片较早发展起来的人类聚居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创造了许多灿烂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就包括许多少数民族节日。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节日的传统仪式被人逐渐简化或者淡忘,有些节日甚至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这些都曾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不曾磨灭。
凤凰山下春醮会
我的故乡凤仪,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风纯朴的地方。西边的凤凰山如彩凤飞舞,东方的波罗江似彩带飘荡,尤其是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举办的“春醮会”更是遐迩闻名。
我出生于l944年,年幼时每年一家人都要参加“春醮会”。父亲要参加耍龙,而且是耍“龙引珠”的,母亲则要参加诵经活动,因此都由爷爷奶奶抱着或者牵着我观看表演。这项活动也被称为“办隍坛”,主要内容是接“帅老爷”和群众文艺展演活动。每年由凤仪的东、南、西、北街轮流主办,主办的街道负责扎“帅老爷”,并组织参会群众的文艺展演活动。
每年正月十三举行“接帅”活动,“帅老爷”是用纸扎的全身站立的殷蛟神像,高一丈二尺,粉面红眉三只眼,中间一只称慧眼,左手拿摄魂镜,右手执方天画戟,全身披金盔甲,着实威武。
值日太帅,是迎会的崇拜中心,由大会主办街道在一个月前选一名年纪在十二岁的男孩装扮,“侍帅”是“主帅”的陪衬,由四条街各选一名年十二岁的男孩,由家长陪伴到文昌宫化装。被选上的四个小孩,按赵、马、殷、温四将化装成红、白、黑、蓝四个花脸,拼凑成殷蛟下山收四将的故事。
1956年,我刚好十二岁,就读于凤仪小学五年级,被选为“侍帅”的扮演者。按传统习俗的规定,选出的男孩必须三天前就得吃素。因我是家中的长子,又是独子,父母对我关爱有加,怕我忍受不了饥饿,晚上悄悄地给我端来一碗红烧肉。但这些关爱都被我一一谢绝了,因为在我心里,扮演“侍帅”是一件极为重要和庄重的事情,不想轻易怠慢。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甚至产生了做人就要经得住诱惑的想法,需要时刻保持正直、虔诚。于是我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天。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整个凤仪城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四乡八村的群众都聚集到一起,载歌载舞。四条街都有一条龙(分红、黄、蓝、黑四色),一场花灯,一架抬阁,有的还外加狮舞、高跷、龙船、秧歌等表演。整个巡演的队伍分为四队,第一队属朝天堂,第二队属赐禄堂,笫三队属宥罪堂,第四队是都天堂。
一大早,四面八方的游客就汇聚在“雷都府”,向“帅老爷”朝拜、敬香。下午一时,游行队伍开始出发,一队接一队,锣鼓喧天,花团锦簇,五彩缤纷。一开始的是拈香队伍,接着是洞经会、圣谕会、莲池会的善男信女,他们分别演奏着庄严典雅的古乐,乐声悠悠,香烟缥缈。看着前方涌动的人潮,我的内心感到既激动又紧张,因为马上就轮到我们几位“侍帅”上场了。包括我在内的马、赵、殷、温四位“侍帅”,个个都穿得光鲜亮丽,在马上昂首挺胸,显得威风凛凛,气宇轩昂,马的两侧还有家人随行侍候,显得场面极大。最后出场的是“主帅”,他躺坐在用各色彩绸扎成的敞篷大轿中,由十六个人抬着,左右一对童男子捧着上方宝剑护驾,后面一对玉女高撑长柄羽扇交叉于帅后,一名武士高高地打着一把万民伞,笼罩着整个大轿,好一派威严气势。
虽然这一次作为“侍帅”的我没办法目睹“主帅”之后队伍的行进情况,但凭借多年观看游行的经验,我对这只队伍的构成也十分了解。此刻尾随在轿后的应该是一群身穿道袍,手中敲击着法器的道师队伍。走在最后的一位道师是掌坛大法师,此人左手端一碗净水,右手执一口宝剑,踏着方步,俨然摆出一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架势,展示着降妖除魔的本领。这支形态各异、气势磅礴的游行队伍,沿着东、南、西、北四条街缓慢游走,两旁的观众聚精会神地欣赏着演出,不时欢呼雀跃,游行一直到下午三点才结束。活动结束后,我紧绷的身体也终于放松下来,那种自豪又欢乐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天。
正月十六这一天,人们把“龙船”抬到十字街口,摆案供奉,叩头祈求四季平安,风调雨顺。爷爷奶奶也带着我到十字街口凑热闹。印象里总有很多游人会放一些纸钱在船内,祈求平安;而像我这样的小孩,则会似懂非懂地用手触摸龙舟,据说可保百病消除。傍晚时分,会有两个人手执画有驱邪章的黄旗到每家信户进行“扫荡”,意思是把人间瘟神全部赶上龙船送走。
天色渐渐变暗,到了半夜时分,道师开始在龙船前做法事。年幼的我虽然不清楚这是什么仪式,心中满是好奇和惊异,但看着周围大人肃穆的神情,我的心中仍充满一种莫名的敬畏感。这样的仪式之后,由一群青年抬着龙船、“帅老爷”站像及各种祭品,敲打着法器,一直送到北街的锁水阁地带,立即撕鸡放鸭,鞭炮齐鸣,火光缭绕。一时烈焰冲天,龙船、太帅等顿时化为灰烬。在滚滚烟雾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此时大家还不能互相讲话,道师走在最后。至此,“春醮会”的全部活动才划上圆满的句号。
这段独特而又珍贵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磨练了我的心性,为我的课外活动经历增添了色彩。随后我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学校敲锣打鼓地向家中送喜报。一年后,我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凤仪中学,在八十多名毕业生中只有三人被保送。
幼年时参加“春醮会”的经历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直到我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也不曾忘却这段记忆。2005年,“春醮会”被评为大理市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名文化和新闻工作者,我也积极、自觉地参与到对“春醮会”这一民俗活动的宣传中,为活动多次撰写宣传词,拍摄电视新闻。尤其是在2004年,恰逢我老家居住的南街承办“春醮会”,我专门为此编撰了电视专题片《盛世欢庆元宵节,凤翔龙腾闹元宵》,在大理电视台多次播出。
2018年的“春醮会”,我侄孙子杨金国被选为“侍帅”的扮演者,沿着我六十二年前的足迹巡游一圈。七十四岁的我,仍对故乡的这一盛会深情不绝,念念不忘,唯有写下一诗才能表达我对“春醮会”特殊的感情:
正月十五闹元宵,凤凰山下人如潮。
满街翠绿放异彩,沸地笙歌动地摇。
高台社火显绝招,龙翔狮舞展英豪。
人寿年丰春来早,锦绣山河万代娇!
千年不衰三月街
历经千年不衰的大理三月街是云南闻名遐迩的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三月街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开始,在大理古城苍山中和峰下举行,会期五至七天。节日期间,结棚为市、万商云集,南来北往的商客广泛进行着中草药、骡马牲畜和日用百货的交易。其间,还举办传统的赛马、秋千、射弩等民间体育比赛以及大本曲、洞经音乐、民族歌舞的表演,热闹非凡。
记得我第一次赶三月街是在1950年,我当时刚满六岁。当年根本没有公共汽车,只能靠马车或者步行。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搭着一架小马车,从凤仪一路颠簸到下关。我和父亲简单地吃了碗米线后,再步行到新桥,改乘另一辆马车,一直奔波到大理。长时间坐马车,我甚至能感觉到我的全身骨头快被颠得散架了,一身疲惫的我和父亲终于风尘仆仆、一身狼狈地赶到了大理。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显然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和多余的时间去三月街街场了。当夜,我和父亲住宿在父亲的妹妹,即我的阿孃家中。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起床了,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来到街场。我的叔叔在三月街街口开了一间茶室,我和父亲找到茶室的位置,在那里饮了几口茶水后就进入了主街道。
街上人如潮水,人头攒动,人们摩肩接踵,仿佛不用自行走动就能被人流推搡着移动。我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琳琅满目的摊贩和商品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你来我往的砍价声也让我设身处地地明白人声鼎沸的含义——热闹的声响如同开锅的沸水,炸得耳朵轰轰直响。热闹的气氛也感染着我,我恨不得立马涌入人潮,冲向人群最为密集的区域去凑凑热闹。
令人目不暇接的各色商品牢牢地吸引了我的双眸,让我自动过滤了双耳因嘈杂感到的不适。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个简易的小摊,周围围满了正在认真挑选商品的大人,只见小摊上摆着自家制作的土特产品,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有豆粉、卤腐、乳扇、酸枣、腌梨、糖果等,馋得我口水直流。但是一想到前面还有更吸引我的东西,我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再走几步是卖中草药的区域,摊位上堆着一袋袋小山似的中草药,在我打听之下得知这些草药都是山民们种植的或是从山上采来的,旁边还摆着自家制作加工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有的摊位上架着简易的帐篷,但大多数是露天的,显得比较简陋。在不远的地方,立着一棵棵树桩,上面拴着几匹马、几头牛,有几个农民在交谈生意。当年的三月街就是以药材、大牲畜、日用百货为主的交易市场。
我抬眼望去,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有几位上了年纪的白族大娘敲着木鱼,在认真地念经祈祷。长大后我才明白,原来三月街起源于观音讲经的庙会,所以这些白族大娘是在延续着传统。像我一样的小孩子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做工精巧,能吹会摇的小玩具,于是父亲掏出两毛钱,为我买了一支放进水能吹响的“小雀”玩具。我高兴得欢呼雀跃,仿佛得到了一件珍贵的宝物。记得当年我们在三月街上走累了,就在田埂上歇一会儿。口渴了,父亲就花两分钱买上一碗农人从苍山上背下来的雪水,并放上一小勺糖稀,喝上一碗,顿时清凉舒爽;饥饿了,父亲就会买上一碗米凉粉给我吃。在三月街的出口处,围着一群人,我挤进去一看,是在耍猴戏,只见两只小猴在主人的锣鼓声中,时而登上高梯,时而骑着小车绕场一周,四周人群不时发出笑声和欢呼声,并不断地向场中丢钱币。一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父亲和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街场。
第一次去三月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这样的交易环境在现在看来显得较为简陋且不够规范。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重视,三月街的交易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的三月街,有了规范的交易场所、摊位和分区,街面环境变得更为卫生、整洁。
第二次到三月街是1959年。我从小就是一个影迷,为看一场电影可行走十多里路。拍电影《五朵金花》时,我正在凤仪中学读初三。我的一位同学在大理一中读书,老师告诉他们要拍摄赛马一场戏,需要群众演员,同学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我,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拍摄现场。
到现场后,我立即窜入人群,像一条泥鳅一样往人群的最前方钻。当我站定,终于看到扮演阿鹏的演员莫梓江,牵着一匹马走进赛场。他在导演的指挥下,骑上马表演赛马夺红旗的片段。当他骑上马的那一刻,周围的群众欢呼雀跃,人人都目光灼灼地望向他。也许是周围人群给予他的压力太大或是由于不擅长骑马,“阿鹏”过度紧张,连连失手。赛马的这场戏结束后,我也离开了现场,但当电影放映时,阿鹏最终还是把夺得的一把红旗送到主席台上,并获得了一支猎枪的奖励,同时也赢得了副社长金花的爱情。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还在心中猜测着这个镜头的完成是因为导演找了替身还是因为最终的巧妙剪接,总之这一幕在我脑海深处久久定格着,困扰我多年。

作者与电视剧《五朵金花的儿女们》演员的合影
直到1990年,莫梓江为拍摄电视剧《五朵金花的儿女们》时,我也为拍摄、编撰电视片《金花阿鹏故乡行》,与他亲密相处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把当年心中的疑惑告诉了莫梓江,问他最终如何完成骑马夺红旗的戏。他对我说,当年他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王家乙选中了他扮演阿鹏一角。当时他心中一点没底,骑马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由于他自己的骑马技术达不到要求,为了完成骑马夺红旗的戏,导演只好请道具师找来一辆敞篷吉普车,他坐在车上侧身出来拔旗。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共同完成的杰作啊!
第二次游三月街的记忆和对《五朵金花》电影的深刻回忆,让我深刻意识到三月街与《五朵金花》有着不解的缘分。电影《五朵金花》里出现的三月街的盛况,也唤醒了我对三月街久远的记忆,弥补了某些被我遗忘的细节,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对过去三月街传统的一种留存和保护。记得当年看电影时心中的惊叹,电影的各个场面和细节仿佛完美复制了印象中的三月街,电影开场里出现了热情奔放的青年男女,打着霸王鞭,敲起八角鼓,唱着欢快的民歌,热情地庆祝着节日的到来,也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四方宾客。镜头中的赛马场也与如今大不相同,当年的赛马场是苍山脚下一片空地,马蹄子一蹬便尘土飞扬,而如今的赛马场,设立了整齐的跑道和看台,越来越规范化。在我心里,三月街与《五朵金花》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三月街让《五朵金花》增添异彩,而《五朵金花》使三月街声名远播,二者如同珠联璧合般相互辉映,照耀世间。
历经“文革”的冲击和物资的匮乏,三月街曾经一度萧条。直到1969年,大理市革命委员会将三月街改为了“五月忠字大会”。这一年,我被当时的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派往三月街负责大会广播的宣传。我从当时的大理县借了收扩音机、唱机、话筒等设备,组织人员在街场四周架设了十多只高音喇叭,并抽调了两位女播音员来负责播音工作。
当年的三月街广播工作也异常辛苦,我们每天从早上六点三十分就开始播音了,首先播放《东方红》等革命歌曲,接着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我用尽千方百计,找到电影《五朵金花》歌曲准备播放,可领导说,那是一部“三无”影片(即无党的领导、无总路线、无三面红旗),宣传恋爱至上,不能播。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只好忍痛割爱。我们每天循环播放革命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播有关三月街的新闻、通告、交易情况及文娱表演,有时还播寻人启事。为了制造热闹气氛,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达到十多个小时。“忠字大会”从5月1日开幕到5月8日闭幕,由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为大会营造了热烈、欢乐的气氛,在组委会总结、表彰时,我得到了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和一枚毛主席大像章的奖励。
1991年,大理州人民政府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条款决定将三月街定为民族节。我以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性,第一时间在大理电视台《大理新闻》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同年1月30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的决议》,自此三月街就成了大理州各族人民进行盛大欢庆的法定节日。此后的二十多年,每年三月街都会举行隆重的开幕式、盛大的文娱表演、丰富多彩的欢庆活动、异彩纷呈的赛马活动及热闹的经贸交易活动。而所有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地参与了宣传报道,成为最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我对三月街充满了深深的回忆和满满的感情,我与它的不解之缘还促使我编撰了《三月春光漫苍洱》《大理三月好风光》《美好的三月,欢乐的白州》《白州三月涌春潮》《民族盛会喜空前》等五部电视专题片。这些专题片先后多次在大理台和云南台播出,同时还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播放,更广泛地向世界宣传了这一民族盛会。
白族狂欢绕三灵
绕三灵是大理白族人民最盛大的传统歌舞节日,是白族人的狂欢节、情人节。
1986年,台湾长乐公司制片人刘家庸先生在云南省广电厅处李本钊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大理,打算拍摄《万里江——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刘先生到大理后指定要我协助拍摄,我非常荣幸地两次陪刘先生在大理拍摄关于博南古道和巍宝山的电视片。其间我俩配合密切,使拍摄获得很好的效果。这个节目在台湾的影响力很大,连续在台湾被评为收视率最高、最受观众喜爱的十大电视节目第一名,还曾获得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金钟奖”。为了让更多台湾观众了解大理的风土人情,这次刘先生来大理就是专门拍摄绕三灵活动的。
绕三灵是大理洱海地区白族农村的一种游春、歌舞节会,它主要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绕三灵是一种宗教活动,包含着对神灵的信仰和朝拜,白族人民在节日中祈求神灵赐福消灾,风调雨顺,寄托美好的节日祝福;其次绕三灵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男女之间的纵情歌舞,颇具民族特色。绕三灵在时间和空间上也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长,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共三天;二是地点分散,涉及三个地点,分为“佛都”崇圣寺、“神都”喜洲庆洞圣源寺、“仙都”喜洲河矣村金圭寺三处,此外还具有自发聚集、自愿组合等特点,这些特点也给我们的拍摄带来一定困难。
根据上述特点,我们首先做了认真的案头工作,精心策划,周密布局,合理安排。由于刘先生只带来摄像师,没有主持人,他邀请我当该片的主持人,所以我身上的担子很重,压力也陡然增加。
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清晨,我们赶往“佛都”崇圣寺三塔,绕三灵活动就从这里拉开了序幕。当我们抵达崇圣寺,就被眼前的壮观场面震撼住了。只见一队队红男绿女,身着颜色艳丽的民族服饰,在边舞边唱。每个歌舞队列领头者均为男女二人,他们各以一手共执一株齐人高的柏树技,另一手则分别挥舞牦牛尾和花手巾,一边跳着动作极为夸张的舞蹈,一边用白语唱着曲调悠扬的民歌。紧接着的人群则围绕在崇圣寺周围,打着霸王鞭,跳起八角鼓舞,男男女女配合密切,背靠背、心合心、脚勾脚,无拘无束地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对节日的热忱。
现场的热闹气氛感染着我,我甚至也想置身于着歌舞的海洋中,同他们一起欢快地舞蹈,然而当我看到眼前的摄像师傅时,一种职业的敏感性让我立刻专注起来。摄像师以我身后打歌的人群为背景,把镜头对准了我这个现场主持人。我面带微笑地向着镜头简要地介绍了绕三灵的来源和活动的内容。我身后热闹的人声、歌声快将我的声音淹没了,我不得不放开嗓门,声音洪亮地介绍着。随后,被这里的气氛所感染,我声情并茂地朗诵了白族学者赵甲南的《咏绕三灵》一诗:
淡抹浓妆分外艳,游行手执霸王鞭。
咚咚更有金钱鼓,且舞且歌为飘然。
欣逢四月最清和,簇簇游人此日多。
六诏遗风今尚在,诸君莫笑是夷歌。
红男绿女喜春游,山麓海滨绕一周,
廿四已过人影散,归家返道事田畴!
情景交融的诗歌与我身后载歌载舞的人群相得益彰,现场的活动如此真实地反映了诗歌描述的场面,而这首诗也成为对这一盛会的最好注解。
中午,活动暂停一个段落,我们也在附近吃了点东西。填饱肚子后,我们找了一辆马车,载着摄像机、录像机、脚架等仪器,紧跟着春游队伍,且行且拍。马车跟随着游行队伍,直到下午五时,队伍到达了苍山脚下五台峰庆洞村的圣源寺。这里以供奉“中央本主”南诏清平官段宗榜而有“神都”之称,从而成为绕三灵的中心活动地点。
我们刚到达这里,顾不上休息,立即架起摄像机,拍下了人们烧香磕头,唱诵经文,祈祷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镜头。紧接着又到野外拍摄了群众打起霸王鞭,跳起八角鼓,男女唱曲对歌的动人场景。这样热闹的歌舞活动彻夜不休,通宵达旦。看着摄像师捕捉着一个个生动而有价值的画面,我的内心也异常激动澎湃。顾不上鬓角的汗水和早已干渴的喉咙,我也颇为卖力地讲解着每一个画面。
第二天清晨,青纱般的薄雾像是给洱海铺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在苍山五台峰上时,人们又整装出发了。人们一路载歌载舞,路过一畦畦绿色的田野,四处荡漾着节日的喜悦。在经过喜洲各村庄之后,游行的队伍来到洱海边河矣村号称“仙都”的金圭寺。金圭寺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气势恢宏、典雅古朴的庙宇沐浴在一片金色的日光下,让人感到一阵庄严肃穆。人们在这里停下,并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狂欢活动。我们照例跟拍着,工作人员们早已对拍摄驾轻就熟,选择最佳角度,拍下许多精彩镜头。待夜幕降临,我们才停止拍摄。
第三天,欢度节日的队伍又再沿着波光粼粼的洱海,一路南行,绕回大理古城城东的马久邑村。在马久邑的本主庙前,人们又开始载歌载舞,唱和对答。在祈祷仪式后,大家尽欢而散。至此,持续了三天的绕三灵狂欢活动终于落下了帷幕。让我深感震撼的是,这三天来,参加歌舞活动的大多数是老年人,然而大家的身姿依旧矫健灵活,脸上时刻都保持着热情洋溢的笑容,丝毫让人感觉不到他们的疲惫。
我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终于也可以放下主持人的包袱,虚心向他们学习了霸王鞭和大本曲。我紧跟着万人狂欢的队伍,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着舞蹈着融入他们,虽然歌声不是那么悦耳,舞姿也不甚优美,但我相信我的热情早已掩盖了我的不足。我跟着他们边跳边唱道:
万众欢腾不停步,
佛都神都又仙都。
四天三夜尽狂欢,
人间情永驻!
在欢庆的间隙,我们釆访到一位扮成女巫的白族大妈。大妈已有七十二岁,她一共参加了五十多年的绕三灵活动。在询问她为何坚持不懈地来参加绕三灵活动时,大妈说道,参加绕三灵活动,不仅能让心情愉悦,还能让身体也越来越健康。我们都相信大妈说的话是真的,因为在亲自参与过后,我们的心情明显更加愉悦了,而且歌舞唱跳确实能起到锻炼身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在她的带动下,她的儿子、女儿也都多次参加绕三灵活动,儿子的对象也是当年在绕三灵活动时找到的。可见绕三灵在当地是一个全民参与度极高的盛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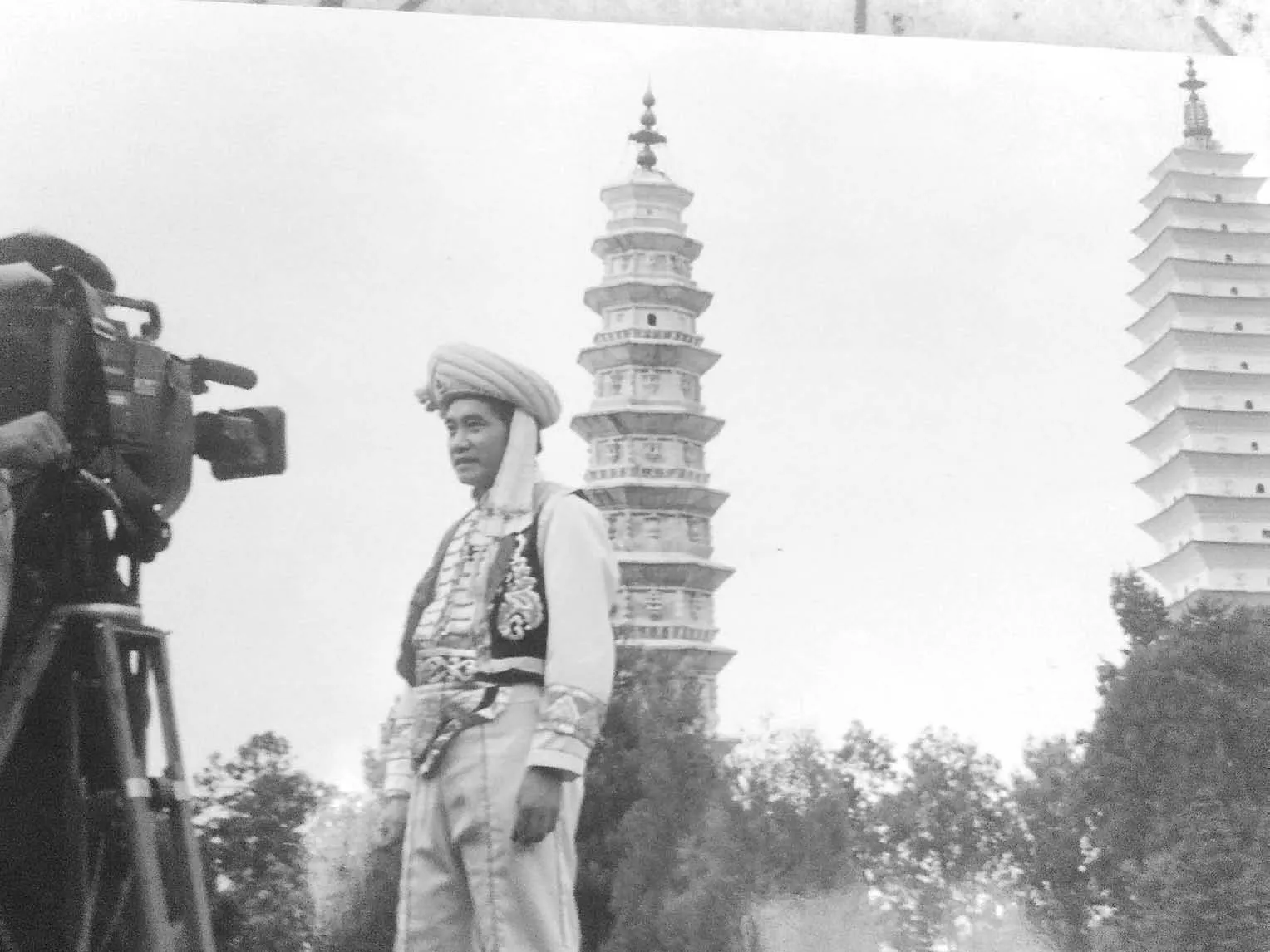
作者主持绕三灵活动
这次狂欢活动,我们共拍摄了十多盘录像,刘先生真是满载而归。回到台湾后,这些录像带经过后期剪辑、制作之后,在电视上顺利播出,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刘先生来电说,许多台湾观众看了后,纷纷表示要到大陆来,亲自感受这狂欢的节日,歌舞的盛宴。
神奇白族火把节
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白族传统的火把节,白语称为“夫旺舞”,意为“六月狂欢”。这一天,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山区、坝区,皆普天同庆。在白族人心目中,这是仅次于春节的最隆重的节日,也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里,火把节是幼年时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好时机。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全家一起同心协力地准备过节的各项事宜。首先,大家要一起动手制作“升斗”和三角小旗。“升斗”和三角小旗都是火把节上燃烧的吉祥物,“升斗”是用彩纸制成的形似三个升斗的装饰物,一般置于火把顶端,象征着“连升三级”的美好寓意。三角小旗则是用彩纸做成的三角形的小旗子。这些吉祥物都是用于装饰火把的。此外,我家还会买回来火把、松香、水果等庆祝节日的必需品。火把节这天的清晨,我在自家门前栽下火把,插上“升斗”和彩旗,同时挂上一串串海棠、苹果、梨等被称为“火把果”的水果,寄托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美好祝福。原本朴素无华的“光秃秃”的火把被吉祥物和形形色色的水果装点得如同一棵圣诞树一般灿烂绚丽。
待吃晚饭时,家里还会喝上点雄黄酒,寓意去除邪祟。傍晚时分,还会有一个个骑手骑着马从家门前飞奔而过。晚饭过后,夜幕降临,家家开始燃起小火把。顷刻间,整条街化为一条火的长龙。一条接一条的街被火把点亮了,宛如一条又一条蛰伏的巨龙在渐渐苏醒,往日里寂静的街市被火光照耀得宛如一片火海,真如诗里写的那般“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落人间”。然而火把节最吸引人和最有参与感的环节并非欣赏火把燃烧的姿态,而是“闹”火把。当火把燃烧到一半时,我把小火把拔出来高举着走向人群,从包里抓出一把松香末儿,对着火把撒向人群。这样的举动看似危险,却是一种出于善意的传统习俗,将火光引向他人其实是为别人消灾驱邪,寓意清吉平安。小时候我也会有玩火把烧到衣角甚至头发的时候,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年幼时天真爱玩的心性。紧接着,我举着火把走向田野,将火光照向田野的庄稼,据说这样会让庄稼长得更好,可保五谷丰登。
时光匆匆而逝,1965年,我正从事水利工作。六月中旬,我到邓川检查弥苴河防洪堤坝时,正值白族火把节。吃过晚饭后,我登上了德源山,走进德源城,朝拜柏洁夫人。这里就是白族火把节的发祥之地。
关于柏洁夫人的故事,我也早已烂熟于心。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为吞并洱海地区的五诏,于农历六月二十五日邀请五诏国王到松明楼上赴宴。洱源的邓赕诏王妻子柏洁夫人,聪明睿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给诏王夫君打了一副金手镯带在手上。入夜,五诏国王在松明楼上狂欢,此时南诏王掷杯为号,顷刻松明楼火光四起,五诏国王全部被烧死。柏洁夫人得到噩耗后,星夜骑马飞奔到松明楼前,用双手从废墟中刨出带着金镯的丈夫的遗骸。柏洁夫人的十指都被刨出了赤红的鲜血,所以火把节时白族青年妇女都要将指甲用凤仙花的汁液染红,以示纪念。
正当我在追忆这段感人肺腑的历史时,周围的群众开始抬着供果,举着香案,向这位聪明善良的柏洁夫人朝拜。朝拜完毕,我走出庙门,站在山顶,眺望整个邓川县。只见右所等区域火光一片,鞭炮的响声远远传来,如阵阵雷鸣,响彻夜空。除熊熊燃烧的大火把之外,星星点点的小火把也在夜空中闪烁。小火把们像一颗颗明亮的星子,点缀、映衬着绽放得如同一朵莲花般绚丽的主火把,呈现出“星宿别从天畔出,莲花不向水中芳”的壮丽景象。这一夜的盛景一直停留在我脑海中,不曾忘却。
时间又到了2000年农历六月,我应日本NHK电视摄制组的邀请,到周城拍摄白族火把节盛况。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这天清晨,我们赶到周城菜市场的古戏台前准备拍摄工作。当我们刚架好摄像机,就看见一群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的盛装,络绎不绝地向这里走来。在欢快的唢呐声中,人们忙着扎制大火把。这棵火把长约五六丈,整体以木柴、松香、稻草等捆绑,上面插满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三角旗、红香,再挂上梨串、苹果、海棠等水果,最后还要在顶端装饰上一个比我家自制“升斗”大很多倍的大型“升斗”,上面写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字样,象征着村民们的美好祝福。
周围的老爷爷们演奏洞经音乐,老奶奶们齐声念诵经文,一时间乐声、诵经声、孩童们的欢笑声不绝于耳。当家妇女则带着孩子,端着米、盐、酒、茶等食品前来供奉。火把扎好后,要由老人们以“三牲酒礼”祭祀,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在此之后,火把便由村里年内生男孩的父亲们竖立起来。
当暮色降临,所有群众围着火把绕三圈后,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在唢呐鼓队的护送下,从本主庙中取出火种,将火把点燃。顷刻间,烈焰熊熊燃起,鞭炮齐鸣,人声沸腾。男女老少载歌载舞,围着火把转圈,孩子们则争抢烧落下来的“火把果”,意为迎祥纳福。这时青少年们高举着手中的小火把,不断向人群撒松香,顷刻飞出一团团烈焰。人们互相追逐着,喷撒着,以示祝福。
看着热闹的人群,我也不自觉地被这样欢腾喜悦的气氛所感染,融入到欢乐的人群中,与人们一起烧火把、撒松香。我将一把松香撒下去,腾起的火光和烟雾掩映着周围人的笑颜。即便大家的衣物在这一夜过后都可能被染上一股烟火味,但大家都毫不在意,而是放松而尽情地享受着节日带来的欢乐。这时整个广场人声鼎沸,火光璀璨,呈现出一派“火树银花不夜天,欢歌曼舞铺锦霞”的景象。
日本电视摄像师用三台摄像机,在不同地方,从各个角度,全过程拍摄下这狂欢场景。导演还不断地向我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回到住地,他高兴地说,这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有诗意,最令人激动的场景,要精心制作好这部《云南之春——白族火把节》专辑,大力向日本人民宣传美丽神奇的大理。
多少年过去了,这些传统节日继续在大理洱海地区延续着,传承着。虽然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对很多传统习俗的来源不甚了解,许多过去必要的节日仪式也在不断被简化,但每当节日来临,喜悦的氛围仍旧会笼罩着整个苍洱大地。每次过这些传统节庆的时候,那些深藏在我记忆中的现在已经逐渐被人遗忘的节日细节,都会被我一一捡拾,一一回味,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编辑手记: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地在向前行进,留下一道道或浅或深的车辙,却很少有人会沿着这些车辙去回溯历史从前的面貌。许多在过去隆重、热闹的传统节日庆典也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人们不再会严谨地按照传统仪式、习俗去庆祝这些节日,而是纯粹地把它们当作一个个休闲放松甚至娱乐狂欢的假日。在如今的大理,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并不知道“春醮会”是什么节日;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没有参加过“绕三灵”;对于“三月街”的印象标签就是“人挤人”,宁愿在这个节日里去外地旅游;“火把节”里高举着火把肆意挥舞却不知有何意义……时代在进步,有些传统被摒弃了,被遗忘了,有些传统虽然在延续却丢失了原本的面貌。而本文作者郭锋则在记忆中回溯这些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通过自己从前过节的经历,向我们介绍和再现了大理洱海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如:“春醮会”、三月街、火把节、“绕三灵”等。由于作者是一位媒体工作者,他的工作能让他有机会以媒体人的视角近距离接触这些节庆活动,并能快速敏锐地发掘这些节日的特点,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传统节日的流程和主要活动,还原一些早已丢失的节日细节,再现传统节庆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