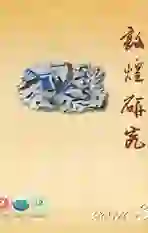四件散见敦煌契约文书
2018-09-17陈丽萍
陈丽萍
内容摘要:以四件散见的敦煌契约文书为主题,介绍了四件文书的收藏背景,对文书的物质形态和内容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过录,并就同类契约涉及的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对敦煌契约文书的收藏状态和研究路径也有所展望。
关键词:敦煌;散见;契约
中图分类号:G256.1;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3-0101-06
Abstract: Focusing on four newly-found Dunhuang contract manuscript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historyof their collection, then mak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contents, and finally discusses sever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type and nature of the contracts. It concludes with a short commentary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Dunhuang contract documents.
Keywords: Dunhuang; scattered; contract manuscripts
筆者近年对敦煌(汉文)契约文书颇为关注,也为新刊敦煌文书图版所吸引,对日本杏雨书屋藏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契约文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刊布{1}。前有池田温与山本达郎[1,2]、唐耕耦[3]、沙知[4]、乜小红[5]等先生的成就累积,可以说,世界各国大宗所藏敦煌契约文书的刊布,目前已几近全面了{1}。但因敦煌文书的流散状态和不同收藏机构的公布程度,使得仍有一些零散文书,近年才渐次为大家所知。本文即以散见的四件敦煌契约文书勉成小文,以示对同类文书的持续关注。
据王素等先生介绍,故宫博物院所藏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契约,暂定名《丙戌年五月十日敦煌百姓李福延借贷契》。该契约所属的文书编为新152372号,与新152095《酒帐》、新152369《财产分配帐》、新152371《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新153255《修道六观门讲经》等几件文书皆为上海文化名人邵洵美旧藏,于1963年7月购入[6,7]。
经向故宫博物院申请并获批,笔者于2017年初得以查阅新152372号原卷。该文书高31厘米、长42.5厘米,正反面皆为比较工整的楷书,所抄内容也较多。正面抄三种内容,依次为:“梵字佛顶尊胜真言”9行、“李福延契”4行、“六念唱本”5行。背面所抄也是三种内容:“十二时唱本”9行、“十二时唱本”8行、“六念唱本”4行。值得注意的是,正、背面所抄的两段“六念唱本”内容无差,但各有文字脱漏;背面所抄的两段“十二时唱本”内容也大致相同。不过以上各类所抄的内容皆不完整,结合本文所要探讨的契约(详下),可知该卷是一件混抄了各种内容的稿本,皆非实用文书。现将其中所抄契约摘录如下,以便论述:
1 丙戌年五月十日立契。敦煌[乡]百姓李福延欠少匹白(帛),遂于
2 慈惠乡百姓李不勿面上贷白生[绢]一匹,其绢和长叁仗(丈),匹
3 叁仗(丈)捌尺伍寸,幅阔壹尺伍寸。其绢利头{2},限至来年五月十日
4 填还本绢者,若于限不[还]本绢者,看乡元生(后空缺)
“李福延契”与前“真言”间约有两行间隔,首行也略为下移书写。从内容来看,这是敦煌乡百姓李福延向慈惠乡百姓李不勿贷白生绢一匹,借期为一年的一份借贷契,但仅抄至违约生利部分结束,既没有契尾借贷双方的画押签字,也没有保人证人等出现,故这是一份夹抄在其他内容之间的契约文稿,而不是实用文书。据笔者对敦煌借贷契约的定名标准,为该契约重拟名《丙戌年五月十日敦煌乡百姓李福延贷绢契(稿)》。
目前所见的敦煌借贷契约,主要分为粮食和纺织品两类,其中纺织品又可细分为褐、布、缯、绫、绢等的借贷,但最为常见的还是绢类借贷契,约有30多件。李福延契的发现,为现存的敦煌契约文书中又增添一件绢类借贷契。
新152372号被王素等先生确定为归义军时期的抄本,其中李福延契中的“丙戌年”应是确定抄本时期的一个重要依据。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丙戌年,有唐咸通七年(866)、后唐天成元年(926)、北宋雍熙三年(986)三个年份,参照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系,当依次在张议潮、曹议金和曹延恭时期[8]。但敦煌契约文书中可资参照比较的“丙戌年”契极少,笔者所见仅有P.3211v《丙戌年(926?)庆奴借地凭(习字)》、S.5504《丙戌年(986?)丁亥年(987?)付令狐愿德身价麦粟凭》两件[4]336,406,沙知先生对它们的所属时期其实也不确定。
结合“李福延契”与其他纺织品借贷契中的关键词(如“面上”“利头”“乡元生利”)及书写格式相较,如P.2817v《辛巳年(921)敦煌乡百姓郝猎丹贷生绢契(习字)》“辛巳年四月廿日,敦煌乡百姓郝猎丹家中欠少匹帛,遂于张丑奴面上贷生绢一匹……其绢利头须还麦粟四硕……若于限不还者,便看乡原生利”[4]180。Дx.1377正背《乙酉年(925)莫高乡百姓张保全贷绢契》“乙酉年五月十二日立契。莫高乡百姓张保全伏缘家中欠少匹帛,遂于慈惠乡百姓李阿察面上贷黄丝生绢一匹……若于限不还者,准乡原例生利”[4]185-186。S.766v《甲申年(984)平康乡百姓曹延延贷绢契》“甲申年五月廿二日立契。平康乡百姓曹延延伏缘家中欠少匹帛,遂于龙勒乡百姓张万子面上贷白丝生绢一匹……其绢利头现还麦粟四石……若于限不还者,便看乡元生利”[4]234。
可见,敦煌纺织品借贷契的书写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在没有其他判断标准辅助时,“李福延契”中的“丙戌年”为926年还是986年,很难确定。
有意思的是,新152372号正面所抄“六念唱本”第2—3行中有“第三念,岁次丙戌五月四日得受具足戒”句;背面所抄“六念唱本”第2—3行中有“第三念,岁次丙戌五月十日寅时初分初时受具足戒”句。两句中的时间与李福延契中的“丙戌年五月十日”几乎一致。这说明,可能抄手当时转抄的契约和六念唱本皆是“丙戌年”的底稿,抄写时间或在当年,或已在之后;而且从该文书所抄的六种内容来看,其中五种集中于佛教方面,契约其实并非该卷的重点,这与敦煌文书中不少杂抄于其他内容中的契约稿本存在模式相类,也透露出一点信息,即可以从这种模式中审视(被抄写的)契约范本的流传程度,以及对时人将契约与其他类型文书混抄的心态理解。
据施萍婷[9]、荣新江[10]、方广锠[11]、司马立心[11]6-8、王惠民[12]几位先生介绍,日本收藏家滨田德海所藏的一百多件敦煌文书,大部分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购入的,其中不少為李盛铎旧藏品。在其身后的1960年12月,家人将部分藏品售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部分仍秘藏于本家族内。近年,中国的伍伦拍卖公司一次性回购了36件滨田德海旧藏品,并于2016年9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拍卖会上将这36件文书再次售出(少数流拍),方广锠先生编著的《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所收正是这批文书的彩色图版并配以详细题解。对敦煌学界而言,滨田德海藏品的这次面世,可谓意外之喜。
《蒐藏》所收的36件敦煌文书皆以“伍伦”编号,绝大多数为佛经,其中仅有四件社会经济文书,其中伍伦03号与伍伦36v号或皆为契约,另外两件分别为伍伦27-1《黄仕强传》、伍伦32《五月五日下菜人名目钞》,因与本文主题无关,也不过多涉及。
伍伦03号(滨田德海旧编13号),存5行,高6厘米、长10.8厘米,拟名《敦煌洪润乡洪池乡百姓借贷契约》,判定为9—10世纪的归义军时期写本(图1){1}。因《蒐藏》的录文断句与笔者有所不同,先将该卷过录如下:
伍伦03号墨色不均,字迹潦草,文书的四周剪裁齐整,故上下左右文字皆缺。因该卷又经现代托裱在纸板上,其背面情况无法得知。据敦煌文书中的常见状态判断,这种被裁剪成齐整碎片状的文书,很可能是(或备用于)其他文书(主要是佛经)背面的裱补纸。笔者所见国图藏敦煌契约文书中,如BD16030、BD16111I、BD16115、BD16130、BD16134、BD16162等号,皆是揭自佛经背面的残片。但因缺少初始文字记载,不知伍伦03号是单独的一件残片,还是揭自某件文书的背面。
还据方广锠先生的题解及图版,伍伦03号左下角的纸板上还有椭圆形阳文小朱印,印文为“杨氏/永宝”,说明该卷曾属于某杨姓人物,因笔者对敦煌文书的流散状况及收藏印鉴没有专门研究,一时无法核查此人的具体身份。
伍伦03号因头尾皆失,很难判断文书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性质。从文中存有“阔壹尺玖寸”“生利”“故立此契”句,可初步判知该契与纺织品有关。与其内容相类的敦煌契约还有,如S.4504v《乙未年(935?)押衙就弘子贷绢契(习字)》“就弘子……遂于押衙阎全子面上贷生绢一匹……幅阔一尺八寸三分……其绢限一个月还……逐月于乡原生利”[4]197。P.3501v《戊午年(958)兵马使康员进贷绢契(习字)》“康员进……遂于兵马使索儿儿面上贷生绢一匹……幅阔一尺九寸……其绢西州到来,限一月填还”[4]219-220。可推知伍伦03号似为一件绢类借贷契,但因首尾皆失,也不知该卷是稿本还是实用文书。
至于借贷人的属籍,方广锠先生认定的“洪润乡”之“润”,其所存笔画过少,故为求稳妥,为伍伦03号重拟名《三月廿二日某人向洪池乡百姓贷绢契》。
伍伦36号(滨田德海旧编149号),存66行,高29.2厘米、长92厘米,拟名为《瑜伽师地论义疏》,判定为9世纪的归义军时期写本。该卷背面有古代裱补纸,今编伍伦36v号,仅存3行,拟名《残地契》,判定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2){1}。同样,因《蒐藏》的录文断句与笔者有所不同,本文仍将该卷过录如下:
伍伦36v号字迹较为清晰,个别字有改动,上下左右文字皆缺,同样是被裁作裱补纸斜贴在《义疏》的背面。关于该卷的性质,因为其中出现了东、西、南、北四至,以及“地”“园”“步”等表示土地和丈量单位的词,首先能确定这是一件与土地有关的文书,进一步推想,该件可能会是有关土地交易的契约。
从现存敦煌土地交易契约的内容来看,房屋地基类的契约,一般以“丈”“尺”为丈量单位,而田园类的契约,一般以“亩”“畦”“步”为丈量单位,伍伦36v号可能与后者相关,其所存内容与S.3877v《天复九年己巳(909)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卖地契(习字)》[4]18-19、P.3649v《后周显德四年(957)敦煌乡百姓吴盈顺卖地契(习字)》[4]30-31等卖地契中田地四至丈量的部分有接近的地方,但格式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仅从格式看,S.4661正背《园地计簿》、S.4760《园地计簿》{2}两件文书,也是仅残存了丈量田园四至的残片,伍伦36v号与它们更加接近,但学界对这两件文书的性质也没有确切的说法,若将它们都看做田地交易时的一个丈量记载,也能说得过去,故方广锠先生将该件定名为《残地契》,应该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不过鉴于该文书的内容及抄写格式与现存土地交易类的契约文书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笔者可能更倾向于将伍伦36v号笼统定名为《园地计簿》。
众所周知,敦煌藏经洞内的藏品,除了数量居多的纸质抄本外,还有少量的绢、麻、纸质的图画,以及纸质拓本与印本,这些图画与印本等也分藏于世界各收藏机构。其中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纸质印本统一编为Or.8210/1-20号,学界惯于以简编号S.P1-20表示。这批印本的图版在《英藏敦煌文献》中已集中刊布[13],其中S.P6《乾符四年具注历日》(高29厘米、长115.5厘米),首部由某残(存3行)契约抄本裱衬,拟名《残契(写本)》。这一残契也见录于沙知、池田温先生书中,前者说明“此件写于刻本具注历日右侧,当系习字”,后者分辨了其为“具注历日贴片”[4]560[2]64-65。可能由于英藏敦煌文书出版时,文书的修复和拆分工作尚未进行到S.P6号,或者是刊布者仅关注了其印本特性,对其他部分有所忽视(详下)。
除了S.P6号卷首的裱衬残契外,《英藏敦煌文献》还刊印了其卷尾1件和背面2件抄本裱补纸的图版。其中卷尾处的抄本存1行,未有定名和说明。背面的一件抄本存4行,拟名《翟都头守州学博士赠麴大德文书一本记(写本)》;另一件抄本存8行,每行仅存1—2字,未有拟名和说明。如今,IDP网站上的彩色图版,为我们展现了S.P6号正面2块以及背面4块裱补纸的原貌,笔者据排列次序将它们分编为S.P61-2(裱补纸)与S.P6v1-3(裱补纸),以便行文叙述。
S.P61(裱补纸)即前贤关注过的残契,经拆分后约高29厘米、长16厘米,可看到存有7行文字,背面即为已刊印过的翟博士写书记;S.P62(裱补纸)约高29厘米、长3厘米,可见2行文字,即“四月廿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写(墨书)为{1}/报麴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朱书)”,背面无字。从内容判断,S.P6号所附的这两件翟博士残片当出自同一卷。
S.P6号背面裱补纸的情况较为复杂,如
S.P6v1(裱补纸)与另一块残片粘连,皆为3厘米左右见方,残存文字很少,书法也潦草,勉强可辨识“骨、头、为”几字;S.P6v2(裱补纸)也是一块3厘米见方的残片,背面无字,正面可辨识“项、骨、火”几字。S.P6v3(裱补纸)即残存8行文字的那块残片(高29厘米、长26厘米),背面还有“慈惠”二字,据其内容分析,S.P6v3(裱补纸)从第5行起与S.P61(裱补纸)可完全缀合,位置在其正上方。先将缀合后的文字过录如下,其中加黑字为S.P6v3(裱补纸),加圈字为两卷共存笔画的字,原字部分出自S.P61(裱补纸)(图3)。
前贤与《英藏敦煌文献》编者对这件残契没有全面关注,实际上,沙知先生等仅做了其第6—8行的部分录文。缀合后的残契有11行,虽然依然缺少起首、第1—4行的下半段,以及第5行中段的内容,但据第9—11行的内容可知,该件是王盈信为某事的雇人契,与其兄长、表叔皆有画押,说明这是一件实用文书,其价值颇高,也因此将其拟名为《某年王盈信僱工契》。
敦煌文书中的雇佣契有近40件,雇人的缘由也很多,参考契约的书写格式与内容,还有如BD06359v《寅年(822)僧慈灯雇博士氾英振造佛堂契》“一定已后,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麦三驮,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此契”[4]242-243;S.3877v《戊戌年(878)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雇工契(习字)》“不得抛功,一日勒物一斗。……两共对面稳审平章,更不许休悔”[4]248-249;S.5578《戊申年(948?)敦煌乡百姓李员昌雇工契(习字)》“若忙时抛一日,尅物二斗;闲抛功一日,尅物一斗。两共对平章,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麦叁驮,充入不悔”[4]272-273等雇工契中的用词与王盈信契颇为接近,可进一步推断这是一件雇人从事农活的契约。此外,S.4654v《丙午年(946)前后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百姓王盈子兄弟四人状》[3]300是王盈子兄弟为其弟盈进死后债务问题的诉状,但其中并无盈信出现。不过,王盈信契的背面也有“慈惠”二字,或许这两件文书中的王盈子是同一人,如此,可能会对判断王盈信契的年代提供更多的参考。
本文刊布了四件散见的敦煌契约文书,并为其录文和重拟定名。这四件文书,从藏地来看,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两件旧藏于滨田德海(私人),一件藏于大英图书馆,正好涵盖了我们所知的三种(国家、地方、私人)敦煌文书收藏形式。从性质来看,两件为绢类借贷契,一件可能为土地交易契,一件为雇佣契,其中可以确定新152372号为稿本、S.P6v3+S.P61(裱补纸)号为实用文书,其他两件则不详。尽管这四件文书皆为残片,但它们的再次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笔者以为,敦煌契约文书的刊布、汇集、再整理的数年间,学界可能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品相较好、内容相对完整的契约,对一些残片、稿本(乃至杂写类)契约的关注不是太多,随着各国各地所藏敦煌文书的不断刊布,这类文书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關注。
首先,各地所藏的契约残片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缀合或衔接关系,这需要根据契约的内容或物质形态进一步判断。尤其是被切分为若干块裱补纸的契约,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再追踪,应该还会有所收获,这对复原敦煌文书的原貌而言,也是一项有所裨益的工作。
其次,从文书使用和作废的角度出发,统计出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敦煌文书背面裱补纸的不同内容,应该也会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再次,将各类杂抄于其他内容之间的契约稿本再次融入原属的文书,将每件文书同时所抄的其他内容进行罗列对比,分析契约和其他内容出现的比率,将会对古代敦煌地区的文书抄写历史或理念有更深的理解。
最后,虽然大家熟知的英、法、中、俄等国家级机构所藏的敦煌文书图版刊布已毕,但因为各种原因限制,很多文书的原貌并未完全展现,要研究相关文书,仍然需要再次找寻原卷或借助IDP上公布的彩色图版。至于一些小众机构所藏敦煌文书的刊布,仍有很多未知因素困扰。
附 记
本文的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锦绣、刘晓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的王素研究员与陈秋速、郎为先生,浙江大学的刘进宝教授、国家图书馆刘波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赵贞教授、西北大学裴成国副教授的大力帮助,谨致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
[1]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Tokyo,1986—1987.
[2]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Ⅴ,Tokyo,2001.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4]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王素,任昉, 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J].敦煌研究,2006(6):173-182.
[7]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提要(写经、文书类)[M].故宫学刊: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561-581.
[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章: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0-147.
[9]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三)[J].敦煌研究,1995(4):51-70.
[10]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215-217.
[11]方广锠,编著.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序言[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1-5.
[12]王惠民.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简介[OL].[2016-9-26].http://public.dha.ac.cn/centent.aspx?id=816685432177.
[13]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4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