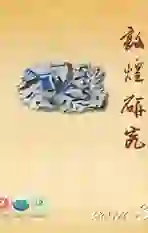敦煌藏3叶婆罗谜字梵语—回鹘语双语《法身经》残片释读
2018-09-17范晶晶彭金章王海云
范晶晶 彭金章 王海云
内容摘要:敦煌研究院藏3叶婆罗谜字梵语-回鹘语双语残片。本文认定这3叶残片所书文本为《法身经》。通过对目前已经发布的《法身经》的不同写本进行比较归类,进一步判断这3叶残片属于丝路北道的《法身经》写本系统,与南道的《法身经》写本系统有所区别。本文还对残片进行了换写、转写与释读,并参照《法身经》的五个汉译本,对经文的性质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梵语;回鹘语;婆罗谜字;双语;写本;《法身经》
中图分类号:G256.1;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3-0091-10
Abstract: Three leaves written in Brāhmī script kept in the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parts of a bilingual text of Dharmaarīrasūtra in Sanskrit and Uigur. After analyzing several versions of
Dharmaarīrasūtra,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se three fragments belong to the Northern Brāhmī recensions circulated along the Northern Silk Road, which differ from the Southern Brāhmī recensions popular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Road, such as the Khotanese ver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nscribe these fragments and make a thorough research on Dharmaarīrasūtra, taking the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s into account.
Keywords: Sanskrit; Uigur; Brāhmī; bilingual; manuscript; Dharmaarīrasūtra
一 残片的最初发现、收藏以及再发现
敦煌研究院旧藏的3叶婆罗谜字残片,原为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期间获得并收藏。据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在其撰写的《西征小记》中记载:“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帖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1]而这编号为
D203-1、D203-2、D203-3的3叶残片,所书内容即为梵语-回鹘语的双语文本。虽然莫高窟的南区文书在上世纪40年代初早被取走一空,但彭金章研究员等在近年对北区的考古依然发现了数百件多种文字的文书[2-3]。其中就有婆罗谜字的梵文文书残片10件,并经北京大学段晴教授进行了研究[4-5]。以此推断,这3叶婆罗谜字的双语文书,应该出自莫高窟的北区。
原为任子宜先生所收藏的“写经六卷”,于上世纪50年代初捐献给了敦煌县博物馆(现敦煌市博物馆),而任子宜先生的其余收藏,则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并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由于任子宜先生和接受捐献的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均无人认识该文书所书写之文字,故而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收藏记录中将它们统称之为“西域古文书”残片,并长期深藏文物库房,不为世人所知。2014年春季,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梁旭澍、王海云等学者在调查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时,于院陈列中心文物库房发现了由任子宜先生所捐献的一批“西域古文书”残片。这批残片才得以重新面世并由相关学者予以研究。
二 残片的形制、内容归属
D203-1、D203-2、D203-3均为白麻纸,纸张似经过特殊处理,泛青。纸张纤维粗糙,交织不匀。纸质较厚。文书的文字为手书,字体较大。两侧有朱丝栏,文中有朱点标示。3叶残片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就现存尺寸规格来看,D203-1页面残宽12厘米,残高9.6厘米,残存文字5行;D203-2页面残宽11.7厘米,残高6.5厘米,残存文字4行;D203-3页面残宽10.8厘米,残高4.4厘米,残存文字2行。
通过书写形制与内容上的比对,这3叶双语残片与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第79号文书[6]、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第63与67号文书[7]应该是同一批,所抄写的经文均为梵语-回鹘语双语对照《法身经》{1}。首先,从字体来看,毛迪特(Maue)判断有邻馆所藏文书为婆罗谜字体b型u体,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国图藏文书与这3叶残片。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这6叶残片都有两种区别性特征。一是书写区的左右两侧均有朱丝栏,所书字母均不超出朱丝范围。经过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每行文字之上都有纤细的朱色画线,应该是用来作为上下对齐标准的。尤为特殊的第二点是:为了区别容易混淆的两组字形c-/v-与n-/t-,常常在c-与n-下加朱点标示。此外,双语文本的翻译形式也很有特点:梵语原文均以关键词、重要词组为翻译单位,而非句子;梵语原文与回鹘译文之间以分隔符区分开来。至于书写的行数与字数问题,由于敦煌所藏3叶残片破损严重,根据现存文字来看只能判断每一行大约抄写13至15个音节,行数不清。而借助于保存完好的京都、国图藏片,大致可推断残片的双面均抄录7行文字。就内容而言,D203-3的经文正好位于國图63、67号文书之前,二者可以顺利地衔接起来。6叶残片所书内容均为梵语-回鹘语双语《法身经》。
《法身经》在汉语佛教史上曾经数译:后汉安世高译《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萧梁僧伽婆罗译《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隋闍那崛多译《入法界体性经》、唐不空译《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经》、北宋法贤译《佛说法身经》等,均为一卷本。在新疆地区,也出土过不同语言的数种写本。根据其书写文字,可以大略区分为丝路北道本和丝路南道本两个系统{1}。
丝路北道本系统以北道婆罗谜字体书写,主要有以下三种。
1. 1904年斯忒纳(Stnner)公布的来自亦都护城的梵语本[8],并收录于《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写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以下简称SHT)系列丛书,编号为596。仅有一叶。由于是卷起来的形式,只有正面书写文字,背面完全空白。内容是对一些名相的罗列,如“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等,并未详细阐述,但通过经文的开头结尾可判断是全本。此外,SHT中893号残片(原编号为T Ⅲ MQ54,来自克孜尔),对应亦都护城本第11至21行。英藏霍恩勒藏品Or.15015/301号残片,对应亦都护城本第2至24行。这两种写本残片与亦都护城本都只有个别字母上的不同,应属于同一写本的不同抄本。另有法藏伯希和藏品divers D.A.G号残片,来自库木吐喇附近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首尾稍有不同,但正文中的术语基本上全都一致{2}。这可能也是同一写本的不同变体。
2. SHT中623号(原编号为T Ⅱ Y2,25,来自交河故城)与1689号(原编号为T Ⅲ S9,来自焉耆硕尔楚克,即七个星遗址){3}梵语残片,联缀而成,并未形成全本,但通过仔细的比对、勾连,大致能推断归属于《法身经》[9-10]。根据两件残片重合的内容部分,即623号 Bl.[5]正面第5行至背面第7行对应1689号Bl.a正面第1至3行,623号Bl.27正面第4行至背面第7行对应1689号Bl.b背面第2至5行,623号Bl.33对应1689号Bl.d背面第3行至Bl.e正面第1行,623号Bl.(36){4}对应1689号Bl.f正面,623号Bl.42背面第4至5行对应1689号Bl.h正面第1行,似乎可推测这两种残片属于同一写本的抄本。从现存内容来看,这一写本比亦都护城写本要详细许多,将经文中罗列的术语都进一步具体展开论述。同属这一写本的抄本的,目前所知还有以下几件残片: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梵语残片627号,对应623号Bl.40与1689号Bl.g[9-10];克洛特科夫(Krotkov)藏品中的梵语残片SI 2Kr/9(3)、SI KrIV/787与SI KrIV/788,但残片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11];柏孜克里克发现的80TBI 764号与772号两叶残片,大约可对应623号Bl.[5]与1689号Bl.a{5}。两叶残片的一面书写梵语,另一面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36《宣化品》的内容,对应CBETA,T07,no.220,p.755,a19-b10。
3. 6叶梵语-回鹘语双语残片,不仅属于北道婆罗谜字体,而且内容的比对也显示与SHT623号、1689号高度重合。除了已经释读出的3叶外,本文所处理的敦煌3叶残片将在下文予以详细比对。
丝路南道本系统以南道婆罗谜字体书写,目前所发现的主要有以下两种。
1. 1985年榜迦德-列文(Bongard-Levin)与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Vorobyova-Desyatovskaya)公布的圣彼得堡藏品中的5叶梵语《法身经》残片[12]。从首尾文字看,残片为全本,主体内容依然是罗列名相,但所选择的罗列内容与亦都护城本有所不同,尤其突出的是加入了“菩萨十地”“十波罗蜜”等内容。这大概反映了丝路南道佛教不同于北道的特点。榜迦德—列文等指出: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这个写本大约出现在公元7至8世纪{1}。文本内容比亦都护城本详尽,但比SHT所收的其他残片简略。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合作,展出了其中第5叶的背面,但不知为何将残片年代定在了1至3世纪[13]。
2. 榜迦德-列文与托姆金(Tyomkin)公布的圣彼得堡同一批藏品中的2叶《法身经》于阗语译本残片[14]。这2叶残片曾在喀什停留,之后被运往圣彼得堡。从文字上来看,大约抄写于公元6、7世纪{2}。通过内容的比对,榜迦德-列文等认为:该于阗语译本的内容与亦都护城本差距较大,与圣彼得堡藏的梵文本差距稍小,但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它所依据的梵语源文很可能另有其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于阗语本非常强调“大乘”(mahāyāa),其中甚至提到《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入楞伽经》《十地经》,等等,或许反映了于阗当地佛教的特色。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种写本外,可能还有一些散藏于各地的残片并未刊布。因此,对《法身经》各种写本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充深入。
三 3叶双语残片的换写、转写与平行文本{3}
翻译为现代汉语是:“众比丘,如来拥有十力。具足此十力,如来、应供、正遍觉宣告其最胜地位,转动梵轮,于大众中吼正狮子吼。哪十力?如来在此如实了知道理为道理,非理为非理。”
相对应的古译有两种{3}:
唐勿提提犀鱼《佛说十力经》:“汝等当知诸佛、如来、应(供)、正等觉具足十力,具十力故得名如来、应(供)、正等觉,尊胜、殊特、雄猛、自在,能转无上清净梵轮,于大众中正师子吼。何等为十?所谓如来、应(供)、正等觉,于是处如实知是处,于非处如实知非处,皆如实知。”
宋施护《佛说佛十力经》:“汝等当知,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有十种力,具是力者,即能了知{4}广大胜处,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转妙梵轮。何等为十?所谓如来于一切处如实了知,一切非处亦如实知。”
這一叶的内容不见于现在所知的《法身经》梵语本,但在宋代法贤所译《佛说法身经》中能够找到平行文本:
“于时方处,昼三夜三常善观察如是诸佛内功德法。无有能者而为广说,是故我今略说此法。”
或许说明法贤译《法身经》与回鹘语《法身经》所参照的梵语源文本,是SHT所收文本之外的一种?但由于SHT收录的残片与6叶双语残片都不是全本,尚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四 汉译《法身经》与相关问题探讨
上文已经提到过,在汉译佛经系统里,《法身经》先后有五个不同的译本。与梵语、回鹘语《法身经》内容最为近似的则是北宋法贤翻译的《佛说法身经》,尽管比对起来也有不小的差异。
安世高所译《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虽然文字与现存梵本很不相同,但基本内核是一致的:“无所坏法故致佛,无所得法能成佛,佛者则法身,诸种力、无所畏,悉法身之所入”、“譬如四渎悉归于海,合为一味,若干名法为一法身”。
僧伽婆罗译《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虽然说法背景与安世高译本一致,即文殊师利问法、佛陀作出详解,但内容有所扩充,多以譬喻阐释“佛身无为,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色非非色,不可见非不可见,非世间非非世间,非心非非心”等道理,经末偈颂有言“若有受持此,微妙法身经,所得功德利,不可得称量”之语,可见此经又名《法身经》。这部经文的特点是明确提出了“菩萨”“菩萨行”,带有大乘色彩。
阇那崛多译《入法界体性经》与安世高译本乃是同经异译。
不空译《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经》基本上是以偈颂体对僧伽婆罗的译本进行总结。经文开始前,不空交代了编译目的:“窃见《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经》,据其梵本有四十一礼。先道所行,但唯有十礼。于文不备,叹德未圆。恐乖圣者恳诚,又阙群生胜利。不空先有所持梵本,并皆具足。今译流传,庶裨弘益。其余忏悔仪轨等并如旧本。”不空的译文中有40次“敬礼无所观”,最后一次是总结性的“同归实相体”。可见是将《法身经》当作念佛功德的仪轨本来使用的。
法贤译《佛说法身经》则开章明义点明经文所讲乃佛陀的“化身”与“法身”,但在說法形式上比较特殊:并无提问者,而是佛陀自说。《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交代了翻译背景,是在咸平元年(998)七月十五中元节时,与其他六部译经——《频婆娑罗王经》《旧城喻经》《人仙经》《信佛功德经》《信解智力经》《善乐长者经》——一起敬献皇帝的译作。值得注意的是:前六部佛经均为“天竺语龟兹国书”,只有《法身经》是“中天竺梵本所出”。与龟兹地区的六部经同归一批翻译,是否说明《法身经》与西域龟兹有所联系呢?此外,《法宝录》还有对经文的简介:“大乘经藏收,析出别译。此中所明,广显佛之法身功德,及说化身种种胜用。若有求成正等觉智诸苾刍等,应当如理如实了知,随所了知,如理应修等。”说明了这部《法身经》的大乘性质。
除了《明义疏》之外,《阿毗昙毗婆沙论》也多处引用《法身经》,但引文内容不见于今存任何《法身经》文本。僧叡《喻疑论》(收入《出三藏记集》卷五)提到《法身经》时说:“什公时虽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即是泥洹,与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衿、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唐代慧沼的《能显中边慧日论》在判教时则将《文殊师利问法身经》判在第五时说法:“皆广明如来藏佛性法身一切生有,如今者云第五时说于佛性。”由上大略可以推测:在汉地的佛教传统中,《法身经》是被当作阐释佛性、法身的文献来接受的。
从源文本来看,《法身经》的梵语题名是Dharmaarīrasūtra,dharmaarīra意译为“法身”,音译则为“法舍利”。《妙法莲华经·法师品》:“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大唐西域记》卷九:“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也就是说,法舍利其实就是指佛的说教、经文。就此而言,《法身经》似乎不仅是对佛陀法身的颂扬,还是对法舍利{1}的一个总结性的文本,将佛陀的各种说法浓缩在一处。起初大概是以名数的形式对佛法进行概括,如亦都护城本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四念处、五根、七觉支、八正道等{2},后来内容逐渐丰满。正是由于其内容是歌颂佛陀法身,又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佛法精要,短小精悍,故而在丝路北道、丝路南道都非常流行。斯忒纳在介绍他所解读的亦都护城残片时,曾提及残片以咒语的形式被卷起来,而咒语往往被用来填充铜佛像的中空部分,可能这件残片原本也是用于类似的目的[8]。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牵涉到书写《法身经》经文的功用。与丝路北道本相比,于阗地区流行的南道本体现出了明显的大乘特色,如上文所述的“十地”“十波罗蜜”等,说明经文的内容也会随着传播的地域而有所改变,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和本土化特色。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段晴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特此深表谢意!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帮助通读初稿,惠赐相关残片的照片,并对写本的发现与收藏地提出指导意见,特此感谢!慕尼黑大学哈特曼(Hartmann)教授,茨默(Zieme)教授,韦勒(Wille)博士,以及毛迪特(Maue)博士惠赐相关写本资料并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向达.西征小记[C]//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8.
[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3]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3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4]段晴.A Newly Found Sanskrit Fragment from Dunhuang[J].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平成14年,2003(6):197.
[5]段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一件梵语残卷[C]//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447.
[6]Maue,Dieter.The equanimity of the tathāgata[C].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ed.by Zieme,Peter.Turnhout:Brepols Publishers,2008:179-190.
[7]Maue,Dieter,Peter Zieme.Two More Leaves of the Dharmaarīrasūtra in Sanskrit and Uigur[J].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2012(5):145-155.
[8]Stnner,H.Zentralasiatische Sanskrittexte in Brāhmīschrift aus Idikutahri,Chinesisch-Turkis-tān.I[J].Sitzungsberichte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XLIV.1904(44):1282-1287.
[9]Shinichirō Hori(堀伸一郎).Notes on the Unidentified Sanskrit Fragments in the Otani Collection at Ryukoku University Library[J].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 2003(6):132-126.
[10]Shinichirō Hori(堀伸一郎).Additional notes on the unidentified Sanskrit fragments in the Otani collection at Ryukoku University Library[J].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2005(9):91-97.
[11]Shinichirō Hori(堀伸一郎). Sanskrit Fragments from Central Asia a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t.Petersburg.Bukkyōgaku[J].佛教學,2011(53):1-24.
[12]Bongard-Levin,Vorobyova-Desyatovskaya.Pamjatniki indijskoj pismennosti iz Centralnoj Azii[C].Moscow,1985:66-76.
[13]Kyoto National Museum &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特別展覧会シルクロード文字を辿って——ロシア探検隊収集の文物[C].Kyoto,2009:48.
[14]Bongard-Levin,Tyomkin.Fragment of the Saka version of the Dharmaarīra-sūtra from the NE Petrovsky collection[J].Indo-Iranian Journal,1969(11):269-280.
[15]Shōgaito(庄垣内正弘), M.Fragments of Uighur Da-abala sūtra[C]// M.?魻lmez and S.-C.Raschmann.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Istanbul/Berlin,2002:291-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