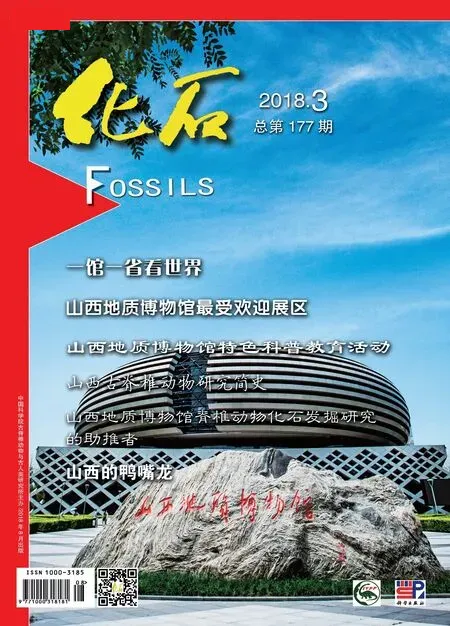进化论系列讲座(十一)达尔文
——(二)改变个人与世界的航行
2018-09-12郭建崴
郭建崴
达尔文带着《圣经》及对其的虔诚登上了贝格尔号,他那正统的基督徒形象最初常常招致水手们的取笑。但这样的情形随着航程一站又一站的延续在逐渐地改变。
改变源于他随身携带的另一本书——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书是行前亨斯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海上的航行漫长乏味,达尔文还倍遭晕船的折磨。《地质学原理》成了他忘却痛苦的最佳良药,因为书中描绘的“沧海桑田”给他打开了一个审视世界的全新视角。
不论海岛还是大陆,贝格尔号停靠的每一处海岸,都成为了达尔文观察地质现象的天然课堂,而他似乎总是能够找到《地质学原理》描述的地质变化。但是随着观察的积累和思考的深入,达尔文对于莱伊尔书中已经解答了的问题也开始希望寻找自己的答案,例如对于珊瑚礁成因的解释。
贝格尔号的勘测计划原定只有两年,无常风暴的耽搁以及舰长菲茨罗伊的敬业使它的航期越拉越长。这对一些水手无疑是煎熬;但对达尔文来说,也许反倒是福气。
1832年11月份航行到乌拉圭时,他收到了亨斯罗寄送来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莱伊尔在这一卷书里对拉马克的生物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的进化思想进行了反驳,认为旧物种的灭绝与新物种诞生的过程是上帝不断创造新的、更高级的物种的反映;这些新物种恰好解释了化石记录中那些看似突然的变化:一个物种的灭绝与另一个物种的新生没有任何联系,每一个新物种的出现都是一个奇迹——显然,莱伊尔“均变论”的思想仅限于解释无生命的地质学,而对于生命世界的演变,他还没有跳出自然神学的圈子。
刚刚读到这些的达尔文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随后不久的一系列发现一定使他有了不同的想法。还在收到这第二卷的一个多月前,达尔文已经在阿根廷的蓬塔阿尔塔发现了一件后来被确定是大地懒的含一个牙齿的下颌骨化石;而到了1833年的下半年,他在巴塔哥尼亚以及阿根廷的其他一些地区又先后收集了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动物化石。除了大地懒,还有一些像骆驼的大型动物骨骼化石、一些有着犰狳般的骨骼盔甲但体形却大得多的化石、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比想象得到的所有老鼠都要大得多的巨型老鼠头骨,等等等等。这些奇特远古动物让达尔文联想到其灭绝一定与地壳变化相关,但这种地壳变化似乎与大洪水扯不上任何联系。
随着不断南行,美洲大陆上动物群和植物群逐渐变化的状况也使达尔文陷入深思。自然神学认为,上帝为地球上的每一个地区设计并创造了适应当地生存环境的物种,因此生物就呈现出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地理分布状态,地球上也因此形成了若干“创造中心”。但是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菲,只经过短短1小时的行程就就让达尔文在后者观察到了前者没有的6种鸟,这不能不让达尔文遐想——两个地方如此靠近,纬度仅仅变了3度,地理环境并无大的不同,上帝何必大废周章地造出那么多不同的物种呢?在巴塔哥尼亚考察时,达尔文刚开始只观察到普通美洲鸵;向南行进了一段路程后,同伴捉了一只美洲鸵来准备食用,达尔文才注意到这是一只与普通美洲鸵完全不同的新物种——后来就被称为“达尔文美洲鸵”。疑问也再一次出现在达尔文脑海里,同一片高原上,北方生活着普通美洲鸵、南方生活着不同种的美洲鸵,二者的分布范围在中间地带又重叠着,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如果说北方和南方的环境略有不同,上帝为两地分别创造出一种美洲鸵还勉强说得过去,那么为什么又让它们在中间地带互相竞争呢?
贝格尔号在1834年6月结束了南美洲东海岸的勘测任务,穿越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而后一路向北沿途考察南美洲西海岸,至1835年9月到达了加拉帕戈斯群岛。
达尔文几乎走遍群岛的每一个角落,采集了能够采集到的几乎所有植物标本,同时也采集并亲手剥制了他认为最有意义的重要动物标本,其中尤以鸟类为多。达尔文发现有一种鸟在各个岛屿上都很常见,但是不同岛上鸟喙的大小却存在显著差异,甚至连喙的形状也各有不同,从尖细形到圆钝下弯形应有尽有。达尔文在日记中把这些鸟称为“丹卡”,是西班牙语对知更鸟的称谓,达尔文本以为它们就是他在南美洲大陆上见过的“知更鸟”,但通过对鸟喙的观察,他开始注意到这是支持物种渐变的证据——形成了不同的变种,而渐变的原因正是拉马克提出的生物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但是达尔文想到的更深——生活在相邻岛屿上的鸟儿在基本形态上惊人地相似、却在某些方面(例如喙)同时又存在巨大差异,这并非偶然,它们很可能是从同一祖先演化而来。联想到各个岛屿上象龟之间也存在的异同,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这个群岛的动物学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可能颠覆物种恒定的观念。
结束了加拉帕戈斯的考察之后,贝格尔号一路西行,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经南大西洋再次折向南美洲,最后于1836年10月返回出发地——英国的法尔茅斯港。
令达尔文始料未及的是,他已经成为了在祖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是因为,环球考察的新闻以及达尔文与亨斯罗的通信在5年里从未间断,亨斯罗对达尔文书信中描述的各种地质现象震惊不已,并把达尔文的这些观察笔记编辑成册分享给了众多博物学家。时任英国地质学会主席的莱伊尔便是其中一位,他迫不及待地想见一见在笔记里谦称是自己弟子的年轻人,在贝格尔号“回家”后不久就邀请达尔文来自己位于伦敦的寓所共进晚餐。
两人一见如故并从此成为终生的朋友。在莱伊尔的竭力帮助下,达尔文很快就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地理学会、英国地质学会等重量级学术团体的会员;达尔文还得到了皇室基金的资助,将他在环球旅行中的见闻编为费茨罗伊舰长主编的回忆录中的一卷公开出版。这套四卷本的书籍以《两舰航行记》为题于1839年7月出版,其中的第三卷即达尔文的科学考察日志的读者喜爱度远超其他3卷,以至于这部分内容很快就因热捧而独立成册出版发行,书名重起为《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军舰所到之处的地质历史与自然历史考察日记》,后来通常被简称为《贝格尔号航行日记》。
被莱伊尔热情引入的“朋友圈”里就包括有前文提到过的、创造了“恐龙”一词英文原意的著名解剖学家欧文。虽然后来有些恩恩怨怨,但是欧文在与达尔文相见后的不久,就应后者的请求对其从贝格尔号运下来的数箱化石寄予鉴定分类,其中包括巨型羊驼的骨骼碎片和那件与河马体型相当的巨型啮齿动物头骨。这些化石让达尔文意识到,它们与现代仍然生活着的那些小了好几号的同一谱系的物种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祖裔关系。直觉告诉达尔文,巨型化石羊驼应该是现生羊驼的近亲,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可以用自然法则来解释,而把其差异简单地视为造物主的功劳是牵强的。

达尔文地雀喙部分化的原始绘图(邓涛摄影)
请欧文鉴定化石的同时,达尔文把采集到的80件哺乳动物标本和450件鸟类标本全部交给了伦敦动物学会来鉴定。虽然交接手续一拖再拖,这批标本终于被送到了学会首席标本剥制师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手里。
古尔德对采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小型鸟类标本情有独钟,将它们鉴定出13种地雀(后来被称为达尔文地雀,最新研究表明种数已经是14种)和3种“知更鸟”(实际上是嘲鸫)。
达尔文喜出望外!原以为是同一物种内不同变种的鸟儿居然是不同的物种,这正是他期待看到的证据,物种可变——一个物种分化出不同的变种,变种继续不断地演化,最终形成新的物种。
结合当年对这些鸟儿栖息地所做的详细记录,达尔文终于明白了,过去的某个时候,来自于南美大陆的一种地雀偶然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们散布到不同的岛屿上,而每个岛屿可提供的食物资源各不相同,导致不得不食用相异食物的鸟儿的喙出现了分化,一些鸟儿演化出适合啄食虫子的喙,而另一些则适合啄食仙人掌的种子;虫子和种子还有各自的多样性。因此,在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喙的形态分化使地雀逐渐演化出13个(现在为14个)不同的物种。
原来,并不需要那么一个上帝去为每一个岛屿设计创造出一个特定的鸟儿物种,地理隔离就足以产生新物种。而且,新物种的出现也不是仅仅为了去填补旧物种因“灾变”而绝灭后留下的位置,一个祖先物种在新的地理环境占据不同的生态空间,就可以因适应性辐射而进化出多种不同的物种。地雀如斯,嘲鸫亦然,只是后者的适应性辐射远没有达到前者那样的程度。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物种起源”这一纯自然的过程呢?请看下回——达尔文与自然选择。